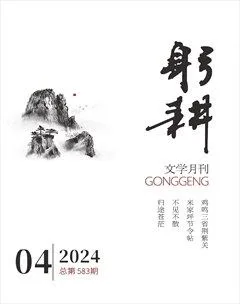詞語的銳度,或言說世界的敞開
劉軍
每一個清醒著的人都必須面對卡夫卡所指認的事實:你端坐不動,大千世界會自動向你涌來。這位20世紀最杰出的作家,性格內向而陰郁,經歷過事業、家庭、婚姻等人生的多重失敗,以及世界陰影的時刻擠壓,內心也曾泅渡到最扁平的地方。即使如此,他也絕不輕易將一絲一毫的苦痛掩埋或拋棄,而是不斷在內心的山谷中堆疊,讓其幽深,以至于逶迤。卡夫卡是苦痛的,卡夫卡也是深刻的,哪怕是靜坐在書房中,也能真切地感知到呼嘯而來的世界的碎片。既然醒來,一個人就很難再進入沉睡的狀態,而一個真實世界的諸多部分也會接著醒來。對于這個世界,你可以稱之為精神,也可稱之為內心。
也許是苦痛太龐大了,它逼迫作為個體的卡夫卡展開發問,世界的敞開也就從發問開始。在一篇文章中,卡夫卡曾將人生比喻為秋天落葉覆蓋下的道路。永遠是這樣,道路未及打掃干凈,又被新的落葉覆蓋。恰如古老的寓言所述,巨石終將滾下山去,這是西緒福斯的命運,但必須推著一樣東西上山,這也是西緒福斯的個人承擔。所有的道路終將被落葉覆蓋,這個絕望的結局并不一定打倒一切人,所以,對于卡夫卡來說,必須亮出語詞,必須展開言說,這是他對真實世界的一種承擔。有過絕境體驗的他,使用小說這一文體,有力地呈現出20世紀人類的普遍困境。我想也正是因為不斷的言說,才使本來的枯葉之上開始印現濕潤的經脈(劉曉楓語)。
醒著的人,不屬于塵世中的幸福者,在世界的黑夜中沉沉睡去,他們起身、站立,在極端孤獨的角落,使用思想、語言重新丈量身邊的泡沫與現實。一個人與時間作戰,他們可能會采取懷疑、反駁、叩問甚至顛覆的方式,直逼人類的荒涼。他們的對抗,不是源于對世界的厭惡,而是源于對存在的深愛,荷爾德林指出:誰曾想過那最深刻的,誰便愛那最現實的。他們的愛不會輕易說出,而是掩埋在文字的深處,等待后來者的撥開。如果以具體的個體作為考察向度,在不同歷史時期,他們可能是懷疑主義者、悲觀論者、流放的官員、在野的知識分子,以及四處漂泊的詩人等等,他們有著不同的職業、身份、地位,但在時間的隧道里,卻是排在一起的人,根須緊緊扎入大地,文辭在彼此的雙手中傳遞。他們不是喋喋不休的聒噪者,舌頭對于他們來說是個可有可無的器官,他們聽從的是內心的聲音,以最少的言辭,說出最重的真理。
當然,醒著的人也常常是焦灼的,因為“常恨言語淺,不如人意深”,因為“這世界上沒有一種痛苦是比語言的痛苦更強烈的了”。找到那些語詞,讓它們上岸,比完美的虛構和高聳的想象更重要。然而,眾多語詞掉落在泥淖里已有多日,不管自身亮度如何,皆混濁依然,如何打撈,或者清洗,這成為精神世界的重要難題。詩,是歷史的孕育基礎,海德格爾如是說,所以我想,在詩人手中,語言、語詞不應該成為魔方,以不同的組合制造宏大的迷宮,語言的自足絕不等于精神個性的自足。詩人的任務應該是仔細地濯洗,抹去附著的灰塵、污穢、權力,過濾多余的雜質并使其澄明,回到太初有詞的形態之中,即艾略特在《四個四重奏》中陳述的那樣:“沿著我們不曾走過的道路/通往那扇我們不曾打開的門。”由此出發,我對當下詩歌中普遍存在的“詩到語言為止”的狀況保持極大的懷疑,我覺得把詩歌扔到語言之山,是件很危險的事情,一座沒有濯洗過的語言之山,就像我們的身體一樣,藏著我們不自知的污泥,這污泥,毫無疑問會稀釋掉詩性。
出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詩人夏漢,早已過了不惑的年歲。這位蜷伏于黃淮平原深處的詩人,追慕鄉人也是偉大先賢的莊子之精神風度,始終保持一種對世界、對現實的警醒與感知力度,通過詩歌的形式,不斷向龐大的現實發問,將擁擠的泡沫擠出,以隱喻的手段暗示那普遍殘缺的存在。在其詩作中,我沒有讀到太多關于情緒纏繞、憂傷記憶等窄小個體的記錄,詩人也沒有癡迷于語言迷宮的制造,而是以有力的沉思,使語言回轉樸素的枝頭,從而照亮現實與記憶。如果加以總括的話,夏漢的作品有兩點突出之處給予我們以啟示,即:一方面是將追問日常現實作為基本的存在視域;另一方面,保持詞語的銳度,由此出發,實現語言自覺與主體自覺的契合。
先來說說第一方面。“感于哀樂,緣事而發”是文學史上源遠流長的詩歌傳統,勇于向現實發問,既是一種對歷史的主動承擔,也是對個體所屬文化的承擔,這承擔背后,內蘊的就是一個作家應有的人文關懷。新詩以降,傳統斷裂,但“緣事而發”的精神還在連綿。朦朧詩之后,社會文化范式進入轉型期,大眾文化興起的背景下,文學尤其是詩歌迅速邊緣化,遠離公眾視野的詩歌寫作,躲進小樓成一統的個體化書寫,成為普遍現實。詩歌與現實之間的精神維系越來越孱弱,即使是一些書寫現實的詩作,也僅僅停留在表面的浮掠。
與之不同的是,夏漢是少有的清醒者,在其詩作中,中原小城的欲望、權力符碼、社會倫常的常數與變數,皆通過與之相關的意象,得以準確呈現。這些意象包括日常的聒噪、夏日的會議、手機短信、墓園等等。且看《會場》這首詩:
上午,我應邀來到會場,看/那里又在演什么鬼把戲—/果然,刮來謊言的沙塵暴/與會場升騰的煙霧媾和//早產的癡呆兒吵醒了繼父/要挾一場酸雨供給他大補丸/“我要你,一天熬一副。”/“噢,你要熬我的鵪鶉?”//我行走于騾馬市經紀人行列/聽他們嬉笑怒罵,看袖口/以內那個看不見的虛偽交易/“喔,你狠!后會有期!”//眾多水妖玩弄小渦輪/在死海掀幾個黑色的波浪/忽然,一條鯊魚躍起/“你們興風,我怎做浪?”//我從噩夢驚醒,看會場/異常:人人抹一臉黃蠟油/此刻我對著空氣吹水泡/祈求它來清洗我多垢的耳根……
詩歌的開頭,會場的雙重污染情景直接從手中亮出。一方面是空話、大話,這是會場的精神生態;另一方面,由香煙繚起的煙霧對每一個與會者形成的現實污染又是那么顯眼。詩人出自生態學的獨特觀察,剝離了“嚴肅”會場的假象,使之回到冷峻的日常現實之中。接著三段,詩人以隱喻的手法,反諷會場上人群間的彼此爭斗,虛與委蛇之間,是暗藏的心機。新批評的代表人物布魯克林說過這樣一段話,大意是隱喻在現當代詩人手中已脫離作為手段的功能,成為詩歌的本體。在夏漢的其他詩作中,我們可以讀到很多隱喻的真實,在這里,隱喻作為手段和本體,交相重疊,抵達寬闊的現實。詩歌的最后,詩人內心的發問開始到場,面對臉抹黃油的他人,“我”吹著無形的水泡,以奇怪的舉動對抗會場的覆蓋與襲擊。這是保存本我的深刻努力,一個敢于向現實發問的人,應該既是一個置入現場者,更應該是個旁觀者。內心的清醒,使詩人與現實之間形成緊迫的張力,這張力通過隱喻可以直達讀者的眼前。
夏漢另外部分的寫作,呈現出指向內心、指向精神自我的形態。詞語與現實的緊張關系得以松開,但語詞的銳度依然。這樣的銳度不是由語詞的顏色而來,而是語言自覺所種下的種子。而語言的自覺,絕非技巧可以達到,需要主體精神自覺的支撐。關于存在的指認、自省,關于自我與外部世界的深刻關系,關于被遮蔽的精神事實,涵蓋了夏漢針對個體寫作的主題。個體的主體性和自我意識的走向自覺,是現代性的本質規定性之一,也是全部現代文化精神的基礎和載體,換言之,個體化是理性化的必然內涵。在前現代的經驗文化模式下,絕大多數個體是按照經驗、常識、習俗、慣例而自發地生存。只有當個體超越純粹的自在自發的日常生活的視域,同科學、技術、理性的自覺的精神再生產或自覺的類本質對象化發生實質性的關聯時,現代社會和傳統社會的斷裂才實質性地發生,現代意義上的人才真正產生。在這種意義上,福柯關于人和主體的論述有一定的道理,即“人”是現代時期推論出來的產物,是一個理性構造。
在一首題為《遠離》的作品中,作者寫道:我突然想遠離人群,走回我自己/因為在眾人的臉上有我的臉/在眾人的笑里有我的笑/在眾人的哭里,我看見我的眼淚……在這里,人群既是自我的一面鏡子,又是自我的一個部分。這是一段關于自我存在的沉思和表述,“我”被確立于“他們”之中。緊接著詩人又寫下了如此句子:人世間,一切都有我在/我想走近一棵樹,在那里看森林/我喜歡一只鳥的啁啾,在那里/聆聽最孤傲的歌唱。這一段,詩人思考的是如何從“他們”中找尋“我”的問題,從“鳥”或者他者身上,看到了“自我”的確立。“我”不會變化,只是會轉化成其他形式。也容易讓人想到莊子“齊物論”的想法。實際上,夏漢的這首作品是對胡塞爾“互為主體的世界”的很好注腳。因為在胡塞爾看來,審美主體與對象間,都具備感知和經驗的能力,彼此之間不是啟蒙哲學以來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兩者的關系實質上是種“主體間性”,即他所講到的“他人在我之中被構造為他人”(胡塞爾《生活世界現象學》)。后來,哈貝馬斯進一步發展了“主體間性”的概念,這是哲學上關于“人”的精神屬性的最新的認識,而夏漢的詩作,由獨立自省的品質,也走向了如此深遠之地,這在當代詩人群體中是罕見的,也是極為難得的。
當然,夏漢恢復寫作后的十年,其語言自覺還在行進的路途之上。在有些作品中,因為過于注重詞語的銳度,而放棄了語詞的沉靜,使詩歌沉思的品格難以像草地那樣鋪展,詞語的湍流而下,也帶來了些許的雜草,這樣一來,就會形成創作的起伏。我想,這應該是詩人以后的寫作要注意的問題。
海德格爾指出:真正的詩人是為人類尋找生存尺度的人。今天的現實里,肉體與精神,個體與世界,存在與現實,它們之間的對立讓醒著的人深深憂慮,從中架設溝通的橋梁,絕非易事。對于從事精神書寫的人們來說,當下的任務也許就是:迎面而上,并作出真實指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