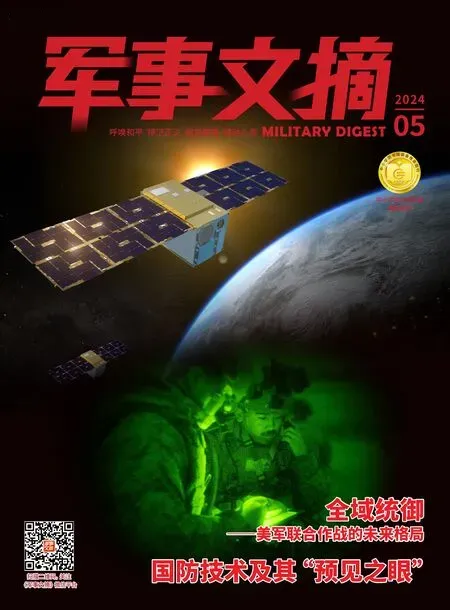印度海洋安全認知及啟示研究
趙 楠 侯翔宇 劉偉超

中印作為亞洲最大的兩個國家,在維護亞洲和平穩定、實現亞洲繁榮振興方面承擔著歷史責任和時代使命。印度因其快速發展的國家實力、位于“印太”地緣要沖的地理位置、長期持有的大國雄心,其對海洋安全認知一直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透過歷史和地緣雙重維度,研習印度海洋安全認知的深層邏輯,分析印度對印度洋、中國南海等關鍵海域的認知變遷歷程,理解其國家戰略邏輯構思,審視其戰略締造動能與政策進展,明辨其對我國實有和潛在影響,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印度海洋安全認知發展的深層邏輯
印度的海洋安全認知是國家海洋傳統和殖民遺產相結合的產物,其形成受復雜的歷史、地理、經濟等邏輯的深刻影響。對印度海洋安全認知的來龍去脈進行解剖梳理,有利于我們更好理解和把握印度當前海洋安全認知的深層邏輯及未來趨勢。
基于歷史邏輯的認知發展。印度學界普遍認為,印度在歷史上長期缺乏對海洋安全的認知,屬于“海洋盲人”。近代歐洲殖民者用歐式的海洋認知重新建立了印度的海洋認知,給印度帶來了“領海”的認知。例如,當葡萄牙從海上侵略南亞次大陸時,印度的莫臥兒王朝卻選擇固守陸地,從沒有想過要組建海軍來展示自己的強大,所以也沒有發現海洋的重要性。莫臥兒王朝的重大戰略失誤,為歐洲人借助海洋稱霸印度鋪下一條坦途。印度前海軍參謀長認為,印度長期以來一直自欺欺人地自認為是陸地國家,忽略了繁榮和充滿活力的海洋。事實上,印度海洋安全認知在漫長的歷史實踐與西方殖民統治的沖擊下,體現為同時秉持“海洋控制”“自由航行”兩種相反觀點的矛盾態度。
基于地理邏輯的認知發展。印度作為瀕海大國有其獨特地緣優勢:擁有7516.6千米的海岸線;被東面孟加拉灣、西面阿拉伯海包圍;地處印度洋腹地,是一條連接歐洲與遠東的主要商路。此外,印度洋是世界上惟一被命名為沿岸國的大洋。地理環境把印度與印度洋緊密相連,這對印度的海上安全認知產生了重要影響。印度開國總理尼赫魯曾于1958年宣稱:“這里三面臨海,第四面是高山……我們和大海息息相關。不管誰掌握印度洋,都會使印度海上貿易任人宰割,印度獨立將不保。”因此印度海權學者認為,假如印度洋已經不是被印度所保護的海洋,那么印度的國家安全是極其危險的。印度自身若沒有一個有效、長遠的海洋政策,其在國際上的位置就難免要寄人籬下。基于地理邏輯產生的印度海洋安全認知的一大特點為:誰掌握了印度洋,印度自由就聽誰的。

印度洋地區是全球能源和貿易的重要通道
基于經濟邏輯的認知發展。海權論認為,海洋是用于海上經濟與貿易的全球交通媒介,所以海上經貿是海權的核心領域。換句話說,各個國家和民族對海洋安全的認知,其本質皆為了增強自身海上經濟與貿易實力,印度也不例外。據統計,印度洋上承載了世界上近1/3的散裝貨輪運輸以及半數以上集裝箱貨輪運輸,其中,石油制品占總運輸量的70%。很顯然,印度洋是世界海運一條重要航線。印度無疑通過海上貿易收獲重大經濟利益,這對其海洋安全認知有著潛移默化的深刻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在經濟高速增長的今天,印度成為能源需求大國。在印度經濟發展所依賴的能源消費中,石油有65%依靠海外進口,越來越多的液態天然氣船舶也通過非洲南部海域前往印度,進口煤炭則開始從澳大利亞、南非等國家運入。印度對海上經貿、能源安全等領域的經濟邏輯,加強了印度對海洋安全的重視。
印度對印度洋的認知變遷歷程
印度政府歷次發布的《印度海洋學說》白皮書中,均強調印度洋對于印度是無比重要的,認為若想確保印度的獨立與主權,就必須控制印度洋。但在對印度洋的具體認知層面,卻在不同時期有所變化。
印度建國初期:側重與鄰國加強協作以彌補權力真空。印度建國之初就指出印度洋是印度繁榮與安全的關鍵,倡導與鄰國加強協作以彌補自身海上實力不足。時任印度海軍參謀長查特古提出:“必須彌補英國戰艦駛離這一區域所帶來的權力真空。印度的生命線主要分布在這里,其前途取決于維護海域自由的能力。支配整個印度國防戰略的是大海。”由于當時印度海軍等海上力量尚不強大,印度在制定政策時,側重與鄰國進行合作,以最終實現印度在印度洋地區的領導地位。具體協作領域是造船工業與海上聯合演習、訓練海軍人員等。
20世紀70年代:創建印度洋和平區以應對冷戰沖擊。印度從20世紀70年代起熱衷創建印度洋和平區,主張大國應對印度洋采取放手政策(hands-off),以應對美蘇冷戰對印度洋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沖擊。印度采取上述“和平區”策略主要基于兩種考量,一是針對印度洋地區各國發展狀況,通過政治經濟多領域分析,認為和平是本區域新生經濟有效增長的關鍵。因此印度有必要采取措施,讓印度洋地區沿岸各國意識到軍備競賽所帶來的風險,為建立和平區事業而努力。二是印度認為自身海軍現代化建設不可能在短期內與美蘇比肩,也就意味著不可能在短期內實現在印度洋地區具有領頭地位的軍事實力。對此,印度積極在不結盟運動、非洲統一組織、英聯邦論壇等平臺發揮重要作用,同印度洋島國及沿海國家發展友好關系。
21世紀初:控制印度洋的軍事觀點成為主流。隨著冷戰的結束以及印度綜合實力的提高,印度的海軍初見雛形,印度開始主張將印度洋變成“印度之洋”。印度國防部于2004年發布了首版《印度海洋學說》,這標志著印度對于印度洋的認識開始帶有軍事色彩,“對印度洋的掌控”是印度的主要認識。印度將海上利益區分為首要利益區和次要利益區,首要利益區是:阿拉伯海和孟加拉灣、進入印度洋的戰略樞紐、位于印度洋的島嶼國家、在印度洋這一區域內的主要海洋航道、波斯灣(印度最大的原油來源地)。《印度海洋學說》修訂版于2009年發布,其在首要利益區中增加了西南印度洋地區。所謂次要利益區則涵蓋了:紅海、東太平洋、南印度洋、中國南海。通過分析上述利益區的劃分,不難發現本世紀初的印度海洋安全認知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首要利益區,對印度洋的認知中心仍然是北印度洋問題,但也開始對中國南海、東太平洋等我國海上利益攸關區有所關注。

印度總理莫迪
莫迪政府時期:向南印度洋、印太地區擴展。2014年5月,莫迪政府執政后,對印度洋的安全認知凸顯三大特色。一是對使用海上軍事力量更加自信。莫迪執政后,承諾充當印度洋“凈安全”提供者,把發展海上力量放在重要位置,印度海軍繼續擴大其對印度洋的介入,印度洋地區的軍事合作日益加深,比如印度洋海軍研討會、多國軍事演習等等。二是對印度洋的關注點從北印度洋繼續南移,試圖填補目前大國關注較少的南印度洋區域。新版海軍戰略報告把東部非洲沿海國家、印度洋島國及西南印度洋劃為首要利益區,提出西南印度洋地區對印度具有重要意義。在經歷了“由陸向海”發展過程后,莫迪政府的印度洋政策反映出“向南看”的新動向。三是對印度洋的認知逐漸擴展至印度——太平洋地區,一定程度上理解并認同印太概念。
印度對中國南海的認知變遷歷程
自1990年印度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印度的經濟和軍事實力都得到了飛速發展,尤其是進入21世紀,印度學界第一次系統論述了“印太”的概念,印太概念是把印度洋區域與西太平洋區域合二為一,形成一個統一的區域。2011年,美國總統奧巴馬訪問印度時提出“印太”概念,之后“印太”概念正式成為一項具有戰略意義的概念計劃,越來越多地被用于地緣政治話語。
印太概念誕生前。在印太概念提出之前,印度對中國南海的認知主要源自其地緣政治位置和與中國的歷史沖突。首先,印度一直將自己定位為“東方大國”,在區域內有著強烈的影響力和利益追求,因此也對中國南海的局勢保持著高度關注。在古代,印度文化曾經傳到了東南亞地區,不僅對當地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還塑造了印度在該地區的精神形象。而在現代,印度認為東南亞是其戰略利益所在地,進一步加重了對該地區的關注。因此,印度一直在加強與周邊國家的合作,并試圖建立符合印度戰略的海洋秩序。
印太概念誕生后。自印太概念提出以來,印度與美國、日本等國家之間的區域合作得到進一步加強,使印度對中國南海的認知情況發生了巨大變化。首先,印度對于中國南海的主張態度日益強硬。此前印度就曾聯合澳大利亞、美國和日本等國舉行過南海問題高層會議。此外,印度還多次表達其支持東南亞國家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并呼吁中方尊重所謂“相關國際法律規定和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其次,印度對于中國南海的戰略意義越發重視。印度認為,中國在南海的主張既威脅了印度的安全,也損害了印度與海上戰略伙伴之間的合作。因此,印度對該地區的態度已經由過去的袖手旁觀轉變為積極參與,并試圖通過加強自身海軍力量和聯盟合作等方式,提升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和戰略優勢。最后,印度對于中國南海的認知不僅局限于外交層面,還逐漸擴展到了軍事領域。近些年來,印度加強了對南海周邊海域的偵察和巡邏活動,試圖更全面地掌握該地區的安全形勢和軍事動態,以應對可能出現的威脅和挑戰。總之,印太概念的出現促使印度對南海問題的關注和介入程度提升。
印太概念催生“向東看”方針。印度于2014年實施了一項有關對標中國經濟發展的一攬子計劃——“向東看”,顯示了印度自身經濟崛起的一種野心。不久后,印度推出“東向行動”,這是“向東看”的升級版,目的是確保自身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利益。“東向行動”方針的主要目標有4點:保障印度洋安全;改善同東南亞國家的聯系;與共同利益國家結成戰略伙伴關系;均衡中印關系。由此可見,印度不僅在戰略上有意創造有利印度發展的國際環境,也意在以多種形式的政治手段,構造印太區域政治格局。把“向東看”政策升級為“東向行動”政策,意味著莫迪政府將加速東進,以求在印太區域有所成績,這與它當前的印太戰略非常吻合。但受限于軍事和經濟,印度的重點目標是對印度洋的完全掌控,對南海問題的干預將分散有限的能量,從而會削弱印度洋管制。因此,印度的南海政策是以“有限干預”為主。

印度日益重視海洋利益,并加強海軍建設
印度海洋安全認知的影響
“印太”認知促使印度配合美國加快戰略合圍。在美國“印太戰略”提速的背景下,美國迫切需要拉攏印度的力量來推動在印太區域的布局。印度為了提升國際地位,聯美遏華,與美國“印太戰略”在政策上的契合度越來越高。而這種發展必然會對我國的對外貿易以及國家的能源安全帶來了嚴重影響。印度在其海軍安全策略中,一貫強調對海路和重要通道的掌控。美國在其“印太戰略”中也清楚地表明,將支持其盟友及合作伙伴加強“對海洋邊境及海洋利益的掌控與維持”能力。考慮到印美兩國已經就馬六甲海峽的共同巡航問題達成一致,在未來,印美兩國很有可能在海軍上進行更多的合作,對印度洋的海運路線以及進入印度洋的主要通道加大控制,這將不可避免地對我國海上貿易航線和能源通道的安全構成進一步威脅。伴隨著“印太戰略”的不斷發展,印度也逐漸加深了與澳大利亞、美國和日本等國的海上合作,美、日、印、澳“四國聯盟”關系逐步走深、走實,一旦形成同盟,未來極有可能對我構成繼“島鏈”封鎖之后的第二層戰略障礙。

第17屆亞洲地區海岸警備機構高官會
“印度之洋”認知的潛在威脅。長久以來,印度洋被印度視為“印度之洋”,對于其他國家的進入存在著強烈的抵觸情緒,隨著其國力的不斷增強,尤其是其海軍力量的迅速發展,這種抵觸情緒逐漸演變成了一種戰略上的針對。印度洋是我國“一帶一路”戰略計劃實施的重要樞紐,以及“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流經區域,這讓印度擔心中國在印度洋上日益增長的影響“侵害”印度的“海洋利益區域”。因此,印度針對性提出“季風計劃”,意圖恢復甚至增強與印度洋上國家之間的外交關系,重塑印度主導的印度洋海上秩序,鞏固其在印度洋上的統治地位,從而實現印度成為“新興強國”的雄心壯志。
“向東看”認知帶來的不穩定因素。隨著“東向行動”的開展,印度與其他國家也從原來軍事交流演變到全面防務合作級別。如與菲律賓和越南簽署一系列軍事合作協定以及在同一地區開展多種軍事活動。此外,印度積極推進海上力量的建設,強化軍事同盟制度建設,以此來應對日趨復雜的地緣政治大環境。最后,印度通過多種途徑加強有關國家同中國就南海問題進行對抗的能力。印度不斷增加自身在中國南海的影響力,使南海問題變得更為錯綜復雜,讓我國在尋求南海問題的雙邊解決時,遇到了較大的掣肘。
結語
近年來,印度在海洋安全戰略設計和執行過程中,均想實現“獨霸”印度洋,同時用“凈安全”的概念提出“拓展安全范圍,達到安全保障的目的”,甚至將南海地區都納入自己的“海上利益區”。印度海洋安全認知呈現出巨大的“排他性”與“擴張性”的特點,并在其威脅設定中體現出諸多中印因素,由此對我國安全和發展利益產生許多消極影響和現實威脅。為此,我們必須從長遠出發,采取積極有效地應對之策,維護我國的海洋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