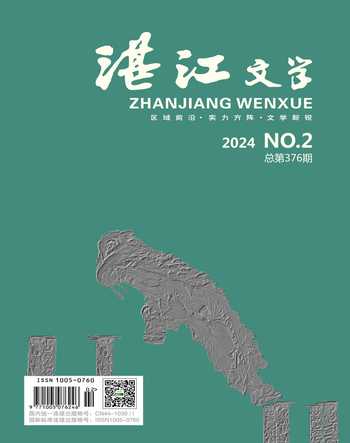飛鳥萬花筒(組章)
塔娜
噪鵑和他的敬護院
他在它的叫聲下面坐。它站在春天的最高處,強行占了整棵杉樹和他的敬護院。它不理。他現在也懶得理了。現在有人照顧他了,一個棕色皮膚的熱帶胖女人。天氣開始熱了,她有時卸下黑色的頭巾,露出更棕色的臉。
它就在她頭上叫。
他現在只是走了五米,他能感覺到時間對他太緩慢了,他開始不討厭它的“喔哦,喔哦”,甚至,他開始羨慕它。杉樹和天空靜靜地聽它傾訴。他過去的一整個冬天,寂靜得像下了79厘米的雪,剛好蓋住他的年紀。那個照顧他的女人,兩只耳朵整日塞著紅色音樂球,熱烈而封閉。
他推著助行器在敬護院灰白色的墻下來回走,看云經過他,看行人路過,看園丁剪短胡亂旺盛的九里香,看他的番茄土豆泥晚餐從廚房煙囪跑出來。他的力氣現在只夠看會動的一切。
他能感覺到,春天正在脫離他而去。
那個棕色皮膚的女人一直跟在他后面,像傾聽它的杉樹和天空一樣,一聲不吭。
少年鶇
少年鶇很小,山雀比它更小。山雀站在風口向它展示飛翔的技巧。將翅膀打開成甜桃葉子的形狀,山雀說。事實上,尤加利樹上的風駕馭著山雀,以及山雀的祖先。
甜桃花開了,芒果花開了,番石榴花開了,指甲花開了。
春天開了。少年的鶇無心向學。
它決定不讓告密者風跟隨。它追隨燕子,壓低飛過甘蔗林,看見橘和柚樹在開花。土地和草在快速生長。它穿過河流,到達炊煙頂端,它的上空布滿風箏。
風再一次占了上風。
太陽城廣場的候鳥
熱帶來的女人們星期天準時聚集在太陽城廣場。像所有遷徙的鳥一樣,它現在也在太陽城廣場參與聚集。圣瑪利亞的頭像上此刻站滿它的家族。
它對陌生的云雀講述旅途的故事。它們出發的地點,遇到的人,咸水河岸盛開碩大的紫玉蘭花,留下了金色記號的電線和電線桿,正方形的捕鳥器。
它為此感到疲倦和滿意。瑪利亞的雕像很大,熱帶女人在她的陰涼里討論即將到來的太平洋季風,沙地上有已經成熟的甘蔗林,輪渡站滿白色候鳥,她們遙遠的孩子大概又長高了一厘米。
星期天的太陽城廣場,現在只有和圣瑪利亞不說話。
它決定不再交談。所有的講述和聽現在都令它感到疲倦。
它從寒冷的西伯利亞凍土飛來,目的地是熱帶的一座死火山。它現在記起來了,它和它的家族在上一次穿越南太平洋時,熱帶來的女人就在它們翅膀下的一只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