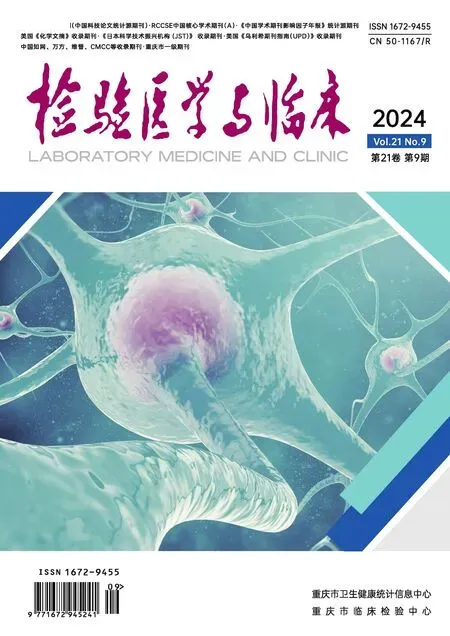甲狀腺癌患者BRAF V600E基因突變與民族及臨床病理特征的關系
劉超宇,黃林達,馬燕飛,潘秀虹,朱曉瑩△
1.右江民族醫(yī)學院附屬醫(yī)院臨床病理診斷與研究中心,廣西百色533000;2.廣西肝膽疾病分子病理學重點實驗室,廣西百色533000;3.廣西高校腫瘤分子病理學重點實驗室,廣西百色 533000;4.右江民族醫(yī)學院附屬醫(yī)院腺體外科,廣西百色 533000;5.右江民族醫(yī)學院附屬醫(yī)院血液內(nèi)科,廣西百色533000
甲狀腺癌是臨床上發(fā)病率最高的一種內(nèi)分泌惡性腫瘤,占全球每年所有診斷癌癥總數(shù)的3%[1]。大多數(shù)甲狀腺腫瘤是由濾泡細胞衍生的甲狀腺惡性腫瘤,可分為濾泡性甲狀腺癌(6%~10%)、甲狀腺乳頭狀癌(65%~93%)、未分化甲狀腺癌(0.3%~6.7%)[2]。雖然,大部分甲狀腺癌惡性程度低,預后較好,但仍有小部分甲狀腺癌患者早期就出現(xiàn)淋巴結轉移。因此,如何對甲狀腺結節(jié)的良惡性做出精準的判斷就顯得尤為重要[3]。近年來,隨著精準醫(yī)學的飛速發(fā)展,腫瘤分子病理學診斷技術日漸成熟,甲狀腺癌的病理診斷也不再僅限于鏡下判讀。研究表明,鼠類肉瘤濾過性毒菌致癌同源體B1(BRAF)基因是甲狀腺癌中最常見的驅(qū)動突變基因,其中翻轉突變導致纈氨酸在600號氨基酸位置(V600E)被谷氨酸取代,與甲狀腺癌的發(fā)生、發(fā)展密切相關[4]。BRAF V600E基因突變是BRAF最常見的突變類型,這一突變可改變其下游編碼產(chǎn)物,激活MAPK信號通路,進而誘導腫瘤細胞的過度增殖及分化[5]。BRAF V600E基因突變在甲狀腺癌的不同病理類型中突變率不同,且BRAF V600E基因突變與甲狀腺癌的高侵襲性、高復發(fā)性及不良的臨床預后明顯相關,進而影響腫瘤細胞的包膜外浸潤、淋巴結轉移、腫瘤多灶性及治療的有效性[5]。現(xiàn)有研究表明,在我國不同地區(qū)及民族人群中,BRAF V600E基因突變率存在明顯差異,且BRAF V600E基因突變與臨床病理特征的關系也有所不同[6]。因此,本研究以壯族人口聚集地廣西壯族自治區(qū)百色市壯族與漢族甲狀腺癌患者300例為研究對象,對壯族與漢族甲狀腺癌患者BRAF V600E基因突變情況及其臨床病理特征進行對比分析,以期為甲狀腺癌個體化診療提供新的臨床依據(jù)。現(xiàn)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隨機選取2021年1月至2023年1月于右江民族醫(yī)學院附屬醫(yī)院確診的甲狀腺癌患者300例作為研究對象,收集其病理標本,其中男150例、女150例,平均年齡(40.2±11.26)歲,腫瘤分型:乳頭狀癌264例(88.00%)、濾泡狀癌15例(5.00%)、未分化癌21例(7.00%),≥40歲150例、<40歲150例,腫瘤最大徑:<2 cm 136例、2~4 cm 164例,淋巴結數(shù)目:0個99例、1~4個109例、>4個92例。根據(jù)患者民族將研究對象分為壯族150例和漢族150例。壯族病例中男75例,女75例;≥40歲78例,<40歲72例;腫瘤分型:乳頭狀癌134例,濾泡狀癌8例,未分化癌8例;腫瘤最大徑:<2 cm 66例,2~4 cm 84例;淋巴結數(shù)目:0個45例,1~4個61例,>4個44例。漢族病例中男75例,女75例;≥40歲72例,<40歲78例;腫瘤分型:乳頭狀癌130例,濾泡狀癌7例,未分化癌13例;腫瘤最大徑:<2 cm 70例,2~4 cm 80例;淋巴結數(shù)目:0個54例,1~4個48例,>4個48例。兩組甲狀腺癌患者的性別、年齡、腫瘤分型、腫瘤最大徑、淋巴結數(shù)目比較,差異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納入標準:(1)均為廣西百色籍常住人口;(2)術后行常規(guī)病理學檢查,由2名病理專家閱片,并明確腫瘤大小、淋巴結數(shù)目及病理分型。排除標準:(1)合并有其他惡性腫瘤的患者;(2)合并有嚴重腎、肺、肝等疾病的患者[7]。所有研究對象均知曉本研究,并簽署知情同意書。本研究經(jīng)右江民族醫(yī)學院附屬醫(yī)院醫(yī)學倫理委員會審批通過(批號:2023061601)。
1.2試劑與儀器 石蠟包埋組織DNA提取試劑盒(北京天根生化科技有限公司,批號:2023021001);BRAF V600E基因突變檢測試劑盒(北京鑫諾美迪基因檢測技術有限公司,批號:2022120802);ABI 7500 fast實時熒光定量聚合酶鏈反應(qRT-PCR)儀(美國ABI公司);超微量分光光度計(美國ThermoScientific公司)。
1.3方法
1.3.1全基因組DNA提取 所有患者的手術標本在離體后30 min內(nèi)經(jīng)10%福爾馬林溶液充分固定、脫水、石蠟包埋、連續(xù)切片(4 μm)后行蘇木精-伊紅(HE)染色。染色后經(jīng)2名高年資病理醫(yī)師閱片明確該標本中腫瘤細胞占比,選取腫瘤細胞占比超20%的石蠟組織標本,連續(xù)切片8~10張(5 μm)制備蠟卷,蠟卷置于無酶EP管中,按照DNA提取試劑盒說明書進行全基因組DNA提取。提取出的DNA經(jīng)超微量分光光度計檢測,以濃度>5 ng/μL,A260/280在1.8~2.0為符合要求的NDA樣本,可以進行基因檢測。
1.3.2BRAF V600E位點的基因突變檢測 采用qRT-PCR對提取出的全基因組DNA進行BRAF基因V600E位點突變檢測,檢測流程中的全部操作均在標準的PCR實驗室中進行,每次檢測時同時設置陰性對照、陽性對照及外控基因。若待測樣本中BRAF基因V600E位點出現(xiàn)明顯的S型擴增曲線,記錄Ct值,將BRAF基因V600E位點Ct值與外控基因Ct值相減,計算出ΔCt值,當ΔCt值≤8時,結果判讀為陽性。

2 結 果
2.1壯族、漢族病例甲狀腺癌患者BRAF V600E基因突變情況比較 BRAF基因V600E位點的基因突變結果發(fā)現(xiàn),300例甲狀腺癌患者中突變型221例,野生型79例。壯族病例中突變型108例(72.00%),野生型42例(28.00%);漢族病例中突變型113例(75.33%),野生型37例(24.67%),不同民族甲狀腺癌患者BRAF V600E基因突變率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壯族、漢族病例BRAF V600E基因突變情況比較[n(%)]
2.2不同年齡、腫瘤最大徑和淋巴結數(shù)量甲狀腺癌患者BRAF V600E基因突變率比較 <40歲的甲狀腺癌患者BRAF V600E基因突變率為88.67%,明顯高于≥40歲患者的58.67%,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但不同腫瘤最大徑及不同淋巴結數(shù)目甲狀腺癌患者BRAF V600E基因突變率比較,差異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不同臨床年齡、腫瘤最大徑和淋巴結數(shù)目甲狀腺癌患者BRAF V600E基因突變情況比較[n(%)]
2.3不同性別、不同民族甲狀腺癌患者BRAF V600E基因突變情況比較 壯族男性甲狀腺癌患者BRAF V600E基因突變率為86.67%、女性為57.33%,漢族男性甲狀腺癌患者BRAF V600E基因突變率為54.67%、女性為96.00。相同民族不同性別甲狀腺癌患者間BRAF V600E基因突變率比較,差異均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1);相同性別不同民族甲狀腺癌患者間BRAF V600E基因突變率比較,差異均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1)。見表3。

表3 不同民族、不同性別之間BRAF V600E基因突變情況比較[n(%)]
2.4不同年齡、不同民族甲狀腺癌患者BRAF V600E基因突變情況比較 ≥40歲壯族甲狀腺癌患者BRAF V600E基因突變率為53.85%,<40歲為91.67%;≥40歲漢族甲狀腺癌患者BRAF V600E基因突變率為63.89%,<40歲為85.90%。同一年齡范圍內(nèi)不同民族間BRAF V600E基因突變率比較,差異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4 不同年齡、不同民族甲狀腺癌患者BRAF V600E基因突變情況比較[n(%)]
2.5不同腫瘤最大徑、不同民族甲狀腺癌患者BRAF V600E基因突變情況比較 腫瘤最大徑<2 cm的壯族甲狀腺癌患者BRAF V600E基因突變率為60.61%,腫瘤最大徑2~4 cm的為80.95%;腫瘤最大徑<2 cm的漢族甲狀腺癌患者BRAF V600E基因突變率為92.86%,腫瘤最大徑2~4 cm的為60.00%。腫瘤最大徑<2 cm的不同民族甲狀腺癌患者間BRAF V600E基因突變率比較,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01),腫瘤最大徑為2~4 cm的不同民族甲狀腺患者間BRAF V600E基因突變率比較,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03),見表5。

表5 不同腫瘤最大徑、不同民族甲狀腺癌患者BRAFV600E基因突變情況比較[n(%)]
2.6不同淋巴結數(shù)目、不同民族甲狀腺癌患者BRAF V600E基因突變情況比較 0個淋巴結的壯族甲狀腺癌患者BRAF V600E基因突變率為73.33%,1~4個為72.13%,>4個為70.46%;0個淋巴結漢族甲狀腺癌患者BRAF V600E基因突變率為74.07%,1~4個為75.00%,>4個為77.08%。相同淋巴結數(shù)目的不同民族甲狀腺患者間BRAF V600E基因突變率比較,差異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見表6。

表6 不同淋巴結數(shù)目、不同民族甲狀腺癌患者BRAF V600E基因突變情況比較[n(%)]
2.7不同民族、不同甲狀腺癌分型患者BRAF V600E基因突變情況比較 不同民族甲狀腺乳頭狀癌、甲狀腺濾泡狀癌及甲狀腺未分化癌患者BRAF V600E基因突變率比較,差異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見表7。

表7 不同民族、不同甲狀腺癌分型患者BRAF V600E基因突變情況比較[n(%)]
3 討 論
甲狀腺癌是臨床上常見的一種惡性腫瘤,且近年來發(fā)病率呈逐年上升趨勢[8]。2002年報道首次在人類癌癥中檢測到BRAF基因突變,此后,陸續(xù)鑒定出40多種BRAF基因突變[9-10]。大多數(shù)激活BRAF基因突變的病例涉及密碼子600并導致V600E突變[11]。另有研究表明,甲狀腺癌BRAF V600E基因突變與遺傳因素明顯相關,其在不同國家、地區(qū)及人群中的突變情況各有不同[12-14]。
BRAF是編碼絲氨酸的特異性蛋白激酶,該激酶是影響細胞增殖、分化和成熟細胞功能的細胞信號通路的關鍵換能器。BRAF基因經(jīng)常在許多不同的癌癥類型中發(fā)生突變,包括甲狀腺癌、黑色素瘤、結直腸腺癌、膠質(zhì)母細胞瘤等,在發(fā)生BRAF基因突變的癌癥中觀察到的激活點突變或小的幀內(nèi)缺失通常發(fā)生在編碼蛋白激酶結構域的序列中[15-18]。最常見的是BRAF突變(T1799A)編碼的BRAF V600E突變,其中活化環(huán)內(nèi)氨基酸600處的纈氨酸被谷氨酸取代,可使BRAF激酶活性持續(xù)活躍,活性增加高達500倍[19-21]。突變激活的 BRAF V600E可進一步驅(qū)動下游 MEK1/2→ERK1/2 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信號通路的激活,為癌細胞中BRAF→MEK→ERK通路的組成性激活提供了促進細胞分裂周期的信號[22-24]。在既往文獻中報道了不同國家、人種甲狀腺癌患者BRAF V600E突變情況,如希臘的甲狀腺乳頭狀癌患者BRAF V600E突變率為17%[12]。我國西北地區(qū)甲狀腺癌患者BRAF V600E突變率為86.7%[13-14]。本研究結果顯示,相同民族不同性別甲狀腺癌患者BRAF V600E基因突變率比較,差異均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1);壯族病例組和漢族病例組相同性別甲狀腺癌患者BRAF V600E基因突變率比較,差異均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1)。上述結果提示,百色市甲狀腺癌患者BRAF V600E的基因突變率存在性別差異。
本研究結果還發(fā)現(xiàn),不同年齡患者BRAF V600E基因突變率比較,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ZHANG等[25]在一項25 241 例甲狀腺乳頭狀癌患者的Meta分析中表明BRAF基因V600E突變與年齡無關;SHEN等[26]進行的一項多中心研究顯示,甲狀腺乳頭狀癌患者BRAF V600E基因突變與年齡相關,且患者病死率與年齡的增長呈正相關。盡管本研究結果顯示BRAF V600E基因突變與年齡相關,但有可能是因樣本量小所致,仍需進一步研究。
本研究結果還發(fā)現(xiàn),腫瘤最大徑<2 cm的漢族甲狀腺癌患者BRAF V600E基因突變率明顯高于壯族,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腫瘤最大徑為2~4 cm的壯族甲狀腺癌患者BRAF V600E基因突變率明顯高于漢族,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但在3種不同病理分型甲狀腺癌患者中,壯族與漢族甲狀腺癌患者BRAF V600E突變率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提示病理分型并非甲狀腺癌BRAF V600E基因突變的相關因素。但腫瘤最大徑可能是影響甲狀腺乳頭狀癌患者BRAF V600E基因突變率的因素之一,且該因素可能具有民族差異性。上述結果對了解BRAF V600E基因突變在壯族與漢族甲狀腺癌患者中的分布情況,以及對甲狀腺癌患者的協(xié)助診治和預后評估可能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
綜上所述,百色市甲狀腺癌患者BRAF V600E位點的基因突變率與民族及腫瘤病理分型無關,與年齡、性別及腫瘤最大徑有關,其中年齡在不同民族間無差異,性別在相同及不同民族間均有差異,但腫瘤最大徑只在不同民族間存在差異。本研究BRAF V600E位點基因突變的檢測結果為日后深入開展甲狀腺癌的個體化診療提供了新的臨床參考依據(j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