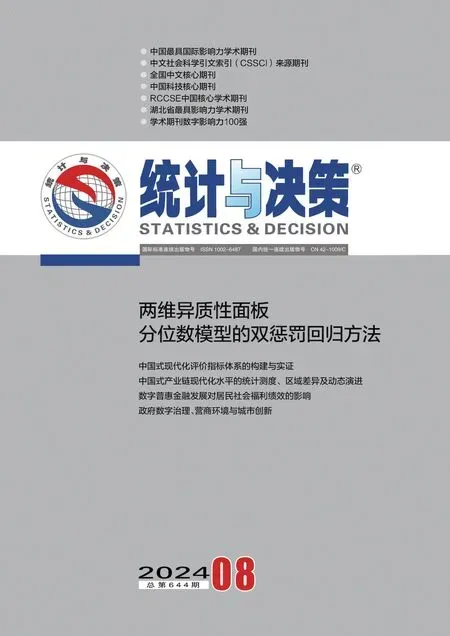數字金融與實體經濟高質量耦合協調發展的統計評價
蒙 恬,姚聰莉
(西北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西安 710127)
0 引言
實體經濟是數字金融發展的基礎和依托,數字金融是推動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技術手段[1]。伴隨著數字技術和虛擬經濟的深度融合,數字金融業務的拓展催生了一批極具活力的金融新業態、新模式和新產業。在全球經濟不確定性明顯增加和我國經濟結構轉型的關鍵時期,研究數字金融與我國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耦合特點,既是實現我國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促進金融科技現代化的重要選擇。
在以往的研究中,學者們從內涵特征、耦合機理、評價指標、區域差異等方面研究了數字金融系統和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系統之間的耦合協調關系。在理論層面上,成瓊文和申萍(2023)[2]指出數字金融已經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金融建設和發展的核心內容,并從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研究了數字金融對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驅動作用。周全等(2024)[3]指出,數字金融突破了傳統金融的服務邊界,重新定義了金融產品價格、融資風控、投融資服務和金融效率等金融要素。張海霞和趙景峰(2023)[4]構建了數字金融生態系統,指出數字金融從多個方面促進了實體經濟產業結構的演化。在數字金融監管方面,白萬平和官倩倩(2022)[5]研究了網絡金融數據交易的隱蔽性和傳染性,指出數字金融業務存在客戶金融信息泄露、融資數據流卡斷、金融區塊鏈詐騙、金融數字畫像侵權和元宇宙金融游戲化等弊端,因此必須加大政府金融監管力度。在實證層面上,李林漢和田衛民(2021)[6]構建了基于傾向性得分匹配法的數字金融評價指標體系,指出數字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推動作用正在逐步加強。在區域異質性方面,謝婷婷和高麗麗(2021)[7]研究了“新基建”背景下數字金融的區域創新效應,指出數字金融對于中國不同地區的經濟驅動效應存在差異。在數字金融促進實體經濟發展方面,姚鳳閣等(2022)[8]利用耦合度模型實證分析了數字普惠金融和實體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關系,指出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和數字金融之間的耦合存在顯著的省際差異。
總體上看,現有文獻對數字金融與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協調關系的理論研究相對較多,但是對于數字金融與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關系的實證研究相對較少。基于此,本文選取2011—2022 年中國31 個省份數字金融和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面板數據,運用熵權法分別測算數字金融和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兩個子系統的綜合評價值。運用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協調度模型從時間演化上研究了數字金融子系統與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子系統的發展軌跡和未來趨勢;從省域層面上研究了數字金融子系統和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子系統的省際差異,以期為推動數字金融創新和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參考。
1 理論基礎
從理論上看,數字金融系統和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系統之間存在著錯綜復雜的“耦合”關系。一方面,實體經濟通過資本利潤、技術進步、制度優化和管理效率提升為數字金融系統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和保障;另一方面,數字金融通過融資產品創新、交易機制、信息供給、數據治理等便利性服務促進實體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1.1 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為數字金融提供物質基礎和保障
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為數字金融提供保障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為數字金融產業提供資本和利潤,如“新基建”為通信技術的發展和數字金融業務的拓展提供后發動力。二是實體經濟通過創設“金融需求”推動數字金融的發展。三是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通過激勵機制促進數字金融產業發展。一方面,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通過人才競爭戰略和科技研發投資推動數字金融發展;另一方面,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通過區域協作交流機制和區域比較優勢戰略推動數字金融產業發展。
1.2 數字金融通過便捷性服務推動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
數字金融推動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數字金融通過緩解實體經濟投融資過程中的“金融排斥”效應促進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數字金融降低了網點服務的信息處理成本和柜臺交易成本,有效緩解了中小企業融資約束和農村居民融資難等“金融排斥”問題。二是在“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下,數字金融通過數字交換技術和數字安全技術為廣大用戶提供了優質的消費保障,從而間接推動了實體產業結構的優化和產業效益的提升。三是通過創新創業驅動促進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在數字金融的協助下,我國經濟已經由高速增長階段開始向穩態增長、和諧增長、包容性增長、生態綠色增長、創業增長和共享式增長階段過渡。而數字技術的創新和金融科技產品的有效供給則是保證綠色發展、和諧包容發展和穩態發展的重要條件。四是通過金融數據治理保證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數據本身的比特屬性使得數字金融監管和治理變得更加緊迫和必要,在基數龐大的金融數據流中,數字金融技術通過監督機制設計和監督平臺建設有力保證了實體經濟交易的后臺安全性和順暢性。
2 研究設計
2.1 指標體系構建
為了客觀、全面地評價數字金融和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的耦合協調關系,本文借鑒已有的研究成果[1,6,8],按照縱橫可比、分類科學和數據可計量的原則,從數字金融覆蓋廣度、數字金融演化深度、數字金融交易便利化程度和數字金融安全4 個維度出發構建了數字金融評價指標體系;從創新驅動能力、協調發展水平、綠色生態發展和開放穩定水平4 個方面構建了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相關評價指標的計量單位、權重和屬性如表1和表2所示。

表1 數字金融評價指標體系

表2 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2.2 研究方法
2.2.1 子系統綜合評價模型
本文參照李向陽等(2022)[9]的研究,根據熵權法構建子系統綜合評價模型。其過程如下:
第一,對相關指標進行無量綱化處理:
其中,xmax和xmin分別代表指標的最大值和最小值;x和y分別表示指標的原始數值和標準化后的數值,i(i=1,2,…,m)代表年份,j(j=1,2,…,n)代表指標數。
第二,根據各指標標準值矩陣Xij,計算出第i年第j個指標的特征比重pij:
第三,由pij計算第j個指標的熵值ej:
第四,計算出第j個指標的權重wj:
第五,在此基礎上建立子系統綜合評價模型:
其中,Zi為綜合評價值,Yij為標準化值,Wj為各指標權重。將根據此模型計算出數字金融子系統綜合評價值S(x)和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子系統綜合評價值f(y)。
2.2.2 復合系統耦合協調度模型
(1)耦合度模型。變異系數(CV)法是采用數據標準差與均值的比值作為度量方法的耦合比較法。本文采用變異系數法來度量數字金融子系統與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子系統之間的耦合度,認為變異系數越小耦合度越高,系統達到最優化的概率越大;變異系數越大耦合度越低,系統達到最優化的概率越小。耦合度的計算公式為:
其中,c表示子系統耦合度,取值范圍為0~1;k表示彈性調節系數,取值范圍為1~5,為適應本文的研究需要,取k=4。
(2)耦合協調度模型。耦合度模型能夠識數字金融子系統與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子系統之間相互作用的強度和區間,但是對兩個子系統發展水平均很低的系統的耦合程度不能進行有效識別(也就是說兩個實際發展水平很低的系統可能表現出極高的“偽耦合”),為此,必須引進耦合協調度模型來修正耦合度模型的錯誤判斷。耦合協調度計算公式為:
其中,c表示耦合度,p為兩個系統的綜合評價值,R為耦合協調度,α和β分別代表為數字金融權重和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權重。在難以確定兩個系統數據優先權的前提下,本文假定數字金融權重和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權重相等,即α=β=0.5。一般來說,耦合協調度越高,復合系統協調發展水平則越高,系統的“真耦合”程度則越高;反之,耦合協調程度越低,復合系統協調發展水平則越低,系統則越不和諧。
(3)耦合協調類型。本文借鑒徐玉蓮等(2017)[10]的研究成果,將耦合協調類型按照遞進式分布函數劃分為失調衰退型和協調發展型兩種類型,見表3和表4。

表3 數字金融與實體經濟高質量耦合發展類型

表4 數字金融與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主導類型
2.3 數據來源
本文以我國31 個省份(不含港澳臺)為研究對象,選取2011—2022年的相關數據進行研究。本文數據主要來源于官方統計年鑒和官網權威數據,如《中國金融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有些數據來源于《中國創業風險投資發展報告》及中國銀行官方網站,還有少部分數據來源于《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國家統計信息中心、“騰訊互聯網+”數字經濟大數據平臺等。為保證實證分析的準確度,在使用過程中對相關數據進行了無量綱化處理。
3 實證分析
3.1 時序演變分析
本文利用子系統評價模型分別計算2011—2022年的數字金融廣度指數、數字金融深度指數、數字金融便利度指數、數字金融安全指數、創新驅動指數、協調發展指數、綠色生態指數和開放穩定指數,然后根據復合系統耦合度模型計算出數字金融子系統和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子系統之間的耦合度和耦合協調度,據此評價兩大系統的耦合協調水平,具體結果見下頁表5。

表5 2011—2022數字金融與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評價結果
(1)數字金融指數的時序演變趨勢
總體上看,2011—2015 年是我國數字金融初步發展的階段。除2014年數字金融便利度指數和數字金融安全指數躍進到較高水平外,其他年份的數字金融子系統評價指數均保持在較低水平。盡管從2011年開始中國已經出現了電子銀行、網絡對沖基金交易、P2P 網絡信貸交易等數字金融活動,但是受制于普惠金融背景下金融交易成本、電子交易手續和網絡交易安全性的制約,數字金融業務開展的深度和廣度相對有限,最終導致這5年的數字金融指數出現較為“低迷”的現象。2016—2017 年是我國數字金融快速發展的階段。特別是2015年年底至2016年年初,四大數字金融指數普遍增長,其可能的原因是:得益于“一帶一路”金融合作的推進、絲路基金的設立、亞洲開發銀行的支持和跨境電商模式的興起,數字金融業務出現了大幅增長的態勢。而“微金融”對實體金融的沖擊也是不可忽視的原因,紙幣運輸業務、紙幣存儲業務、紙幣修復業務、現金流、紙幣收藏業務以及與此相關的投融資業務均出現了大幅度減少,與此同時,電商模式引發的“無紙化貨幣交易”進一步蠶食了銀行對人力資源的需求[11]。2018—2022 年是我國數字金融業務穩步發展的時期,推進數字金融發展的相關政策文件無疑為包括P2P、眾籌、第三方支付等在內的數字金融業務確定了監管原則,指明了業務邊界,從而推動了數字金融業務的健康發展[12]。2019 年《區塊鏈金融發展白皮書》、2020 年清華大學新媒體研究中心發布的《2020—2021 年元宇宙發展研究報告》、中國區塊鏈專業協會發布的《2020—2021 中國元宇宙產業白皮書》和2022年中國金融信息中心公布的《金融元宇宙研究白皮書》是推動“數字金融”快速發展的政策性指導文件[13]。
(2)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的時序演化趨勢
2011—2014 年是我國實體經濟低質量發展的階段。其中,2012 年的綠色發展指數和協調發展指數較低。可能的原因是:伴隨著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和“新舊動能”的轉換,國家先后出臺了規范實體經濟發展的文件和政策,這些政策的出臺使得高速發展的實體經濟出現了向“穩步健康發展”轉化的態勢。而2011年以前“竭澤而漁”式的、短視的、急功近利式的、加大貧富分化差異的、招致貧困現象愈發嚴重的發展模式則是導致這幾年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偏低的重要因素。2015—2018 是我國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起步階段。在前一階段相關規范治理政策的激勵下,從2015 年開始我國實體經濟出現了向高質量發展的跡象。如《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以及《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實施使得實體經濟創新活力明顯增強,到2017 年“創新驅動指數”已經達到0.689。各種產業協調政策、貧困治理政策和生態治理政策的推行使得“協調發展指數”和“綠色生態指數”飆升到0.729 和0.881 的較高水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2018 年的開放穩定指數卻出現了局部下降的情況,這應該與當年我國對外貿易方面的政策調整有關。從2019年開始,在內部結構調整和矛盾釋放、全球經濟和貿易下滑、中美貿易摩擦等不利因素的影響下,實體經濟運行壓力逐漸顯現[14]。從表5 來看,除綠色發展指數仍然保持著較高水平外,2019—2021 年的創新驅動指數、協調發展指數和開放穩定指數均出現了緩慢下行的態勢并與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保持一致,從2022 年開始4 個子系統評價指數才出現了緩慢上升的態勢。合理的解釋是:新冠肺炎疫情對實體經濟產生了重要影響,盡管從2021 年開始國家就制定了盡快恢復實體經濟運行的諸多政策,但是后疫情時代的投資壓力和內需壓力仍然巨大,導致實體經濟恢復乏力[15]。
(3)數字金融與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水平的時序演變趨勢
2011—2022 年,中國數字金融與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耦合關系經歷了“中度失調—良好協調—優質協調”的發展階段,與此相適應主導發展類型也經歷了“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滯后型—數字金融主導型—同步型”的發展軌跡。2011—2015 年是數字金融與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中度失調”的階段。除2011 年耦合協調度保持在“輕度失調”水平之外,其他年份數字金融系統和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系統均呈現中度失調的走勢。可能的解釋是:盡管此時期我國實體經濟總產值躍居世界前列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由于長期以來積累的結構性矛盾和財富配置上的兩極分化現象,使得數字金融業務的發展缺乏強有力的利潤支撐和資金支持,銀行和保險機構普遍對數字金融持有“謹慎觀望”的態度[16],再加上數字金融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技術型安全漏洞等問題,最終導致這6年數字金融與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中度失調”局面的形成。2016—2021 年我國數字金融系統與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系統進入了“良好協調”的穩步階段,盡管2019—2021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了實體經濟的發展,但是數字金融業務恰好借機發展并出現了“數字金融主導型”的發展格局。2022 年以來,伴隨著央行數字貨幣加密技術的創新和現實增強技術(AR)的發展,數字金融的應用已經延伸到“虛擬現實”和“物理世界”交互體驗的全新領域,在金融元宇宙技術的支持下現實世界的金融交易均可以在智能區塊鏈平臺上實現即時交割并逆向追溯,這種全新的數字金融平臺引起了全球金融資本的密切關注,《金融標準化“十四五”發展規劃》中也明確了國家對數字金融業務的政策支持和產業傾斜,這些都為我國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堅實的技術支撐和金融保障[17]。與此同時,2022年我國數字金融系統和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系統進入“同步”發展的時期。
3.2 省際差異分析
為準確把握我國數字金融和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水平的省際差異性,本文首先計算了2022 年我國31 個省份的數字金融指數和實體經濟高質量指數;然后,根據復合系統耦合度模型計算出不同省份數字金融子系統和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子系統之間的耦合度;最后,根據復合系統耦合協調度模型計算出各省份數字金融子系統和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子系統之間的耦合度和耦合協調度,據此評價兩大系統耦合協調水平的省際差異。結果見表6。

表6 2022年數字金融與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省際差異評價結果
(1)數字金融指數的省際差異分析
2022 年數字金融指數呈現東高西低、依次遞減的態勢。數字金融廣度指數與數字金融指數較為一致,呈現東高西低、依次遞減的態勢,東南沿海省份表現比較突出,如北京、河北、廣東、江蘇、浙江等。較高的數字化和智能化技術為數字金融發展提供了優越條件;而數字金融深度指數并不與數字金融指數高度一致,其中湖北和重慶的數字金融深度指數較高,這說明湖北和重慶作為數字金融高度發達的省份的影響不可忽視;就數字金融便利度指數來說,除去西部發達地區較高之外,山西和內蒙古的綜合評價值較高;就數字金融安全性指數來說,甘肅和青海的綜合評價值達到了高位水平。
(2)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的省際差異分析
總體來看,2022 年我國實體經濟高質量指數存在著顯著的區域差異,呈現東高西低、自東向西依次遞減的態勢。其中,江蘇、上海、浙江和廣東的實體經濟高質量水平處于良好水平;其次是北京、天津、河北、山東和四川,這些地區的技術創新實力雄厚、高端制造業發達、經濟活力和經濟效率較高,推動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產業、技術、設施配套較為完善;其他省份處于綜合評價較差水平。具體來說,創新驅動指數、協調發展指數、綠色生態指數和開放穩定指數在不同省份之間存在不同特點。創新驅動指數呈現南高北低、自南向北依次遞減的態勢,其中,海南、四川、廣東和江蘇的指數較高,原因是這些省份的土地生產率、資本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普遍較高,科技研發投入強度較,經濟發展充滿活力;協調發展指數呈現不規則的空間異質性態勢,其中廣東、陜西、西藏和河北的指數較高,這說明這些省份在高端制造業占比、產業結構優化、消除GDP 異化、降低逆向城鎮化比率、促進第三產業發展方面成效較為突出。綠色生態指數大體上與創新驅動指數保持一致,呈現南高北低、自南向北依次遞減的態勢,其中,云南、廣西、海南、湖北、湖南和江蘇的指數較高,原因是這些地區屬于國家生態治理的示范區域,無論是森林覆蓋率還是空氣質量都呈現常年“優質”的狀態,工業三廢治理的補償性投資進一步優化了環境質量,從而為實體產業高質量發展創造了環境條件。開放穩定指數的空間分布基本上與實體經濟高質量指數一致,呈現東高西低依次遞減的態勢,其中,廣東、山東、吉林和河北的指數較高。這很可能與這些省份和諧的開放政策和較低的外貿依存度有關,當然也與這些省份較低的經濟糾紛發生率、失業率、資產負債率和CPI波動率有關。
(3)數字金融與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水平的省際差異分析
2022年我國數字金融與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水平與子系統綜合評價指數總體上呈現東南沿海和中部地區較高、西部地區較低的態勢。具體來看,東部地區優于中部地區。合理的解釋是:東部沿海地區擁有較為完善的數字金融基礎設施、數字金融驅動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較為強勁,兩系統耦合狀況優質;盡管中部地區的數字產業化水平較高,數字金融支持政策力度較大,但是受制于實體經濟資源瓶頸、人力資源瓶頸和貿易瓶頸的制約,導致數字金融與實體經濟高質量耦合發展的水平低于東部沿海地區[18]。處于良好耦合的省份有6個、中級耦合協調的省份有4個、初級耦合協調的省份有3個。耦合失調的省份有2 個,分別是安徽和西藏。其中,西藏屬于唯一嚴重失調的省份,近年來西藏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和消費結構優化,大大提高了實體經濟活力,在旅游業和畜牧業的支撐下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實體產業質量效益明顯增強。但是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氣候因素的影響,西藏數字金融基礎設施較為落后,沒有金融大數據中心和順暢的電商交易平臺,快遞業務到達困難,導致數字金融和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處于嚴重失調的狀態[19]。
4 結論
本文利用熵權法、耦合度和耦合協調度模型評估了我國31個省份2011—2022年的數字金融和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發展水平,結論如下:
(1)從時序演變來看,2011—2022 年中國數字金融與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的耦合協調水平經歷了“中度失調—良好協調—優質協調”的發展階段,與此相適應主導發展類型也經歷了“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滯后型—數字金融主導型—同步型”的發展軌跡。其中,2011—2015年是我國數字金融系統和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系統中度失調的階段,主導發展類型為“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滯后型”;2016—2021 年是數字金融系統和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系統的良好協調發展時期,主導發展類型轉變為“數字金融主導型”;2019—2021年是中國數字金融系統和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系統的高耦合新階段;2022年開始,數字金融系統和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系統進入“優質協調發展”的新階段,主導發展類型也由“數字金融主導型”逐漸演化為“同步型”,這說明數字金融系統和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協同效用逐漸提升,國家科技金融創新戰略進入優質運行狀態。
(2)從省際差異來看,2022年中國數字金融和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的耦合協調水平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均為東部地區最高,中部地區次之,西部地區最低。從具體指標層次上看,2022年我國數字金融深度指數、數字金融廣度指數與創新驅動子系統綜合評價指數、綠色發展子系統綜合評價指數基本一致,呈現東高西低的態勢。這說明實體經濟創新驅動、生態可持續性發展為數字金融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和環境條件;協調發展指數、開放穩定指數與數字金融便利度指數、數字金融安全指數較為一致,呈現東部地區最高、中部地區次之、西部地區最低的態勢。這說明安全穩定的數字金融服務是推動實體經濟開放、共享、和諧發展的重要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