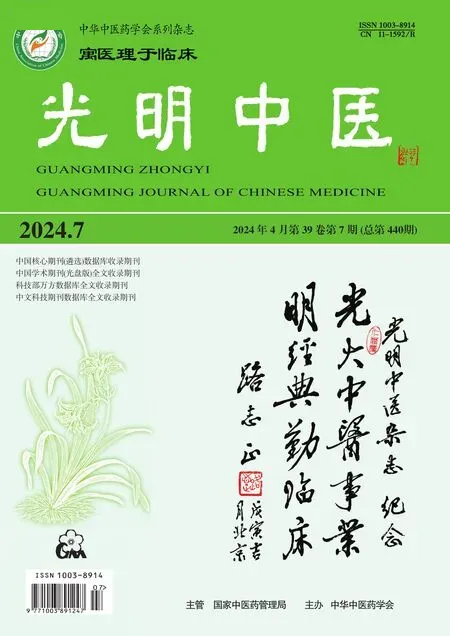基于《金匱要略》論治潰瘍性結腸炎*
周臘英 林愛珍
潰瘍性結腸炎(UC)是慢性非特異性腸道炎癥性疾病,其臨床主要癥狀為腹痛、腹瀉、下利黏液膿血、里急后重感,并呈反復發作的慢性病程。現代醫學認為UC是由于環境因素作用于遺傳易感者,在腸道菌群的參與下,啟動了難以停止的、發作與緩解交替的腸道天然免疫及獲得性免疫反應,最終導致腸黏膜屏障損失,潰瘍經久不愈及炎癥增生等病理改變[1]。《金匱要略》是中醫經典寶庫,本文將基于《金匱要略》,結合現代醫學研究成果,從病因病機、治則治法、具體辨治、疾病調護4個角度論治UC。
1 《金匱要略》對UC病因病機的認識
1.1 以趺陽脈微弦角度認識UC的遺傳易感及免疫異常“趺陽脈微弦”以脈證論病機,即下焦陰寒盛,中焦陽氣虛。究其根本,蓋先天不足,五臟元真空虛。脾腎陽虛,火不暖土,下犯腸腑,致生下利;脾陽虛弱,土敗木賊,故出現腹痛;脾失健運,水濕內生,加之統血失司,致血不循常道而行,溢于脈外而下利黏液血便。
現代醫學認為,遺傳易感、免疫系統異常是導致UC發病的一個關鍵因素。遺傳或外界環境因素致使腸道黏膜屏障受到破壞,病原微生物侵犯腸黏膜,引起急性炎癥反應,若此時免疫效應細胞持續活化或者病原體持續刺激免疫系統,而免疫調節細胞的功能又受到了抑制,腸道免疫穩態失衡,引發UC。上述二者皆因機體自身的缺陷及(或)異常引發此病,這與“趺陽脈微弦”的觀點不謀而合。
1.2 以脾色病黃 瘀熱以行角度認識UC的腸黏膜微循環障礙“脾色病黃,瘀熱以行”在《金匱要略》中詮釋的是黃疸的病機,“脾色病黃”是定位性癥狀,病位為脾胃,“瘀熱以行”描述病機,即濕熱久郁,由氣分內陷血分。UC的病位雖在大腸,但與脾胃關系密切,其病機亦可用“瘀熱以行”理解:飲食不節(潔),致脾運化失職,水濕停聚,郁而化熱,濕熱纏綿,日久內陷營血成瘀,熱蒸肉腐化膿,下走腸腑,引起腹痛、腹瀉、下利黏液膿血。
現代醫學研究發現,UC患者血液中血小板活化,腸道炎癥狀態又激活炎癥細胞,使血液呈高凝狀態,阻礙腸黏膜微循環;腸黏膜微循環障礙使腸黏膜通透性增加,腸腔內有害物質易進入血循環,加重腸黏膜組織缺血、壞死,誘導黏膜發生異常炎癥反應,二者形成惡性循環,使慢性UC反復發作[3,4]。在慢性UC腸黏膜活檢病理組織學中常見大量黏膜毛細血管微血栓形成,這亦證實腸黏膜微循環障礙是UC發病的重要一環[4]。腸黏膜微循環障礙和“瘀”這一繼發病理產物對UC發病的影響有共通之處,符合“瘀熱以行”所言的病機之義。
1.3 以腸內有癰膿角度認識UC的感染因素“腸內有癰膿”見于《金匱要略》中關于“腸癰”的論述。《說文解字》言:“癰,腫也……癰,壅也,氣壅否結里而潰也”。由此可見,“癰”有兩層含義:一言病機,乃感受熱毒,氣血壅塞不通而發;二言證候,為紅腫疼痛。“腸內有癰膿”其意可概括為腸腑感火熱毒邪,熱毒煎灼腸絡,營血瘀滯不通,熱盛肉腐釀膿,可以看作是UC活動期的病機。
現代醫學普遍認為感染是UC發病的啟動因子,且活動期抗生素治療有效,但至今未發現導致此病的直接或特異性的病原體及感染因子[5]。當腸道受病原微生物侵襲,炎性細胞因子活化,使T淋巴細胞大量聚集于受損腸黏膜,而T淋巴細胞又促進炎性細胞因子分泌,二者相互作用,使T淋巴細胞凋亡抵抗,削弱腸道黏膜穩態,上述過程為UC發生的中心環節[6]。人體染毒,氣血壅塞致癰的發病過程與腸道感染、炎癥活化、免疫持續激活,導致黏膜損傷的發病過程切合。
綜上,UC的病機以先天不足、脾腎陽虛為本虛,以無形之寒熱毒邪、有形之痰瘀實邪為標實,本虛標實共致氣血瘀滯、脂絡受損,引發腹痛、腹瀉、下利膿血。這與現代醫學對UC遺傳易感、免疫異常、腸黏膜微循環障礙、感染等發病機制的認識有相通之處。
2 《金匱要略》對UC治則治法的理解
2.1 從當以溫藥和之理解UC的治本之法脾腎陽虛為UC的發病基礎,需運用“溫藥”以溫補脾腎、振奮陽氣。“痰、飲、水、濕、瘀血”為陰邪,易阻滯氣機,具有“遇寒則凝,得陽始化,得溫則行”的特點,對UC的發病起著重要作用,使用“溫藥”不僅可溫化邪氣,還能開發腠理,通行水道,給邪以出路,達到陰邪得化、氣機通暢、陽氣漸復的治療目的。原文中“和之”提示溫藥的使用以“通陽”為主,勿專于溫補,以防太過溫燥,主以調和臟腑,恢復氣化功能,行消開導并行,以期達到標本兼顧的目的。
2.2 從各隨其所得而攻之理解UC的治標之法《金匱要略》云:“諸病在臟,欲攻之,各隨其所得而攻之”。無形之邪常與有形實邪相合,需先攻伐其所依附的邪氣,使邪無所依而解。臨證中UC患者病情復雜,多見寒、熱等無形邪氣裹挾痰濕、瘀血等有形實邪,故需明確患者所感邪氣的性質及特點,有針對性的祛除有形實邪,步步為營,邪去正復而使人安和。
2.3 從見肝之病 知肝傳脾 當先實脾理解UC的臟腑整體觀辨治從臟腑整體觀論治疾病,思及UC的發病與脾胃功能的失調關系緊密,可由此衍生得到“見脾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肝”“見脾之病,知脾傳腎,當先實腎”。且“實”字非補之意,而言明調補,即根據實際情況選擇補、瀉或補瀉兼施。以下分而論之。
2.3.1 見脾之病 知肝傳脾 當先實肝“《內經》云‘諸嘔吐酸,暴注下迫,皆屬于熱’,下迫與吐酸同言,則知其屬于肝熱也。仲景于下利后重便膿血者,亦詳于厥陰篇中,皆以痢屬肝經也”[7]。肝主疏泄,脾主運化,兩臟關系密切,肝實或肝虛均可引起脾臟功能障礙,進而出現一系列病證。因而經嚴格的辨證論治,并基于兩臟的關系,可在治療UC的時候考慮加用調脾緩肝的藥物。
2.3.2 見脾之病 知脾傳腎 當先實腎《金匱要略》中“腎著”為寒濕痹阻腎之外府,氣血經絡阻滯不通的疾病,但仲景方用甘姜苓術湯溫中健脾化濕,正是“見腎之病,知脾傳腎,當先實脾”之義的體現,可見脾腎兩臟不可分割而看。腎陽為全身諸陽之根,腎不暖土,脾陽虛衰,故在臨證治療時可在溫脾陽的同時加入補腎陽之品以助火源,增強溫化力量,恢復臟腑的氣化功能,并能借此祛除繼發的病理產物,達到“溫補不斂邪,祛邪不傷正”的目的。
3 《金匱要略》對UC的具體辨治及病后調護
3.1 辨證施治
3.1.1 清熱解毒 消癰排膿大黃牡丹湯、薏苡附子敗醬散此二方見于“腸癰”篇,通過上述的論述可知UC活動期與腸癰的臨床主證相似,臨證可參考“腸癰”來進行辨治。在原條文中,兩方以“膿成與否”相區分,在實際臨床應用時可不囿于此。兩方皆可清熱解毒,消散癰腫,化瘀排膿,但二者各有側重。薏苡附子敗醬散證偏重于正氣已虛,故方中運用附子通陽散結;大黃牡丹湯證則傾向于正氣未虛,確有正邪相爭,營衛郁滯之瘀形成,因此在方中用大量瀉熱解毒、攻下逐瘀藥物,如大黃、芒硝清泄血熱、以通瘀滯,牡丹皮、桃仁涼血行瘀。
3.1.2 清熱燥濕 涼血止利“熱利下重者,白頭翁湯主之”言及白頭翁湯證,其病機為濕熱下注腸腑,熱盛燔灼營血則肉腐成膿。故臨床上若辨證為濕熱下利,且熱重于濕,可選用白頭翁湯進行靈活加減。方中白頭翁味苦性寒,擅清腸熱而解毒,并能疏達厥陰肝木之氣,輔以苦寒的秦皮,清肝膽與大腸濕熱,黃連、黃柏清熱燥濕,堅陰厚腸以止利[8]。
3.1.3 溫中健脾 養腸固脫“下利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講述桃花湯證的病機及主要臨床癥狀,方藥組成為赤石脂、干姜、粳米。以方推測病機,可知此為久利,傷及脾腎之陽,不能固攝氣血。故臨證遇到久病證屬脾腎陽虛、氣不攝血者,可選用本方酌情加減。此外,《金匱要略》所載方劑眾多,臨證只要符合患者的病機,即可選用。如“赤小豆當歸散”,在原文中出現2次,仲景用于治療狐惑釀毒證及近血證。方中赤小豆功擅解毒、消腫排膿行瘀熱,當歸長于補血和血消瘀,故可應用于證屬濕熱內蘊、瘀熱內集、化腐成膿的UC患者。
3.2 病后調護在《金匱要略》第1篇就提出治未病的預防觀念,其中包括“未病早防、既病防變,瘥后防復”,本文著重講述原文中對于UC病后的調理。“五臟病中各有所得者愈,五臟病各有所惡,各隨其所不喜者為病”明確患者病后的飲食、起居調護需與病情相適應。臨床上應重視對UC患者飲食起居的指導:在飲食上,應以少渣為主,忌酒酪炙煿、肥甘厚味、辛辣生冷;在起居上,需適寒溫,規律作息,情緒穩定。此外,“房室勿令竭乏,服食節其冷熱苦酸辛甘,不遺形體有衰,病則無由入其腠理”亦強調已愈防復的重要性。
4 小結
《金匱要略》中可以發掘到許多關于UC病因病機、治療方法、病后調護的思路與理念:UC的病機以先天不足,脾腎陽虛為本虛,以無形之寒熱毒邪、有形之痰瘀實邪為標實,本虛標實共致氣血瘀滯、脂絡受損,合而為病。治療方面,立足病機,本虛“當以溫藥和之”,標實輔以行氣化瘀、緩肝解郁、清熱解毒、消癰排膿等。在病后調護方面,著重強調對患者飲食、起居的宣教,已愈防復,以改善疾病的預后。一言以蔽之,《金匱要略》是中醫寶庫,其中蘊藏豐富的潰瘍性結腸炎相關的理論知識,能為現代臨床認識、治療、調護潰瘍性結腸炎提供有價值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