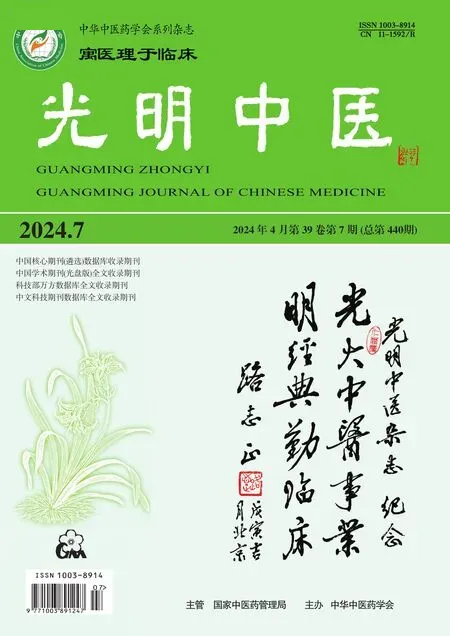曹正柳教授治療大腸癌的經驗介紹*
彭中娟 曹正柳 王 康
根據國際癌癥研究機構數據,2020年全球大腸癌新發病例數達193.1萬,發病率位居全球第三;死亡病例數達93.5萬,僅次于肺癌排在第二位,其中28.6萬死亡病例發生在中國[1]。據統計,中國結直腸癌已高居癌癥發病譜的第二位[2]。在中醫領域,大腸癌歸屬“痞塊、癥瘕、積聚、腸積、巖”等。曹正柳教授從事中醫藥臨床工作近60年,治療大腸癌經驗豐富,現整理如下。
1 病因病機
《醫宗必讀》說:“積之成也,正氣不足,而后邪氣居之”。《活法機要》有:“壯人無積,虛人則有之”。《景岳全書》有:“脾胃不足及虛弱失調之人,多有積聚之病”。可見正氣虧虛為內因。《濟生方》說:“過餐五味……強食生冷果菜……久則積結為癥瘕”。提示過食肥甘厚味、生冷果菜久積成癥瘕。《景岳全書》所謂:“飲食不節,以漸留滯者,多成痞塊”。《濟生續方》亦指出:“飲食過度,或生冷過度,不能克化,致成積聚結塊”。可見飲食不節是其外因。若五臟六腑功能正常,正氣旺盛,內邪難于產生,脾胃功能正常,運化正常,則邪難以滯留。
曹教授分析如下:其一,各種電器、磁場所形成的電輻射以及核輻射圍繞,這些輻射皆為熱邪,熱邪灼爍津血,使陰血濃、黏、稠、凝而成濁[3,4]。其二,現在物質生活非常豐富,肥甘厚膩食物、生冷飲料、各種進口或反季節蔬菜瓜果、酒、燒烤、火鍋等充斥在生活中,肥胖或大腹便便的人隨處可見。肥甘厚膩食物容易生痰生濕,生冷飲料瓜果容易損傷脾陽,脾運化功能失常,痰濁內生;飲酒、燒烤、火鍋等辛辣刺激食物會傷陰、傷津、陰傷血稠、血凝而成濁。其三,熬夜、勞累已成為習慣。熬夜、勞累耗氣傷陰。氣不足則津不布,津不布則易成痰濁。其四,藥房滿布,各種保健品、減肥藥琳瑯滿目,一些蔬菜、水果以及肉類食物中的各種殘留農藥、抗生素、防腐劑、保鮮劑及快餐、外賣中不明的添加劑、增味劑,環境污染以及裝修的污染等多種毒邪的侵襲。綜上分析,大腸癌的形成是在正虛之氣陰兩傷的基礎上,濕痰濁毒互結而成。
《醫原·濕氣論》云:“濕為濁邪,以濁歸濁,故傳里者居多”。《醫方考·中風門》中提到:“濁邪風涌而上,則清陽失位而倒置矣,故令人暴仆。所以痰涎壅塞者,風盛氣涌而然也”。《醫碥·眩暈》曰:“痰涎隨風火上襲,濁陰干于清陽也,故頭風眩暈多痰涎”。可見濕、痰均可以歸屬于“濁邪”范疇。而《靈樞·陰陽清濁》曰:“濁者其氣澀”,濁邪內生,充斥脈道,血濁不清,血澀不暢,運行無力,血流緩慢瘀滯,重則形成血瘀。可見濁邪可以導致血瘀。血瘀則氣滯,氣滯則濁不去、毒不行。
綜上所述,大腸癌是在人體正虛之氣陰兩虛的狀態下,由濁、毒、瘀相互膠結而成,氣機郁滯貫穿其中。曹教授總結認為,大腸癌的病機是以氣陰兩虛為本、濁毒瘀互結為標、氣機郁滯為特點。大腸癌是虛實夾雜、正虛邪實的疾病。
2 治療與調護
2.1 治療原則
2.1.1 中西醫協同治療①手術是治療首選,中醫以健脾益氣養血為主。早期大腸癌應當選擇手術治療,通過根治性的手術切除,將大腸癌較徹底地剔除干凈,其治愈率非常高,這是完整地將瘤體與人體分開的首選方案。正如《醫宗必讀》云:“初者,病邪初起,正氣尚強,邪氣尚淺,則任受攻”。《證治準繩》曰:“初治其邪入客后積塊之未堅者,治其始感之邪與留結之,客者除之、散之”。手術切除是祛邪的主要手段,但術中創傷失血、術后恢復均會耗傷人體的正氣,故治療宜以益氣健脾養血為主。②放化療應適可而止。中醫在化療期間以健脾益氣和胃為主,放療期間健脾益氣養陰為主。中晚期大腸癌患者,需要借助化療、放療、靶向治療、內分泌治療、免疫治療等。化療的治療方法是全身性的治療,對于有擴散的患者比較適合;放療是局部治療,對于大腸癌局限性的病灶治療效果較好。化療減瘤、消瘤作用明顯,但因其毒副作用顯著,常常導致化療不能按時足量完成。化療的患者常有食欲不振、惡心、反酸、乏力、嘔吐等癥狀。此期治宜以益氣健脾和胃。放療屬于火熱性質的毒邪,最易耗傷人體陰液。此階段中醫治療宜益氣健脾養陰為主。③終末期營養對癥支持治療,中醫以補氣、補血、補陰、補陽為主,兼顧泄濁解毒。終末期患者既無手術指征,亦不能耐受放化療。此期邪盛正衰,治療當以扶正為主,根據其氣血陰陽的偏向,分別予以補氣、補血、補陰、補陽治療,根據其耐受力度,佐以泄濁解毒,目的是盡可能改善患者虛弱之癥,減緩癌毒生長擴散的速度,改善患者的生活質量,延長其生存時間。
2.1.2 中醫治療原則——扶正祛邪扶正祛邪是治療大腸癌的基本原則,它貫穿于大腸癌防治的全過程。扶正即是扶助正氣,應根據患者氣虛、陰虛之本,結合其體質和疾病的不同階段,調整其失調和不足之處,具體方法包括益氣、養陰、生津、健脾等。①扶正之益氣健脾法。正如《黃帝內經》云:“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醫學心悟》云:“虛人患積者,必先補其虛,理其脾”。故調氣健脾在大腸癌治療中很關鍵。脾為后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脾主運化。脾虛濁邪內生,脾虛則氣血生化乏源。益氣健脾,一方面脾運則濁消,利于腫塊的消除;另一方面,脾氣者氣充血旺盛,利于抗邪。因此,大腸癌的治療,要處處照顧脾胃,重視胃氣的恢復,所謂“有胃氣則生,無胃氣則死”。其扶正以益氣健脾為重。代表藥物有黨參、太子參、人參、西洋參、黃芪、山藥、白術、靈芝等。②扶正之養陰、生津法。氣陰兩虛是大腸癌的病機之一。加之放療手段的介入或一些化療藥物的影響,陰虛津傷在大腸癌的過程中常常出現,主要表現為口干、口苦、煩躁、盜汗、大便干結難解,舌質紅,苔少,脈細數等陰虛傷津癥狀。常用藥物選用玄參、沙參、人參、西洋參、石斛、天花粉、生地黃、麥冬、玉竹、枸杞子等。③祛邪之泄濁法。《丹溪心法》云:“諸病皆由痰而生,凡人身上、中、下有塊者多是痰”。痰濁是病理產物,是大腸癌產生的因素之一。以舌苔膩、脈滑為辨證要點。濕、痰均歸屬于濁邪。化痰、消痰之泄濁選用浙貝母、芥子、薏苡仁、雞內金、陳皮、化橘紅等。其中浙貝母清熱化痰,芥子溫肺化痰、豁痰利氣、散結通絡。芥子和浙貝母溫寒并調,相得不偏,氣機疏暢,痰濁得解。薏苡仁性涼,味甘、淡,健脾滲濕以泄濁。④祛邪之解毒法。中醫認為,濁毒瘀膠結,郁積而化熱,加之大腸癌治療所運用的放化療,放療(熱邪)和化療(抗大腸癌藥物的不良作用)的影響。大腸癌患者常有灼熱疼痛、發熱、便秘、舌苔黃膩等熱性證候。根據《黃帝內經》中“治熱以寒、熱者寒之”的治療原則,臨床上常需要選用清熱解毒藥。清熱解毒藥在抗大腸癌的同時也能控制和消除大腸癌周圍的炎癥和水腫,因此清熱解毒也就成為治療惡性大腸癌的一個重要方法,成為阻止大腸癌發展的關鍵之一。常用藥物有白花蛇舌草、夏枯草、石上柏、半枝蓮、腫節風等。⑤攻補兼施之調氣化瘀法。氣機失常是大腸癌發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病理變化,而氣機郁滯則貫穿大腸癌的始終。正如《諸氣源流》曰:“凡人清純元氣,與血流行,循環無端,若沖擊橫行于臟腑間,而為痛、為痞滿、為積聚等病者,氣失其平也”。由此可見,氣機失常是大腸癌發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病理變化之一。《靈蘭要覽》云:“治積之法,理氣為先”。《景岳全書·血》云:“血必由氣,氣行則血行,故凡欲治血,則或攻或補,皆當以調氣為先”。因此,調理氣機在大腸癌治療中至關重要。理氣寬中選用枳殼、陳皮、佛手、香櫞等以散氣滯于中。理氣止痛選用川楝子、香附、延胡索等。濁毒瘀互結是大腸癌發生的主要病機,其中血瘀是大腸癌的病因之一,活血化瘀是治療大腸癌的重要治法。但是,曹教授認為,活血化瘀藥可能會促進大腸癌的轉移。根據明代徐靈胎 “氣為血帥”“氣行則血行”的觀點,曹正柳教授認為,補氣如黃芪、黨參、太子參,行氣如枳殼、陳皮、香附、厚樸等均可達到化瘀的目的。氣虛一則無力鼓動血液,瘀血乃生。益氣健脾,氣血充盈,氣充則血行。理氣活血,氣行則血行。但如大腸癌已有轉移者且有明確血瘀之癥者,可適當加用蟲類藥如蜈蚣、穿山甲破瘀通絡,促進癌腫消散。⑥強調通腑藥的運用。《素問·五臟別論》謂:“六腑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能滿也”。金元時期張從正認為通腑可使“壅礙既奪,重積得減,則氣血流通,而自身體健,勝于補藥”。大腸癌患者無論是否行手術治療,都要注意通腑藥的使用。一方面,保持腸道通暢可使癌邪有路可出;另一方面,保持腑氣通暢,幫助恢復胃腸道的功能,從而正常發揮其傳化物而不藏的功效。常用通腑藥分為清、溫、潤。常用藥有大黃、枳實、虎杖、生地黃、玄參、紫蘇子、杏仁、萊菔子、瓜蔞仁、肉蓯蓉、火麻仁、郁李仁等。曹教授強調,六腑以通為用,以降為順,具有瀉而不藏的特點。因此,大腸癌在用藥時常使用通腑藥,可以起到“邪去正自安”的功效。
2.2 常用方藥分析
2.2.1 加味五磨飲子大腸癌術后容易發生腸梗阻或大網膜粘連綜合征,而出現腹痛、惡心、嘔吐以及大便不暢等癥狀。手術過程會導致機體氣機運行不暢或阻滯,血行受阻,形成血瘀。治宜調氣化瘀泄濁,擬加味五磨飲子作為治療的經驗方。五磨飲子由檳榔、枳實、木香、烏藥、沉香、檀香、炒萊菔子、厚樸、延胡索、神曲、虎杖組成。全方共奏調氣、活血、泄濁之功。如疼痛明顯加失笑散,便秘加火麻仁、柏子仁或大黃,濕困脾胃加茯苓、蒼術或者薏苡仁,中氣不足加黃芪、黨參,呃逆明顯加旋覆花、柿蒂或小半夏湯[5-7]。
2.2 加味消瘰丸加味消瘰丸由浙貝母、玄參、夏枯草、生牡蠣組成。浙貝母別名象貝、珠貝、元寶貝,是百合科植物浙貝母的干燥鱗莖,其性味苦、寒,歸肺經,具化痰止咳、清熱散結之功[8]。現代藥理研究表明,浙貝母具有止咳,祛痰,鎮痛,抗炎,溶石,抗潰瘍,抗大腸癌,抗菌,止瀉,松弛平滑肌等多種活性[9]。玄參苦、甘、咸、寒,能清熱、解毒、養陰。李醫明等[10]發現玄參中具有抗大腸癌活性的苯丙素苷類化合物。《神農本草經》[11]言:“夏枯草味苦、辛、寒,治療熱瘰疬,鼠瘺,頭瘡,散癭,結氣,腳腫,濕痹,輕身”。黃元御《玉楸藥解》認為夏枯草入足厥陰肝經、足少陽膽經。涼營瀉熱,消腫散堅。馬偉等[12]對夏枯草的現代藥理學活性研究發現,夏枯草具有明顯的抗甲狀腺癌、抗淋巴瘤、抗乳腺癌的作用。生牡蠣,咸、微寒,歸肝、膽、腎經,有軟堅散結、平肝潛陽、重鎮安神、收斂固澀的功效。牡蠣有增強免疫、抗疲勞、抗病毒、保護肝臟、降糖、抗大腸癌、抗氧化、抑菌等作用。
2.3 日常調養
2.3.1 調暢情志患者首診一定先行話療治心以調暢其情志。對患者進行心理疏導,解其疑惑,可以調動腫瘤者機體的積極因素,發揮其機體內在能力有利于配合治療,此亦即扶正治療之大法。正如《丹溪心法》云:“氣血沖積,萬病不生,一有怫郁,諸病生焉……人身諸病,多生于郁”。倘若能保持樂觀向好的心態,可以提高機體免疫力,有利于疾病的康復。
2.3.2 生活調理生活調理首先是避免受涼,少食生冷食品;其次應注重飲食調節,包括細嚼慢咽、不宜過飽、定時定量、少食堅果類及不易消化之食品、少食油膩等;避免情志過分波動,保持心情愉悅狀態。總結起來就是要注意三件事六個問題,以防疾病誘發[4]。
2.3.3 飲食禁忌應盡量避免服食中醫發物。對于大腸癌及感染性疾病者而言,應盡量禁食鯽魚、蝦、雞、狗肉、黃花菜、竹筍(不包括冬筍)等[4]。
3 驗案舉隅
3.1 大腸癌術后反復復發腸梗阻曹某某,男,54歲。2019年10月10日初診。患者2019年1月因大便帶血在外院行直腸癌手術,術后病理提示直腸中分化腺癌伴部分粘液腺癌。術后行6次化療。2019年5月份因腸梗阻入院行造瘺口回納術加闌尾切除術。術后再次出現腹脹如鼓,伴有腹痛。外院考慮腸梗阻,建議患者再次手術治療。患者因不愿意手術治療而求助南昌大學第二附屬醫院中醫科服用中藥。患者緣于2 d前因受涼出現腹脹、腹痛,予以藥物(具體不詳)后癥狀無明顯緩解。刻下見腹部脹痛、進食加重、大便不暢、不思飲食、嘔吐,食則吐甚、口干、口苦,舌質暗紅,苔白稍厚膩,脈弦滑。西醫診斷:考慮腸梗阻。中醫診斷:痞證(氣滯血瘀)。治療予以調氣泄濁。予以加味五磨飲子。藥予檳榔 15 g,炒萊菔子 30 g,厚樸 15 g,檀香 4 g,烏藥 10 g,延胡索15 g,木香10 g,枳實 15 g,沉香 4 g,神曲 20 g。共3劑。水煎服,日1劑,分2次溫服。3劑藥后患者大便通,腹痛、腹脹消失而飲食逐漸恢復正常。考慮患者為直腸中分化腺癌伴部分粘液腺癌,為防止大腸癌復發或腸梗阻復發。平時予以益氣養陰、泄濁解毒、調氣通腑中藥治療。具體用藥如下:浙貝母20 g,玄參10 g,牡蠣15 g,夏枯草15 g,貓人參15 g,藤梨根15 g,薏苡仁30 g,蜈蚣3 g,敗醬草10 g,降香10 g,沉香5 g,枳實15 g,貓爪草15 g,山慈姑10 g,白花蛇舌草15 g,靈芝10 g,南方紅豆杉8 g,太子參30 g,厚樸15 g,香櫞15 g,重樓 6 g。如食欲差加神曲、麥芽,如大便不暢加郁李仁、火麻仁,呃逆加柿蒂、旋覆花,乏力加黃芪或黨參或人參。2020年4月13日因腹痛再次入院。1周前患者因進食較雜食物(糯米以及堅果)后出現腹痛,以脹痛為主,伴有呃逆,進食后嘔吐,大便未解,自己口服藥物后癥狀無明顯緩解。腹部立位片提示腸梗阻。治療予以調氣泄濁。予以檳榔15 g,枳實15 g,烏藥10 g,木香10 g,沉香5 g,大黃15 g,厚樸15 g,芒硝10 g,炒川楝子15 g,醋延胡索15 g,降香10 g,炒萊菔子30 g。2劑藥后患者大便通暢,腹痛消失。平時繼續予以益氣養陰、泄濁解毒、調氣通腑中藥治療。患者服藥至今。體質量增加約8 kg,期間未復發腸梗阻。電子腸鏡以及腹部CT檢查均未見大腸癌轉移或復方征像。患者治療過程中CT復查如下:2019年12月12日CT提示:直腸癌術后改變,右側髂血管旁囊性灶(30 mm×37 mm),增強后輕度強化。2020年3月13日CT提示直徑直大腸癌術后改變,右側髂血管旁囊性灶(47 mm×43 mm)。2020年7月22日CT提示直徑直大腸癌術后改變,右側髂血管旁囊性灶(27 mm×19 mm)。2021年12月28日CT提示直徑直大腸癌術后改變,右側髂血管旁囊性灶未見顯示。每年復查電子腸鏡均未見異常。
按語:術后腸梗阻是大腸癌腹部手術后常見的并發癥,此患者為大腸癌術后患者,腸梗阻者發作時予以加味五磨飲子作為經驗方。以防復發,平時治療上選用消瘰丸加貓人參、藤梨根、敗醬草、貓爪草、山慈姑、白花蛇舌草、重樓、南方紅豆杉、薏苡仁泄濁解毒,太子參、降香、沉香、厚樸、香櫞以益氣養陰,調氣通腑。平時牢記如上所述三件事6個問題,以防疾病誘發。
3.2 大腸癌術后復發張某某,男,47歲。2010年11月因在外院行直腸癌根治術(Parks術),術后反復出現腸梗阻,于2010年底在南昌大學第二附屬醫院服用中藥治療。服藥至2015年11月未發作腸梗阻,每年復查未見復發及轉移征像而停藥。2020年5月17日因肛周疼痛不適行腹部CT檢查提示直腸癌術后,直腸右側壁稍厚,建議結合腸鏡;直腸右側旁﹣盆壁囊性灶并鈣化,考慮良性病變可能(48 mm×72 mm)。電子腸鏡提示直腸癌術后。2020年8月PET﹣CT 報告直腸下段腸壁增厚。2020年8月7日在外院經陰盆腔腫物穿刺報告:盆腔粘液腺癌。后行多次放化療以及靶向治療。2020年8月21日外院CT提示腫塊為76 ×56×88 mm。因腫塊未見縮小,病情無法控制而于2020年9月3日開始服用純中藥治療。癥見肛門疼痛不適,身體疲倦乏力,時有腹脹以及腹痛。舌質暗紅,體胖,邊有齒痕,苔薄白,脈弦滑。予以益氣養陰、泄濁解毒、調氣通腑中藥治療。浙貝母20 g,玄參10 g,牡蠣15 g,貓人參15 g,靈芝10 g,太子參30 g,姜黃15 g,山慈姑10 g,炮山甲5 g,蛇六谷10 g,腫節風20 g,藤梨根15 g,貓爪草15 g,白花蛇舌草15 g,南方紅豆杉8 g,薏苡仁 30 g,炒川楝子15 g,蜈蚣3 g,重樓6 g,鹽橘核30 g,鹽車前子8 g,人參10 g。共30劑,顆粒劑,泡水沖服。2021年6月10日復查CT提示腫塊為89 mm×71mm,CA724 為414.8。治療繼續以上方為主,每天1劑。2022年3月13日復查提示腫塊縮小,大腸癌標志物下降。腫塊為76 mm×58 mm,CA724為 229。大便不爽,日行數次,時感右側肩關節疼痛,夜寐欠佳。舌質暗紅,體胖,邊有齒痕,苔薄白,脈弦滑。予以化益氣養陰,泄濁解毒、調氣通腑,兼理氣止痛中藥治療。具體用藥:浙貝母20 g,夏枯草10 g,玄參10 g,牡蠣(先煎)15 g,車前子15 g,升麻20 g,獼猴桃根15 g,蜈蚣1條、重樓6 g,火麻仁30 g,黨參30 g,仙鶴草30 g,山慈菇10 g,白馬骨15 g,貓爪草15 g,芥子8 g,白豆蔻(后下)10 g,厚樸15 g,鱉甲(先煎)30 g,腫節風20 g,延胡索15 g,白術20 g,白花蛇舌草15 g,砂仁(后下)10 g,橘核子30 g,蛇莓6 g。共30劑,水煎服,日1劑,分2次溫服。2022年4月18日復診,2022年4月12日被車撞傷腰骶部至醫院就診。MRI示直腸右側旁間隙及鄰近盆璧強化灶伴鄰近軟組織水腫改變,較前病灶稍有縮小,考慮感染性病變可能。CT示盆腔內混雜密度腫塊結合病史考慮轉移,不除外感染可能。右側肩關節疼痛,夜寐欠佳。舌質暗紅,體胖,邊有齒痕,苔薄白,脈弦滑。加用西黃膠囊0.75 g每天2次。中藥:浙貝母20 g,升麻20 g,牡蠣(先煎)15 g,玄參10 g,重樓6 g,黨參30 g,仙鶴草30 g,白馬骨15 g,千里光15 g,夏枯草10 g,芥子8 g,貓爪草15 g,白豆蔻(后下)10 g,獼猴桃根15 g,白花蛇舌草15 g,白術20 g,厚樸15 g,鱉甲(先煎)30 g,蜈蚣1條、橘核子30 g,蛇莓6 g,腫節風20 g,延胡索15 g,砂仁(后下)10 g,山慈菇10 g,火麻仁30 g。共30劑,水煎服1次用量。2022年6月20日復診大便難下,余未訴明顯不適。浙貝母20 g,升麻20 g,牡蠣(先煎)15 g,玄參10 g,重樓6 g,黨參30 g,仙鶴草30 g,白馬骨15 g,千里光 15 g,夏枯草10 g,芥子8 g,貓爪草15 g,白豆蔻(后下)10 g,獼猴桃根15 g,白花蛇舌草15 g,虎杖15 g,山慈菇10 g,白術20 g,厚樸15 g,鱉甲(先煎)30 g,蜈蚣1條、火麻仁30 g,橘核子30 g,蛇莓6 g,腫節風 20 g,延胡索15 g。共30劑,水煎服,日1劑,分2次溫服。半年后患者因腸梗阻住院。患者于2022年12月死于肺部感染。
按:該患者術后10年復發,復發后無手術指征而化療及靶向治療效果不佳。中藥以泄濁、解毒、調氣、通腑、軟堅、散結為主,健脾、益氣、養陰為輔的治療原則。治療上選用消瘰丸加減。曹教授主張復發之前謹慎使用活血化瘀藥,但該患者為大腸癌復發患者,且放化療乏效,故治療中蜈蚣聯合穿山甲破瘀通絡以泄濁,大劑量鱉甲以軟堅散結,從而促進癌腫消散。太子參、人參、白術以益氣健脾固護后天之本。六腑以通為用,以降為順,加厚樸、砂仁、白豆蔻、火麻仁等理氣潤腸通便,以順應六腑之性。
4 結語
曹教授結合多年臨床經驗,臨證治療大腸癌時,立足于氣陰兩虛為本、濁毒瘀互結為標、氣機郁滯為特點,補虛泄實。用藥注意以通為用,以降為順,順應其六腑通降之性。同時將固護脾胃貫穿于大腸癌治療的始終,在改善患者臨床癥狀、增效減毒、提高患者生活質量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值得臨床參考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