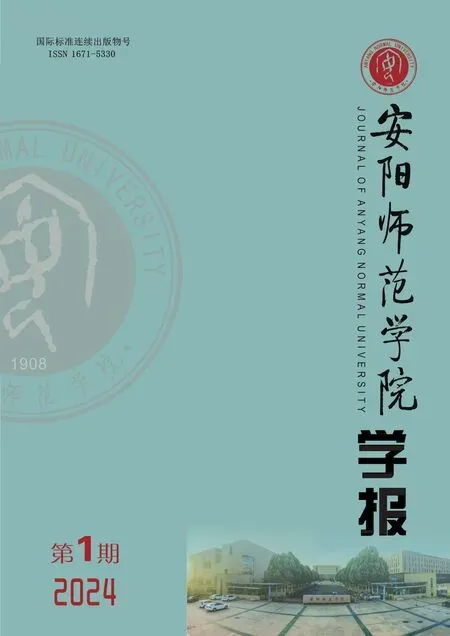《寶水》的魅力
——評第十一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寶水》
周艷麗
(安陽師范學院 文學院,河南 安陽 455000)
“70后”女作家喬葉的長篇小說《寶水》,2022年一經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就引起了讀者和評論界的廣泛關注,并獲得了第十一屆茅盾文學獎。這部以書寫新時期新農村發展變化為主題的小說,被文學界稱之為是“70后”作家的突圍之作,是中國式現代化鄉土文學的力作[1]。
若嚴格按大眾閱讀審美去界定這部小說,似乎還不能夠完全吻合。因為大多數小說都是以故事情節的跌宕起伏和引人入勝立腳的。這部小說缺少跌宕和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有散文或詩化傾向。令人不解的是,就是這樣一部不太符合傳統審美標準的小說,卻反而討喜了讀者,得到了讀者和評論界的廣泛認可。這又是為什么呢?可否這樣認為,當今讀者已經看厭了大多數小說的紛繁復雜、高潮迭起,故事情節光怪陸離、跌宕起伏等,突然出現了這么一部將農村的四季寫得分明,將農民的生活寫得細致入微,不急不緩,有張有弛,有板有眼的作品,卻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我想恰恰是新型農村這種“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隨常百姓生活才是人們最感興趣和最想了解的,這也是《寶水》的魅力所在。
一、 篇章結構簡潔明了,讓人一目了然
《寶水》的故事一點也不復雜,寫的是位于太行山深處的一個叫寶水的村莊。像大多數中國現代農村一樣,寶水也在經歷著一個由傳統農村向以文化旅游為特色的新型農村的轉變中。而這種轉變又不是急風驟雨式的,而是發生在每一時,每一刻,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中,發生在農村人的開門七件事中,是新農村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像普通農村人過日子一樣,沒有大起大落,也沒有驚天動地,就是普通百姓隨常的日子、平淡的生活。正是在這一點一滴看似無卻又有的變化中,被受嚴重失眠癥困擾、為治愈失眠癥提前退休的媒體人地青萍遇到了。看似無心,實則有意。作品寫的就是地青萍在寶水村居住的一年中,親眼所看、親身體驗、親自感悟到的,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中寶水村的流水生活。將一個新時代新農村豐富而深刻的嬗變,呈現在了讀者的面前。
30多萬字的一部著作,總共分了4章,這4章不是按故事情節的跌宕起伏、高高低低劃分的,而是像農村人過日子要經歷春夏秋冬一樣,按一年的四季來劃分。第一章《冬——春》,正像大自然會走過春夏秋冬一樣,冬季的時候,地青萍因為失眠無法治愈,提前退休去了好朋友老原的家鄉寶水村。為什么要選擇寶水村呢?因從小在農村長大,對農村有著深厚的情感,她不僅喜歡農村的麥香草香,就連“大糞”那種別人難以容忍的味道,地青萍都能適應。于是,地青萍來到寶水村,一個和她自己生活過的福田莊很相似的山村。在替老原管理民宿的過程中,她自然也參與了《敬倉神》《吃懶龍》《挖茵陳》等活動,感受了悠、亂、扯云話等地方特有的話語,結識了大英、九奶等寶水村的一概人等。表面上,第一章30小節,每一節似乎只是作者將發生的事情按時間順序寫下來了,并無太大聯系,仔細回味就會發現,節與節之間仿佛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卻并不突兀。于是就在那個冬季里有《肥水不流外人田》《敲瓷磚》《開大會》等故事發生。在此,我們也認識了《大英家》的大英和《九奶家》的九奶等人,還了解了寶水人所說的《扯云話》《愿語》等農村的一些風俗人情。冬季是個萬物蕭瑟的季節,又恰恰是孕育新生命的好時節,春天已經到了,距夏天還會遠嗎?于是有了第二章《春——夏》,夏在四季中應該說是一個萬物茁壯生長,充滿生機、充滿希望和活力的季節,發生在春夏之間的事情,看似弱小卻蘊含著生機和力量。于是就有了《豆家事》《玉蘭吾妻》《梀花開,吃碾饌》《捋槐花》《衣錦還鄉》《上梁》等從春走向夏時寶水村所發生的事。第三章《夏——秋》,秋天是成熟和收獲的季節,一切都充滿了喜慶和歡樂,所以就有了《人身小天地》《不受罪咋享福》《過命交情》《送行宴》《萬柿如意》《大地色》等林林總總。第四章則是《秋——冬》,冬的關鍵節點在于一個“藏”字,為下一年春的孕育,搭好橋鋪好路。這一章主要以寶水村靈魂式的人物九奶下葬為主線。就有了寶水村靈魂人物九奶的去世。有了《丟魂兒》《咱回家吧》《神針》《野菊花》《酸黃菜》《流水盛宴》《過小年》等故事和為九奶送行的《喜喪》《暖土》等。整個篇章前后照應,開篇從正月十七寶水村要將請來的祖宗和神靈送走為起始,稱之為“落燈”,而篇終卻到了這一年的大年三十,寶水村按照當地的風俗,要接祖宗和神靈回家過年,稱之為“點燈”。“落燈”始,“點燈”終,恰恰是一個輪回。而新型農村的發展正像在四季中孕育一樣,歲歲年年,周而復始。
二、 寫活了新農村中的鄉土人物
如果說,一部小說一定要確立一個主人公的話,那《寶水》中的主人公是誰呢?細算下,《寶水》中出現的人物林林總總有幾十位之多,最主要的人物有寶水村的村支書大英、婦女主任秀梅、會計張有富、團委書記小曹曹建華等;有村子里的文化人村醫徐先兒和風水先生趙先兒;有普通村民張大包、老安夫婦、豆哥與豆嫂、七成與香梅兩口子、小曹的堂兄大曹曹建業、大英的兒子鵬程和兒媳雪梅,還有德高望重的老人九奶等,此外,還有從寶水村走出去的老原和發達了的趙順等;“外來者”——有媒體人地青萍和鄉建專家孟胡子、在寶水附近山溝租地養雞的馬菲亞兩口子以及來寶水實習的大學生肖睿和周寧等等。
這一眾人等到底誰是主人公呢?地青萍?大英?孟胡子?楊鎮長?老原?抑或是九奶?似乎從整體去看,這些人物都是主人公,就個體而言,這些人又都不是主人公。他們在整個故事中都出現過,但又時常有缺場。故事從前到后,惟一全程在場的只有地青萍一人,但在整個寶水村她似乎又不是真正能擔綱的主角。如果硬要給《寶水》這部著作找一個主人公,無疑寶水村就是這部作品真正的主人公。這主角不僅有我們以上所提到的人物,還有寶水村的四時喜樂、豬馬牛羊和春夏秋冬等的四季更替。是他們集體撐起了整個寶水村的故事,撐起了《寶水》這部著作。盡管沒法確定真正意義上的主人公,但有幾個關鍵性的人物在《寶水》這部著作中還是起扛鼎作用的。
地青萍是個飽受失眠癥折磨,剛剛失去丈夫不久的一位中年知識女性。她的童年也是在農村度過的,所以,對于鄉村她懷有濃厚的情愫。而童年記憶中的村莊福田莊給她留下的并不全是美好的回憶,反而因為農村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給她在城里的家庭帶來了很大的困擾,父親就是因為受這種關系的影響失去生命的,使她的家庭處于殘缺之中。為此,她恨上了自己很崇拜的奶奶和培育過自己成長的福田莊。對于農村對于農村人,地青萍一直處于愛恨交織之中。正因為處于這樣的情感之中,她對于鄉村的態度也是既想親近,又想躲開,自始至終都有很強的疏離感。渴望接近它,成為它之中的一員,又希望遠離它,擔心變成它中的一員。
是的,無論看起來多么像村里人,這些細枝末節總能讓我覺得自己還是個外人。
終究是個外人。
果然是個外人。
幸好是個外人。[2](P143)
正因為對于鄉村有一種“欲罷不能,欲說還休”的愛恨情仇,所以,她心里明白,自己的失眠癥也只有鄉村能夠治愈,因為她童年生活過的福田莊已經被拆得面目全非,她來到了寶水村。在此后的一年中,她不僅參與和見證了寶水村的各種變化,同時,對于她自己的家鄉福田莊也有了不同以往的認識,對于奶奶的積怨也在一點點消解。在寶水村居住的這一年之中,她不僅見證了當代鄉村生活新與舊的碰撞和交融,也使自己獲得了新生和蛻變。
大英,是寶水村的黨支部書記,是寶水村的領頭羊、帶頭人,是當代新農村干部的典型。在寶水村由傳統村落向以文化旅游為特色的新型農村轉型中起著關鍵的作用。應該說寶水村能成功轉型,成為網紅打卡地,跟有大英這樣一位帶頭人是分不開的。大英潑辣、能干、善良、正直,有大情懷,既有服務意識也有奉獻精神,還能認清自己,給自己準確定位。同時,她還很精明、狡黠、圓滑,很善于在各種利益層面間斡旋。大英生在農村,長在農村,她十分懂得農村和農民,處理問題能夠站在農村和農民的立場,設身處地地為農民著想,能巧妙地化解農村中的各種矛盾。但身上也不乏一些農村保守和落后的舊觀念,舊觀念主要表現在她對于兒媳雪梅學畫的態度上。大英是直接從村小組長一下子提到村黨支部書記這個位置上的,也算是坐著火箭往上升的村干部,對此,她自己卻沒一點驕傲自滿,能正確認識自己:“升啥升,一升不如半斗。農村的官兒算個官兒?像咱這,有名聲是個村干部,說到底也是平頭老百姓。”大英知道她當村干部已經不是拉票賄選,好處多多,人人都爭著搶著想干的時代了。“留下的凈是些老弱病殘。村干部已經沒人眼紅了。再后來農業稅也不用再交了,村里也沒了提留款,計劃生育也不再成個事兒,村干部也就沒了一點兒掐人的實惠,只剩下了討人嫌……”[2](P33)即使這樣,大英干起工作也是毫不含糊,仍然丁是丁,卯是卯。大英心里明白,要想當好村干部,就得立場堅定,旗幟鮮明,秉公辦事,一碗水端平,還得有奉獻精神。大英最可貴之處在于,她當村支書不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而是心里有想法,行動有章法。她心中有一個執念,就是要把寶水村的根留下,大英明白只有留住了寶水村的根,才能留住寶水村的人。即使在寶水村“男男女女青壯年,生出小的老人兒去帶,反正是,胳膊腿兒全的,能動彈的,有辦法的,都往城里跑”[2](P33)的情況下,大英還在想盡一切辦法,想把寶水村的人從城市里拽回來。因此,無論別人出多少錢,她都不把村子里面“五摟粗,八百年”的老祖槐賣了。大英知道老祖槐就是寶水村人的根,留住了老祖槐就留住了寶水村的根。正是有了這種情結,大英也有了建設好新農村的決心和力量。孟胡子之所以把寶水村作為新鄉村建設的試點,看中的也是寶水村的領頭人大英有大情懷。
最能體現大英在各種層面間斡旋的是趙順回村蓋房子那件事,按村子里規定,任何人不經村委會允許不準蓋房子,偏偏趙先兒的兒子趙順在城里發達了,想在村里翻建房子。趙順因為有錢,曾經多次幫助過村里,要是論對村子里的貢獻,大英不應該駁了趙順的面子。但畢竟有村規民約在那里擺著,作為村支書的大英不該厚此薄彼。怕大英為難,趙順就選了個大英外出考察的日子,開始翻建房子。等大英從外地回來,房子已經蓋得差不多了。作為村支書的大英對此事又不能沒個態度。于是,她就找到趙先兒,質問他為啥違犯規定,只是發了通脾氣便不了了之。而對上級(楊鎮長)的指責,大英卻敢撒潑耍橫:“反正不是該死的罪!哪家鍋底不冒煙?沒出人命就不算亂。你要是覺得真過不去,那等著你撤我。我跟你說,你就是撤了書記,我還是村長,我還有人民群眾支持我,咋的?”[2](P257)表面上這么說,大英其實心里跟明鏡似的,在處理村民的問題上,知道哪輕哪重:“你們是公家人,能調來調去,我們這些人,當啥村長書記都是個活意思,今年不頂明年事,打根兒起就是村里人,一輩子都在這個村,往哪兒調去?哪兒也去不了。做官不做官不要緊,你先得好好為人。不好好為人,將來結下的疙瘩多了,走平路說不定就摔個嘴啃泥。”[2](P258)正因為大英懂得農村的人情世故,辦事才不死板,既有立場也會變通,連楊鎮長也十分欣賞像大英這樣的農村干部:“我問,大英的能力算是強的吧。他沉吟片刻道,算是中上等吧。但人品好,這個沒的說,這比能力重要。村干部,咱不要打江山的,就要守江山的。你要能力那么強的人干啥,要是能力強還人品差,那跟你鬧事的花樣也新,可難收服。”[2](P259)
另一位是鄉建專家孟胡子,孟胡子是近些年在新農村建設中才出現的新人物形象。他和他的團隊為新農村建設做規劃搞建設,專門服務于農民,是推動新農村建設必不可少的外部力量。千萬不能小看了這股力量,在新農村建設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是構建政府和新農村的中堅和橋梁。
孟胡子是帶著鄉村建設的項目來農村找落地的,經過千挑萬選,看中了寶水村,他的主要任務是改造寶水村的民宿,為寶水村的整體建設和長遠發展出謀劃策。像這樣的一個人物對于寶水村來說是十分關鍵和重要的,他若看不上寶水村,寶水村就成不了新農村建設的典型,也得不到政府的支持,沒有政府的支持寶水村也不可能快速發展起來。因此,像孟胡子那樣的鄉土專家不僅需要有一定的專業知識和文化素養,還要懂得農村的人情世故,能和農村農民融為一體,同時,也得了解政府,能游刃于官場。鄉建專家孟胡子就是這樣一位既懂農村人情世故也了解官場上的種種規則。他游走在縣政府、鄉政府、村干部和村民之間,善于察言觀色,他既明白新理念,也知道舊風俗,既熟諳政府運行規則也很接民間地氣,是個典型的文化商人。就拿農村的隨禮來說,孟胡子就很有一套自己的哲學:“不知怎么又說起秀梅的民宿過些天應‘好兒’的事兒來,便問他該怎么隨禮。孟胡子道,我可不隨。這些年,那么多村子,要是都隨禮,那可有的隨。第一個村子我老老實實隨了禮,隨時人家也挺高興。后來發現隨一家就得隨百家,要不然就得罪人。他們本村人之間有遠近親疏愛恨情仇,隨禮都有高低,可咱這外人不行,尤其是有工作關系的外人,必須一碗水端平。可家家都隨碗碗端平也就等于零。打那起我才知道,人際關系這事,有厚有薄才能顯得出來,你全加厚了一層,那就等于一點兒也沒加,無用功。從此我總結了八個字:感情投入,經濟絕緣。到哪個村我都不再隨禮。我那兒備有紅紙,回頭寫副賀聯就成。”[2](P71)就這一番話,把孟胡子那種深諳農村人情世故,又狡黯圓滑的商人形象活脫脫地刻畫了出來。孟胡子不僅知農村的舊禮俗,對于現今的官場也有他自己的行道:作為鄉村建設方面的專家,開過太多的會,見過太多的領導,他能從眾多的領導中,找到那位想干事,又能干成事的真正領導來,“要想在基層做成事,村民、村干部和主要上級領導缺一不可,尤其是主要上級領導。對,必須是主要上級領導。閔縣長要還是副縣長,我就還下不了決心。他當了縣長,按常規下一步就能當書記,我前面這六年就能做得有連續性,就能踏實。”應該說,作為鄉建專家,孟胡子可算是混得風聲水起,如魚得水,他既要地方政府扶持又不要地方政府干涉,既大權在握又不承擔責任,能做到這一點,的確不容易,但孟胡子做到了,因為他深諳經營之道,他始終掌握著:當他的意見和村干部意見不一致時,聽村干部的,當村干部和村民意見不一致時,聽村民的。因為孟胡子明白,最終村子還是村民的。應該說,孟胡子既是一個文化商人,同時他也是美麗鄉村的實踐者和傳統文化的守護者。
可以這么說,《寶水》中出現的許多人物,無論是否主角,只要出場,就被塑造得栩栩如生、活靈活現。實事求是說,在如今的鄉土文學寫作中,我們已經好久沒有看到如此生動和豐滿的形象了。
三、 敘事語言精準、細膩、恰當、富有意味
有人說,《寶水》寫出了豫北新農村的根脈、筋骨和血肉,寫活了豫北農村生活的真相和現實感[3]。而這一切靠的是作者喬葉精準、細膩、恰當、富有意味的語言來實現的。毫不夸張地說,《寶水》這部長篇小說,最大的魅力就在于作者扎實的語言敘事能力。在整部作品中,作者幾乎把寶水的人、事、物全部寫盡了。從生活日常、人際交往、風俗習慣、各種節日到四季輪回等;還有山川河流,花草樹木,莊稼和鳥蟲;包括寶水人說的家鄉話和俚語全部都寫到了,可以這么說,《寶水》所描繪的就是豫北新農村的生活畫卷,不僅有很強的帶入感,還有很強的現實感。而在對寶水村的人事物的敘述描寫中,作者既能做到面面俱到,又各具特色,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此可見作者敘事功底的深厚,駕馭語言能力的強大。
(1)著墨于自然景物和事物的細膩描寫。在《寶水》這部著作中所呈現的鄉村世界,是一個被豐富的“物”所環抱著的世界。從無生命的山川河流,犁耬鋤耙等器物,到有生命的花草樹木,豬馬牛羊,作者都寫到了。值得一提的是,在其他作品中,也有關于山川河流、花草樹木的描寫,但給人的感覺是為敘述故事作陪襯的。而《寶水》是將這些景物器物作為主角來描繪的。《寶水》第一章中有一節叫《早春花》,作者專門把寶水村所生長的開在早春的花如漆桃花、野杏花、山茱萸、燈臺草、茵陳等拿出,不急不緩,慢條斯理地娓娓道來:
跟著這批花最早萌顯出來的還有燈臺草,只是一個高,一個低,沒人去看這低的。剛出土的燈臺草貼著地皮,雖是草,卻極像花,嬌小玲瓏,泛著嬌嬌嫩嫩的紅。它還有一個名兒叫五朵云。幼時莖頂就生五葉,再長高些就歧出了五枝,枝上再開出黃中帶綠的花,花下還有五葉。總之它的花葉是離不了五這個數,這應該就是五朵云的來由。五朵云雖好聽,我卻更喜歡叫它燈臺草。小時候受過它的害。有一回采了一把玩,回家后肚子和腿又疼又癢,鬧了兩天才好。奶奶仔細詢問,知道我碰的是它,就說,再碰就會爛腸子瞎眼睛。是毒草。按中醫的說法,凡草皆是藥,是藥。不過常人都是不知其藥性卻易惹了毒性的,那還是躲著點兒吧。[2](P80—81)
寫花花草草的內容,居然敢拿出一節三四千字的篇幅,也只有像喬葉這樣的作家才敢。別說,由于作者觀察細致,描寫精微,細細讀來,這些花花草草仿佛就在眼前,而農村的生活氣息一下子也躍然紙上了。
除山川河流,一草一木寫得細致入微外,就連城市里早已經退出歷史舞臺,農村人還在用于傳遞信息的大喇叭,作者也不怕浪費筆墨,好好地敘述了一番。
喇叭是一種特別威風且神秘的存在。只要耳朵還好用,這就是鄉村里誰也躲不掉的聲音,是可以在任何時刻入侵到各個角落的聲音。里面傳出的話似乎都是重要的話,說出的事似乎都是重要的事。誰家孩子考上學了,高中、中專、大專、大學都算,誰家要給孩子辦滿月酒,誰家要給老人過大壽,誰家要給亡人辦三周年,更別說男婚女嫁,起房蓋屋,都得通過大喇叭吆喝得全村皆知。還有那些涉及錢的事,交教育附加費、交電費、交什么提留款,買化肥………有時候也不說什么事,就是村長支書在里面訓人,也不指名道姓,只是指桑罵槐。過后村民們會在私下里討論他在罵誰,因為什么事。討論得津津有味。[2](P78)
(2)人物刻畫得生動、形象、逼真,真正做到了什么樣的人就該說什么樣的話。將寶水村的風俗習慣、人情世故和家長里短等日常瑣事,用精確、細膩、恰當和富有意味的筆墨描繪出來,將一幅活色生香的農村生活畫展現在讀者面前。
有人說,文學的魅力取決于語言的藝術魅力。我們之所以說文學語言有藝術魅力,在于文學的語言不同于其他藝術語言,它有更強的張力,給人更大的想象空間。比如繪畫可以用顏色或線條將繪畫的魅力展現出來,音樂用音符將音樂的律動表現出來,而文學靠的就是語言,而語言的張力就在于它可以幫助人們展開想象的翅膀,使人們產生更加多情而豐富的聯想。像《寶水》這樣一部故事情節不是特別跌宕起伏的作品,能吸引著讀者讀下去,甚至能達到愛不釋手,放不下的程度,完全靠的就是作者極具風趣幽默又十分接地氣的語言。
大英在寶水村應該說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我”與之初次相識,自然會問到她是如何當上村支書的?這是個既繞不開又令人很好奇的問題。我問也不是直接問她何時當上村干部的,而是問她何時在村里“當家”的,千萬別小看這“當家”兩字,既顯示了我入鄉隨俗,說的是當地百姓的家常話,又引出了大英當家一系列的話題:“千當家萬當家,提起當家亂如麻。當個啥家?當誰的家?誰的家都不好當。雖是沒幾個人,是非卻也不少,人心里也稠杠杠的。”[2](P32)為什么就輪到大英當家了呢?“十來年前,村干部還是個有人眼紅的差使,后來村里的青壯年都跑出去打工,留下的凈是老弱病殘。再后來農業稅也不用再交,村里也沒了提留款,計劃生育也不再成個事兒,村干部也就沒了一點掐人的實惠,只剩下了討人嫌,這才輪到了她。”[2](P33)像“千當家,萬當家,提起當家亂如麻”“人心里稠杠杠”“掐人的實惠”等是這段話中關鍵的字眼,正是在這些個字眼的帶動下,了了數語,將一個明事理、有情懷、潑辣、敢想敢干又樂于奉獻的大英和有著縝密心思的村民全部活畫了出來。
(3)擅長用“卓”“景”“典故”“好兒”“維”等當地人特有的口頭俚語,將農村人之間的人情世故禮尚往來“活”畫出來。這些描述不僅帶有濃郁的鄉土氣息,有鮮明的地域特色,更揭示了農村在數千年歷史中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人情冷暖和世態炎涼。
如在《寶水》第二章中有一節叫《維》,說的就是豫北地區農村的人情世故和你來我往。其實,像這種為人處世的“維”,豈止是農村特有的?在當今的人情社會里處處都有,只是表現方式不同而已。
什么是“維”呢?按作者的理解,“維”就是“對各種人脈資源的經營繕護”[2](P189)。整個寶水村和福田莊的人都很看中這個“維”,其中包括奶奶、叔叔、父親。尤其是奶奶將“維”作為她一孤兒寡母安身立命的根本:“哪怕丈夫長年不在家,哪怕自己成了拖著兩個孩子的寡婦,她也依然能讓小門小戶的地家在村里支撐住穩定的地位。”[2](P190)甚至包括父親后來能被推薦去讀大學,全部是靠奶奶的“維”。所以奶奶是極看中“維”的,“你叔小時候有回害肚疼,跑了幾家才湊出錢來。你爸小時候也沒少得村里人的力。有一回他在集上叫一個人牙子摟跑了,要不是咱村去趕會的幾十號人八面抓著去尋,哪還有他,哪還有你。你小時候好上樹耍,有一回爬到兩丈高的樹杈上,耍著耍著還睡著了,要不是你七娘看見,早就跌殘了。”[2](P193)而作為不諳世事,年少時的地青萍極討厭這種“維”,“有一次,目睹了村里人又來上門說要去象城找父親辦什么事而奶奶滿口答應時,那人剛出門,我便忍無可忍地質問了她。我說奶奶你干嗎非得這樣?為啥非要把我們家拖到深淵里,拖到陷阱里,拖到泥潭時,拖到火坑里?”[2](P189)后來,父親的意外死亡,其實也是為“維”付出的代價,這更激起了地青萍對自己的家鄉福田莊和奶奶產生了怨恨。而只有成年后,特別是在寶水村生活一段時間后,處在農村的人情世故和禮尚往來中,地青萍慢慢地才理解了奶奶和福田莊人的“維”,最終才能走向與奶奶和福田莊的和解。
其實,就《寶水》整部作品看,表面上寫的是寶水村的日常瑣碎,或者說寫的是新舊農村的變改,但內地里作者寫的就是寶水村的人情往來,就是寶水村的“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