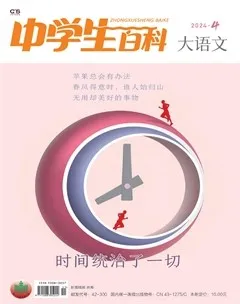春風得意時,誰人始歸山
銀瓶盛雪
在歷經盛大的科舉考試之后,落第的舉子在眾人的歡欣中獨自落寞。落第,是一種抵入生命的真實痛感。之后或進或退,都不是一種輕易的選擇。
幽微的文字光亮,在浩瀚的時空中,留下了詩人某一刻的心情寫意。失意的人咀嚼著疼痛,在寂靜的夜里,在雨聲淅瀝中,仿佛聽到,有平緩的吟詠聲隱約從遠處傳來: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星夜趕科場。
一
那一天,是孟郊一生中最快樂的一天。他寫下一首《登科后》為證 :“昔日齷齪不足夸,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那一天,他高中進士,美夢成真。他打馬長安街,令無數男子羨慕,又令無數女子愛慕。這年,他46歲了。為了半紙功名,他用半生穿越風雪千山。
孟郊幼時喪父,由母親養育成人。平日里他除了種地,就是讀書和作詩。而立之年,他出門遠行,到過很多地方,寫過很多詩。或許是迫于生計想找份體面的工作,又或許是求取功名之心覺醒,總之,孟郊踏上了科考之路。
屢戰屢敗的孟郊喜歡寫詩,數次落榜,數次寫詩,或抒發自己的失意,或感慨命運不公。在他諸多落第詩中,一首《失意歸吳因寄東臺劉復侍御》,讓我們看到了他不肯放棄的倔強。詩是這樣寫的:
自念西上身,忽隨東歸風。
長安日下影,又落江湖中。
離婁豈不明,子野豈不聰。
至寶非眼別,至音非耳通。
因緘俗外詞,仰寄高天鴻。
孟郊的故鄉在今天的浙江省德清縣,寫詩時他人在長安,所以說“東歸”。“離婁豈不明,子野豈不聰”,這里用了兩個典故。離婁是傳說中的目明者,“能視于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黃帝丟了一顆寶珠,離婁可以在百步之外看見。子野是春秋時晉國樂師師曠的字。他目盲,善彈琴,辨音能力極強,據說能聽到千里之外的聲音。離婁和子野正是神話中千里眼和順風耳的原型。
詩人用離婁和子野來指代主考官。在孟郊看來,這次落第不是考官“不明”“不聰”,而是因為自己是“至寶”“至音”,絕非凡眼能別、凡耳能通。孟郊的自我感覺不是一般的好,總之就是我不同凡俗,有鴻鵠之志。

孟郊的這種自我肯定是非常可貴的。因為他沒有放棄,我們才能感受他壓抑太久之后、成功上岸時的狂喜——“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從某種意義上講,孟郊就是一個勵志典范。
二
與孟郊同病相憐的唐代詩人盧綸,也是從小就失去了父親。他被寄養在舅舅家中,幼年時即遍讀詩書,還未成年就已聲名遠揚。他在唐玄宗天寶末年舉進士,遇亂不第;在唐代宗時期,多次參加科舉考試,屢試不第。于是,他寫了《落第后歸終南別業》:
久為名所誤,春盡始歸山。
落羽羞言命,逢人強破顏。
交疏貧病里,身老是非間。
不及東溪月,漁翁夜往還。
盧綸開篇就說自己“久為名所誤”。學而優則仕,本是天下士子的心愿,但詩人意識到自己可能為功名所耽誤,被名韁利鎖捆束了心。“春盡始歸山”,既指春天自然結束,也指曾經的春風得意消散殆盡了。歸,是回家,也是歸隱。進士考試的時間是在春天,詩人落榜之后,想回家了,照應了標題“歸終南別業”。
“落羽羞言命,逢人強破顏。”落榜了,我羞于說自己命不好,遇到人都強顏歡笑,不怨命運,也不向他人訴苦。“交疏貧病里,身老是非間。”沒有幾個朋友,自己還貧病交加,在是是非非間老去。“不及東溪月,漁翁夜往還。”月亮照在東邊的溪水之上,漁翁自由來往。這令人向往的生活,正是詩人想要的歸宿。
“漁翁”這個意象里,仿佛有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人,仙氣飄飄。漁翁所指代的,是一種超脫于世的文化境界。唐代柳宗元在《漁翁》中寫道:“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云相逐。”漁翁意味著自由自在,是詩人對科舉為官之外的另一種盼望。
總的來說,盧綸落第之后很痛苦,卻沒有抱怨命運 ;盡管貧病交加,以落第為恥,仍然能夠以微笑面對他人,對漁翁式的美好生活充滿期待。這體現了“退一步海闊天空”的人生智慧。
三
作家張曉風有一篇散文叫《不朽的失眠》,寫的是晚唐時期的張繼在某個夜晚想起自己落榜的事情,于是在萬千愁思縈繞中寫下了《楓橋夜泊》。這是一個誤讀。據考證,張繼在公元753年第一次科舉考試中就已進士及第,并無落榜經歷。
需要注意的是,古代的進士及第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資格。進士們要做官,還要經過銓選,即通過吏部審查。銓選制度在隋朝已有雛形,到了中唐時期進一步完善,是唐朝選拔人才的重要方式。如果說科舉考試考查的是一個人的才學,那么銓選則側重于考查一個人的口才、反應能力等。
在中舉之后,有人很快就得到了任命,有人要等上好幾年,有人甚至一直在等待,像被朝廷遺忘了一樣。張繼在長安等了幾年,也沒有等到被任命的消息。他沒有繼續等下去,而是棄筆從戎,投身軍旅。軍旅生涯加深了張繼憂國憂民的情懷。在安史之亂爆發之后,他流離失所,漂泊在江南一帶,其間寫下的詩作都比較哀愁,包括《楓橋夜泊》。
《楓橋夜泊》是張繼在家國動蕩之時、滿腹憂愁之際,途經蘇州寒山寺,偶然寫下的一首羈旅詩。“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僅僅28個字,寫盡了羈旅之思、家國之愁與漂泊之苦。這首詩,有人將之譽為“唐詩第一”,在海外也有很大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