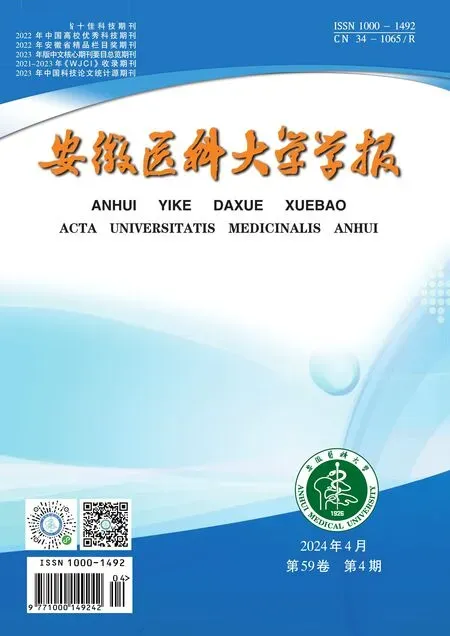從缺血性卒中角度再看視網膜中央動脈阻塞
周 杰,郭珍妮,姜 宇,孫藝寧, 岳飛學 ,宋康佳 ,張文彬綜述 王守春審校
視網膜中央動脈阻塞(central retinal artery occlusion,CRAO)是一種眼科急癥,臨床預后差。以往傳統的治療方案被認為可能對患者有害。視網膜中央動脈(central retinal artery, CRA)是眼動脈發出的第一分支,CRAO更被認為是一種輕型缺血性卒中,具有多種心血管疾病危險因素,且具有較高的心血管疾病及死亡風險。隨著國內卒中中心建設的逐漸完善,早期溶栓治療能夠極大降低缺血性卒中患者致殘率、致死率,已作為臨床診療指南被廣泛推廣。突發CRAO能否盡早治療尚存在患者癥狀不能被及時識別、不能有效轉運至急診、未能與現今卒中中心硬件發展有效銜接、未能實現心血管疾病危險因素早期緊急識別與管控等問題需要逐步攻克,望搭載于國內日趨完善的卒中救治綠色通道,進行眼科、神經眼科、卒中中心、神經內科等多學科協同合作,使得從根本上改善CRAO患者預后。
1 CRAO定義和流行病學
CRAO是指經視網膜中央動脈至視網膜內層的血流受阻導致的急性視網膜梗死,是一種眼科急癥,往往給患者帶來災難性視覺預后。它在視覺上相當于缺血性腦卒中[1-2]。只有17.7%~20.0%的CRAO患者在未干預的自然病程中恢復了功能性視力[2-3]。韓國國家健康保險系統2002—2015年數據顯示,標準化發病率2.00/100 000/年(95%CI,1.97~2.04/100 000/年)[4],日本為2.53/100 000/年[5]。男性高于女性,且發病率隨著年齡增長而增長,80~84歲人群,發病率上升至9.85/100 000/年[4],在人口老齡化更為嚴重的日本上升至16.05/100 000/年[5]。
2 CRA解剖和CRAO機制
CRA是眼動脈發出的第一分支,自眼動脈發出后,沿視神經下方前行,后穿入視神經的硬腦膜和蛛網膜,此處CRA管腔最狹窄,于下腔中前行后穿過軟腦膜,達到視神經中軸,穿過篩板后于視盤中部分為細小分支,供應內核層以內的五層視網膜、視盤最表面的神經纖維層及篩板后視神經;視網膜外五層由睫狀動脈分支的毛細血管提供,睫狀視網膜動脈也是眼動脈的一個分支[5]。49.5%患者存在睫狀視網膜動脈,其大小、數量和分布各異,如參與黃斑供血,CRAO時視力可能保留[6]。CRAO的發病與缺血性腦卒中類似,由不同的潛在條件導致血流的急性中斷引起的。CRAO最常見的原因是血栓栓塞,主要來源于同側頸動脈動脈粥樣硬化斑塊,而不是同側頸動脈的嚴重狹窄或房顫等心臟疾病[7]。最常見的位置在CRA穿出視神經硬膜鞘的部位。急性CRAO與急性缺血性卒中(acute ischemic stroke, AIS)相似,其預后均具有時間依賴性。視網膜缺血的耐受時間尚未可知,對于老年、動脈粥樣硬化性、高血壓的恒河猴CRAO動物模型發現,在CRA閉塞97 min后未檢測到視網膜缺血損傷,持續約240 min后導致全部或幾乎全部視神經萎縮和神經纖維損傷[8]。
3 CRAO診斷及分類
3.1 CRAO診斷CRAO通常表現為突然、無痛的單眼視力下降,74.9%的患者視力下降至數指或更差[3]。查體可有相對性瞳孔傳入障礙。發病早期最常見的眼底改變為黃斑區櫻桃紅斑,其次為視網膜后極部混濁水腫、視盤蒼白、視網膜動脈變細和視盤水腫,隨著時間的推移,可能會出現視盤萎縮、黃斑視網膜色素上皮變化等表現[3]。CRAO診斷依賴于癥狀、典型的眼底表現外,常依賴于熒光素血管造影術(fundus fluorescein angiography, FFA )、光學相干斷層掃描(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OCT)等輔助檢查進行鑒別診斷[9]。
FFA可發現CRA的充盈延遲、動脈管徑減小以及動脈內節段狀的“貨車車廂”樣血柱等特征、評估中央和周邊視網膜灌注,識別睫狀視網膜動脈存在與否,有助于CRAO細化分類[3]。同樣可早期發現CRAO后的視網膜新生血管[10]。另外FFA存在檢查耗時長、并發癥等缺點,很難在急診情況下進行。OCT可顯示由于視網膜水腫和視神經腫脹,急性期視網膜內層厚度增加。CRAO早期,眼底可能出現相對正常,OCT可在快速地檢測視網膜水腫及顯著的中界膜征(OCT上外叢狀層內層出現高反射線),有利于醒后發病或發病時間不明的CRAO早期識別與診斷[9]。對于超過50歲以上人群,行C反應蛋白及血沉以排除動脈炎性CRAO是必要的。
3.2 CRAO分類Hayreh et al[3]研究表明CRAO并不是單一的疾病,而是由4種不同臨床實體構成,初始視力及預后均有明顯差異[11]。① 一過性-非動脈炎性CRAO(non-arteritic CRAO, NA-CRAO):明顯的突然視力喪失(而非黑蒙)持續時間可能從幾分鐘到數小時不等,具有CRAO的經典眼底表現及FFA上正常的視網膜循環;② 持續性NA-CRAO:是最常見的CRAO類型,占比66.9%,診斷基于CRAO的經典眼底表現,FFA顯示視網膜動脈灌注的延遲或缺失,且同時排除動脈炎性CRAO;③ 保留睫狀視網膜動脈的持續性NA-CRAO:大約占比20%,睫狀視網膜動脈存在與否和分布情況會對CRAO視覺結果和視網膜循環產生顯著影響;④ 動脈炎性CRAO:占比<5%,最常見的原因是巨細胞動脈炎,急性的視力喪失源于視網膜缺血及前部視神經缺血,這類患者除了經典眼底表現以外,還同時存在FFA上睫狀視網膜動脈的閉塞,治療方案與NA-CRAO不同。
Schmidt et al[12]依據CRAO患者視力受損嚴重程度及輔助檢查等將其分為3個階段:① 1期-不完全CRAO:存在視力下降和殘余視野,但沒有完全的視力喪失,眼底檢查發現輕度視網膜水腫,黃斑區略呈櫻桃紅斑,數小時內視網膜體征無增加或自發恢復,FFA 顯示動脈血流延遲但未完全中斷;② 2期-次全CRAO:視力高度降低,視野中遺留一最大測試標志的小島,眼底檢查顯示中央視網膜明顯水腫伴黃斑區櫻桃紅斑,視網膜動脈狹窄,可見動脈內節段狀的“貨車車廂”樣血柱。FFA顯示動脈血流明顯延遲,尤其是在黃斑周圍小動脈;③ 3期-完全CRAO:視力可完全喪失至無光感,眼底檢查視網膜偶有從中心(黃斑區)向視網膜鼻側延伸的大面積水腫、黃斑周圍小動脈內無血流、無櫻桃紅斑。不完全及次全CRAO預后相對較好。
4 CRAO早期溶栓治療
傳統的CRAO治療的原則是通過血管擴張、清除栓塞和降低眼壓等方式來改善視網膜血流,包括球后注射阿托品或山莨菪堿、硝酸甘油類或己酮可可堿藥物應用、高壓氧或Carbogen氣體吸入、前房穿刺、Nd:YAG激光治療或全視網膜光凝治療等,然而薈萃分析顯示,與自然史相比,傳統治療方式惡化了CRAO后的視力結果(17.7%vs7.4%)[2];發病4.5 h內的阿替普酶(alteplase, rt-PA)或發病6 h以內的尿激酶靜脈溶栓治療已經成為AIS超早期的標準治療方案而被指南推薦[13]。CRAO作為視網膜卒中,是輕型卒中(美國國立衛生院卒中量表≤5分),回顧性研究表明溶栓治療可改善CRAO患者的視力[2,14-19],CRAO溶栓治療包括靜脈溶栓(intravenous thrombosis, IVT)和動脈溶栓(intra-arterial thrombolysis, IAT),當在視力喪失后不久給予溶栓,可能會在視網膜細胞死亡前誘導閉塞動脈的快速再通和缺血視網膜的再灌注。理想的治療窗口尚不清楚,但有研究者認為越早越好[2,17-18]。
4.1 靜脈溶栓首個針對CRAO發病24 h內使用rt-PA的隨機對照試驗[20]結果于2011年公布,結果顯示rt-PA組與安慰劑組患者6個月后視力改善無顯著差異,盡管如此,2例發病6 h內應用rt-PA患者視力明顯改善,可能提示在發病早期IVT可能獲益。2015年Schrag et al[2]薈萃分析將干預后視力恢復統一定義為初始視力至少為1.0 logMAR(Snellen等效值為20/200)或更差,并提高到0.7 logMAR或更低(Snellen等效值為20/100或更好),與自然史(17.7%)相比,在癥狀出現后4.5 h內IVT,可使50%患者視力改善,這一結果在該團隊隨后病例對照研究[16]中得到驗證;Huang et al[17]薈萃分析得出相似結果。IVT后出血轉化往往是研究者主要擔心的問題。Schrag et al[2]綜述IVT后出血事件發生率為3.5%,均為應用鏈激酶患者,可能源于rt-PA能夠更好地與纖維蛋白特異性結合發揮作用。薈萃分析[17]顯示,發病4.5 h內CRAO進行rt-PA靜脈溶栓后癥狀性顱內出血(symptomatic intracranial hemorrhage,sICH)發生率與輕型卒中相似,為1.3%,低于所有AIS患者的2.5%~5.0%[21]。
替萘普酶(tenecteplase, TNK)是rt-PA的一種基因修飾變體,具有更高的纖維蛋白特異性和更長的半衰期,能夠單次靜推給藥,給藥后24 h,TNK消耗更少的纖溶酶原和纖維蛋白原,TNK與更低的出血事件發生率相關[22]。基于中國人群的多中心、隨機對照、非劣效性研究[23]顯示,應用低劑量TNK(0.25 mg/kg)良好預后不劣于rt-PA(62.7%vs59.2%),且sICH發生率2.0%與rt-PA相同,肯定了TNK在中國人群AIS患者中的臨床適用性。
4.2 動脈溶栓為避免IVT相關全身出血事件及可能延長治療的時間窗,20世紀90年代開始使用超選擇局部眼動脈或頸動脈IAT。霍普金斯醫院IAT治療發病時間15 h內的CRAO經驗顯示,與傳統治療相比,IAT組患者視力改善(Snellen視力表≥3行)可能性是對照組的13倍(P=0.03)[24]。2010年歐洲眼局部溶栓評估小組(The European Assessment Group for Lysis in the Eye study, EAGLE )開展rt-PA-IAT治療發病20 h內CRAO的隨機對照試驗[19]結果,與傳統治療相比,IAT組干預后1個月視力有所改善,但兩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69),該試驗因出血性事件的發生與過高不良反應(34.3%vs2.1%)被終止;值得推敲的是,入組患者癥狀出現-治療時間平均間隔12 h,IAT組患者癥狀-治療時間平均晚于對照組2 h,而且在主要研究者中心IAT組呈現更好的視力預后趨勢,可能提示在具有更多經驗的介入團隊中,盡早進行IAT可能有更好的視覺預后。Huang et al[18]薈萃分析顯示,與對照組相比,IAT患者視力改善率高于非IAT患者[ 56%vs32%,OR3.55, 95%CI(1.74,7.24) ],6 h內患者尤著。同時有學者發現發病1周內不完全及24 h內次全CRAO能從IAT中獲益[12]。這也說明不完全CRAO患者及次全CRAO可能具有更好的側支循環,可能具有更長的治療時間窗。
部分學者認為對于溶栓所帶來的臨床獲益存在部分夸大。首先,恒河猴動物試驗研究[6,8]表明,當CRA持續缺血時間超過240 min后將出現不可逆的損傷,超過該時間進行的溶栓都沒有實驗依據。而該動脈模型選擇機械性夾閉CRA穿入視神經硬腦膜之前的部分,并不符合臨床實際,且CRAO預后不單單取決于閉塞持續時間,同時也與閉塞位置、閉塞程度、側支循環代償等相關[12]。其次,一過性NA-CRAO及持續性NA-CRAO合并睫狀視網膜動脈患者病程中的自發緩解,被誤認為溶栓所帶來的臨床獲益[3,6]。這兩類患者中分別有18%及33%患者遺留數指或更差的視力。存在自發緩解的患者是否需要溶栓治療?借鑒歐洲卒中協會對于快速緩解型AIS靜脈溶栓的推薦[25]:治療決策基于當時的臨床情況,為了觀察癥狀是否改善而延遲靜脈rt-PA治療是不合理的。第三,僅僅用視力改善作為評價視網膜功能改善指標往往是不足的,約10%患者可能學會了偏心固定[3],從而夸大溶栓患者良好預后率,然而視野檢測并未在以往研究中作為衡量預后的主要終點事件,期待后續更多研究結果公布。
對于急性期CRAO來說,盡管缺少大樣本、隨機對照研究的循證醫學證據,但在真實世界,51.5%的醫師,以神經科或神經眼科醫師為主,會為適合的患者進行溶栓治療[26]。目前針對發病4.5 h內的急性CRAO患者的多中心、隨機、對照臨床試驗正在進行,1項為低劑量TNK(NCT04526951),2項為rt-PA(NCT03197194,NCT04965038),期待后續結果發表。
5 CRAO與卒中
NA-CRAO患者與卒中患者具有相似的心血管疾病危險因素,如高血壓、頸動脈疾病、心臟疾病、腎臟疾病、糖尿病、高脂血癥、高尿酸血癥和慢性吸煙等[7,27-28],62.8%患者合并至少一項心血管疾病危險因素[27]。Lavin et al[29]研究表明住院治療、神經科與眼科醫師的聯合診治能夠更徹底、更標準化篩查、評估心血管疾病危險因素,92%的CRAO患者因住院評估而發生了藥物治療的變化,針對CRAO心血管疾病危險因素緊急、全面篩查與評估是非常有必要的。
NA-CRAO患者伴發心血管疾病率較高[7],CRAO患者的病死率是正常人的9.95倍,死亡原因首位是急性心肌梗死與急性腦梗死[28];37.3%CRAO急性期合并頭部核磁共振彌散成像陽性的急性腦梗死[29],以病后2周常見[30]。患者往往無明顯臨床癥狀而被忽視[7,29]。Yoo et al[31]對急性視網膜動脈閉塞性疾病患者平均隨訪6.4年顯示,7.4%患者發生遠期卒中或心肌梗死等心血管事件,其中2/3 為缺血性卒中。CRAO患者與高危短暫性腦缺血發作(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 TIA)(ABCD2評分6~7分)具有相似的1年卒中發生率[29]。同側頸動脈≥70%狹窄的早期干預、及時規范地抗血小板聚集藥物及他汀類藥物、心源性因素系統篩查與規范抗凝被認為有效減低卒中再發風險。
回顧性研究[31]顯示他汀應用能夠顯著減低CRAO患者遠期缺血性卒中;服用時間越長,心血管疾病風險越低。然而頸動脈斑塊破裂導致的栓塞雖被認為CRAO栓塞最常見的病因[7],真實世界中,僅有40%患者在CRAO后服用他汀[31]。非瓣膜病房顫卒中危險因素CHA2DS2-VASc評分≥1分,卻只有55%患者采用抗凝治療[32]。綜上所述,CRAO后及早進行心血管疾病危險因素篩查、評估及啟動卒中二級預防治療措施是十分必要的[29,31]。
6 多學科合作
CRAO早期治療尚缺少循證醫學證據。真實世界中,患者癥狀不能被及時識別、不能有效轉運至急診、未能與現今卒中中心硬件發展有效銜接、未能實現心血管疾病危險因素早期緊急識別與管控等問題依然存在。預期得到更多的循證醫學證據還需要幾年時間。首先,患者對疾病缺乏認識,發病后不能及時發現及就診。Uhr et al[33]對內科門診就診人群的調查顯示,僅有4.6%患者知道CRAO,僅有0.5%患者了解CRAO病理生理特征。加強宣教在以往的急性心肌梗死及急性腦梗死的溶栓治療上發揮了很大作用,同樣,提高公眾對CRAO疾病認識,提高時間窗內的急診就診率是十分有必要的。其次,院內未建立有效識別、篩選、評估及多學科合作治療模式。2012—2018年美國急診就診數據[34]顯示,僅45%視網膜動脈閉塞性疾病患者急診就診,即便是在三甲級別教學醫院,發病后4.5 h內CRAO患者只有1.65%接受溶栓治療[35]。建立院前與院內的有效銜接,簡化院內跨學科合作流程,可有效縮短入院到治療時間,在此前中國卒中中心建設模式中已經得到驗證,中國卒中中心報告[36]顯示自2015年國內卒中中心建設逐步完善,設置7×24 h卒中救治綠色通道,實現AIS患者入院至給藥的時間控制在黃金1 h,中位數46 min,AIS患者靜脈溶栓及機械取栓數量逐年增長。在這樣硬件完善的基礎上,眼科專家在診斷CRAO后第一時間轉運至急診,進入卒中救治綠色通道,由神經科醫師進行IVT及IAT適應證的評估,盡早開展全面的心血管疾病危險因素篩查,識別高風險患者,盡早采取他汀、抗血小板聚集、抗凝藥物治療等有效二級預防措施, 從而減少遠期卒中等心血管事件的發生及死亡,這一簡化學科合作模式可能更適合中國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