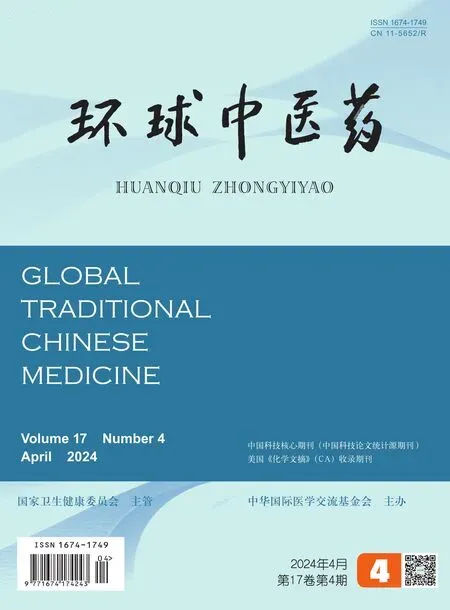仲景欲癥思辨
范航 張迪 張富榮 陳萌
作為疾病狀態下生命活動的外在表現,癥狀是確立診斷、指導治療的依據。中醫臨證高度重視癥狀發生根源與演變過程,醫圣張仲景以傷寒病、雜病和婦人病診治為引,通過臨床觀察,綜合分析各類癥狀,明晰病位、病性,把握疾病轉歸預后,構建了辨病為綱,辨證為目的經典診療體系。
《傷寒論》《金匱要略》醫理與文理并重,真實客觀、全面細致地描述各類疾病臨床表現,尤強調特殊癥狀的重要性,如“陰性癥狀”[1]“或然癥”[2]“暝眩反應”[3]等。以“欲”為眼目的特殊癥狀在原著中出現頻率高,不僅體現了一定臨證價值,而且蘊含了中醫的獨特思維與認知方式。現對張仲景原著欲癥進行如下探討。
1 欲癥的分類、理論特色
欲字的本義,總體上可劃分為兩大類,一指希望實現、想要達到某種目標的心理活動、精神需求,如“食欲”“情欲”“愛欲”,《說文解字》指出:“欲,貪欲也。”《荀子·正名》亦言:“欲者,情之應也。”二指將要發生某事的趨勢,如“搖搖欲墜”“風雨欲來山滿樓”。
基于含義差別,對張仲景著作中的欲癥進行歸納、分析,可將其分為“欲求癥”與“欲作癥”,前者有“但欲臥”“欲飲水”“欲得衣”等表述,帶有急迫解除身體不適或試圖達到某種渴求的意圖,是患者強烈主觀意愿的表達;后者有“欲作固瘕”“欲作奔豚”“欲作剛痙”等表述,預示疾病演變的趨勢。
1.1 欲求癥:形神一體觀
形神一體思想肇源于《黃帝內經》,它強調形、神辨證統一的關系,即人體結構與功能、人體生理屬性與精神意識屬性的和諧統一[4],兩者相互依存、彼此影響,滲透于中醫對人體生理、病理、治療、預防各方面認識[5],尤在養生保健、心身調治方面發揮了廣泛性作用。形神一體的生命理念既重視“守神全形”,又不輕視“保形全神”。正如《靈樞·本神》所言:“順四時而適寒暑,和喜怒而安居處,節陰陽而調剛柔,如是則僻邪不至,長生久視。”
疾病狀態下,人體處于陰陽不和、臟腑失調的異常狀態,臨床表現紛繁復雜,倘若癥狀難以得到有效改善,將引發形神同病。作為機體自發產生的不適表現,“欲求癥”是生命自我調節,實現內部穩定的體現。《傷寒論》第300條:“少陰病,脈微細沉,但欲臥,汗出不煩,自欲吐,五六日自利。”病至少陰,患者脈象微細沉,陽氣虛怯,氣血不得外張,心神難以振奮。不經吐下而出現自發性吐利,導致水谷亡失,精微耗散,加劇氣血虧虛,精神疲憊,氣血困頓之際,病家別無所求,以“但欲臥”求得精神安寧,減少氣血不必要消耗,發揮睡眠對人體臟腑功能調整與氣血運行狀態改善的作用。從現代醫學角度上看,少陰病與休克相似[6-7],是外感病衰竭期,全身處于急性虛衰狀態,機體血液循環障礙,微循環灌注不足,由于缺血、缺氧,引發細胞損害、代謝紊亂,易造成心、腦等重要器官受損。處于休克早期,機體可通過代償機制,自主調節和矯正病理變化,以維持重要器官的正常工作。
形神同病時,“欲求癥”具有暗示病情程度的作用。以“欲飲水”為例,它常與“渴”組成“渴欲飲水”的癥狀表述,這一概念首見于《黃帝內經》,屬同義詞連用[8],在張仲景著作中多處可見。“渴”本為水竭之意,《說文解字·水部》:“渴,水盡也”,段玉裁注曰“渴、竭古今字,古水竭字多用渴”[9]。張仲景原著中“渴”代表津液亡失,與“消”組合形成“消渴”病名,本意應該是指津液的嚴重匱乏[10],而“口燥”“口干舌燥”“咽燥”等癥狀應則明顯輕于“渴欲飲水”,即當今所理解之渴。《傷寒論》第71條:“太陽病,發汗后,胃中干,煩躁不得眠,欲得飲水者,少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太陽病誤用汗法后,津液嚴重耗傷,造成人體嚴重脫水。水津之源受損,胃津干涸,陰傷陽亢,難以和合交濟,引發煩躁、不寐,欲得飲水為外求水源,內補津液之虧損,而使陰陽暫安,以求自解。“煩躁”“不得眠”一方面表明津液損失,波及血脈,影響心神,另一方面,通過“渴欲飲水”,促進人體飲水,少與飲之以和胃安神。現代醫學機制表明,脫水引發的各種變化與下丘腦的神經—內分泌調節活動密切相關,汗出過多導致體液代謝失常,既可引發下丘腦滲透壓感受器興奮,促進垂體釋放抗利尿激素,調控水鹽平衡,維持內穩態,又可將興奮傳至大腦皮層,產生渴覺,引發飲水活動。若飲不解渴,在多飲暖水基礎上,予以五苓散通陽化氣,布散水津,得汗出而愈。
不難看出,“欲求癥”可視為機體反饋調控機制的中醫表達形式。由于它既可以提供病家主觀不適的基礎信息,即神的層次;又是醫者直接可見的臨床表現,即形的層次。因此,可將欲癥視為癥狀鑒別診斷的一種方法。以“心悸”一癥為例,小建中湯證、炙甘草湯證、小柴胡湯或然證、小半夏加茯苓湯證均有涉及,而與“欲求癥”相搭配者,只見桂枝甘草湯證“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一處。“欲得按”一癥兼具形神特點,不僅表明病家為心悸所困苦之甚,以致雙手護心,方可安頓,而且不安之狀儼然外顯,易為醫者所察,病情、病勢望之初曉,簡化了辨證的復雜過程,利于把握基本病性變化,誠如柯琴[11]所言:“叉手自冒,則外有護衛,得按則內有所憑,則望之而知其虛。”現代社會,心血管疾病患者常伴發精神、心理活動異常,亦呈現出形神同病的特點,經方辨治雙心疾病注重從整體出發,強調“一元論”辨證思維,實現“雙心”同調[12]。
1.2 欲作癥:既病防變觀
《金匱要略》開篇明確提出“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補之”的治未病治療策略,并踐行于臨證各處,貫穿未病早防、既病防傳、既傳防盛、到病后防復的疾病全過程[13-14]。
張仲景注重癥狀發生的前后秩序,展現病情的動態過程,如汗出前可見發熱、煩熱、身振,下利可見腹痛、腸鳴,衄血可見發煩、眩暈。從疾病演變的因果聯系出發,通過當下異常臨床表現,對后續病證變化進行分析、判斷,實現早期識別、寓防于治的目標。
“欲作癥”反映了疾病發展變化的一種趨勢[15],它緊密圍繞“既病防變”這一臨證核心思想,對未發而將發之病進行臨床預判,并在當下治療過程運用藥物截斷病勢,未雨綢繆,防患未病。做出“欲作癥”的臨床預判,一方面要求醫家具備深厚的理論基礎、豐富的臨床經驗,另一方面要求觀察細致,充分收集癥狀信息,把握關鍵癥狀在疾病發展的重要作用。欲作奔豚”與“欲作谷疸”是具有代表性的病勢演變。
《傷寒論》第64條:“發汗后,臍下悸,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主之”。發汗失當,損傷心陽,心火難制腎水,津液停遏,水飲泛作,動蕩不安,以致病家出現臍下異常悸動感。倘若臍下水飲不得消除,有演變為奔豚病的可能,而奔豚病發作迅速,癥狀顯著而劇烈,氣沖少腹上沖心,病家常有難以承受的發作欲死感。此時,水勢尚在下焦,欲作奔豚,尚未發也,當先其時而治之[11]。故予苓桂甘棗湯,溫陽健脾,利水止悸,防止“臍下悸”之微轉變為“氣從少腹上沖胸”奔豚之著。
《傷寒論》第195條:“陽明病,脈遲,食難用飽,飽則微煩頭眩,必小便難,此欲作谷疸。”中焦虛弱,納運失職,氣血阻滯,脈行遲緩。水谷難消,聚生濕濁,壅塞三焦,上犯清陽,見有煩熱、頭眩之象,下注膀胱,膀胱氣化失職,小便不利。濕邪蘊郁,不得外泄內入血脈,發為黃疸。從“食難用飽”“頭眩”到“小便難”,再至谷疸發生,展示了病位由氣分至水分,入血分的變化過程。“欲作”點明從氣分階段的臟腑功能失常出發,進行早期識別,積極預防的重要意義。臨床實踐表明,黃疸患者早期多表現為食欲減退、惡心、嘔吐、疲勞乏力、發熱畏寒等非特異性癥狀,伴隨相關生化指標異常,而針對病因的基礎治療是貫穿防治始終的主線。
2 欲癥的形成動力與證治規律
病癥為標,氣化為本。人體之氣的異常變化是疾病從潛在形成到癥狀的發生、變化的內在根源。
《素問·六微旨大論篇》指出:“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故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升降出入是氣機運動的基本形式,但兩者立足點不同。
“出”“入”為整體視角下的運動描述,實為“陽化氣,陰成形”在空間上的具體狀態[16],它依賴人體各處氣血門戶的開闔為前提,由內在自我調整、穩定的功能系統——神機[17]所發動,如熱盛,腠理開則汗出,增加散熱;寒盛,腠理閉則無汗,減少散熱。神機開闔有度,則出入有序,開闔失常,則出入無序,引發疾病,《素問·生氣通天論篇》有言:“開闔不得,寒氣從之,乃生大僂”。
“升”“降”則是局部視角下的運動過程,聯系個體局部之間的關系,如肝升肺降,脾升胃降[16],心火降腎水升。它通過參與外部環境之間物質、能量、信息交換并適應外部環境的功能系統——氣立所發揮作用[17]。氣長則顯盛于外,氣消則隱衰于外。氣立之安危牽涉升降能否相接、相和,升降進一步招致盛衰之變(生長化收藏)[18],呈現出氣的數量變化。
氣的運動變化與數量變化聯系密切,互為因果,“開則氣消、消后氣闔、闔則氣長、長后氣開”的變化連貫形成了“闔—長—開—消”的運動節律,往復交替的循環過程推動著生命活動的正常進行。疾病狀態下,亦是如此。正如《景岳全書》所言:“病隨氣動,必察其機,治之得其要,是無失氣宜也”[19],癥狀發生的根源動力在于人體之“氣”在運動、數量變化,而欲癥則是“闔—長—開—消”運行失常前提下所引發的一類代表性癥狀。
2.1 開則氣消,因勢逐邪
“欲自利”“欲得小便”等常見欲癥提示疾病存在向愈的轉機,治療理當順勢而為。《金匱要略·痰飲病脈證并治第十二》:“病者脈伏,其人欲自利,利反快,雖利,心下續堅滿,此為留飲欲去故也,甘遂半夏湯主之。” 水飲蓄積,深伏久居,氣血郁遏,脈象沉伏難及。未經吐下之法,正氣蓄積,起而爭抗,占據主導,藉胃腸逐水飲外出,人體之氣的門戶處于外開狀態,表現為自發性下利,而飲停水滯,心下硬滿不解,遵循因勢利導的治療思路,以甘遂半夏湯攻堅逐飲,乘勝祛邪,推動氣開走向氣消階段。
2.2 消后當闔,逆勢內收
氣的數量變化與運動過程彼此聯系,數量基礎的不足是引發開闔運動失常的重要原因。《傷寒論》第397條指出:“傷寒解后,虛羸少氣,氣逆欲吐,竹葉石膏湯主之。”病家傷寒初瘥,邪祛正損,氣血未復,臟腑虛弱,機體尚處于氣闔階段,理當補益人體精氣,助力氣血增長,而胃氣反因津傷陰損,失于闔降,逆迫于上,呈現出“欲吐”的外張之勢。仲景以安氣復形為要旨,運用竹葉石膏湯清熱生津,益氣養陰,竹葉與半夏相伍,清熱降逆,通順胃氣,助氣闔降,合以麥冬、人參、粳米、甘草等,扶助脾胃,益氣養津,裨助中焦化源,復生氣血,即暗合闔后氣長之理,從而實現消長相適、開闔有度的運動過程。
2.3 長而不開,因郁生欲
人體之氣處于長盛狀態時,生命活動亢進、劇烈。倘若氣機郁遏,臨床表現不得改善,機體自發產生欲癥,促邪外出。如黃連湯證之“腹中痛,欲嘔吐”。作為胃痞病的前驅癥狀,黃連湯證由于腸寒阻滯于下,胃氣不得通降,腹痛不解,郁熱上迫,以求外解,產生自發性嘔吐。《傷寒論》第123條:“太陽病,過經十余日,心下嗢嗢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溏,其腹微滿,郁郁微煩,先時自極吐下者,可與承氣湯。”病初在太陽,因過度使用吐下之法,邪氣內陷,病至數日,長而不消,氣機閉郁,阻遏生熱,擾亂心胸,引發心中繚亂煩悶,邪無他路可出,欲吐以得自解。
2.4 開闔失職,欲而不能
人體門戶的開闔與臟腑強弱密切相關。開闔一方失常,病情尚屬輕淺,臟腑功能未衰。開闔雙方皆失,病情趨于嚴重,提示臟腑功能虛弱,診治不易。以百合病為例,《金匱要略·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脈證治第三》指出:“百合病者,百脈一宗,悉致其病,意欲食復不能食,常默默,欲臥不能臥,欲行不能行。”外感熱病,失于診治,以致諸藥難治之地。經汗吐下等法后,心肺津虧營損,虛熱燔灼,氣傷陰耗,虛火擾動,氣機欲收不能,其人“欲臥”“不能臥”,而心神馳張于外、氣羸難支,氣機欲開不能,其人“欲行”“不能行”。欲開不得,欲闔亦不得,疲憊困頓之際,徒勞氣血。病情遷延,有達一月、四十日、六十日者,諸治失策,張仲景唯言隨證治之,以應變機。
《金匱要略·腹滿寒疝宿食病脈證治第十》:“中寒,其人下利,以里虛也,欲嚏不能,此人肚中寒。”虛寒病家,陽氣頹靡而水谷不化,門戶欲闔不能,精微下迫,無端亡失。雖有欲嚏之勢,提示陽氣來復,陰寒尚存驅散之冀,但沉寒痼結于里,陰氣閉郁日久,陽氣伸展不能,竅閉氣滯,門戶欲開不能,陳氏[20]所注:“欲嚏不能者,正為邪迫,陽欲動而中止,邪欲去而仍留,陰寒凝滯于里”亦為同理。
3 欲癥的臨證指導作用
3.1 體現病機變化
《素問·至真要大論篇》:“謹守病機,各司其屬,有者求之,無者求之,盛者責之,虛者責之。”欲癥的有無、性質的差異與病機變化密切相關。
《傷寒論·霍亂病脈證并治第十三》:“霍亂,頭痛發熱,身疼痛,熱多欲飲水,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湯主之。”霍亂之病,表里失常,正邪紛爭,上吐下瀉,揮霍繚亂之際,虛實的病機轉變迅速。張仲景言“熱多欲飲水”以示正氣抗邪有力,邪犯未深,表實有甚于里虛之勢,予五苓散通陽化氣,解表和里兼升清降濁,安和脾胃;而“寒多不用水”則與之相反,提示寒濕內盛,表證尚淺,里虛有甚于表實之勢,以理中丸溫陽益氣,健脾燥濕。作為反映病機的關鍵,“熱多欲飲水”一癥簡明深刻,直擊疾病鑒別要點。類似闡釋,亦見于白頭翁湯證,《傷寒論·辨厥陰病脈證并治第十二》:“下利,欲飲水者,以有熱故也,白頭翁湯主之。”白頭翁湯證之下利,乃濕熱下迫所致,氣滯壅塞,穢濁郁滯,血敗肉腐,隨便而出,“欲飲水”之詞言簡意賅,指明邪實熱盛之病機。
3.2 反映病勢轉歸
張仲景著作強調臨證的常變思維[21-22]、動態思維[23-24],通過六經傳變展示傷寒病時空演變過程、突出“隨證治之”的思想,反映中醫診療的靈活、多維、恒動的特點。
欲癥為未發而將發之癥,是疾病發生轉變的前驅表現。太陽病篇之始即以“欲吐”表明疾病的傳變,《傷寒論·太陽病脈證并治上第五》有言:“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為不傳;頗欲吐,躁煩脈數急者,乃為傳。”寒邪侵襲,先犯肌腠,太陽迎之。太陽病是否傳變與感邪輕重、體質強弱虛實密切相關,集中反映于脈癥變化中。邪氣不傳則脈癥不變,邪氣內傳,波及胃腸,引發氣機升降失常,病家有欲吐之勢,脈象數急不安,提示病位已然深入,疾病出現轉變。
疾病轉歸、預后亦見于欲癥相關的臨床表現中,《傷寒論》第339條:“傷寒熱少厥微,指頭寒,嘿嘿不欲食,煩躁數日,小便利,色白者,此熱除也,欲得食,其病為愈”。傷寒病,邪正兩微,交鋒勢輕,陽郁輕淺,熱擾心神,胃氣郁滯,數日后熱勢得以退卻,由“不欲食”轉變為“欲得食”,標示病情轉好,陰陽自平,胃氣復和,氣血漸生。
3.3 切入疑難病證辨析
臨床實踐中,疑難危重疾病的臨床表現矛盾突出,患者癥狀、舌象、脈象等各方面均存在寒熱真假,疑似難辨的狀態時,探查此時患者真實的欲望往往是鑒別寒熱真假證候的最確鑿依據[25]。
《傷寒論》對于寒熱真假辨證提出了精準獨到的察機思路,即把患者之苦欲作為判斷寒熱真實本質的重要依據[26]。第11條:“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衣者,熱在皮膚,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也。”條文中“身大熱”與“欲得衣”,“身大寒”與“不欲近衣”兩組癥狀看似矛盾,但彼此由同一病機主導,前者指向陰氣內盛,格陽于外的病機,后者指向陽氣過盛,格陰于外的病機,臨床表現差異的關鍵在于癥狀產生的場所,在表之“發熱”“惡寒”主觀感受不僅與肌表衛外職能正常與否有關,而且受聯系臟腑、體表的經絡氣血運行狀態與外部環境多重影響,并非營衛盛衰、臟腑虛實的直接證據;在里之“欲得衣”“不欲近衣”作為身心異常的主觀感受與行為異常,不受外部因素影響,是臟腑氣血盛衰變化失常的直接反映,為寒熱矛盾,為真假錯亂的疾病本質提供了真實參考。
因此,危重疾病出現真假矛盾的臨床表現時,假象多在遠離基本疾病場所的四肢百骸、肌膚腠理等處,而臟腑虛實、氣血盛衰、津液盈虧的內在表現,卻真實反映了疾病本質[27]。張仲景指出“熱在皮膚,寒在骨髓”與“熱在骨髓”“寒在皮膚”正是點明真假癥狀的病位差異所在。
《寓意草》記載一案[28]:“徐國楨傷寒六七日,身熱目赤,索水到前,置而不飲,異常大躁,將門牖大啟,身臥地上,展轉不快,更求入井。”醫家只察身熱、煩躁、目赤之象,不審病家所欲所苦,僅憑某類表現定為陽熱之證,予承氣法釜底抽薪,通腑泄熱,而施治無效。喻嘉言來診,切其脈象,輕取洪大,重按無力,不僅與前醫所斷相悖,而且“索水到前,復置不飲”的表現與煩燥、身熱性質迥異,兩者必有一真一假,而治療結局已暗示疾病本質,世醫不明,故失其機,喻嘉言予回陽救逆之法,令病家微汗后,熱退而愈。
自古以來,寒熱真假疑似證候是臨床誤診誤治的最多見情況,而且常見于生死存亡之際[26],常規思路易使診療陷入被動,尋找臨證突破點往往在于特殊臨床表現,通過獨取其要,把握病機,即張景岳[19]所言:“諸部無恙,惟此稍乖,乖處藏奸,此其獨也。”
明確了以欲癥為代表的特殊癥狀的臨證適用范圍,不難理解四診合參,統籌全局的重要性。《傷寒論》第284條:“少陰病,惡寒而蜷,時自煩,欲去衣被者,可治”。《千金翼方》相同條文則指出“少陰病,惡寒而蜷,時自煩,欲去衣被者,不可治”[29]。陳亦人指出:“一為可治療,一為不可治,似相徑庭,實有異曲同工之妙,更可示詳于辨證分析”[30]。臨床實踐表明,僅憑“時自煩,欲去衣被”就斷言可治,尚失全面。因而,劉渡舟教授認為:“本條雖為陽氣來復的可治之癥,應注意與手足不溫,脈緊不去,躁擾不寧,陰陽離絕之死證鑒別。”
4 總結
《素問·湯液醪醴論篇》有言:“病為本,工為標,標本不得,邪氣不服,此之謂也。”《傷寒論》強調:“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中醫臨證始終以人為本,高度重視癥狀反映的疾病本質,謹守病機,不離脈證。倘若拘于方證對應,以方度病,以藥度癥,不別癥狀,不識病源,不察病機,相對斯須,便處湯藥,雖執經方,實違醫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