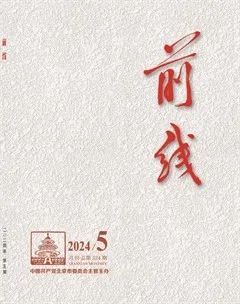一卷長城錦繡 千年文明傳承
作為我國現存體量最大、分布最廣的文化遺產,作為我國超大型軍事防御工程體系以及農牧交錯地帶人地互動的古代文化遺存,長城以其上下兩千年、縱橫數萬里的時空跨度,無愧為人類歷史上宏偉壯麗的建筑奇跡和無與倫比的歷史文化景觀。在漫長歲月里,長城絕非一道隔絕的屏障,而是和平的象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紐帶。在國破家亡的危難時刻,長城以磚石之軀、各族兒女以血肉之軀,頑強地保家衛國,彰顯著中華民族的鐵骨丹心。唯其如此,長城凝聚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和眾志成城、堅韌不屈的愛國情懷,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代表性符號和中華文明的重要象征。
軍事阻隔與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
長城沿線是我國古代重要的文化界限。長城所在區域,與我國北方年平均400毫米等降水量線基本相符。此線以南是降水量比較豐富的中原漢族聚集區,以種植業為主要經濟形態,代表了安土重遷的農耕文明;此線以北是降水量逐漸減少的草原區域,主要活動著以畜牧業為主的游牧民族,形成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明。長城的出現、長城沿線的形成,正是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互動碰撞的結果。
歷史上,長城的建造始于春秋中期,一直延續至清代晚期。它是中原政權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侵擾,依據天然地形而修筑的軍事防御工程體系,其中北京地區的長城不乏雄關險隘。北京段長城分布呈半環形,各處關隘的設置反映出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的空間原則:古北口長城是燕山山脈通向華北平原的最重要關口之一,史稱“南控幽燕,北捍朔漠”,其關城和配套設施是明代在北齊長城遺址基礎上修建而成的。以“險、密、奇、巧、全”聞名的司馬臺長城素有“長城博物館”之稱,此處依然保留著明代薊鎮總兵戚繼光督建時的原貌,“天梯”與“望京樓”顯現出司馬臺長城險要的特質。內外長城分界樞紐“北京結”是箭扣長城的一部分,此處墻體高大、城臺密集,城墻體系完整。慕田峪長城東連古北口、西接八達嶺,被稱為“危嶺雄關”,是拱衛京畿的軍事要沖。慕田峪長城城墻兩側均有箭垛,氣勢更加雄偉。居庸關長城與八達嶺長城是北京西北重要屏障,二者共同構成了完整的防御體系。先秦時期燕國的“居庸塞”被稱為天下“九塞”之一,“居庸”之意為“能夠擔當建立功業的職責”;八達嶺意指“路從此分,四通八達”。長城各處的關隘恰如穿越高山阻隔、溝通南北交流的鑰匙,發揮著防御與交通功能。
和平時期,長城也是南北各民族廣泛交往的經濟橋梁和文化紐帶。自秦代起,農耕經濟地區與游牧經濟地區間的文化交流、交往、碰撞與融合日益發展,兩種經濟形態互為補充和依賴,長城地帶遂匯聚了不同的文明。西漢司馬遷記載,漢武帝曾經給匈奴以優厚待遇,開展長城沿線的關市貿易,出現了“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的和諧局面。到了明代,長城沿線廣大地區各民族紛紛加入邊境貿易,貿易方式主要是互市,包含官方的關市、榷場及民間的日常貿易等。長城沿線逐漸形成眾多商業城市,如北京、張家口、西安等。這些商業城市成為農牧兩大經濟區的重要連接點,在民族商業貿易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民族團結與奮斗的精神象征
“大江南北、長城內外”是形容祖國遼闊領土的常用語。隨著廣袤的蒙古高原、遼闊的東北平原與中原大地在政治上融為一體,長城的軍事功能逐漸衰退。長城翻崇山、越峻嶺、穿草原、涉沙漠、跨河海、攀絕壁,逶迤萬里、翻騰飛舞,像巨龍一樣起伏盤旋,雄踞于我國北方遼闊的土地上,恰與中國傳統文化中龍的形象相吻合。于是,長城作為文化符號的標志意義被不斷強化、凝練,升華為整個國家和民族的精神象征。近代以來,外患嚴重,巍然屹立的萬里長城就成為全民族團結御敵的精神象征,不斷激發著中華兒女的家國情懷、鼓舞著他們前赴后繼抗擊外來敵寇。
“萬里長城萬里長,長城外面是故鄉,四萬萬同胞心一樣,新的長城萬里長。”1933年,關外東三省等地淪陷后,愛國將士展開了收復國土的艱苦卓絕的斗爭。同年3月至5月,中國軍隊在長城沿線的獨石口、古北口、喜峰口、冷口等處,依托長城關隘抗擊日本侵略者。堅守在帽兒山的古北口七勇士,憑借險要地形堅持戰斗,用機槍手榴彈連續打退日軍數次進攻,斃傷日軍100多人。七勇士奮勇抗敵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未退后半步,全部壯烈殉國。在與日軍爭奪喜峰口長城高地的戰斗中,武器裝備落后,二十九軍的“大刀隊”就采用近距離搏斗戰術御敵,筑起了抵抗日寇的血肉長城。
1935年5月上映的電影《風云兒女》,是中國最早號召民眾拿起武器抗日救亡的電影。當時,長城地區激戰猶酣,田漢組織人員到前線采訪,與聶耳共同創作了電影主題曲《義勇軍進行曲》,發出了全民族的吶喊。其中,“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一句,極大地激發了中華兒女全民抗戰、收復河山的決心和力量。這首誕生于抗戰風云中的歌曲后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
文明傳承與發展的重要載體
回溯過往,長城歷經了戰爭與和平的滄桑變遷,特別是近代以來反侵略戰爭的烽火硝煙。今天,長城的城墻、關隘、敵臺、烽燧已經不僅僅是建筑構成,更成為重要的歷史遺產和文化載體,見證和推動了中華文明的傳承與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時強調:“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習近平總書記還凝練地概括出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性: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為中華文明“精準畫像”。長城作為中華民族的代表性符號和中華文明的重要象征,也突出體現了中華文明的這五個特性。
長城體現了中華文明的綿延賡續。歷史上,除了作為軍事防御工程,長城還曾經被用作糧倉和祭祀的場所。長城上發生過許多傳奇故事,諸如屈原登長城、木蘭從戍樓上瞭望敵情等。長城的一些關隘,曾經是古代絲綢之路的重要通道,見證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可以說,一部長城史,半部中國史。長城是中華燦爛歷史文化的縮影,不斷向世人展示中華文明發展進步的演進歷程。
長城見證了工藝技術的持續創新。古人在建造長城的過程中不斷摸索、創新,逐漸積累了工程管理、構筑技術等方面的經驗。長城由單純的線狀防御工程逐漸演化為包含衛所、關口、城邑、堡寨、村鎮等在內的完整體系。建造長城的施工方式也在不斷優化。明代在施工過程中,已將待建長城劃分為若干工段,并在地表設置工段標志,配置人力、分區建造,以便明確各支施工隊伍的工程質量責任。
長城維護了多元一體的共同信念。歷史上的長城為民族融合營造了一個相對固定的地理空間,在建立新的社會秩序,規范、協調民族關系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長城內外各民族及政權,在不斷調整中兼容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最終形成多元一體的共同信念。這種信念使得中華民族有著堅強、牢固的領土意識和國家觀念,在面臨外敵入侵時能夠團結一心,共同抵御外侮,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
長城彰顯了中華文明兼容并蓄的精神特質。歷史上,長城的修建一方面保護了農耕文明的持續發展,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的繁榮,農耕文明對長城之外的游牧文明也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修建長城沒有隔絕文明交往,反而促進了不同文明的碰撞與融合。應該說,長城見證了沿線各地區、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進程,為進一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出了突出貢獻。
長城承載了長治久安的和平訴求。修建長城是一種軍事防御措施,更是對和平生活的向往。盡管長城內外,各民族之間偶有短暫戰事,但“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還是常態。特別是明朝“隆慶和議”后,長城沿線基本沒有發生大規模戰事,長城的關口成為互市之地,“貢使絡繹、商隊接踵”傳為佳話。應該說,通商互市開拓了長城內外各民族互通有無、相互依存的貿易通道,使得各民族之間的關系更加融洽友好,真正實現了山水相連、人文相親、經濟相融。
巨龍綿延,護佑神州。萬里長城是中華民族勤勞智慧的結晶,是世界上規模、體量最大的線性文化遺產,而自東向西蜿蜒經過平谷、密云、懷柔、延慶、昌平和門頭溝6區的長城北京段,則是萬里長城重要的組成部分。如何守護好巍巍長城、留住歷史根脈,需要一代又一代后來者接續努力。在這個過程中,北京先行先試,率先提出以文化帶方式推進長城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利用工作,探索出一條具有首都特色的長城保護新路徑,讓這條長城文化帶成為新時代中華兒女凝心聚力的紐帶,并以此進一步堅定文化自信、砥礪民族風骨、共建美好家園。
(作者簡介:李誠,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責任編輯 / 金蕾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