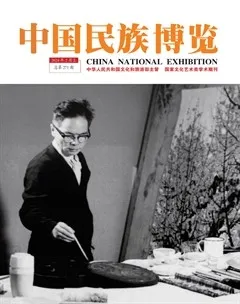主旋律電視劇的年輕化表達
趙程遠 任珂
【摘 要】影視劇中主旋律的說法,最早可追溯到1987年提出的“倡導主旋律,堅持多樣化”口號,但早期主旋律電視劇或多或少存在著說教性強、受眾接受度不高等刻板印象。如今重大歷史題材被不斷創新的過程中,《覺醒年代》在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之際,以其新穎的方式演繹出偉大的建黨精神,展現出中華民族的一段崢嶸歲月。該劇通過年輕化的影像方式書寫歷史,以新穎獨特的審美視角建構起受眾對黨和國家的自信心和認同感,喚醒中國民族的共同體意識,從而激發出受眾對歷史事件重新解讀、激發出全民學黨史的熱潮和愛國精神。本文以《覺醒年代》電視劇為例,通過歷史文化層面、影視語言層面和媒介傳播層面的多維度分析,探尋主旋律電視劇的年輕化變革,旨在研究主旋律電視劇如何打破“曲高和寡”的刻板印象,真正走上一條具備創新性、發展性的道路。成功“出圈”的《覺醒年代》亦可作為借鑒范式,為今后更多主旋律作品的年輕化創作指明方向。
【關鍵詞】主旋律電視劇;《覺醒年代》;精神建構;創作手法;宣發手段
【中圖分類號】J9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198(2024)03—017—03
主旋律電視劇是具有主旋律色彩、能夠反映特定時代、展現時代精神和人民美好風貌的電視劇作品。[1]始終承擔著弘揚主旋律、引導主流價值觀和傳播正能量的職能。作為一部現象級熱播劇,《覺醒年代》用獨特手法表現出陳獨秀、李大釗等先進知識分子覺醒的過程到中國共產黨成立這段恢宏歷史。以豐富的藝術質感和優美的鏡頭語言引發了受眾的強烈反響。在厘清紅色信仰生成的歷史邏輯基礎上,使作品充滿了藝術張力和詩意品格。[2]
一、歷史文化層面的年輕化演繹
(一)建構集體記憶背景
阿爾都塞揭示意識形態是如何改造民眾思想的,他認為:因為意識形態所反映的不是人類同自己生存條件的關系,而是他們體驗這種關系的方式,也就是社會與主題是召喚與被召喚的關系,兩者相互識別,既存在真實的關系,又存在體驗和想象的關系。主旋律電視劇蘊含的意識形態作為一種獨特符號,它既傳達出作品的內涵思想,同時也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故事的發展。《覺醒年代》是在尊重歷史的基礎上,通過藝術和真實相結合的方式建構起一個影視的記憶場景,從而引起受眾記憶。
《覺醒年代》能夠引發受眾共鳴,因為當年緊密契合了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主題,以新穎的方式迎合了大眾審美。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期間,中華民族正處于內憂外患之際,此時人們正探尋救國方法,各類仁人志士紛紛投身于偉大革命中去,繼而建立中國共產黨,引領中華民族走向了光明的前景。
(二)塑造多面英雄人物
“人活則歷史活,歷史活則電視劇活。”為使劇中的人物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人物就需要與受眾產生一定的身份認同。近些年的主旋律影視劇不僅注重主流意識形態的表現,還充分考慮受眾的審美心理及觀演體驗。伴隨電視劇的制作日益完備,人物塑造的重點從臉譜化、性格單一的扁平人物,向帶有思想內涵和審美價值更為突出的立體人物轉變。導演在采訪中強調“立體的人”,不止展現人物的高大全形象,還要展現性格的多面性,家庭生活、個人性格,甚至是性格中的一些小瑕疵。
陳獨秀是無畏、博學但也不拘小節的。作為父親,他對陳延年和陳喬年實行過“空乏其身、餓其體膚、勞其筋骨”的教育過程。[3]將劇中人物形象不再是高高在上、曲高和寡的形象,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有義的普通人,每個人都被賦予了完整的人物弧光。
二、影視語言層面的年輕化演繹
(一)視覺畫面藝術且豐富
豐富的鏡頭手法能夠增加影片的感染力和戲劇張力,展現出一種視覺景觀。“景觀”指在作品實踐中所追求的影像視覺造型效果。[4]主旋律電視劇作為一門藝術,為使劇情更加契合真實生活,創作者需要靈活運用影像手法,依托視覺畫面來構建完整的故事內核。
1.畫面意蘊豐富
劇中蘊含了大量富有哲理的隱喻鏡頭,其美感是通過形象化的信息表征向受眾呈遞某種效果。受眾進行個性化解碼之后,在特定的場域中重新編碼,完成傳播效果。[5]如馬車車轍的畫面,表達了在秦朝時期“車同軌,書同文”,說明時代在改變,人們要趕上時代,不僅思想要變,道路亦要變。同時大量對比鏡頭展現時代背景,如有錢人的少爺西裝革履,坐人力車出行,而與少爺年齡相仿的窮人家姑娘還蜷縮在街頭,頭上插著稻草準備賣掉。
劇中還有大量運用運動空鏡,展示特定人物情感和時代背景,當陳獨秀和李大釗看到居無定所、受盡折磨的百姓時,決定進行無產階級革命,成立中國共產黨時,鏡頭逐漸模糊,暗示了選擇這條道路將會是充滿阻礙和險峻的道路。
2.鏡頭色彩鮮明
色彩的價值可以理解為導演基于色彩的物理屬性,根據受眾的視覺心理、生理特點和生活經驗,遵從作品的主題思想、題材選擇,映襯出導演對作品特有的思考。豐富多樣的色彩能夠對人物刻畫、劇情發展起到一定作用。詩意化的色彩鏡頭也散發著東方美感。[6]
劇中陳獨秀邀請易白沙跟隨他去北大任教,但易白沙看不到革命的希望,也看不到中國的未來,執意留在長沙,二人交談中,畫面色彩頗為黑暗,加上大全景展現人物站位,映襯出易白沙個人的心理情感,讓受眾感受到他作為愛國人士卻無能為力,產生出悲涼之感。在陳延年和陳喬年被捕入獄后,當局決定對二人進行處決,此時畫面色彩灰白,加以二人臉上的鮮血,以紅色的視覺沖擊帶給受眾深刻的印象,展現出二人無懼面對生死的豪邁英雄氣概。
(二)聲音景觀生動且真實
音樂作為一種蘊含規律和節奏的聲音系統,也是一種文化藝術活動形式,在影視作品中被廣泛使用。電視劇中,音樂作為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它能夠烘托故事情節,同時奠定整個影片的感情基調。不同的配樂,營造出的場景各有不同,能夠將受眾帶入相應的時代與空間。
1.配樂激昂雄壯 展現時代精神
“聲音景觀”強調的是一種經由聲音符號的修辭表達而建構的聲音環境或聽覺形象。[7]劇中不同場景下所演奏的音樂也有所不同,為展現出熱鬧繁華的市井氣息,導演安排輕松愉快的背景音混合街邊叫賣的嘈雜聲;而在以學習為主的北大校園內,則是讀書與嬉鬧聲營造出世外桃源般的學習環境。《覺醒年代》中經典的配樂當屬陳獨秀和李大釗出京,看到逃荒的百姓民不聊生、居無定所,兩人悲憤不已,毅然決定建立中國共產黨,讓全國百姓不再流離失所、衣食不飽,此時響起激昂悲壯的配樂,配合二人握拳一同建黨宣誓的畫面,讓受眾感受到劇中人物的堅毅豪邁之情,真切感受到陳獨秀和李大釗胸懷天下,引起青年群體觀看的愛國熱情。
2.臺詞生動有趣 貼近現實生活
部分受眾對于主旋律影視作品的印象依然是刻板的說教臺詞,所以主旋律電視劇想要取得良好的口碑,首先要在臺詞上做到創新。劇中有些臺詞以輕松幽默的風格展現,將內容用受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呈現出來。如在北大在陳獨秀的倡導下正在轟轟烈烈地舉辦新文化運動,但守舊派和保皇派的辜鴻銘、黃侃和劉師培等人卻不以為然,處處和陳獨秀、李大釗等人意見不合,甚至有些故意作對,臺詞頗有韻味,使受眾在了解到北大不同文化思潮的背景下,產生一絲輕松愉悅感。此外街邊上特色的叫賣聲也充當了人物臺詞的作用,用攤主吟唱的生動方式來講述民國總統袁世凱下臺、張勛復辟等多個歷史事件。
(三)敘事善于用典且新穎
該劇的敘事線索遵循歷史發展的客觀事實,也符合歷史發展規律,以“年輕化”語態與“我”視角為切入點進行敘事。劇中所引用的典故也都基于真實歷史事件打造而來,在尊重史實的基礎上結合一定的藝術加工方式,從而達到讓受眾共情共鳴的感覺。第一集陳獨秀因對舊中國的前途和命運看法不同,在早稻田大學里與中國留學生辯論,被罵,甚至留學生對他吐口水,但陳獨秀并不在意,抬手將臉上口水擦凈,生動展現出“唾面自干”的典故。再者為了表現蔡元培校長重視人才,他曾多次在風雪天前往陳獨秀家,邀請陳獨秀出任北大教師,是對三國時期劉備“三顧茅廬”典故的再現。后因陳獨秀飲酒后臥床不起,校長蔡元培在家靜等陳獨秀蘇醒,展現的是“程門立雪”典故。片中陳獨秀提出著名的“新青年的六條標準”,之后黨在六條標準之后加上“健壯的而非體弱的”,這七條標準在電視劇中激勵著一批批青年人無畏生死,投身于民族獨立和國家解放的任務中。
三、媒介傳播層面的年輕化宣發
(一)傳統媒體宣發
作為建黨百年的獻禮劇,傳統媒體是主要的傳播平臺。官方平臺很早就開始宣傳,如中央八臺在2020年底就曾播放過宣傳片,《新聞聯播》也報道過“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破曉》七一晚會節目,同時李大釗和趙紉蘭的演員也曾到北京衛視春晚舞臺上朗誦李大釗的詩詞作品。電視劇在晚間黃金檔熱播之前,《新聞聯播》節目結束后會播放關于該劇每集的預告花絮,進行全方位的宣傳和推薦。除上星衛視外,其他傳統媒體也都紛紛發聲,先后登報發表《覺醒年代》相關文章,予以較高評價助陣。
(二)新媒體宣發
除傳統媒體,劇組的宣傳推廣也希望覆蓋到社交平臺上掌握話語權的年輕用戶們。打破主旋律劇收視圈層和傳播壁壘,收獲青年觀眾。[8]2021年該劇在互聯網平臺播出之時,受到主旋律題材因素限制,加之缺少流量明星助陣和宣發方式單一等各類原因,導致在播出一段時間內并沒有取得熱烈的反響,但部分群體觀看后在豆瓣、知乎等平臺為這部劇發聲,通過口碑傳播人氣逐漸提高,讓更多的人關注到這部被忽略的現象級電視劇。
在抖音和嗶哩嗶哩上,用戶通過《覺醒年代》的花絮和片段進行解讀,也通過結合紅色歌曲制作MV,都為該劇的宣傳起到了重要。在愛奇藝、優酷等平臺的彈幕中可發現部分受眾是通過抖音、快手等短視頻平臺吸引過來的,再次證實新媒體的環境下,通過多種途徑對于《覺醒年代》的宣發有著積極意義。部分受眾也通過微博、小紅書等社交軟件參與留言討論,在被問其這部電視劇有沒有續集,有網友留言回答道:可以說我們今天的美好生活就是《覺醒年代》的續集。[9]
四、結語
主旋律作品一直承擔著引導主流價值觀和傳播正能量的職能,近年來選題更加多元。《覺醒年代》以精良的制作消除了正劇特有的距離感,打破了年輕受眾對主旋律作品呆板的固有認知,實現專業精神的立體重塑。該劇一方面具有藝術特性,能夠給受眾帶來視聽上的享受;另一方面其獨有的意識形態能夠向受眾呈遞政治思想和社會價值,從而獲得受眾對社會的文化認同。《覺醒年代》的走紅,不只局限于作品的年輕化演繹,也是在尊重歷史的基礎上再現了中國共產黨成立的險阻與艱辛,以更加新穎的方式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展現中國力量。
參考文獻:
[1]張智華,孫汶.論近年來我國主旋律電視劇的發展和變化[J].現代視聽,2021(2).
[2]敬鵬林.歷史記憶、影像修辭與情感認同:《覺醒年代》的意義生成[J].四川戲劇,2021(8).
[3]唐寶林.陳獨秀全傳[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4]路春艷,高歌.布景·奇觀·祛魅——景觀研究視域中的藏族題材電影創作[J].藝術廣角,2022(1).
[5]欒軼玫.視覺說服與國家形象建構——對外傳播中的視聽新話語[J].新聞與寫作,2017(8).
[6]馬昆鵬.讓歷史鮮活地走進當代:重大歷史題材劇《覺醒年代》創作談[J].視聽,2021(12).
[7]劉濤,朱思敏.融合新聞的聲音“景觀”及其敘事語言[J].新聞與寫作,2020(12).
[8]郭人旗.《覺醒年代》火爆“出圈”對黨史文化傳播的有益啟示[J].新聞世界,2021(5).
[9]王志宏,伊文臣.借力影視藝術講好奮斗故事:以熱播主旋律題材電視劇為例[J].當代電視,2021(4).
作者簡介:趙程遠(1997—),男,漢族,河南洛陽人,碩士在讀,河北傳媒學院,研究方向為電視編導與制作;任珂(1994—),女,漢族,河南洛陽人,碩士研究生,廣東科貿職業學院信息中心,研究方向為電視編導與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