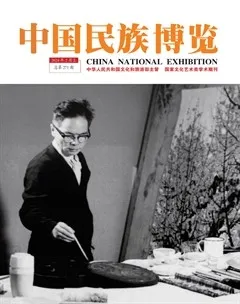文學尋根與莫言的文化反思研究
【摘 要】莫言成名于20世紀80年代尋根文學浪潮的鼎盛時期,其創作符合尋根文學的思想追求與價值取向,但卻存在獨特之處。90年代以后,莫言的文學創作將尋根文學導向更深層次的文化維度。本文從尋根文學的根本任務入手,分析莫言尋根文學的獨特之處與不變主題,深入分析莫言作品中人性與文化的沖突與矛盾,進而從莫言的文化反思入手,探究莫言從文化批判到文化認同與批判的過程,從而探索莫言文學作品的思想內涵與內核。
【關鍵詞】文學尋根;莫言;文化反思
【中圖分類號】I20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198(2024)03—023—03
引言
在我國文學史上,莫言是極為罕見的“異數”,他超凡的創造力,輝煌的藝術成就,使許多同時代作家黯然失色,從《紅高粱》到《食草家族》、從《透明的蘿卜》到《酒國》,再到近些年的《檀香刑》與《豐乳肥臀》,莫言以旺盛的文學創造力、雄健的文學生命力,掀起五六次的文壇轟動。然而拋開浮華,探究莫言文學創作的思想底蘊,不難發現一個價值指向,就是“尋根”。尋根文學是在文化尋根的浪潮中所形成的文學流派。文化尋根形成于20世紀末,進入新時代后,我國社會各階層多層次、多方面地反思中國發展的歷程,特別對西方文化的傳入,使得文化界更加關切、反思中國現實與社會歷史的發展歷程,一部分文化學者及作家開始提倡“文化尋根”,渴望在梳理優秀傳統文化的過程中,探尋中華民族賴以為生的根脈。在該層面上文化尋根與尋根文學得以交匯,并推進了我國“尋根文學”的發展。莫言的文學生命力植根于尋根文學,并賦予其地域文化與民族文化的特性。
一、尋根文學的根本任務
地域文化是我國尋根文學最為典型的特征,莫言的文學創造契合了該特征。尋根文學創作者韓少功認為:“文學有根,文學之根應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尋根文學作家都在“尋根”,他們也不斷找到了“根”,通過對地理風情、山川地貌的描寫,讓“根”貫穿于作品創作的“字里行間”。這種對“根”的表達,體現出中國人對人生、對世界的感知與體驗,能夠營造出獨具中國特色的情調與意境。實質上,我國擁有歷史悠久的文化藝術,在歷朝歷代擁有不同的氣韻,如在唐朝時擁有雄渾、狂放、瑰麗的氣魄;在宋朝擁有含蓄、典雅的意蘊。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歷史的演變,優秀傳統文化形態也不斷沒落。然而那股潛藏在優秀傳統文化中的藝術元氣并沒有斷絕,他融入到遼闊的民間大地、鄉土土壤中,隱藏在山野角落、山川地貌中。尋根文學作家認為尋根的根本任務就是將散落在山村、偏地的生機盎然的民族文化與民間文化發掘出來,營造出植根于文學創作維度的自然生態、人文環境、地域特色,讓中國人能把握住“根”“抓住根”。
然而尋根文學作家也意識到兩個問題。首先是魔幻現實主義作品之所以會帶來“爆炸性”影響,在于他們不僅擁有遼闊的文學事業,還能執著地扎根于本土文化。其次民族文化的溝通與交流是雙向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為現代文化做出了突出的貢獻,譬如老莊思想便成為“亞斯貝斯”等人探尋人生感悟與尋求哲思的新路徑。基于此,尋根作家將學習西方文學的精髓,建構在對本土文化的認識上;將發揚民族文化作為新的目標指向。在文學創作上,有描寫吳越文化的《沙灶遺風》與《最后的漁佬》;有描寫草原文化的《北方的河》與《黑駿馬》;有道家文化侵潤的《棋王》。在這些作家作品中,我們能夠看到文化尋根在對鄉風民俗與文化傳統的描繪中,所帶來的文化反思的意蘊及性質。尋根文化所梳理與尋找的“根”是優劣兼顧的,是豐富而飽滿的,它在批判劣根的同時,弘揚“優根”,在從古至今的進步與發展中,體現野蠻、蒙昧、封閉的文化生態對人性的“抑制”;體現出積極、優秀、和諧的文化對社會發展的裨益,通過尋根,讓民族文化真正成為改善國民性的一把“標桿”,讓中國文學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獲得新的前進方向。
二、莫言與尋根文學
莫言的文學創作屬于尋根文學“尺度”所規范的范疇內,他的作品觸及到民俗民風、民間文化及古代文化思潮,并且從多維度及多視角出發,莫言的文學創造普遍契合尋根文學的審美特征與內在意蘊,并且擁有獨具特色的文化理念與文學價值取向,即生命力、文化批判。這種獨特性讓莫言的尋根文學從“同時代的尋根文學作品”中脫穎而出,讓莫言在文化尋根中,真正達到啟迪國民心智,發掘、傳承民俗文化的效果。為深入分析莫言的尋根文學及其獨特性,我們應從“其文學創作”的獨特性出發。
首先是生命力。莫言的文學創作內核是呈現民間社會的“野文化”,即與傳統規范文化相對立的,注重描寫人的生存欲望與天性的內容。一般來講“食色性也”。這是人生存的前提條件,合理而自然的。所以莫言將其放在高于一切的文化規范中。《飛艇》《老槍》《五個餑餑》在創作技法上都各有千秋,但共同涉及了一個主題——“食”。由食物匱乏出發,發掘人類種種最為原始的欲望,是莫言文學創作的主題之一。譬如在《老槍》中,大鎖是為了填飽肚子,不惜違背家訓去打獵;支持他“意志”的正是以“食”為主的本能欲望,正是以“生存”為主的基本需求。然而一個人打獵未果,卻因槍管炸膛而殞命,讓人不得不思考,人追求“生存”的欲望,到底是對,還是錯。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空氣、睡眠、住所、飲料、食物等都是人類賴以為生的基礎,人們需要他們,沒有他們,就會喪失生存的動機,而莫言植根于人類最原始的“需求”亦或者“欲望”,從發掘民俗文化的視角出發,探究人最原始的本能與欲望同文化之間的沖突與矛盾。譬如在《透明的紅蘿卜》中,莫言展現了人類在物質生存條件匱乏的情況下,與村規、村俗之間的沖突。對生命力的贊美也體現在《紅高粱家族》中,莫言通過描寫“紅高粱”,贊美生命的不屈與熱烈。高粱是鄉村居民的物質糧食,是他們“打埋伏”的重要場所。“這里是死亡、生命的聚集地,紅高粱旺盛與野性的生命力,逐漸成為中國農民的生命力的象征。”莫言在《紅高粱家族》中描寫了余占鰲他殺單扁郎父子,都是為了生存,這是他生存的一種方式。這種生命活力是一種難以言表的“生存意蘊”。從創作背景出發,莫言創作《紅高粱家族》是因為痛感都市中生命力的萎縮及人性的骯臟,進而在東北鄉村那一片野性、粗狂的土地上尋找人性最原始、最真切、最透徹的本性。繼而在追溯歷史底蘊的過程中,發現父輩那種強悍的生命力,以及無所畏懼、無所顧忌的生命方式。莫言渴望以這種生命力的詮釋與展示,改造現代都市人的“家兔氣”。我們可以從尋根文學的根本任務出發(即提高國民性),認為莫言的文學創作植根于最原始、最本能的生存本能,從生命力的維度,探尋改造國民性的新路徑。
其次是文化批判。莫言贊美生命力的前提下,也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文化批判,這種文化批判是基于生命力與民俗文化之間的矛盾與沖突,基于封建文化對人性的壓抑、抑制、迫害的,是植根于文化傳統與生存本能的對立面的,能夠讓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歷史文化的劣根性得到充分地體現。譬如在《紅高粱家族》中,在高粱地中的行為放蕩與傳統倫理文化的沖突,奶奶的自由奔放與三綱五常的沖突,角色們殺人放火與傳統道德倫理的沖突,這種生命力與民俗文化的沖突,建構了莫言文學尋根的底蘊,鑄就了莫言文學的價值取向。這是莫言與傳統“尋根派”的最大區別,但他沒有將文學創作視角拘泥于對民族文化、地域文化、鄉土文化的發掘上,也沒有將文化發掘、文化尋根作為故事背景的架構“要件”,而是將文化尋根與生命活力對峙起來,通過矛盾沖突,發掘文化最底層、最根本的特質。這種生命特質是現代的視角出發,以改造國民性這一根本任務入手,從主體意識的層面,建構出“尋根文學”的新范式。譬如莫言以現代女性主義觀念出發,充分反映出傳統對女性的壓迫,如《紅處方》中的簡方寧等。可以說,莫言是在推崇、贊美生命活力的前提下,對抑制人性的民俗文化、封建文化、鄉土文化進行了批判,從揭示傳統的劣根性出發,呈現自己獨特的文化思想、文化理念。
三、莫言的文學變遷
尋根文學作為一股文學思潮,早在20世紀末便煙消云散,然而根據文學理論研究發現,尋根文學并沒有斷絕,反而以潛隱的方式植入于當代文學創作的不同環節中。很多作家的作品如《九月寓言》《我與地壇》《心靈史》等都說明了這一點。他們在作品中植入了尋根文學對民族文化的探尋與追求,讓尋根文學以全新的方式,流傳在世間。莫言的尋根文學創作也沒有斷絕,他的文學創作更加深入到民族文化的精神底蘊之中,將自己對文化的反思與思考,融入到諸如《檀香刑》《酒國》的創作中。
首先是理性探索。在莫言早期的文學創作中,莫言植根于對人性的贊美。通過人性與文化的沖突,架構起尋根文學的新范式,并讓莫言在眾多的尋根文學作家中脫穎而出。然而在后期的文學創作中,莫言不斷思考民族文化、鄉土文化、鄉村文化與人性的關系,表現出一種理性探索,同時也將矛盾沖突聚焦于城市的虛偽與浮躁上。譬如在《食草家族》中,作者以“我”橫跨鄉村與城市的空間架構,對城市的虛偽與野蠻進行了批判,對鄉土民間進行了贊美,并且在贊美中,持有一種批判的意味。這樣我們能夠體悟到主人公的生存困境,以及精神上的兩難抉擇。而在《豐乳肥臀》中,莫言充分展示了民間文化的多面性與復雜性,例如主人公為了愛殺人,為生存殺人,完全違背了中國基本的人倫情理,但贊美生命活力依舊是作品的不變主題。與此同時,作者也展現了一個廣闊的民間社會,贊美了這個本色、淳樸、熱氣騰騰的民間,通過謳歌民間文化與批判傳統,突出了作者對人性的思考及對民俗文化的理性探索。在《檀香刑》中,作者引入說唱藝術,通過多視角敘事的方式,架構起山東農民起義的敘事框架。這種敘事形態,靈活呈現了主人公沖破封建道德的枷鎖,追求自由愛情的進取精神,同時也表達了莫言對傳統文明中“榮辱與共”“拼搏奮斗”“自強不息”等文化精神的認可。可以說莫言對民俗文化、民族文化、民間文化發生了變化,從單向性批判,轉變為理性的思考。
其次是對“劣根”的再批判。在早期的文學創作中,莫言以“生命活力”為契機,對所有壓抑人性、個性的封建道德進行批判。然而在后期,莫言雖然理性思考了文化的“優根”與“劣根”,但更加明確了批判的方向。即深入發掘壓抑“生命活力”的劣根文化的本質——“吃人”與“主奴”。在“吃人”文化上,魯迅先生立足于中國歷史,批判了民族文化中吃人本質,直指“精神吞噬與扼殺”對“社會進步”帶來的阻遏。莫言延續了“精神吞噬與扼殺”的批判意蘊,并將“吃人”作為傳統文明與人性自由的沖突點。通過描寫精神扼殺,直擊民族文化的劣根性。譬如在《豐乳肥臀》中,作者描寫了一批被權利異化的野獸,描寫了主人翁所遭受的精神破壞。雖然沒有實寫“傳統”,但卻體現了傳統中的“吃人實質”。其二是“主奴”。奴才與主子的關系,體現了對人的抑制、壓抑、撲殺,以及對人性的毀滅與摧殘。在莫言的文學創作中,如《食草家族》《豐乳肥臀》《二姑隨后嫁到》中作者都設定了“專制者”這一角色,通過主奴對立,深層次地批判了封建文化對人性的扼殺。
四、結語
尋根文學旨在探尋并梳理文化的優根和劣根,提高國民性。作為尋根文學的代表,莫言以贊美生命活力為契機,批判傳統文明中的劣根性。但隨著時代的發展,莫言的文學創作也發生了變化。他對待民俗文化、民族文化、鄉土文化的態度更加理性,但依舊保留著批判的態度,只不過他的“文化批判”變得更深刻、更具體。
參考文獻:
[1]郭洪雷.莫言小說創作與閱讀關系新論——兼及作為方法的作家閱讀史研究[J].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4).
[2]劉聿秋.論莫言與鄉土的動態關系——以《晚熟的人》人性書寫為中心[J].四川文理學院學報,2023(4).
[3]王學謙.讓現實體驗插上神話的翅膀——莫言《罪過》的魔幻敘事及其與魯迅文學的互文性分析[J].求是學刊,2023(3).
[4]段愛松.莫言《生死疲勞》:超拔的后現代主義拓展[J].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3(4).
[5]呂悅.“孤獨”的內在特征——敘事倫理視域下莫言《枯河》中的兒童生存困境[J].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2023(1).
[6]蔣紅.魔幻與現實的糅合——探究莫言《生死疲勞》魔幻的民間敘事[J].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2(4).
作者簡介:蘇兆峰(1970—),男,漢族,山東菏澤人,本科,山東省菏澤技師學院,高級講師,研究方向為中等職業學校語文教學及文學賞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