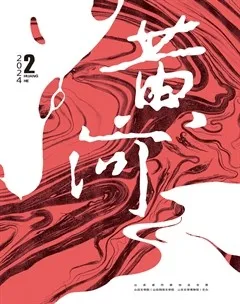尋找一塊堅硬的鐵
提云積
這個位置以前是村子的東頭。
這里的人們在稱呼村子位置的時候,習慣在方位名詞后面加綴一個“頭”字,村子的南頭、北頭、西頭,或者是東南頭、西南頭、東北頭、西北頭,等等。這樣稱呼,村子就比較擬人化了。有了“頭”的村莊,可以像人們一樣記憶與思考。何況,村子經歷了那么多的歲月過往,還有曾經在這個村莊里生活的人們自古至今發生的所有故事。這一切,都需要村莊認真地刻印在每一個時間節點上,留待后人隨時翻檢。
現在這個位置已經是村子的中心地帶,如果在比以前更早的古時,或許這里就沒有村莊,只是一片丘陵地帶,丘陵上生長著各種各樣的喬木、灌木、荒草,有開花的樹,有不開花的草。直到某一天,它帶著造物主的使命誕生了。從它誕生的那一刻起,就與眾不同,它是有大志向的。它營構的所有的生機,就是為了吸引在人世間奔走的人們到它所在的位置建立一座村莊。
它是樹,當它于這世間生根發芽的時候,路過的人們,或者是其他生靈都是這樣稱呼它的。這個名字具有普遍性,是眾多中的一個。直到歲月將它熬成了一個獨立的個體,才有了專屬自己的名字。現在人們是這樣稱呼它的:一棵老槐樹。在槐樹的前面加了一個“老”字,說明它經歷的歲月豐厚。它站在這個位置有多少年了?誰也無法說得清楚。村子里的老人說,有一年,從泰山腳下的一個城市來了一幫人,這個城市自古以來便為皇家祭天的地方。這些人想把它挪移到那個城市去,他們事先用一些鋼鐵儀器測量了它的樹徑,估測有一千一百余年。村里的老人都不同意,原因有兩個,一個是怕挪不活,人們都關心它的生死,它與人們朝夕相處,共飲一井水,共呼吸一方空氣,已經同氣連枝,誰也無法割裂這份情感;一個是既然它在此已經一千余年,與村莊的緣分根深蒂固,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村莊的守護神,就更不能挪。聽說那個城市的人出價二十萬元,村子的老人們說,出再多的錢也不挪,這是村莊的神。
樹沒有挪走,人們照例在茶余飯后、休閑納涼的時候到樹下來站站、坐坐、說說、聽聽、看看、想想。后來,因為一些機緣,在我到村子來尋訪關于古樹與村莊的來歷時,老人們給我講了這個過程。我以自己所了解的經驗,感覺那些鋼鐵儀器測量的它的年紀是有水分的。理由也是兩點,一是那個城市的人為了讓村里同意把樹挪走,故意將樹的年紀說小了。畢竟,在那些人的眼里,它是一件商品,與其他明碼標價的商品沒有任何區別。商人的狡黠,在與商品所持有的主人討價還價時,是要隱藏一些小心思的。好在,村子里的人們沒有把它當做商品,他們尊奉它為神,或者是村子不可或缺的一個“人”,是村子血脈的一部分;另一個理由是,與萊州區域內的一千余年以上的古樹橫向比較,它的樹徑明顯比其他的樹粗大了許多。
有一個生活常識,一棵剛栽種的小樹,它的生長可以用肉眼感知到,在小樹長成參天大樹,樹徑達到一個圍度時,它的外觀變化便會緩慢下來,我們用肉眼很難感知到它的細微變化。在其他的村莊聽一些老人說到古樹的時候,都會有一句說辭,意思差不多:聽老輩人說,這棵樹沒有什么變化,在幾百年前就是這個樣子,現在還是這個樣子。看到這棵古槐樹的時候,我推測它的年紀至少在一千三百年左右,或是更多一些,但不超出一千五百年。那時候,這個位置沒有村莊,這個村莊老人的說辭一致,先有樹后有村莊。至于是什么時候有了村莊的,老人們一說七百余年,一說明洪武二年。我傾向第一個說辭,第二個說辭錯訛,是受了某一官方部門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做的社會調查,那次調查是失敗的,以想當然的態度,使調查結果錯漏百出。村莊有李、吳二姓,遺憾的是祖傳的族譜都早已遺失,無法查詢到具體的文字記載。
我在文檔里敲下前面的這些文字時,忽然發現,稱呼它為“樹”好像是有一些欠缺的。它剛站立此處時,或許是一棵樹,這是它的外觀決定了它的名字。當它于這人世間以千年為計的時候,它已經不是樹了。樹只是它的外觀,現在它的內涵遠比它的外觀更豐厚,更加吸引世人。如同村里的老人們說的那樣,它已經是“神”了。它站立于此,知道村莊里每一戶人家日子里的酸甜苦辣,知道每一戶人家的人情世故。
村子叫作“鐵民村”,在村東進村的路口有一塊石碑,記載了村名的來歷:一九四五年,為紀念在抗戰中犧牲的原膠東五旅十五團政治部主任李鐵民同志命名。村子之前叫作“曹村李家”。落款是現在的村民委員會。我第一次到鐵民村,是辛丑年的正月初四,北方大地上還是寒冷的氣息。立春是在春節前,確切的時間是在庚子年庚寅月壬午日,冷峻寒涼的空氣里已有了春天的氣息。
從東面轉向進村的路口,第一眼看到的便是這棵古槐樹。古槐樹在村子的東西主路上,偏于北側,北側是一戶老宅,小門樓,外墻刷了白粉。冬日的陽光照射過來,這個空間便顯得格外亮氣,陽光將樹冠雜亂的枝丫投放在外墻上,勾勒出不同的圖案。
老宅沒有參與到村莊的統一規劃,位置比較靠后。再加之古槐樹所處的空間是一個十字路口,古樹所在的這段道路的南北寬度就比這條道路的其他位置的空間寬敞了許多。這應該是在規劃村莊時刻意為古樹留出的生存空間。
古槐樹的樹冠圓整,遮蓋了它所處空間的上空。樹冠的主枝上佇立著一根旗桿,懸掛著一面鮮紅的國旗,高過樹冠有一兩米的樣子,在清亮的陽光里被清寒的春風吹拂得獵獵作響。樹冠中部的樹枝上均衡分布懸掛了十幾個紅色燈籠,底部的樹枝上捆扎著許多紅布條,想必是人們于此祈福的,想求得這人世間的一些身外之物。
人們為古槐樹修建了圍欄,圍欄的基座是麻色花崗石,花崗石基座上鑲嵌了木質圍欄,圍欄是斜方塊形狀,刷了清漆,透出木質本初的顏色。陽光穿過方格,照射在圍欄里沒有凋零的不知名綠葉植物上,它們來自上個年度。在古槐樹根部的東側有一個矮小的供臺,臺上有一個小香爐,香爐里有一支燃盡的深粉色的線香的殘枝,圍欄方格被太陽投射過來的陰影把供臺切割成不規則的形狀。
古槐樹的樹干太粗了,這是我能想得到最能體現古槐樹樹體的字眼。早年古樹曾被人為鋸掉樹冠外延的樹枝,遺留了碩大的疤痕。疤痕的截面粗糲、毛糙,在樹冠的南側、西側、東北側各有一個,疤痕已經中空,應該已經通向樹體的內部。在樹體的西北方向,是一道上下貫通的水泥皮,有四十余公分的寬度,在水泥皮的上端有脫落的灰皮,露出幾節紅磚的殘角。
我在古槐樹下蹲下身來,努力將相機的鏡頭壓低,幾乎貼近地面,我想取一個藍天下古樹高聳的影像。鏡頭里的影像非常有層次感,最上空是藍天白云,及下是朱紅的國旗,再下是古槐樹黑??樹冠上靜默無言的枝杈。樹冠與樹體銜接的地方,是樹體皸裂的豁口。陽光穿過那些細碎的樹枝,投射在粗大的樹體上,陰影部分黝黑生出的暗,給人一種極有硬度的想象。有陽光的部分,雖有溫和,作為陰影的延伸部分,也具有硬的特質。如同人類,有的人是硬中生硬,有的人是綿里藏針。
天空中被寒風從北邊吹來的白色云彩,與瓦藍的天色相互映襯,這世間的樣子便顯得極為明凈。相機鏡頭里的古樹是一幅高古的形態,在我按下快門的那一刻,有一個想法在腦子里很突兀地顯現出來。這個想法應該不是憑空虛想,曾經在鏡頭里呈現的那些影像給我留下的短暫記憶,使我想到,這棵古槐樹,以及那些以它為依托生長的枝枝杈杈帶有的某種硬質,是只有堅硬的“鐵”才具有的特性。
有一刻,我甚至想過,我在瞬時出現的這個想法是不是受了鐵民村來歷的影響。后來,在我深入的走訪過程中,我才恍然,不管是因為古槐樹的硬質形成的關于鐵的特性的想象,還是因為李鐵民為追求民族解放從而形成的骨子里具有鐵的特性的想象,都是依托這一方水土的養育使然。
隨著太陽的上升,街上有了三三兩兩的行人。有出村的,他們無暇顧及我的存在,開著車,或者騎著電動車,從我身邊瞬時而過。那些不出村的,只有一個人時,遠遠地站著,看我在古樹下的一行一動。再來一位不出村的,他們就二人扎在一起,交頭接耳,看著我的方向指指點點,隨著寒風刮過來的語音根本聽不清他們在說些什么。
在我繞到古槐樹的東側位置時,看到從古槐樹西側的一個胡同里轉出來一位中年男子,與我年紀相仿,牽著一條寵物狗,徑直走到老宅前打開街門走了進去,在進去之前還刻意回頭多看了我幾眼。不過幾分鐘的時間,聽到院子里有送客的聲音,不一會兒男子出來了,這時我已經故意繞到了老宅的門前,想站在這里等他出來。
我只是隨意問話,向他請教古槐樹的來歷。他答不出,但很熱情地邀請我去他家里坐坐,他父親在家,應該知道一些關于古槐樹的故事。我稍作謙讓,說到疫情。他并不以為然,極力邀請我去。我樂得他的堅持,隨他回家。
其父年七十五歲,屬豬,吳姓。村子有兩個姓,除了李姓,便是吳姓了。向老人請教關于村莊的來歷,吳姓一族于此村莊的來歷,以及古槐樹的來歷皆語焉不詳。曾有族譜已失落,吳姓來自何處也沒有口傳的史料。關于古槐樹只是聽老人們說是“先有樹后有村莊”。
老人給我講了年輕時聽聞那時的老人講的關于古槐樹的一個故事。早年,有老人早起務工。其時,古槐樹比現在的形狀還要龐大,伸向南側的一根樹枝就有三十米的樣子,在樹枝將盡的位置下方有一口古井,這也是古井與古槐樹之間的距離。古井圓口,麻條石砌邊。早起務工的老人遠遠地看到有一截樹枝伸在古井里,待至到得近前,才猛然發現,竟然是一條粗大的蛇。蛇把尾巴盤在古槐樹的主樹干上,身子匍匐在伸向南側的樹枝上,蛇頭伸在古井里喝水。老人受了驚嚇,愣怔不能說話,清醒過來的時候,驚叫一聲,喝水的大蛇受了驚嚇,瞬即遁去,不知蹤影。
對于民間的一些傳說,我只是做一個忠實的記錄者,不去考證故事的真偽,這樣的故事本身就是一個虛妄的存在。在整理這個故事的時候,老人末了講的一句話極有意義:不知來去。在老人說出這四個字的時候,我無意加了追問,老人再次說了“不知來去”。這四個字為故事的本身,以及故事里的蛇的本身都有一種特別鮮明的指向,二者都是虛幻的。
近午時分,主家客至,我不便繼續打擾,婉拒主人的熱情挽留,告辭出來。從古樹下經過的時候,我還在想著,血肉之軀是如何成為一塊有硬度的鋼鐵的,是歲月的淬煉,還是血與火的洗禮……
作為行走的習慣,在每一個村莊,我要走遍整個村莊的每一個角落,搜尋這個村莊于此世間有別于其他村莊的不同細節。何況正是春節期間,我對家家戶戶張貼的對聯比較感興趣,對聯能真實地反映這家主人的處世哲學。從胡同里出來,向西幾步遠,向北又出現一條胡同,信步拐進去。胡同西側一戶人家,街門向東,落鎖已生出干褐色的鐵銹,應該也已多年無有開啟,我不免對主人的境況多生了一些想法。木門多年未油漆過,早年涂抹過黑色的油漆,早已被風雨剝蝕一盡,只殘留了黑灰的底色,露出枯敗的木紋,竟有高山浪濤的意象。早年用黃色油漆書寫的對聯勉強可識,書體行草,右側的門扇上書寫了“天若有情天亦老”,左側的門扇上書寫了“人間正道是滄桑”。其時,我并無多想,隨手拍照,也只為留存一些影像資料。
再來已是盛夏,那一日是陽歷的七月十日,農歷六月初一,本地的習俗是過半年,也叫作過小年。盛夏時節的古槐樹枝葉繁密,勃發的生機在每一張細碎的葉片上都得到淋漓盡致的體現。夏日的陽光覆蓋其上,泛著油綠的光。春節期間的燈籠已經換過,新掛的燈籠閃耀著紅彤彤喜樂的色彩。
這一次來,我是要來尋找的,帶著具體目的的尋找。須承認一點,我的尋找是建立在別人的等待基礎之上的。
尋找是主動狀態,等待是被動狀態。
尋找的主動狀態建立在我對等待狀態的認知上。
尋找是在多年后才開始的,近一個世紀的時間;等待則是在那個故事的主人公還在這人世間為中國人的生命與領土完整東拼西殺的時候就開始了。
其實,她的等待是具有尋找意義的。在尋找之前,我與她從未有過任何的交集,我們不是一個時代的人。因為他,在我的尋找過程中,知道了她,她是他的母親。由此我還想過,古槐樹與村莊也處在等待的狀態中,從它們于這世間開始便進入了等待狀態,它們的等待狀態與它們的存世狀態成正比。等待李、吳二姓的始祖到此建立村莊,等待由村莊出走的每一個人的平安回歸。不可否認的是,村莊、古槐樹,以及藉由它們在此人世間生出的所有的故事也在等待著我的到來。這一世,我不負它們的等待,在辛丑年的春日和夏日,我分兩次來到了這里。
我承認,在尋找初期,我的尋找是否有結果是未知的;當然,等待的結果是已經明了,這是我在尋找的過程中得到的最明確的答案。
那一日,我坐在李鐵民侄子家的堂屋里,他的侄媳邊包餃子邊根據記憶里家中老人講述的關于李鐵民的一些事跡給我做了轉述。李鐵民侄媳在人民教師的崗位上退休,對于李鐵民的事跡沒有清晰的時間脈絡,想到什么便講什么。對于我提的問題,她承認與其他所有曾經來訪的人問的都不一樣,她無法按照以前形成的敘述習慣進行轉述。我提的問題給她造成了難題,也給我自己出了難題,我只能根據她零碎的說辭進行整理,努力還原那個時代,還原那個時代背景下的李鐵民。
已經是春天,村頭的古槐樹又開始發芽了。村莊周圍那么多的樹木與野草都在等待著萌發一場生機,這一場生機需要一個引領者。古槐樹是春天的引子,也是這些樹木與野草勃發生機的領路人。現在,村子的人們還一直有這樣的說辭,每年春天,古槐樹不發芽,方圓地域內的樹木荒草都沒有發芽的,及至秋后寒冬來,樹木百草皆葉落盡后,古槐樹才始落葉。如同,一段歲月的開啟與閉合,需要一個搜集的容器,或者是一個在場者以作證明。古槐樹做到了,由此可以印證,它是這里的王。
古槐樹的萌發不僅帶動了人世間歲月的更替,也帶動了新人的誕生。他出生于古歷一九一九年三月初三日,得名李榮升,因為生日占了兩個“三”,得字“級三”。他的誕生,如古槐樹一般,也是帶了春天的旨意的,他也是春天的引領者。有一刻,在我知道了他與古樹的一些傳奇故事的時候,我曾把他們二者視為一體。他們都是為美好的春天而生,他們都是為了這個村莊而生,他們都是為了這片為千萬萬人迷戀的泥土而生。
春風開始勁吹,把古槐樹萌發的號令帶向四面八方。紙鳶在孩子們的手里搖搖晃晃地飛上藍天,每個孩子都有一個飛翔的夢想,每一個夢想所處的時代不同,飛翔的意義也不同。在他決心要將春天的旨意帶到這個人世間的時候還不到二十歲,他的夢想是拯救苦難的中國,拯救列強蹂躪下的國土,拯救在日寇鐵蹄下生活朝不保夕的窮苦人民。
“知子莫若母”,他的聰慧、機敏、倔強,“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秉性母親是知曉的。在他決心走出家門,走出這個村莊時候,她知道,誰也無法改變他的想法。她只能日夜為他提心吊膽,日夜盼望著他能快一點將日寇趕出掖縣,趕出膠東,趕出中國,盼得他平平安安回家來。
他走得決絕。她不知道他的決心有多大。他轉身離去時,再沒有回頭。甚至,她想把他上衣后背掖住的一個衣角扯平了都來不及。她們母子一場,她只是記住了他朝氣青春的臉龐和一個結實充滿力量的后背。他步履堅定,行色匆匆,義無反顧走向前方的那片藍天里。她在古樹下站了多長時間,沒有人知道。她日日來此,早晨與傍晚的霞光、雨雪都無法說得清楚。有時候,深夜時分,月光孤寒,霜落大地,她也要到古樹下站一站,看一看,聽一聽。她的等待何嘗不是一種尋找方式,她用心搜羅了他走過的每一條路,每一道溝坎,甚至能聽到他在戰場上與敵人搏斗嘶喊的聲音……她多想在某一個時刻,他遠遠地出現在通向村子的路口,向他招招手,再喊她一聲:娘!
他離開家,離開她的時間太久了。在他走后,她便重病纏身,不知道她被病痛折磨的思維神經是否還有記憶功能?是否還能記得他離開家多少年了?她應該是早已忘記了吧。唯一沒有忘記的就是帶著病中的殘軀日日去村東頭的古樹下等他回來,就像那一年,他離開家時,她送他到古樹下,她那時想把他摟在懷里,就像他是赤子之時日日摟在懷里一樣。她是否知道,那一刻的離別,便是她們母子一場于此世間最后的離別。她應該知道,那時的天下,日寇蹂躪,民不聊生,生死只在一瞬間。何況,他要去血與火的戰場上和日寇討一個天底下最大的公道,這是中國,是中國的領土,不允許任何外寇恣肆踐踏。
古槐樹不能勸說什么,它在她一次次地失望而歸的時候,總是沉默地勸說著自己,把想要給她說的話,默默地說給自己聽。只是,世人聽不到它說了什么,它確確實實地說了,一遍又一遍。你看那片片飄落的葉子,每一片都回到了泥土,這便是古槐樹想要說的話。夜晚的月亮聽到了,月亮降低了亮度,用閃耀的星星代替它心里的淚滴;白日的太陽聽到了,太陽隱于流云,用磅礴的雨、青絲的雨點綴它的心事,荒原里開出耀眼的花。
她雖思兒心切,終究沒有等得他的回來,在她病重期間,家書輾轉到了他的手中,書中是病母思兒,還有別人家未婚的女子待嫁。他回書:現在鬼子還沒有打出去;革命勝利以后再說。這是兩句話,第一句話是說給母親及家人的,第二句話是說給待嫁女子的。
我今天到村里來尋找古樹,并知道了他的時候,才知道,他自1938年3月8日夜參加掖縣玉皇頂抗日武裝起義,直到她過世也沒有回來。她去世的那一年,根據她孫媳的說辭推測,應該是在1941年以后了。1940年12月,他率領五旅兩個主力團攻打駐郭家店日寇據點,經過五個晝夜的鏖戰,取得了郭家店戰斗的勝利。戰后不久,時近年關,再苦難的日子,因為春節,家人也要聚一聚的。何況,他已離家多年,郭家店在他的村莊東面,距離只不過二十余公里,在家門口與日寇作戰,何況是已經取得了勝利。他的父親李萬緒看著思兒的病妻,下了決心要尋兒回家,讓病妻得以寬心,或許看到兒子后,妻子的病會好起來。
李萬緒決心去郭家店尋找兒子。他是在一個夜晚出的村,日寇占領下的古掖縣,作為抗日軍屬,是在日寇清殺范圍之內的。古槐樹在寒風里睜了睜昏睡的眼睛,或許是古槐樹一直是清醒的。它不能阻攔,作為神一樣的存在,它應該知道他尋找的結果,只是它無法言說。兒子沒有跟隨著李萬緒回來,他知道軍情的嚴峻,驅除日寇不是一場勝仗就能決定輸贏。戰后的工作更加忙碌,比如打掃戰場、準備軍事物資、救治傷病員、修筑工事、研究敵情、防備日寇的反撲等等,他是指揮官無法脫身。根據史料記載,一九四○年十二月,日軍首領大島帶領日偽軍二百多人在郭家店修筑據點。郭家店地處平度、招遠、萊西、掖縣四地的交通要道,是膠東半島的門戶地區,日寇企圖占據優勢地理位置,控制整個膠東半島。
年關夜,李萬緒披著漫天的寒雪回來了。站在午夜里的古槐樹依舊不說話,它早已知道了結果。李萬緒站在古槐樹下,回頭看一眼他行過的那條路,風吹著新落下的寒雪填補了那些深淺不一的腳印。我以一個父親的心思猜度李萬緒當時的心理,作為父親,作為丈夫,兩個至親的人,對于他們的生與死都是他日夜擔心的,他應該是哭過,這是一個人的正常生理與正常的情感反應。他的哭應該是壓抑的,無法嚎啕大哭,他需要承受來自世間所有的壓力,古槐樹應該知道李萬緒是否哭過,但古槐樹沒有告訴任何人。回家后,李萬緒沒有看妻子迎上來的熱切期盼的眼神,只是很輕淡地說:“他挺好的,只是太艱苦了,睡覺都是穿著破棉衣囫圇個兒著滾。”李萬緒看著妻子眼里剛升起來的亮光瞬時暗淡下去。
她沒有等得兒子的回來,她離去的時候,兒子正在與日寇周旋,繼續奔赴在一場場血與火的戰場上。她不知道,在她離開這世間不久,他回到了村子,不是為了吊唁,是帶著殘破的肉體回來的。他回到村子的時候,是在一個夜晚,被人用一副血跡斑斑的擔架抬回來的。那些血,甚至骨肉,都是她給予的。他離開這個村莊時,是陽歷的1938年3月8日,農歷的二月初七日,龍剛抬起頭,距離他的生日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他只有十九歲,就像人生里初春的樣子,他帶著春天的氣息離開村莊。那時,古槐樹應該已經感知到了春天的氣息,開始做著萌發的準備了。他離開這個世間的時候,是陽歷的1943年5月2日,陰歷的四月二十八日,年24歲,如同人生里春末夏初的樣子,正是燦爛、繁華、美好的時節。那時,古槐樹已經是枝葉繁茂了。他從這個村莊走出去時,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他回到這個村莊時,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神。
文字無力,不能確切還原他離開的那個時刻。何況,血與火的戰場,不是一個個蒼白文字的簡單堆積,只能簡述那個時刻與故事。一九四三年五月一日,南海軍分區司令部進駐平度縣古硯鎮山上村。五月二日,日偽軍李德元部率領大隊人馬呈包圍之勢向山上村開來。司令部撤離,他本應隨司令部一起轉移,但因警衛營阻擊東面的兩股敵人壓力較大,他安排好政治處的其他同志和司令部轉移后,馬上帶領通訊連的十幾個同志增援警衛營。面對裝備精良的敵人瘋狂進攻,警衛營和通訊連傷亡很大,最終寡不敵眾,他拉響了最后一顆手榴彈。
相信他的離去,已經把春天萌發的旨意傳遞出去。在他離開后,受他的影響,一個僅有七十余戶的村莊,與他年齡相仿的青年人悉數奔赴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戰場。全國解放后,經過清點,村里有三戶烈屬,其中一戶有兩名烈士。團職以上人員有七人,這些人的職位或者是榮光都是在生死無常的戰場上用熱血拼來的。
他犧牲后,時掖縣縣委、縣人民政府授予一塊木匾,上有鐫刻:民族之光。其時,日本鬼子還在掖縣有駐軍,經常下鄉掃蕩,家中不敢保存,怕給整個家族及村莊引來禍端,被其父李萬緒損毀。
他起初安葬在村莊南三里外的義地,三年后,也就是一九四六年,他的靈柩移于掖縣烈士陵園。同年二月,掖南縣委、縣政府將曹村李家以他的名字命名為鐵民村。他是何時將“李榮升”改為“李鐵民”的,家中無人知曉。國人的名字不但有傳承意義,還有承載一個家族興旺的意義。我大膽做一個猜測,其于本村私塾發蒙及至萊陽鄉試畢業,成績皆優異,“李榮升”這個名字是他的祖輩或父輩對他給予的厚望,以學業光耀門楣,這是一個家族的意義;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他走出小家投國之時,他所接受的教育,注定不能以小家為己任,外面有一個更加廣闊的天地,須要擔起一個國家的重任。“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想,這是他更改名字的動機,也是他以名明志的初心。
初心不敢忘懷,使命以熱血澆鑄,李鐵民似一塊堅硬的鐵于這世間,熠熠輝光映照后世。
李鐵民逝去后,早年家中保存的李鐵民求學期間的書本及其他遺物都被焚毀隨他而去,免得家人睹物思人,悲痛不已。李鐵民侄媳說早年家中還保管有一根他浴血殺敵的槍刺,近幾年也已無蹤。我囑她假如能夠找到一定要電話告知我,我來看一看,拍一張照片留存,并留了我的電話號碼。
從李鐵民侄子家告辭出來,李鐵民侄媳送我到大門外,與她家相鄰的南戶人家只剩了平口的山墻,山墻是碎石拼接壘成的,有的石塊呈現黃褐色。屋頂不知何時被拆除,一枝金銀花攀上了山墻,開著黃白色的花,有暗香撲鼻。院子里栽種了蔬菜,在夏日陽光下顯露出綠油油的生機。李鐵民侄媳告訴我說,“這是李鐵民的故居,也是李鐵民出生的地方。”我拍了照片,取了不同的角度,一張是山墻與金銀花搭配,一張是院子里的綠油油的蔬菜與院子的搭配。照片的主題有動有靜,無一例外的,山墻和院子為金銀花與蔬菜提供了堅強的支撐。夏日陽光明晃晃地覆蓋了面前的一切,呈現一幅祥和的畫面。
在我離開鐵民村時,我又刻意回到門扇上書寫了“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對聯的那條胡同。兩次到了鐵民村,第一次與它相遇是無意之舉,第二次是刻意為之。相信這世間的相遇,冥冥之中定有緣由。在知曉了李鐵民的故事后,我感覺這段詩詞竟然是李鐵民一生的真實寫照,是對我在鐵民村尋找過程的一個總結,這也是我刻意再回到這里的原因。
站在殘舊的門扇前,那些斑駁陸離的字體殘跡,似乎要告訴我一些什么。以我粗淺的理解,在李鐵民從曹村李家村出走投奔革命后,一直走在抗日救國的道路上,這條路是中國共產黨創立的,他是這條路上醒目的路標,值得后來人緊緊跟進。
責任編輯:李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