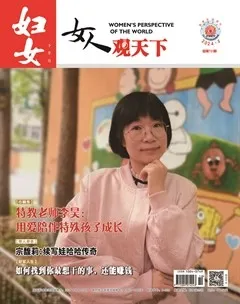夢中身是忘憂草
初夏時節,陽光燦爛,正是花開的季節,空氣中彌漫著令人陶醉的香氣。在千嬌百媚的群芳中,有一種毫不驚艷的花草自然樸素、清新雅致,它就是萱草,又名忘憂草。
張潮在《幽夢影》中寫道:“當為花中之萱草,毋為鳥中之杜鵑。”
杜鵑,又名子規鳥,相傳是蜀帝杜宇的冤魂所化,鳴聲凄切,勸人還鄉,因而又名“思歸”“催歸”。而萱草呢?《說文》中稱之為“忘憂草”,《本草綱目》中叫它“療愁”,據說人服食萱草可以忘憂。因為萱草的花朵里含有微毒的秋水仙堿,服食之后讓人感覺忘記憂愁,應該是一種中毒或成癮反應。但古人哪里管這許多,萱草在他們看來,就是能讓人忘卻塵世煩憂的神花。
春秋時代,衛國一位充當前鋒的士兵戰死沙場,他的妻子聽到死訊,傷心地吟詠一首詩,這就是《詩經·衛風·伯兮》。詩的最后四句說:“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諼,是忘記的意思。詩歌的意思是,哪里能找到忘憂的草啊,好讓我種在北堂的階下?一想起我的愛人啊,心如刀割繩絞一樣的悲痛啊!
三國曹魏時期思想家嵇康在《養生論》中說,萱草是會令人心情越來越好的。擁有好心情,是天下母親對孩子最基本的祝愿了。相傳陳勝幼時家境貧寒,身患疾病,全身浮腫,常常乞食度日,幸得一位好心的老媽媽贈送萱草,教他煮食。陳勝食用一段時間后,慢慢忘記憂愁,身體痊愈,并逐漸強壯起來。他和吳廣組織農民樹幟起義,成為歷史上有名的農民領袖。
萱草還有“母萱”之說。《幼學瓊林》中說:“父母俱在,稱為椿萱開茂;子孫發達,謂之蘭桂騰芳。”如果說康乃馨是西方的母親花,萱草應當是中國的母親花了。古時當游子要離家遠行時,就會先在北堂種一些萱草,希望母親因為照顧萱草而減輕對孩子的思念,忘卻煩憂。后來,母親住的屋子就被稱為“萱堂”,以萱草代表母愛。人們熟悉的唐代詩人孟郊的《游子吟》中的“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中的小草,也是指作為慈母與游子情感寄托的、母子連心的萱草。
關于萱草的故事和傳說,大多都令人傷悲。
斗轉星移,歲月流逝。昔日,去鄉村游玩時,在一戶農舍門口貼著對聯,上下聯早已忘記,只真切地記得,橫批是“椿萱并茂”。想來,這戶主人應是個知書達禮的孝子,希望父母健康長壽。除此之外,稱母親為“萱堂”的文章、書籍都極少看到了。
我們平時經常吃的“金針菜”,又叫“黃花菜”,就是萱草中最常見的品種。她綻開黃色的花兒,在花還是淡青色狀如金針的花骨朵的時候,就被摘下,用開水燙熟后摻上調料,涼拌來吃,脆香可口,這是比較講究的吃法。如果用金針菜、木耳炒的“木須肉”,才是最家常的吃法。忽然想起去親戚家,還試過用金針菜炒新鮮蘑菇,鮮美無比,這該是創新的吃法了。最恬淡清爽的吃法,是在漳州市郊的一家野菜館,用新鮮的金針菜做湯,清澈見影,味淡而鮮甜。還吃過一種用晾干的金針菜煨的紅燒肉,鄉下人的做法,美味無比。
《詩經·衛風》之后,歷代文人對萱草多有吟詠,曹植給它頌揚,夏侯湛為它作賦,李白、蘇東坡等大文豪都寫過萱草詩。李白題詠:“托陰當樹李,忘憂當樹萱。”宋代詩人蘇軾和陸游分別有“我非兒女萱”和“萱草石榴相續開,數枝晚筍破蒼苔”的詩句。最有名的應該還是蘇軾的“萱草雖微花,孤秀能自拔。亭亭亂葉中,一一芳心插。”
記得一個叫張謙德的古人,寫過一篇叫《瓶花譜》的小文,把六十八種植物分為上下九品,這六十八種之外的,便是不入流的俗物了,為文人雅士所不屑于賞玩的。位列一品的,有蘭、臘梅、水仙和牡丹等九種;二品有黃白山茶、松枝、茉莉等十種;三品有芍藥、蓮與丁香等六種;四品有秋海棠、薔薇、杏花等十一種,竟然把萱草排到五品。不知道張謙德依據什么來做這個排序的。若是按照這個排法,萱草應是個小家碧玉了,沒有高貴的身世,也沒有絕色的姿容。
如果僅論詩詞,最喜歡的,還是曾經讀過的一首:“幾許紅桃白李,一掊紫蕙青萱。夢中身是忘憂草,杯底人如解語花。”或許,只有陪伴三杯兩盞清茶淡酒,遁入夢中才可以解憂,忘卻許多紅塵俗事、情緣的侵擾和牽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