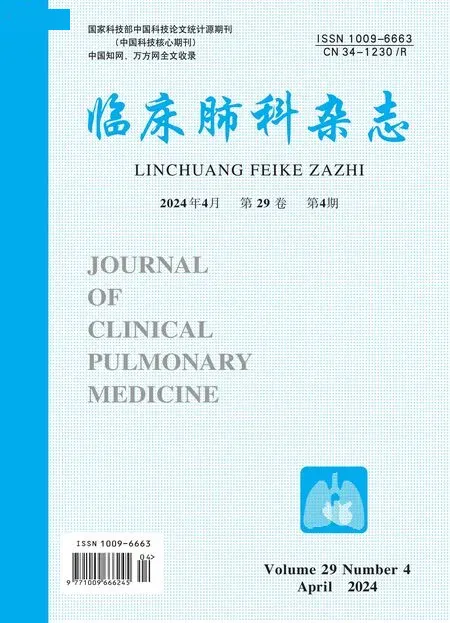新冠病毒感染相關性肌病發病機制的研究進展
吳明軍 崔小麗 薛慶亮
新冠病毒感染(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最初以肺部感染為主,典型癥狀為發熱、咳嗽和呼吸困難等,隨著病毒不斷發生變異,COVID-19誘發的肌病被越來越多的文獻報道,包含典型的皮肌炎及可導致多器官衰竭甚至死亡的橫紋肌溶解癥。因此,進一步明確COVID-19相關性肌病發生的病理生理機制可能對改善新冠患者預后具有重要臨床價值。
一、COVID-19相關性肌病發病
臨床研究顯示,COVID-19患者的肌痛發生率在19%~59%[1,2]。新冠死亡患者尸檢發現20%~60%存在炎癥性肌肉損害[3];另一項43例新冠死亡患者尸檢研究[3]發現26例發生炎癥性肌肉改變,以上臨床研究提示COVID-19會誘發肌病。Aschman T.等人[4]在人體肌肉標本中發現了SARS-CoV-2 RNA,進一步證實SARS-CoV-2可能會直接導致肌病。COVID-19綜合征是指部分COVID-19患者出現如氣喘、乏力、反應遲鈍等持續性癥狀,被稱為“長新冠”。臨床研究發現63%的患者在新冠治愈后出現持續肌無力和疲勞等癥狀[5];存在持續神經肌肉癥狀的COVID-19患者肌電圖呈現肌病性改變[3];重癥COVID-19患者出院19周后出現橫紋肌溶解癥[6]。由此推測長新冠中疲乏和肌無力可能與COVID-19相關性肌病有關。有研究指出長時間氣管插管及重癥監護室住院的COVID-19患者更易發生橫紋肌溶解[7]。臨床實驗室化驗多表現為肌酸激酶(Creatine kinase,CK)等肌酶標志物急性升高。一項薈萃分析指出,17%的COVID-19住院患者CK顯著升高,這部分患者病情進展至危重甚至死亡的風險高達49%,而CK正常者僅24%[8],因此CK升高可能是COVID-19患者發生肌病甚至預后不良的預測指標。
通過接種新冠疫苗形成人群免疫屏障,可明顯降低COVID-19導致的重癥及死亡發生率。目前,臨床研究證實SARS-CoV-2疫苗在人群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9,10],但接種SARS-CoV-2疫苗仍存在較高的肌病發生率[3,11-14]。Hannah等[3]在一項納入84例COVID-19相關肌病的回顧性研究中發現,疫苗接種后有1例發生局部肌炎,6例發生完全橫紋肌溶解;Daniel等[11]報道了6例在接種新冠疫苗后出現肌病的病例。研究發現,接種新冠疫苗后出現肌病的大部分個體中抗黑色素瘤分化相關基因5(antimelanoma differentiation-associated gene 5,MDA5)抗體陽性[15],提示新冠疫苗相關肌病可能與疫苗誘發機體表達MDA5抗體滴度升高有關。另有研究[16]指出新冠疫苗通過激活樹突狀細胞而誘導MDA5抗體表達水平升高,從而促使1型干擾素(interferon 1,IFN-1)生成增多,觸發下游炎癥介質的釋放,導致肌肉組織的炎性損害。Chan等[14]研究發現既往患皮肌炎的患者在接種新冠疫苗后病情加重,該研究指出疫苗編碼的刺突蛋白可通過促進“超級抗原”反應的發生而導致遺傳易感個體的全身免疫反應失調。García等[17]研究顯示接種新冠疫苗可能會誘導遺傳易感個體中病毒表面刺突蛋白(Spike protein,S蛋白)與多種組織抗原之間的免疫炎癥反應,從而導致新冠疫苗相關性肌病的發生。另有研究[10]認為肌內注射疫苗會刺激肌細胞釋放肌肉抗原,導致肌肉免疫性損傷,且RNA和DNA疫苗成分可能在肌肉中被吸收,從而誘發人體肌肉組織中自身免疫反應而損傷肌肉組織。
二、COVID-19相關性肌病發病機制
1.缺氧機制
COVID-19通過損傷肺組織而導致低氧血癥甚至呼吸衰竭,缺氧與通氣血流比例失調、死腔樣通氣及肺內分流等有關[18]。尸檢報告發現COVID-19會導致肺血管內皮損害、微血栓及新生毛細血管形成[19],這些病理生理改變都會導致缺氧。缺氧會增加活性氧的產生而上調氧化應激反應并通過誘導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的釋放、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NF-κB)活化而介導炎癥反應[20]。De Luna等[21]研究證實在缺氧的條件下,機體表達缺氧誘導因子1α(Hypoxia inducible factor,HIF-1α)水平升高,HIF-1α通過促使人肌肉組織中的維甲酸誘導基因 I(Retinoic acid-inducible gene I,RIG-I)過表達而激活IFN-I轉錄信號,促使大量炎癥介質產生而導致炎性肌損害。該研究[21]還發現肌炎患者肌肉組織中毛細血管減少,由此推測COVID-19發生長新冠后的肌無力的表現,可能與肌組織中毛細血管減少造成肌肉組織缺氧有關。研究[22]指出,蛋白質合成與降解之間的平衡是維持骨骼肌質量的重要決定因素,機體為適應COVID-19導致的缺氧環境,相關蛋白質的合成和降解會發生適應性調節,然而持續的低氧環境會破壞肌組織蛋白質代謝平衡,導致肌肉損傷。Mineo等[23]發現肺氣腫患者在肺減容手術后,由缺氧引發的肌損害明顯減輕。以上研究均表明COVID-19導致機體發生缺氧的病理生理改變會損害肌肉組織而導致肌病的發生。
2.免疫、炎癥反應機制
SARS-CoV-2入侵人體后,在遺傳易感個體中可通過分子模擬、表位擴散、旁位活化及B細胞活化等途徑誘導自身免疫、炎癥反應[24]。臨床研究發現,重癥COVID-19患者淋巴細胞顯著減少(85.7%),外周調節性T細胞水平降低、C-反應蛋白及白細胞介素-6(Interleukin 6,IL-6)水平升高(94.7%、89.5%),抗52kDa SSA/Ro(Ro-52)抗體(20%)、抗60kDa SSA/Ro(Ro-60)抗體(25%)和抗核抗體(50%)等表達顯著升高[25,26]。此外,有研究指出COVID-19引起自身免疫、炎癥反應的病理生理機制可能包括:炎癥小體的形成、氧化應激、非編碼RNA反應、細胞自噬、細胞NF-κB等炎性轉錄因子表達增加及細胞因子相關分泌表型的形成等[27]。研究發現,SARS-CoV-2通過激活適應性免疫應答過程而上調IL-1、IL-6、IL-10、IFN-g、單核細胞趨化蛋白-1(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1,MCP-1)和粒細胞-巨噬細胞集落刺激因子等炎癥因子的表達水平,引發機體炎癥風暴,并最終通過與肌細胞內補體相互作用導致肌病發生[28,29]。另有研究顯示,COVID-19相關的炎癥風暴可能與線粒體抗病毒信號蛋白(mitochondrial antiviral-signaling protein,MAVS)/RIG-I樣受體(RIG-I-like receptors,RLR)介導的信號通路異常有關,在內質網和線粒體膜上,SARS-CoV-2可誘導MAVS激活并結合RLR形成RLR-MAVS多功能蛋白質復合物,RLR-MAVS通過與干擾素基因刺激物STING及 TNFR相關因子3相互作用而激活TANK結合激酶1,進而通過激活轉錄因子干擾素調節因子3(Interferon regulatory factor 3,IRF3)和NF-κB而產生大量炎癥介質,在調控機體免疫、炎癥反應中發揮重要作用,使新冠患者肌肉組織發生免疫及炎性損害[27]。
3.MDA5抗體機制
MDA5是一種胞質病毒RNA傳感器,通過識別病毒RNA并觸發先天免疫反應而上調IFN-1、TNF-α,IL-1,IL-6,IL-18等炎癥細胞因子的表達,從而抑制病毒復制。研究指出,人體感染SARS-CoV-2后,體內顯著增加的MDA5通過與細胞質中的雙鏈 RNA 結合,并通過MAVS信號轉導通路激活干擾素的表達并誘導炎癥介質產生,損傷肌細胞[30,31]。一項274例COVID-19患者的臨床研究發現,MDA5抗體陽性率達48.2%[15]。MDA5抗體是一種與皮肌炎發生相關的肌炎特異性自身抗體,MDA5抗體性肌炎是皮肌炎的一種罕見亞型,其特征是明顯的潰瘍性紅斑性皮膚病變和快速進展型間質性肺病[11]。隨著新冠病毒不斷發生變異,SARS-CoV-2感染后MDA5抗體相關性皮肌炎的發病率逐漸升高[11]。多項研究均發現COVID-19和MDA5抗體性皮肌炎都可出現發熱、皮疹、間質性肺炎、乏力肌痛等癥狀[29,31],并存在廣泛的血管內皮功能障礙及血栓形成等病理生理改變[32]。此外,臨床研究發現,COVID-19的肺影像學與MDA5抗體性肌炎所致的間質性肺炎均表現為彌漫性磨玻璃樣改變[29]。有研究證實伴發MDA5抗體相關性皮肌炎的COVID-19患者具有三個與SARS-CoV-2蛋白序列高度一致的免疫原性線性表位[33],提示潛伏病毒感染和分子模擬可能在皮肌炎的病理生理機制中發揮重要作用。
4.分子模擬機制
研究顯示,“分子模擬”可能是另一種引起COVID-19相關性肌病的病理生理機制。SARS-CoV-2表面的結構蛋白S和結構蛋白E及非結構蛋白Orf7a、orf7a、orf8b、orf9、orf2b等,與人體肌肉組織中的結構蛋白存在同源區域[27]。Marino等人將病毒蛋白與人類分子伴侶進行比較,并推測主要包含熱休克蛋白的分子伴侶可能參與了SARS-CoV-2感染后的分子模擬現象[34]。SARS-CoV-2入侵會誘發機體產生針對病毒表面糖蛋白的抗體而造成肌肉組織免疫炎性損害[35]。此外,Lucchese等將SARS-CoV-2的氨基酸序列與免疫介導的多發性神經病相關的人類自身抗原進行了比較,結果顯示嵌入SARS-CoV-2免疫活性表位的肽與人類熱休克蛋白90及60存在相同序列,這兩種熱休克蛋白與吉蘭巴雷綜合癥及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顯著相關[36]。臨床研究發現存在嚴重并發癥的COVID-19患者,大部分患有高血壓和糖尿病,這兩種疾病都會引起血管內皮細胞的慢性炎性應激反應,血管內皮細胞通過胞內蛋白質修飾而異常地表達熱休克蛋白等質膜分子,促使肌肉組織細胞在病毒感染期間出現分子模擬現象而發生肌病[37]。以上研究均提示分子模擬在COVID-19相關性肌病中起重要作用。
5.血管緊張素轉換酶2機制
血管緊張素轉換酶2(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2,ACE2)是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系統(renin angiotensin aldosterone system,RAAS)的調節因子,在心肌細胞、肺泡上皮細胞、呼吸道黏膜上皮、腎臟、結腸粘膜及骨骼肌細胞中高度表達[38,39]。ACE2存在兩種形式:一種是位于細胞膜上的mACE2,由跨膜錨和細胞外結構域組成,是SARS-CoV-2病毒表面S蛋白的受體結合位點;另一種是循環中的可溶性sACE2[40]。目前研究發現,ACE2對SARS-CoV-2 具有高親和力,SARS-CoV-2通過其表面S蛋白與人體細胞上的ACE2受體結合形成病毒-ACE2復合物而引發感染,病毒-ACE2復合物進入宿主細胞后可直接感染骨骼肌細胞并激活骨骼肌細胞中的免疫細胞[41],導致直接性病毒性骨骼肌損傷和間接免疫介導的骨骼肌損傷。Beyerstedt 等[42]研究指出SARS-CoV-2可與血管緊張素Ⅱ(angiotensin Ⅱ,Ang Ⅱ)競爭ACE2受體而抑制ACE2活性,使RAAS失衡,從而收縮骨骼肌血管而導致肌肉組織慢性缺血缺氧,加重骨骼肌細胞氧化應激、炎癥反應及纖維化,最終導致肌病。Brevin等[43]研究通過抑制倉鼠體內法尼醇X受體(Farnesoid X receptor,FXR)而下調ACE2的表達,從而降低肺、胃腸道、膽道等組織細胞對SARS-CoV-2的易感性;此外該研究團隊在人肺和肝臟異位灌注實驗中用熊去氧膽酸和植物類固醇抑制FXR,ACE2的表達明顯下降[43]。在一項納入31例膽汁淤積性肝病合并COVID-19的隊列研究中發現,長期服用熊去氧膽酸的患者COVID-19的患病率、危重率及死亡率明顯低于陰性對照組[44],進一步證實ACE2是SARS-CoV-2引發感染的重要途徑。另一項研究通過下調SARS-CoV-2感染后ACE2的表達而誘導緩激肽產生增加,進而功能失衡的RAAS及激肽釋放酶-激肽系統促使COVID-19患者病情惡化[45]。因此,調節ACE2表達及其受體活性可能是具有較高遺傳耐藥屏障的多種SARS-CoV-2變異株的潛在治療靶點。
三、總結
綜上所述,COVID-19易合并肌肉組織損害,這些可能的機制還需要進一步在臨床實踐和基礎研究中證實和修正。此外,基于MDA5抗體、ACE2及其受體、免疫和炎癥反應等在新冠病毒引發的肌病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研發以抑制MDA5抗體、減輕機體免疫和炎癥反應、降低ACE2表達并阻斷ACE2受體與新冠病毒表面S蛋白結合等為靶點的COVID-19治療藥物,可能成為未來防治COVID-19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