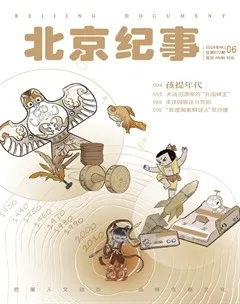京西的青蛇傳說與山區自然
趙靈毓 齊樂遙 鞠熙
在潭柘寺及周邊村莊,“大青爺替天行道,二青爺為民除災”是一副膾炙人口的經典對聯。對聯主人公——大青二青是潭柘寺的兩條靈蛇,它們和以之為核心而產生的一系列傳說故事在京西地區乃至更廣闊的范圍內口口相傳,至今已有三百七十多年的歷史。這個由有靈的動物生發的傳說,受到潭柘寺周邊水源、生境與人類生活的極大影響,并反向塑造和體現著當地山民的動物知識與自然觀。
潭柘寺的富水生境
北京是一座缺水的城市,富水生境因而顯得格外珍貴。潭柘寺即是北京西郊極其珍稀的一片富水生境。“潭柘”二字因寺旁有龍潭與柘樹千枝而得名,直白地點出了潭柘寺周邊生境的兩個突出特點:水源豐沛,山林茂密。
在山中諸多泉流之中,又以龍潭最為著名。龍潭衍生的大青二青傳說則將其推向了更高處:老龍讓宅呼嘯而去,留下龍子大青二青,京西百姓口中“大青爺、二青爺”的故事也就由此展開。對地方百姓而言,龍潭不只是一個名字,更代表一個清晰而美麗的傳說。
大青二青傳說的產生有賴于依山、富水、林茂的生境所提供的宜居環境。時至今日,潭柘寺周邊生境中仍分布著多種顏色、大小各異的蛇。蛇的存在意味著良好的風水、豐沛的水源、茂密的森林與優美的環境,蛇的習性及生活與人類的生產生活息息相關,還因其對水的代表性而與作物豐歉相勾連。因而,對當地山民來說,大青二青并不只是傳說中的“精怪”或有些怪異的動物,更是京西生態世界中有崗哨意味、有符號意義、有社群價值的標志性物種。
傳說發源的寺廟——潭柘寺,建寺于五朝帝都,到清代更是擁有了皇家寺廟的地位。這使得潭柘寺與其周邊山林得到保護,也因佛教圣地與天子授命的雙重加持而成為京郊著名的踏青之地。
在風景之外,大青二青傳說的流傳也得益于周邊百姓的體會與口傳。歷史上,潭柘寺依靠功德金買辦和信眾捐贈獲得了豐厚的廟產,解放前,潭柘寺廟產有“西到涿州,南到良鄉、盧溝橋,東到通州,北到懷柔、延慶,方圓幾百里的土地”。在這片土地上,農林業是最主要的產業。灌溉水以半山龍潭為源頭,由多股山泉不斷匯聚,繞潭柘寺而向下游輻射,供給山腳處的平原村、南辛房村等村落使用。人們的生產生活無時無刻不受到著潭柘寺水源以及潭柘寺文化的影響。這也使得與龍潭關系緊密的大青二青傳說在共享一股山泉的村落內代代流傳,因皇家寺廟背后政治命運的消長而被塑造,在人與生境的互動中被改變。
變遷中的靈蛇傳說
大青二青之于潭柘寺,堪稱“滄海桑田”的見證者。自明代至今,潭柘寺周邊生境不斷變化,大青二青傳說的內容也發生了多處改變,產生了多種不同的細節描述。這些變化,是時間變遷里傳說建構要素與人們自然觀念變動的真實寫照。
(一)“潭龍讓宅”說
在諸多大青二青傳說之中,傳遞脈絡最久、傳播范圍最廣的當數潭柘寺建寺時“潭龍讓宅”的版本,由明清至建國后記載從未間斷。在其中,潭柘寺、老龍、潭水與蛇被聯系起來。
“潭龍讓宅”說的最早記載見于明代,可查于《潭柘山岫云寺志》。到現代,傳說細節已趨于模糊,“龍歸來”“金云煥”的說法消失了,大青二青傳說最通行的版本變為:潭柘寺的寺基原本是青龍潭,是一處“海眼”,與東海相通,潭中有一老龍盤踞修煉。唐武則天時,華嚴禪師主持嘉福寺,天天到青龍潭講經布道。長此以往,老龍被感化,為了讓華嚴禪師在此開山建寺,“龍讓其宅”,呼嘯而去,從此水深千尺的青龍潭變成一片平地。老龍走后,留下兩條像蛇一樣的“龍子”,便是大青、二青。
縱使細節不同,在眾說紛紜的“潭龍讓宅”故事中,有三個共同的情節單元不曾改變:第一,潭龍于“海眼”聽法,受佛心感化;第二,華嚴講經,龍去潭平,雙鴟吻涌出;第三,留下龍子大青二青護佑潭柘寺。三個情節單元的保留,各有其現實意義。
龍潭為“海眼”,既表現了古人“龍生海中”的一般性自然知識,又反映了時人朝夕生存于潭柘寺富水生境這一特殊的地域空間,由感知和經驗而得出的特殊結論。傳說故事的發源與潭柘山九龍戲珠的風水和水源豐沛的自然環境息息相關,也與人們擇良處而居的觀念相切——在自然,尤其是天災面前,人的力量太過渺小。人們傳頌風水絕佳、有龍曾住,也是希望寺廟與潭水的靈性庇佑在此居住的百姓,能夠風調雨順,安居樂業。
在文本中,“華嚴講經而龍讓其宅”贊頌了華嚴禪師佛法之精妙,也為傳說增添了神秘色彩。前文有述,大青二青共同出身的“龍潭”已成寺基,現今山后仍存一“龍潭”供人們用水。在傳說文本里,山后“龍潭”是“海眼”的另一組成部分,借之為其增添靈性;現實中,當地山民則為大青二青各尋了一處棲身之地,進一步提升了賴以生存的“龍潭”之靈:“大青爺二青爺是兩條青龍,潭柘寺就有兩座龍潭,上龍潭就在寶珠峰后面,下龍潭在帝王樹下面。”
至于大青二青對潭柘寺的護佑,則有兩種說法。一種認為,潭柘寺正殿殿角的鴟吻就是大青二青的化身,可以保佑潭柘寺和香客所求平安順遂;另一種則相信大青二青作為靈蛇有所感應,無需實體也能賜福人間。這也進一步表明,大青二青傳說事實上嵌入了當地山民的日常生活,與周圍切實存在的事物和傳說頌揚的精神一道,構成了一種獨屬于地方社會的、理想的生態與社會秩序解釋。
(二)“護送達觀”
與“龍侍盧師”說
化身為龍子的大青二青,則體現了傳說與現實的交互。在明清文獻的記載中,大青二青不僅是具有神性的龍子和具有佛心的感化之物,更是兩條與山林環境密切結合的靈蛇:“小青……與人馴狎,時蟠宿僧榻,禱之能致雨。”早在明代,向大青二青求雨的片段就屢見于地方方志與文人游記。人們相信,龍的加持是潭柘寺靈驗的本源,蛇的存在是潭柘寺靈驗的體現,人們通過蛇溝通自然,祈求風調雨順。生活與信仰、動物與生態、人與自然在大青二青傳說中被統合起來。
此外,大青二青還有著自己的成長故事——“護送達觀朝峨眉”以及“龍侍盧師降下甘霖”。
據“龍侍盧師降下甘霖”所傳,“潭龍讓宅”后,大青二青留居潭柘寺。隋仁壽年間,盧師和尚從江南乘舟北上。他任舟飄蕩,結果小舟到秘魔崖的山腳下停住了,盧師和尚便在秘魔崖下修行,山也因而名為盧師山。不久,有大青、二青兩個童子前來投師,師徒三人面壁而禪三年。某年,久旱不雨,朝廷征召祈雨人,二徒自報限期喚雨,遂乘云氣而去,頃刻暴雨如注,人們方知二徒是龍。二龍回山后便委身于龍潭之中。為了紀念他們,每年春秋兩季,朝廷都要遣官來潭前祭祀青龍神,并在崖下塑了二童子侍師像。雖然又有一說法,認為“大青、二青是呼風喚雨,獨霸西山的兩條妖龍,它們致使非旱即澇,黎民涂炭,盧師和尚則從江南來此,與妖龍斗法將其降服”,但大青二青與降水、與龍的聯系和神性依然沒有改變。
“護送達觀朝峨眉”的版本則來自《送龍子歸潭柘文》,其作者達觀和尚曾是明代的潭柘寺住持。文中講,達觀和尚要前去峨嵋山拜訪普賢大士,但擔心此去水路眾多,夷險莫測,于是請求潭柘寺的老龍保護。老龍為“佛子”,善心悲憫,于是派大青二青兩個“龍子”前去保護達觀,歷經三年平安歸來。后世所傳“護送達觀”說幾無出入,共同強調大青二青為龍子,有善性,化而為蛇,身形能易,不僅護送達觀朝拜峨眉山,逢兇化吉,還能興云致雨,潤澤農產。這則傳說,讓大青二青不僅侍奉高僧,也走入民間,成為可以庇佑百姓的生靈。
至此,老龍之來去、潭柘寺之建成、大青二青之出身與成長都有了著落。可是,大青二青的“歸處”又在何處呢?對此,當地山民補充了“乾隆皇帝駕臨,靈蛇討封不成反被煮粥”的全新情節單元。
(三)“供眾舍粥”說
在潭柘寺周邊,幾乎每一位老人都認可,大青二青中有一蛇的歸處是“被煮粥”:“潭柘寺原來有兩條大蛇,一個叫大青爺,一個叫二青爺。皇上來潭柘寺,大青爺為了上皇帝跟前顯圣一下,好讓皇上給他起個封號,就在大殿的兩邊廂房上頭,從東到西地跑。吊在空中,終于當著皇上面了,結果皇上一看見說:‘這么一個大蛇。皇上沒想到這是潭柘寺的大青,只說是一條大菜蛇。大青爺一聽,壞了,把它說成是菜蛇了,就回潭柘寺來了。它挺郁悶的,說‘這還活了個什么勁兒,所以就順著流杯亭那小水溝流到大銅鍋里面去了。大銅鍋是煮粥的,和尚熬了滿滿一大鍋粥,結果早晨喝粥的時候說‘今天這粥可跟每天的粥不一樣,放了什么這么香?一大鍋粥都給搶著喝了。最后鍋底沉下來,露出一大塊白骨頭,和尚才知道是把大青爺給煮了吃了。”后來,“蛇粥”誤傳為“舍粥”,最終演變成了每年臘八節潭柘寺施粥的傳統,在饑荒時節給地方百姓以極大幫助。
一條靈蛇成粥已是定局,另一條靈蛇的去處則眾說紛紜:有說被一個方丈領去家里,不久后就自行離開了;有說獻身成雨,造福百姓了;更常見的說法是靈蛇跑到了潭柘寺在城里的下院翊教寺,后來消失了……無論哪種傳說,其中不變的特點是:大青二青具有與人親善的物性與成云致雨的能力,不僅是自然界的靈蛇與傳說中的龍子,更參與進上至皇家下及百姓的政治與社會生活,傳說也因此成為了一種表達人與自然關系,體現人們對蛇和更廣泛的動物知識的特殊紐帶。
傳說中的自然觀與生態啟示
在大青二青深度參與生產,影響地方自然與人文秩序的京西社會,傳說早已不是停留在口傳與故紙堆中被棄置的話語,而是切實走入了人們的生活,不斷重塑人們的集體記憶,成為了一種流傳的、生動的動物與生態知識。
在潭柘寺山民眼中,大青二青傳說還有更多特殊之處:對靈蛇大青二青的恭敬祭拜,可以保佑生活順利;這種靈性延展到其他山蛇身上,使得“對普通的蛇保持尊重”成為不可忽視的地方傳統。潭柘寺方丈將傳統總結為“護生的慈悲”,民間傳說則稱之為“佛心感應獸心靈”:一方面,蛇會隨著時間的推移,習得更多能力,具有更強的靈性;另一方面,人對蛇的善意可以被蛇感知,從而在去機心的善性中被感化,得道而成仙。同時,蛇的靈性使其可與人互動:當地百姓如果害怕蛇,只要在遇到蛇時說一聲“我害怕,你快走”或“你嚇著孩子了”,蛇就會聽懂,“一轉眼就自己不見了”;當人做了壞事,也可能被蛇感知到并傳遞給自然,讓人類被自然“懲罰”。由此可見,在潭柘寺周邊,人與蛇的關系并未局限于寺廟影響而產生的宗教意涵或皇權色彩之中,而是因為山民與蛇的聯系而世俗化。在山民眼中,無論是靈是肉,蛇都是存在與山林之中的聯結者和溝通者,參與社會秩序的內部建構,在人類與自然間搭建雙向溝通的橋梁。
后來,隨著生態與氣候變化,潭柘寺的山泉水幾近干涸,靈蛇漸漸不再出沒。與此同時,皇權不再作為社會的最高權威,“受命于天子”的大青二青失去了以往的地位。加之近代以來,人們不再深度依賴和相信動物的能力與生境,而是受人類中心主義影響,主張對自然“祛魅”,用自身力量控制乃至改變自然。這些變化在一些文獻中明顯得見。梅蘭芳曾寫下潭柘寺游記,在住持向他展示二青爺“現身講法”的照片時暗諷:“拿它來蒙騙一般善男信女,當然是很有功效的。”到了現代,隨著門頭溝煤礦資源的開發和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在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生靈逐漸消亡,大青二青傳說失去了其所植根的土壤,神圣性和生態作用大大消減,只能作為一段故事傳說而存在了。
近年來,隨著門頭溝“生態涵養發展區”的職能定位對生態屏障和水源保養的強調,地下水水位開始慢慢上升。加之地方政府以生態補水等多種治理手段齊下,力求以“龍潭”為首的泉水復涌,潭柘寺周邊的生境有望恢復。隨著“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觀念愈發深入人心,人們比以往更加意識到,人類并不是凌駕于自然的主宰,而是與生靈共存于自然之中的生存者和互動者。動物與人類同在統一的社會秩序之內,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才是可持續發展的基石,在潭柘寺,在更廣闊的永定河流域乃至整個自然世界都是如此。
從大青二青傳說為代表的動物敘事中不難發現,古人將人、動物與生態納為一體,共同生成了特殊的故事與地方性知識,從而將人類社會和自然世界聯系起來,從京西的山林看到廣闊的天下和宇宙。而在當今,在人類中心主義愈發受到挑戰的時代,我們更應當懷抱一種“歸田園”的心境與生境。或許有一天,神京右臂的富水生境可以重新成為人類乃至地球命運共同體的縮影,其中亙古而彌新的人與生靈與水、社會與自然的和諧秩序與共生觀念會得到新的運用,古老的傳說也能產生新的啟示。經由大青二青傳說,我們至少可以看到,以潭柘寺為代表的京西地區不僅是有人類建筑與文化的皇家寺廟與田園,更是一個萬物有靈的生態—文化綜合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