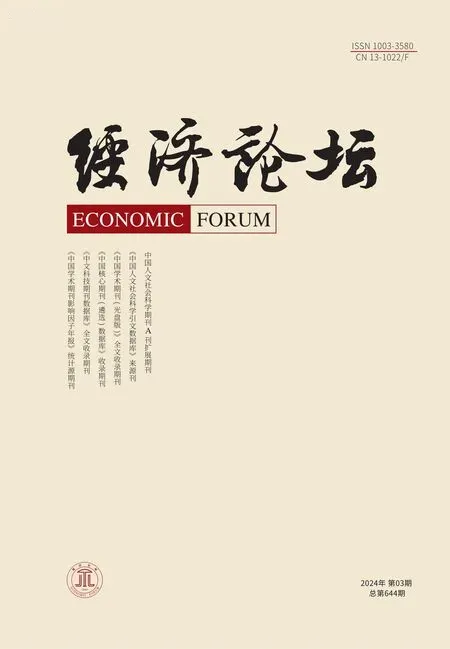馬克思對私有財產的科學批判
——基于《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研究
余同,郭蕙青
(1.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 102488;2.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 100871)
《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下文簡稱《手稿》)自20 世紀30 年代全文發表以來,一直備受國內外研究者的青睞,但同時它也是馬克思所有文獻中爭議性最大的文獻之一。學界圍繞《手稿》形成了豐富的理論成果,但目前對《手稿》中很多的重要理論問題并未達成共識,比如:《手稿》的核心思想、《手稿》中歷史觀的性質、私有財產和異化勞動的關系、馬克思與人道主義的關系、《手稿》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地位,等等。這些理論問題上的爭議,既向后來的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形成了廣闊的探索空間。本文從《手稿》的中心主題——私有財產入手,揭示馬克思在《手稿》中對私有財產的科學批判,以期更加準確地理解《手稿》的思想精髓。
一、《手稿》的中心主題是私有財產
《手稿》的中心主題是什么?我國學者對這個問題的回答莫衷一是。趙家祥(2011)認為異化勞動理論是《手稿》的中心主題,他指出馬克思雖然在《手稿》中沒有明確提出生產關系概念,“但已在這一著作中的核心思想——異化勞動理論中蘊含了生產關系的內容及其本質的思想”。[1]汪成忠(1994)認為:“私有財產問題,即私有財產的本質、私有財產的起源、私有財產的消亡等方面問題,是貫穿于《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之中的紅線,在《手稿》中居于中心地位,其他問題都與這個問題有關。”[2]楊適(1982)則認為:“馬克思在第三個手稿中關于共產主義的論述,是全書的中心部分。”[3]
通過對《手稿》文本內容的梳理,以及把《手稿》放入馬克思一生的思想歷程中來看,本文認為私有財產才是《手稿》的主題。
首先,異化勞動問題以及共產主義思想的確是《手稿》中的重要理論問題,但是異化勞動理論是馬克思唯物史觀還未成熟時,用于分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即私有財產關系的理論工具,而共產主義思想則是他對私有財產進行批判之后,對私有財產揚棄得出的必然結果。
其次,從《手稿》的文本結構來看,私有財產是三個筆記的中心問題。筆記本I主要闡述了兩個問題。前面三個部分,馬克思借用國民經濟學的語言,揭示了工資、資本的利潤和地租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實質,進而揭示了這三種收入背后所代表的工人、資本家和地主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所處的地位,揭露了工人在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被資本家和地主剝削的事實,這是私有財產關系在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的具體內容和表現形式。第四部分主要探究了私有財產起源的問題,即闡明了私有財產和異化勞動之間的關系。馬克思從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勞動異化的事實出發,在批判繼承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異化思想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異化勞動理論,系統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下工人所處的非人的狀態,揭示了私有財產的起源,即異化勞動導致私有財產的發生。因此,我們可以得知,筆記本Ⅰ的主要內容為私有財產在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的具體表現形式以及私有財產的起源。筆記本Ⅱ雖然只殘余4頁,但是通過整個文本的結構分析可以得知,筆記本Ⅱ的主要內容闡述了私有財產的關系,即資本、勞動以及資本和勞動的關系,闡明了私有財產的運動即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對立運動。筆記本Ⅲ主要闡明了私有財產的揚棄,即私有財產和共產主義之間的關系。通過分析《手稿》的主要內容,我們可以得知,私有財產是《手稿》中心主題,馬克思在文中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闡述清楚私有財產的發生、發展和滅亡的規律。
最后,從馬克思思想發展歷程和一生的理論訴求來看,私有財產一直是馬克思研究的中心主題。自《萊茵報》時期發生“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4]588的疑惑后,馬克思就開始致力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其著作《資本論》更是他長達40多年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思想結晶”。恩格斯在《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對馬克思的一生及其貢獻進行了總括性的說明:“因為馬克思首先是一個革命家。他畢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參加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所建立的國家設施的事業,參加現代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正是他第一次使現代無產階級意識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識到自身解放的條件。”[5]從恩格斯晚年對馬克思一生的總結可以得知,馬克思畢生的使命都是致力于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秘密,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實現無產階級及全人類的解放。進而,可以印證私有財產始終都是馬克思研究的中心主題。
二、《手稿》對私有財產內涵的科學界定
目前學界對私有財產概念的理解有兩個維度:一是從法權角度來理解,即認為私有財產指的是法律所規定的對某物的所有權;二是從經濟關系角度來理解私有財產,即認為私有財產指的是私有財產關系,也就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馬克思在《手稿》中所指的私有財產就是私有財產關系,而不僅僅是一個所有權概念。正是馬克思對私有財產的研究超越了法權范圍,才使得馬克思得以揭露私有財產的本質及其運動規律。
馬克思對私有財產的探究經歷了一個從哲學進入到經濟學領域的過程,即從針對“副本”的批判轉向針對“原本”的批判。馬克思一生致力于探究人類解放的現實途徑,揭示私有財產發生、發展和滅亡的規律,但是在其思想發展的不同階段,他使用的理論武器是不同的。在大學時期,馬克思以自我意識為哲學武器,對專制的封建制度進行了猛烈的批判。《萊茵報》時期,在對社會現實進行考察和官方以及其他刊物進行論戰的時候,馬克思第一次發生“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4]588。馬克思發現黑格爾所標榜的國家和法,在現實中并非理性的代表,相反卻成為有產者階級的工具。所謂的理性國家和法與現實的人民利益發生了極大沖突,這使得馬克思對原有的信仰發生了質疑和動搖。馬克思轉而對黑格爾的法哲學進行批判。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發現,“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是家庭和市民社會決定國家,“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找。”[4]591此時馬克思對市民社會的理解還是籠統的、抽象的,但是他已經認識到社會關系和物質利益在人類社會生活中具有決定性作用。隨后在赫斯和恩格斯思想的影響和啟發下,馬克思從市民社會中抽象出私有財產關系這一核心要點,借助異化勞動理論對私有財產關系進行了深刻批判,最終沿著政治經濟學的道路進一步探索,深化了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剖析。馬克思在《手稿》中對私有財產關系的批判正是他思想發展歷程的關鍵一步。
從筆記本Ⅰ、筆記本Ⅱ和筆記本Ⅲ的內容來看,馬克思在文中所指的私有財產就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筆記本Ⅰ中,馬克思首先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異化的現實,他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也是從這里開始的。從馬克思的異化勞動理論中可以得知,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切關系都異化了,而普遍的勞動異化在工人和勞動產品的關系之外生產出一個與勞動無關卻能夠無償獲得勞動產品的資本家與勞動產品之間的關系。馬克思在筆記本Ⅱ中直接指出私有財產關系包含三方面的關系:資本的關系、勞動的關系以及勞動和資本的關系。同時資本和勞動作為私有財產的內部矛盾,相互之間的矛盾對立一旦發展到極端,必然導致私有財產的滅亡。馬克思在《手稿》的筆記本Ⅲ中描述無產和有產的對立的時候,明確指出,有產和無產的對立在“沒有私有財產”的前進運動時,比如在古羅馬、土耳其等,也能以“最初的形式”表現出來。只有到資本主義社會時期,有產和無產之間的對立直接地表現為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對立。可見,馬克思在文中所闡明的私有財產概念指的就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
三、《手稿》對私有財產和異化勞動關系的初步闡釋
(一)馬克思對“異化”概念的唯物主義改造
“異化”一詞,經過德國古典哲學時期的發展后,才成為專門的哲學范疇。起初“異化”是指權力轉讓、關系疏遠和精神錯亂等,后來經過德國古典哲學時期的發展之后,“異化”一詞被用來描述主客體之間的關系,即主體通過自身的活動產生的客體反過來作為一種異己的力量來反對或支配主體的發展。黑格爾從客觀唯心主義角度出發,認為世界的本原是絕對精神,而整個人類社會以及自然不過是絕對精神異化的產物,而后絕對精神經過一段發展之后,又要揚棄異化,回到絕對精神本身。黑格爾利用這套先驗本質異化的邏輯說明人類社會歷史發展,揭示人類社會歷史發展是一個由低級到高級的歷史過程。在黑格爾的邏輯體系中,異化是“在絕對觀念和現實自然界之間架起的一座橋”[6]。
費爾巴哈從人本主義的唯物主義出發,對黑格爾的唯心主義理論體系進行了猛烈批判,翻轉了被黑格爾顛倒的思維和存在的關系,進而系統地闡發了人本主義的唯物主義思想,同時也形成了人本主義的異化思想。費爾巴哈的異化主體是人,人創造了上帝,但是上帝反過來支配和控制著人的發展,即“為了使上帝富有,人就必須赤貧;為了使上帝成為一切,人就成了無。”[7]馬克思在1845 年春寫作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指出,費爾巴哈從唯物主義出發,將整個世界劃分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并且認為世俗世界是宗教世界的基礎,這是費爾巴哈對宗教批判做出的重大貢獻,但是費爾巴哈對宗教的批判止步于此。其根源在于,費爾巴哈雖然提出了“現實的人”的概念,但是費爾巴哈所認為的“現實的人”仍然是抽象的人,并且將人的本質抽象地理解為建立在兩性差別基礎上的愛和友情,同時否認人的實踐活動的客觀性,而只承認思維的活動是人的實踐活動,而對于真正的實踐活動則“只是從它的卑污的猶太人的表現形式去理解和確定”[8]499。因此,費爾巴哈無法進一步從世俗世界的現實矛盾中探討宗教產生的根源。
馬克思對“異化”概念進行了唯物主義改造,將哲學與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結合起來,將異化理解為對現實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相互對立關系,并從資本主義社會異化現象出發,系統地闡釋了科學的異化勞動理論。異化勞動理論的提出表明馬克思沿著唯物史觀的方向又推進了一大步。馬克思從資本主義社會勞動異化的經驗事實出發,首先揭示了最表面現象的異化,即物的異化和勞動者勞動產品的異化;其次,馬克思通過對經濟事實的不斷考察和研究,進一步挖掘到物的異化的原因在于勞動者勞動過程異化以及人的自由自覺的類本質異化;最后,馬克思進一步揭示了物的異化的根源是人和人的關系的異化。由此,我們可以得知,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勞動異化現象的剖析,并沒有停留在現象層面,而是從經濟事實出發,進一步探究人與物異化的根源,科學地闡釋了資本主義社會勞動異化的現象及其實質。
(二)異化勞動理論對私有財產批判的理論價值
馬克思在寫作《手稿》時期,唯物史觀并沒有成熟,但是馬克思借助異化勞動理論,一定程度上深化了馬克思沿著勞動發展史來剖析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路徑探索,促進了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成熟,推動了馬克思自身理論的發展,實現了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找到了工人解放的現實途徑。
異化勞動的四個規定科學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階級對立的實質,揭露了工人所處的非人的狀態。馬克思通過觀察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事實,系統地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勞動異化的事實: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者與勞動產品、勞動過程、類本質相異化,而這些最終必然導致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異化,因為人與自身的關系只有通過他與他人的關系才能夠得到確證和實現。如果勞動者的勞動產品不歸自身所有,那么歸誰所有呢?既不歸大自然所有,也不歸神所有,而是歸人所有,歸與勞動者、與工人階級相對立的那個階級的人所有,“總之,通過異化的、外化的勞動,工人生產出一個同勞動疏遠的、站在勞動之外的人對這個勞動的關系。工人對勞動的關系,生產出資本家——或者不管人們給勞動的主宰起個什么別的名字——對這個勞動的關系。”[8]166馬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勞動異化實質的描述,揭露了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對立實質,同時揭露了工人階級所處的非人狀態,即“勞動為富人生產了奇跡般的東西,但是為工人生產了赤貧。勞動生產了宮殿,但是給工人生產了棚舍。勞動生產了美,但是使工人變成畸形。勞動用機器代替了手工勞動,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蠻的勞動,并使另一部分工人變成機器。勞動生產了智慧,但是給工人生產了愚鈍和癡呆。”[8]158-159
馬克思對私有財產和異化勞動關系的初步闡釋,推動了相關理論的發展。他在《手稿》中明確指出,通過異化勞動理論對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關系的揭示,使得“至今沒有解決的各種矛盾立刻得到闡明”[8]166。這一方面揭示了國民經濟學對勞動和私有財產關系理解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從異化勞動與私有財產的關系中初步得出人類只有通過工人解放這種政治形式才能從私有財產和奴役制中解放出來的結論。進一步,馬克思指出要揭示清楚勞動異化的根源,就要把私有財產起源問題變為外化勞動對人類發展進程的問題。
四、《手稿》對私有財產主體本質及其運動規律的揭示
馬克思對私有財產的主體本質及其運動規律進行了唯物主義的闡釋。
(一)私有財產的主體本質是勞動
對私有財產主體本質的探討,是馬克思完成對私有財產起源的探究之后對自身提出的任務。馬克思在分析完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概念之后,雖然認為我們可以借助這兩個重要概念對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的買賣、競爭、壟斷、資本等問題進行進一步研究,但是馬克思并沒有這樣做。因為他認識到要“從私有財產對真正人的和社會的財產的關系來規定作為異化勞動的結果的私有財產的普遍本質。”[8]167所以,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現象進行深刻研究之前,還必須對兩個基礎問題進行研究,其中一個就是私有財產的本質問題。
馬克思在《手稿》中明確指出私有財產的主體本質就是勞動。從私有財產關系角度來理解,私有財產關系主要包含勞動的關系、資本的關系以及兩者相互之間的關系。盡管在私有財產關系下,勞動表現為資本的奴仆,勞動被資本所奴役,但實際情況是,資本只是私有財產關系的客體存在形式,同時資本本身是人的勞動的產物。之所以會發生這樣的顛倒,是因為在私有財產關系下,人的勞動被異化了。但是不可否認,異化勞動在導致勞動者和勞動產品、勞動過程、自身的類本質以及人和人之間關系的異化的同時,也極大地推動了人類社會的發展。勞動過程既是財富積累的過程,也是對工人階級剝削的過程。人和自身對象——自然界的關系,以及人和人之間的關系都是通過勞動來建立的。如果沒有勞動的過程,也就無所謂人化自然的存在,無所謂人類社會的存在。另外,馬克思在文本中明確指出,勞動創造了人,即“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的過程”[8]196。因此,勞動是私有財產的主體本質。
(二)私有財產的確立過程表現為動產和不動產的斗爭
馬克思在《手稿》的筆記本Ⅰ中,根據國民經濟學的語言和規律,通過對古典政治經濟學對三種收入(工資、資本的利潤和地租)的闡述,揭示了工人、資本家和地主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生存狀況;同時也通過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研究,批判了古典經濟學家理論的階級局限性和歷史局限性,即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不是從歷史的角度、現實的角度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剖析,而是把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看成是一種永恒的關系。但是,在馬克思看來,私有財產關系和奴隸社會生產關系、封建社會生產關系一樣,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因此,私有財產關系也必然會經歷發生、發展和滅亡的過程。私有財產的確立過程即表現為動產和不動產的斗爭。
資本主義社會代替封建社會的過程具體地體現在動產和不動產的斗爭中。一開始作為不動產的土地是占社會統治地位的社會財富形式,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社會總的生產出現了剩余,于是在小范圍內出現了簡單的物物交換,再到以一般等價物為媒介的交換,最后到以貨幣為媒介的交換。而在商品交換不斷擴大的過程中,不動產開始從一種萌芽狀態不斷發展成為具有具體形態的資本,而這個轉變的契機是地租的形成。隨著土地轉變為商品的一種形式,不動產和動產的斗爭開始“搬到臺面上來了”。一開始不動產和動產的斗爭的勝利者總是不動產,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原有的封建主義生產關系已經不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于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逐漸取代了封建主義生產關系,動產和不動產之間的斗爭的形式開始發展變化了,作為“現代工業之子”的動產開始在斗爭的過程中不斷占上風。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取得統治地位之前,代表著不動產的工業生產本身還帶有自身對立面的封建主義的性質,因此,此時的“勞動還具有表面上的社會意義,現實的共同體的意義,還沒有達到對自己的內容漠不關心和完全自為地存在的地步,就是說,還沒有從其他一切存在中抽象出來,從而也還沒有成為獲得自由的資本。”[8]173隨著生產力的不斷向前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取得了獨占的統治地位,勞動也變成了“獲得自由的、本身自為地構成的工業和獲得自由的資本”[8]173,最終動產戰勝了不動產。勝利的一方從一開始的封建地主階級轉變為資產階級,同時土地所有者也變成了“極其普通的、平庸的資本家”[8]172。
(三)私有財產的發展動力是勞動和資本的辯證運動
按照馬克思的辯證法來理解,任何主體發展都是由其內部矛盾運動推動其自身向前發展的,私有財產這個主體也不例外,其內部矛盾就是勞動和資本的矛盾。正是勞動與資本的辯證運動,才使得私有財產關系不斷向前發展。
馬克思指出,有產和無產的對立,只有將其理解為資本和勞動的對立,才是從能動方面理解有產和無產的對立。有產和無產的對立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前的社會形態中就已經存在了,比如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時期,只不過這時有產者和無產者的對立指的是富人和窮人的對立,沒有涉及生產資料的問題。而私有財產關系的建立前提是資本的原始積累,即勞動者和生產資料被迫分離的歷史過程。
在筆記本Ⅲ的最后部分,馬克思對勞動和資本的運動關系進行了初步闡釋。馬克思指出:“私有財產的關系是勞動、資本以及二者的關系。”[8]177勞動、資本以及二者的關系經歷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辯證發展歷程。而這部分內容實質上和馬克思成熟時期闡明的政治經濟學中的有關資本原始積累的原理和歷史運動是一致的。
首先是勞動和資本的直接或間接的統一。馬克思在文中指出,“起初,資本和勞動還是統一的”[8]177。勞動和資本的關系,在一開始的時候,由于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的關系,要么是勞動者同樣作為生產資料與生產資料結合著,要么是有部分的勞動者擁有生產資料,而且在生產力十分低下的時期,生產的目的是滿足自身生存的需要,而沒有產品的剩余,因此,勞動和資本在這個時期是統一的。
其次是勞動和資本的對立。隨著社會生產力以及分工的不斷發展,勞動者生產的產品開始有了剩余,勞動和資本之間的分離也就逐漸開始了。剩余產品的出現,使得人和人之間商品交換關系逐漸普遍化,人們在交換的過程中,一方面能夠極大地滿足自身的消費需求,另一方面也讓更多的人看到這個過程中財富積累的便捷。而因為勞動是財富積累的源泉的同時,又是對人的體力和腦力的耗費,尤其是在私有制社會中,人的體力和腦力勞動的消耗并不是在自身生理的限度范圍內,而是最大限度地對人的壓榨。勞動創造財富的認識以及對勞動消極方面的回避,使得在經濟領域占統治地位的人們開始不斷地加強對人的勞動的剝削。為了獲得更多的利潤,這些土地貴族以及新興的資產階級開始了殘酷地對人的生產資料以及勞動力剝削的過程,也即資本的原始積累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勞動者自由的一無所有,除了出賣屬于自身的勞動力產品之外,他已經沒有任何其他的謀求自身以及后代生存的條件了。可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只是改變了以往剝削的形式,剝削的本質并沒有發生變化,而且對人的剝削更加深重了,整個社會日益分化為兩個階級的對立,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因此,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勞動和資本之間的對立沖突更加激烈也更加普遍化了。
但是馬克思并沒有完全否定勞動和資本的對立,他一方面認為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另一方面也認為勞動和資本的對立,也可以理解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為無產階級及人類解放創造了一切物質前提和力量源泉。
最后是勞動和資本各自和自身的對立,也即勞動和資本的重新統一:“資本=積累的勞動=勞動”[8]177。馬克思明確指出,“勞動和資本的這種對立一達到極端,就必然是整個關系的頂點、最高階段和滅亡。”[8]172勞動和資本的矛盾,在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可以說達到了空前的狀態。無論是無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實質上都成為資本的附屬物,不同的是無產階級在這個關系中充當了被剝削者的角色,而資本家則充當了剝削者的角色。隨著勞動和資本的矛盾尖銳化,必然引起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統治,代之以適應人類自由發展的共產主義制度,實現人的個性的全面的解放。
(四)私有財產的必然歸宿是共產主義
在《手稿》中,馬克思對國民經濟學將私有財產關系當作永恒的社會關系的觀點進行了批判,借助異化勞動理論,“首次從哲學上闡明了消滅異化勞動、揚棄私有財產進而把人失去的人的關系、人的世界還給人自身”[9],私有財產的運動將使私有財產最終揚棄在共產主義社會中。
一方面,馬克思借助異化勞動理論,揭露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內部的對抗,指出要使社會和無產階級從私有財產、從奴役制中解放出來,只能通過工人解放這種政治形式,因為“工人的解放還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8]167另一方面,馬克思從費爾巴哈人本主義哲學出發,借助黑格爾先驗本質異化邏輯,把共產主義社會當作人道主義的最高階段,把人類社會歷史歸結為“人的存在與人的本質的原始統一——人的存在與人的本質的對立——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質重新統一的否定之否定過程”[10],并指出“共產主義是對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并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會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完全的復歸,是自覺實現并在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范圍內實現的復歸。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于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于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8]185由此可知,共產主義社會必然是私有財產揚棄的產物。
私有財產運動為私有財產的揚棄創造積極的現實條件。馬克思總結道:“不難看到,整個革命運動必然在私有財產的運動中,即在經濟的運動中,為自己既找到經驗的基礎,也找到理論的基礎。”[8]186馬克思又進一步指出,“通過私有財產及其富有和貧困——或物質的和精神的富有和貧困——的運動,正在生產的社會發現這種形成所需的全部材料;同樣,已經生成的社會創造著具有人的本質的這種全部豐富性的人,創造著具有豐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覺的人作為這個社會的恒久的現實。”[8]192由此可知,私有財產運動從斗爭經驗、理論基礎、物質資料等方面為私有財產的揚棄創造了條件。
通過對私有財產的內外矛盾運動的論述,我們可以得知,在私有財產運動過程中:其一,在土地所有者和資本家斗爭的過程中,無產階級一方面可以積累斗爭經驗,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分析他們的斗爭過程更加明晰土地所有者和資本家的最終目的和立場,從而揭示其本真面目。而在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斗爭的過程中,一方面隨著雙方矛盾對立的尖銳化,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頻次不斷提高、斗爭范圍不斷擴大、斗爭程度不斷加深,使得無產階級的政治覺悟逐漸由自發轉向自為;另一方面無產階級在與資產階級斗爭的過程中,組織性和戰斗性不斷加強,在政治、文化和科學領域的斗爭經驗與技能也不斷豐富和提高。其二,通過對私有財產運動過程的描述,尤其是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變過程和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轉變過程的研究,能夠為揭示社會歷史規律提供現實依據,為資本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的轉變提供一般的理論指導,為無產階級斗爭提供科學的理論指導。其三,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為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提供了主要的物質基礎和物質資料。其四,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殘酷的、徹底的剝削為無產階級向具有全面深刻感覺的人的轉變提供了基礎。
小結
馬克思在《手稿》中以私有財產為中心主題,按照私有財產的起源—本質—運動—揚棄的邏輯主線,首次從經濟學的維度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了系統的批判,初步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運動發展的一般規律以及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性和非永恒性。盡管此時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還沒有成熟,還不能從生產方式變革的角度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批判,但是馬克思從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出發,初步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了比較系統和深刻的批判。馬克思借助異化勞動理論,揭示了工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所處的非人狀態,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的剝削性質和有產者與無產者之間對立的事實;明晰了私有財產的主體本質是勞動,而不是資本,進一步確立了勞動對人類社會發展的重大意義;通過描述動產與不動產之間歷史的斗爭,揭示了私有財產的確立過程;通過資本與勞動之間的辯證運動,找到了揚棄私有財產的現實道路與物質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