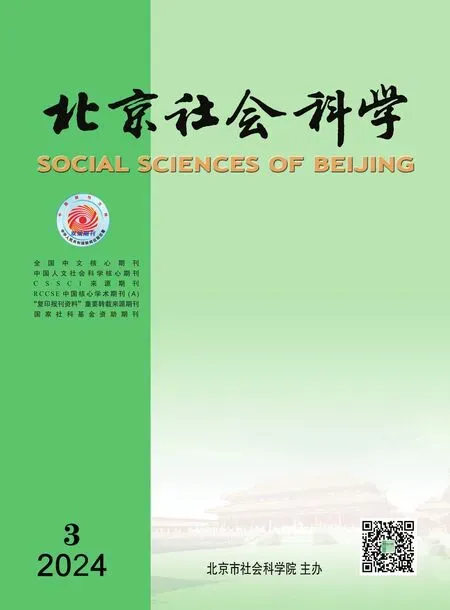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美學意蘊及當代啟示
孫琳瓊
一、引言
黨的二十大將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1],深刻指明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關系。雖然不同群體對美好生活向往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但美好生活應然包含“美”和“好”兩個基本向度,其中,好生活是美生活的現實基礎,美生活則是好生活的理想升華[2]。在政治哲學視閾中,“美好生活”一般內蘊正義、平等、自由、解放等價值尺度,抑或說,是否具有這些“內涵”可以作為審視一種生活是否“美好”的原則和依據。在這個意義上,“美好生活”不僅表征基于需求的個體生活狀態,更表征作為一種社會生活的政治規范性要求。在馬克思主義視閾中,“美好”從來不是抽象的理念預設,也不是與現實相適應的理想狀態,而是深嵌于無產階級的現實生產勞動之中,與個體的自由全面發展相關。無論是在早期還是成熟時期的作品中,馬克思都將藝術活動作為真正自由的勞動的典范來看待[3]。在現實生活中,“美好”的向往既需要具有審美能力的主體,更需要能夠塑造審美主體的政治經濟客觀條件。馬克思就是堅持在理想性與現實性的辯證關系中把握理想生活的建構,不僅確證了“美好生活”的未來景象,還指明了通達“美好生活”的現實之途。深入理解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美學維度,有助于把握馬克思思想的整體性,為人民立足現實創造美好生活提供啟示。
二、基于審美視閾理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人的自由活動之間的對抗性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一般作為我們理解馬克思美學思想的重要參考文本。在《手稿》中,馬克思從哲學意義上闡釋了人的本質與美的規律之間的關系。在恩格斯早期研究的啟發下,馬克思開始轉向政治經濟學研究,嘗試解決困擾他的“苦惱的問題”。馬克思從摘錄他人觀點的《巴黎筆記》開始,逐步過渡到《手稿》的寫作,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成為他持續近40年的研究主題。馬克思在《資本論》及諸多政治經濟學手稿中均提到美的問題,顯然不是隨意提及,也不是為了創造出一套美學理論,而是為了更好地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對抗性。自在自為的審美之境是人生存的理想之境,體現了人的有限性和超越性的內在統一,在現實社會中,審美活動的實現通常需要主客觀方面的條件,即具有審美能力的現實的個人和審美對象。馬克思深刻揭示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損壞了勞動者的身體和精神,現實生活已然成為人民從事自由自覺審美活動的桎梏。
(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審美活動喪失主體條件
審美活動的主體條件是具有健康身心的人。當人經常處于疾苦中或人的精神境界未達到一定水平時,審美活動就不會發生。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展現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無產階級身心造成的損害。
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損害無產階級的身體健康。資本只以增加利潤為目的,根本不關心工人的健康和壽命,除非社會迫使它去關心[4],否則資本家對工人健康問題是毫不關心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工人身體損害的最高程度也是首要表現,就是使工人失去生命。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引用當時醫生的話描述了“累死”現象,這一現象在當時是普遍存在的,特別是在生意興隆的地方。馬克思深刻指出,與從事過度勞動的人的死亡速度相似,死者的空位馬上有人補充上,似乎對生產運轉毫無影響。
即使工人沒有因為勞動直接失去生命,但他也會因超強度的勞動縮短壽命。馬克思引用1864年的公共衛生報告指出,職業造成無止境的肉體折磨致使成千上萬男女工人縮短甚至丟失了生命。對此,馬克思尖銳地指出,資本唯一關心的就是最大限度地使用勞動力,正像貪得無厭的農場主靠掠奪土地肥力來提高收獲量一樣,資本家靠縮短勞動力的壽命來達到這一目的。他們把工人看作與生產資料一樣的消耗品,不斷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無論工人健康與否。馬克思引用北明翰市長在衛生會議上的講話,指出當時曼徹斯特工人階級的平均壽命只有17歲,而在利物浦,工人階級的平均壽命只有15歲。
在工人短暫的生命中,他們的健康狀況是非常惡劣的。1852年至1861年間,在從事花邊生產的女工中,患肺病的比率持續上升。陶工“身材矮小,發育不良,而且胸部往往是畸型的”[5],患瘰疬病的陶工占三分之二以上。從事火柴制造業的工人,“多半是在充滿磷毒的工作室里吃飯”,他們患上一種被稱作“牙關閉鎖癥”的職業病。馬克思引用童工調查委員會的報告痛斥道,資本“依靠工人的勞動和技巧,取得了光輝的成就,但伴隨而來的是工人身體退化”[6]。這意味著,資本主義生產是以工人的畸形為條件的,在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之前的工場手工業階段,工人身體上的畸形化就已經形成了。而工場手工業階段工人畸形化程度的加重則形成了資本統治勞動的新條件,當進入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之后,工人身體的畸形化又得到了進一步加強。在此,馬克思深刻指出,在資本主義體系的內部,“一切發展生產的手段都轉變為統治和剝削生產者的手段”,而一切所謂“提高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方法都是靠犧牲工人個人來實現的”,這些做法的結果就是使工人“被貶低為深受勞動折磨的機器的附屬品”[7],成為局部的人、片面的人,工人的生活喪失豐富性,最終淪為一種謀生行為,畸形發展。
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迫害工人的精神世界。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不僅浪費血和肉,而且也浪費神經和大腦。”[8]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在較差的社會風氣中成長,未能養成合格的道德感。工人難以得到像樣的教育,無法獲得合格的知識。由于道德水準和知識水平的低下,工人獲得藝術修養幾乎是不可能的。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造成了工人道德的敗壞。馬克思引用1866-1867年間童工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對兒童在道德方面產生的極端負面影響,即兒童在社會氛圍的影響下如何逐步走向墮落,在這種生活和工作環境中,少男少女往往“從幼年起就終生淪為放蕩成性的敗類”[9]。而已婚的和未婚的成年男女,經常“擠住在一間狹小的屋子里”的做法,也使得很多人相信,在這種條件下,道德的敗壞已然成為必然的選擇和結果。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工人階級,在惡劣的工作、生活和居住環境下成長,未能形成良好道德修養。
除了限制工人道德水平的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還蠶食了工人的受教育權,使工人在知識水平上也得不到提升。英國法律規定,兒童每天要受到一定的義務教育。資本主義學者則聲稱,兒童時代到10歲就結束了,并成功迫使政府將兒童的界限從13歲下調為12歲。政府要求兒童每天最多只能勞動10小時,以保證他們受教育的權利。工廠主則借口細巧的織物需要靈巧的手指,而這只有年幼兒童才具有,因而反對政府對兒童的保護。事實上,根據工廠視察員的報告,當時社會能夠提供給兒童的教育資源是非常差的,不少學校的教師是否具有教學資格、是否識字是受到質疑的,“兒童只得到上學證明書而受不到教育”的現象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比比皆是。
由于沒有養成較好的道德情感,也沒有得到足夠的知識文化,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工人幾乎不可能具備審美能力。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工人勞動時間盡可能地被延長,以至于就連兒童都不得不面對不犧牲些睡眠時間,就沒有時間游戲的生活狀態。資本主義生產不僅奪去了兒童的游戲時間,還奪去了家庭范圍內滿足某種需要的自由勞動時間。由于沒有游戲和從事自由勞動的時間,工人就不可能形成審美能力,也不可能從事需要較高修養的審美活動。工人只能在酒精的麻醉中逃避現實的殘酷,他們“染上了各種惡習;酗酒、賭錢等等,完全墮落了”[10]。兒童和青少年在街上“亂嚷亂叫,唱著嘲諷輕浮的歌曲”[11]。
(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審美活動喪失客體條件
資本主義不僅摧毀了審美主體,而且摧毀了作為審美客體的精神勞動產品。資本主義摧毀了原有的藝術形式,且不能產生出新的富有靈韻的藝術,使審美活動喪失了客觀條件。馬克思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同以藝術和詩歌為代表的“某些精神生產部門”之間的敵對關系。
一方面,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原有的藝術形式消亡了。一定社會的意識形態受與之相應的經濟基礎制約,但同時,物質生產的發展也同藝術生產存在著不平衡的關系,藝術的繁榮并不同社會的一般發展成比例。鐵道、機車、電報、避雷針、動產信用公司、印刷廠等這些資本主義時代新出現的生產方式,改變了人與自然原有的關系。自然不再是人所敬畏的領域。特別是隨著工業革命的推進,自然逐漸成為人類征服的對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使得希臘神話不再成為人們的信仰,也使在此基礎上產生的希臘式的藝術“停產”。古希臘藝術因此成為再也回不去的絕唱。在資本主義時代寫作史詩,似乎已經不合時宜。
另一方面,資本主義不可能產生新的具有靈韻的藝術作品。資本造成審美觀的扭曲,使藝術品的創作更多關注商業價值而不是精神價值。資本主義審美觀的扭曲最集中地體現在對金銀美的理解上。金銀,原本是因為它獨特的光澤和靈活多變的形式而被贊美,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改變了人們對金銀美學價值的看法。金銀之所以被當作美的,是因為它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強大的“魔力”。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引用莎士比亞《雅典的泰門》中的描述,生動地展示出在資本主義對金銀的崇拜中,財富的創造和占有成為衡量一切的標準,并不可阻擋地向藝術領域擴張,審美的內核自此被消解。金銀作為貨幣,是財富的直接體現,它能使一切美化,因而是最美的東西。美不再屬于藝術,而是屬于金錢,藝術的靈韻變成了金錢的萬能,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審美觀的扭曲。馬克思尖銳地指出,在資本主義統治下,一切勞動必須換算為物質勞動才得到存在的合理性,即便是“最高的精神生產”,如果期待得到承認,也只能因為“被描繪為、被錯誤地解釋為物質財富的直接生產者”[12],從事寫作、繪畫、作曲、雕塑的人作為間接參加生產勞動的人,即非生產勞動者,他們的“服務”只有被加入生產,才能被看作“物化在產品中的”勞動,這樣的勞動才能得到社會認可。于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藝術創作成了和商品生產一樣的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角斗場。馬克思以編書為例,他指出,從事各種科學或藝術生產的人,工匠或行家,都是在“為書商的總的商業資本而勞動”[13]。資本家不關注藝術創作的質量,只看重藝術生產是否給他帶來利潤。利益原則代替了審美原則,成為資本主義社會衡量藝術的標準。在利益標準的指引下,所生產出來的藝術唯利是圖,而非注重精神價值的凝聚,藝術失去了自己的獨立性,成了僅僅為資本增殖服務的沒有靈韻的工具。
綜上所述,資本主義破壞了原有古典藝術,也不能產生出新的具有靈韻的藝術。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自由自覺的審美活動在人們的現實生活中缺席。基于此,馬克思對如何恢復審美活動在人的活動中應有的地位,打破限制人的自由活動的藩籬,進行了深入的思考。
三、基于政治經濟學視閾看審美活動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超越及其限度
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馬克思系統揭示了資本的邏輯并走向人的邏輯。馬克思認為,僅僅依靠審美活動是無法真正超越資本主義的,需要進一步追問審美活動得以存在的基礎。
(一)審美活動自身對資本主義的超越及限度
馬克思發現,審美藝術活動自身具有一定的突破資本原則的可能性。一方面,在藝術鑒賞上,資本主義的價值原則不能完全應用于藝術品的價值上,藝術品價值具有不受資本主義定價原則限制的可能性。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援引富蘭克林的觀點指出,鞋匠的勞動、礦工的勞動、紡織工的勞動,盡管是可以和畫匠的勞動交換的,但用鞋、礦產品、紗來衡量畫的價值卻是錯誤的。資本主義的定價原則,即將一物的價值看作與它交換的物的價值,二者的價值皆可以抽象為一定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于是萬物都有了可以量化的價值。資本主義的定價方式只涉及量,而不涉及質。資本主義是靠一個外在于藝術品的、與之相交換的他物來給藝術品定價的。但藝術品的定價方式決不能是量的,不能是外在的。于是,藝術品自身的價值就與資本主義的定價原則相抵觸,藝術品自身體現出不受資本主義價值原則支配的可能性,即超越資本主義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藝術創作具有不受資本主義生產控制的一面。藝術創作既有為資本增殖服務的一面,同時還有與資本增殖無關的一面。藝術創作作為一種勞動,具有不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控制的一面。對此,馬克思將創作《失樂園》的約翰·彌爾頓與為書商提供工廠式創作的作家相比較,認為密爾頓的創作源于天性的能動表現,雖然《失樂園》的出售使他獲得5英鎊,但他依然是非生產勞動者,而提供工廠式勞動的作家則是生產勞動者。同樣是藝術的創作,既可以落入資本主義的工廠中,成為資本主義生產勞動,也可以不落入資本主義工廠,成為非資本主義生產勞動,即自由活動。馬克思還以歌女的例子來說明藝術生產不受資本主義控制的可能性。自行賣唱的歌女就是非生產勞動者,因為她沒有參與資本的生成過程;但被劇院老板雇傭去唱歌的歌女就是生產勞動者,因為當唱歌是為了賺錢時,她就已然參與了資本的生成進程中,是否參與資本的生成過程也是我們評價藝術活動本身性質的尺度。
藝術能否作為一個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抗衡的獨立領域,如“審美烏托邦主義者”所設想的那樣,成為戰勝資本主義的基礎呢?馬克思在《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就藝術生產對資本主義超越的限度進行了討論,得出了否定性的結論。馬克思認為,這里的大多數情況,他所處的那個時代大多數的書畫和表演等藝術形式,都還只是“向資本主義生產過渡的形式”[14],藝術創作大規模地步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但總體而言,藝術創作正在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過渡。后來的歷史證明了馬克思的預言,今天,西方消費文化的興起,藝術商品化、商品藝術化,文化已成為文化產業,無論是藝術產品還是表演藝術,都被納入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中。藝術活動不僅沒有保持住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獨立性,而且完全被資本化。
通過充分發揮藝術活動相對獨立性,沖破資本主義統治已被證明是不可能的了,這就有必要繼續追問藝術活動的存在基礎,在更深層次的意義上談論恢復人自由活動的方式。
(二)審美維度的恢復表現為自由時間的恢復
什么是社會存在的藝術活動得以存在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人必須先滿足吃、喝、穿、住等一系列基本的生存需要,然后才能從事政治、文化、藝術等活動。當人的生產有了剩余之后,才可以從事藝術活動,人的審美—自由活動才會得以展開。在前資本主義時代,古代人“沒有想到把剩余產品變為資本”,“他們把很大一部分剩余產品用于非生產性支出——用于藝術品,用于宗教的和公共的建筑”[15]。古希臘輝煌的雕刻、神話史詩和建筑藝術,正是發生在物質生產的剩余上。審美意識出現的基礎是剩余產品的出現。
剩余產品本質上是什么呢?馬克思認為,勞動創造財富,剩余產品也是由人的勞動創造的,它是由人的剩余勞動創造的。而勞動,是勞動力在一定時間內的運用。因此,勞動可以歸結為時間,剩余勞動在同等意義上,就可以被歸結為剩余勞動時間。剩余勞動時間是指超出工人再生產自身的那部分勞動能力,這部分對于工人而言,是超出他們必要勞動而進行的那部分勞動時間,是工作存在的需要。人的生命活動表現為需要和滿足需要的活動。勞動即是人為滿足自己的需要所進行的活動。在自然狀態下,當勞動足以滿足人的需要時,滿足需要的勞動就將停止,這是必要勞動時間的截止點。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當工人超過必要勞動時間的限制,在必要勞動時間之外仍要從事勞動時,即剩余勞動時,他的勞動就不是滿足自己的需要,而是滿足了其他人,即滿足了剝削階級的需要。因此,剩余勞動時間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就表現為被剝削的時間。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征,即一部分人的自由以另一部分人的被奴役為條件。在對立的階級之間,“一方的自由時間相應的是另一方的被奴役的時間”[16]。這意味著,一方生產的剩余勞動時間成了另一方的自由時間。剩余勞動時間的本質是自由時間,正如剩余勞動產品、剩余價值從它真正的主人即工人手中轉移到了剝削階級手中,剩余勞動時間的本質,自由時間也轉移到了剝削階級手中,但這并不改變自由時間是剩余勞動時間的本質。于是,我們看到,社會存在的審美維度賴以繁榮的基礎——剩余產品,本質上是自由時間。
什么是自由時間?自由時間和社會存在的審美維度有何聯系?馬克思認為,自由時間是真正的財富,是人全面發展的空間,是人的審美自由活動得以開展的基礎。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指出:“創造出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是財富整個發展的基礎。”[17]對此,馬克思進一步解釋道,“創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可以被理解為“創造產生科學、藝術等等的時間”[18]。《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再次體現了馬克思的基本觀點,即“自由時間,可以支配的時間,就是財富本身”[19]。馬克思反復強調,自由時間即是財富。而“財富”(Verm?gen)一詞在德文也有“能力”的意思。說自由時間是財富,也意味著自由時間是人的能力發展的基礎。自由時間是人的能力獲得全面發展的基礎,人的全面發展自然也包括了人在審美領域的發展,故自由時間是人進行自由活動的基礎,社會存在審美維度的恢復也建立在自由時間的基礎上,因此,對社會存在審美維度的恢復就成了對自由時間的恢復。
(三)實現自由時間恢復的兩個條件
馬克思認為,恢復自由時間有兩個條件,一是在生產關系上取消剝削,二是在生產力上節約勞動時間。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中對這兩個條件給出了說明:“資本一方面會導致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社會上的一部分人靠犧牲另一部分人來強制和壟斷社會發展(包括這種發展的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現象將會消滅;另一方面,這個階段又會為這樣一些關系創造出物質手段和萌芽,這些關系在一個更高級的社會形式中,使這種剩余勞動能夠同物質勞動一般所占用的時間的更大的節制結合在一起。”[20]這段話表明,馬克思、恩格斯視閾中理想社會具有兩個標志:剝削將不復存在;一般物質勞動花費的時間顯著縮短。
自由時間的恢復,首先需要改變現有剝削的生產關系。馬克思痛斥道:“現今財富的基礎是盜竊他人的勞動時間。”[21]資產階級剝奪了屬于工人的自由時間,使社會中占大多數的勞動者喪失了自由時間。要恢復大多數勞動群眾喪失的自由時間,就必須調整生產關系,消滅剝削制度。馬克思看到,迄今為止的一切文明和社會,都是一方能力的發展以另一方發展受到限制為基礎,社會中存在著一些不勞動的人,這些不勞動的人,不僅從勞動者那里獲得了生活的物質條件,而且還獲得了他們的自由時間。必須改變使剝削者不勞而獲的生產關系,即取消資本主義私有制,取而代之以公有制,使工人的剩余價值不歸資本所有,而是歸社會所有,而工人又通過聯合起來,共同占有剩余勞動,從而占有自由時間。
自由時間的恢復,根本要靠生產力的發展和必要勞動時間的節約。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寫道:為了使個體性得到發展,必須“直接把社會必要勞動縮減到最低限度”,這樣才能“由于給所有的人騰出了時間和創造了手段”,使個人“在藝術、科學等等方面得到發展”[22]。也就是說,只有通過將勞動時間縮減到足夠小的范圍內,人才有充足的自由時間從事藝術活動。但縮減必要勞動時間并不意味著降低需求,而是相反,必要勞動時間的縮短要靠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馬克思已經深刻意識到這一點,在馬克思看來,真正的經濟—節約,就是勞動時間的節約,即將生產費用降低到最低限度,而這種節約就等同于在發展生產力,因為“節約勞動時間等于增加自由時間,即增加使個人得到充分發展的時間”[23]。發展生產力就成為恢復人的自由時間,進而恢復人從事審美的自由活動的根本條件。
當工人擁有了自由時間,就意味著過量勞動傷害人身體的情況就能得到遏止,也意味著工人擁有提高精神生產的可能空間。工人恢復了從事審美活動的身心條件,在自由時間里發揮自己的才能,將自己的精神世界作為被改造的對象,由此恢復工人自身活動和勞動產品的審美維度,使自由自覺的活動成為可能。可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變革、生產力的發展、工人重新占有自由時間,是人的自由活動得以恢復的根本途徑。
四、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美學意蘊的當代啟示
我們從審美活動這一自由自覺的典范活動出發來審視理想生活可以看到,馬克思在反思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合理性及其深層次原因時,沒有以純粹的“見物不見人”的經濟學分析范式展開,也拋棄了從抽象國家理性出發的“權力批判”道路,而是以現實人的生存狀態為實際考察對象,在自由理想與現實生存的辯證張力之中,深入現實并尋求現實通達自由理想之途。正確把握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審美維度,有利于更好地把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頑疾,突破“物的關系”的局限性,更好地通達生活之美好。
(一)有助于更好地把握馬克思思想的整體性
近年來,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潮流中,倡導“回到馬克思”,尤其是“回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呼聲越來越高,回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中的哲學語境、歷史語境與國際語境等,也成為一種研究趨勢。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最突出的特點是政治經濟學和哲學相結合,這里所說的哲學,不僅是方法論意義上的,也是生存論意義上的,即從人的生存論意義上考察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虛偽性和欺騙性。有學者指出,馬克思不是從個人主體的預設出發,也不是從個人行為的視角出發,而是從社會結構的視角來考察現代經濟過程。從哲學美學視閾出發,能更好地把握馬克思思想的整體性。在哲學視閾中,我們可以看到審美活動與人的本質以及人的自由之間相關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視閾中,我們不僅看到審美活動與物質生產的關系,更看到審美活動與政治經濟活動以及精神生產等多方面的關系。立足對政治經濟學批判美學意蘊的思考,我們看到馬克思如何將理想社會的生成扎根現實政治經濟批判,以理想的生存狀態照亮現實生活。馬克思強調人但沒有深陷人本主義泥潭,強調現實也沒有走入經濟決定論的怪圈,就根本而言,就在于他很好地處理了理想與現實的辯證關系。馬克思對自由理想的展望更多地體現在實現自由理想的現實道路的思考和規劃中。對馬克思來說,實現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發展,不是倫理的預設和邏輯的推論,而是歷史邏輯與現實邏輯相統一的客觀趨勢和結果。馬克思主義給我們提供的是作為嚴密思想體系的理論武器,而不是支離破碎的思想碎片。[24]只有深刻理解和把握馬克思主義的整體性,才能更好地用馬克思主義洞見時代,以不斷提升的體系化研究和學理化闡釋水平推進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創新進程。
(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美的理想追求在現實生活中的定位
如前所述,在馬克思那里,“美”從來不是抽象的理念預設,也不僅僅是與現實相適應的理想狀態,而是深嵌于無產階級的現實生產勞動活動之中,與個體的自由自覺活動和自由全面發展相關。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開展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始終具有指向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的深切的審美觀照,當然,這里所說的審美不是理論形態的美學,而是內化于改造世界與創造歷史的活動之中的價值追求,是現實的理想性之維。在把握美的追求在現實生活中的定位問題上,許多理論家是背離馬克思初衷的,如以馬爾庫塞、阿多諾為代表的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將關于人類解放的美學話語從對政治經濟學的領域中釋放出來,使之獲得獨立意義。將審美局限于精神解放、個體解放的層面,導致審美活動失去了與現實生活之間的聯系。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關注到這一問題,嘗試以審美介入激活政治話語、塑造感性共同體等方式重建美學與現實的關聯,如巴迪歐(Alain Badiou)以“非美學”概念呈現豐富的政治內涵;齊澤克(Slavoj ?i?ek)嘗試融合美學政治批判和精神分析視閾;阿甘本(Giorgio Agamben)運用美學視閾透視生命政治規范,使美學以非實在性的感知方式重返現實;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維爾默(Albrecht Wellmer)借助交疊辯證法實現對真理的交往拯救,為審美尋求參與政治交往的現實之途;朗西埃(Jacuqes Rancière)以平等預設溝通政治和美學,重思藝術參與政治斗爭的方式等,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理論闡釋,但本質上依然是理論建構,并未真正將美好嵌入現實生活本身。
(三)有助于為人民立足現實創造美好生活提供理論啟示
正是立足審美這一獨特視閾,馬克思更加深刻地認識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弊端和局限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使人失去本質力量的同時,也使審美的藝術活動沾染上資產階級美學的機械化、單質化等習性而走向衰落。為此,馬克思提出,通過歷史的解放進程將人從資本統治的片面性中解放出來,使人重獲精神的富足與文化的繁榮。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明確提出人民美好生活,涵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各領域,并以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為評價標準,既包含了政治經濟學的豐富內容,又體現出審美理想之維,將人的有限的經濟和政治問題躍升為對自由理想與本真生存的更高層次的回歸。這一點,無疑體現了對馬克思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審美維度啟示我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與對現實生活的反思并不是以另一方的完成為邏輯前提。美好生活的追求絕不成為脫離生產領域自娛自樂的消遣,應當多方面和多層次地嵌入人們的實踐活動總體,并與人的理想性追求保持關聯。特別是在物質財富迅速增長的今天,我們更需要冷靜分析資本邏輯與審美價值的博弈,嘗試解答如何在市場洪流中保障社會的公平正義和個體的身心協調發展。深入理解和把握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美學意蘊,有助于指導人們立足現實創造美好生活,把握美好生活追求的理想之維和現實之意,為新時代審美文化建設提供啟示。
五、結語
綜上所述,審美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延展和開辟的重要維度。正是基于對審美維度的自覺關照,馬克思逐步實現了對隱藏在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背后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在此基礎上人的整體生存結構的考察。這一考察,從更深層次來看,是馬克思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和人的活動方式與存在方式的考察,是立足現代工業社會內在矛盾對未來社會的考察,是對人的自由解放的現實途徑的考察。在上述意義上,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審美維度,為我們回答了人類存在的理想性與現實性的關系問題,這對于理解新時代“美好生活”的內涵及其內在標準,深入推進當代精神文明建設無疑具有重要的思想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