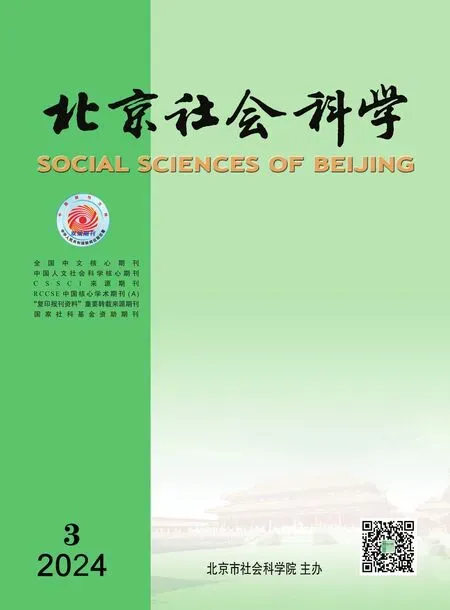漢唐賦稅制度比較及其對稅收現代化的啟示
——理想、技術與效能
周志波 張衛國
一、引言
所有的古代史,都是一部當代史。歷史是一面鏡子,以史為鑒,鑒古知今,可以明得失、知興替、導未來。縱觀中國歷史,一部王朝的興衰史,就是一部政權的更迭史,但在本質上卻是一部財政危機的應對史和稅收制度的變遷史。事實上,封建王朝的所有社會危機均源于財政危機,所有的農民戰爭均是因為國家財政出了問題,而財政危機的根源則在于稅收制度出了問題,由此可見稅收制度對于國家治理的重要性。也可以說,稅收在國家治理中發揮著基礎性、支柱性和保障性作用,稅收制度是社會經濟制度體系的重要基石和支撐[1]。研究中國古代稅收制度史,總結歷史經驗與教訓,對于當下完善稅收制度,推進稅收治理現代化,具有重要的鏡鑒意義。
漢代和唐代是封建王朝的巔峰時代,中國國力達到全盛狀態,但所有的繁榮與鼎盛均有一整套底層邏輯,而制度則是解密這一底層邏輯的關鍵所在。稅收制度作為最基礎的社會經濟制度,其背后潛藏著王朝興衰更替、社會變遷發展的“密碼”。漢代和唐代作為封建王朝的兩大盛世,其稅收制度代表了中國稅收制度史的兩大發展階段。前者因襲秦法,完善了以“稅—賦—役”為基礎的“三位一體”的賦稅制度體系,雖然這一制度體系中途經歷了多次調整與變革,但基本框架并未發生實質性改變,且為兩晉南北朝時期的稅制改革提供了最基本的架構,形成了唐初租庸調制的雛形。后者則將漢代建立的“稅—賦—役”轉換為租庸調制度體系,并在“安史之亂”以后叛亂此起彼伏、稅基侵蝕愈發加重的雙重壓力之下不得已實施“兩稅法”改革,實現了中國稅制由“舍地稅人”的傳統向“履畝而稅”模式的轉變,為后世的稅制設計提供了藍本。
二、文獻述評
漢、唐兩代的國家財政管理體制均具有獨特的歷史地位[2],尤其是兩代的稅收制度及其改革,在中國財政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引發了經濟學、歷史學、社會學等諸多領域學者的關注,并形成了十分豐富的理論文獻。
有關漢代賦稅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西漢時期,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西漢賦稅制度具有很強的代表性,并為后世的稅收制度奠定了基準框架,東漢的賦稅制度只不過是因襲西漢的基本框架而做了一些結構性調整。有關西漢賦稅制度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田稅、戶賦、稾稅及鹽鐵專賣制度方面。比如,陳登原所著《中國田賦史》對戰國至民國時期的田租制度演化過程進行了全面考察,其中對漢代田租的征收方式、實際稅率、稅負減免等問題做了深入考證,是該領域比較權威的文獻[3]。高敏基于《張家山漢墓竹簡》的史料解讀,研究了西漢前期芻、稾稅制度的變化發展歷程[4]。此后,高敏從《張家山漢墓竹簡》中找到了漢代有“戶賦”“質錢”及各種礦產稅的新證據[5]。臧知非以張家山漢簡為基礎材料,全面研究了西漢授田制度與田稅征收方式,其研究認為,西漢以授田制為基礎,對田稅實行定額征收制度,明確規定按頃計算、按戶征收,并改實物稅制為實物、貨幣并舉而以貨幣為主[6]。但是,這一觀點遭到了李恒全的質疑:第一,漢初土地制度實行私有制,漢代不存在戰國授田制性質的土地制度;第二,芻稿稅與田稅是不同的稅種,秦朝芻稿稅按頃計征,但田稅按實有畝數征收;第三,張家山漢簡《算數書》的大量材料證明,漢初田稅以畝為單位,按實有畝數計征,所謂西漢田稅以頃征收的說法不能成立[7]。朱圣明對秦至漢初戶賦的變化進行再考察并指出,漢武帝前,“以算所征之賦”包括上繳國家財政的算錢和上繳帝室財政的算錢(口錢);漢武帝后,“以算所征之賦”僅指前者,后者(口錢)則獨立為專門針對3歲或7歲至14歲人群征收的人頭稅[8]。
有關漢代唐代賦稅制度,從時間上大致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前半段為租庸調時期,自唐初到德宗時期楊炎“兩稅法”改革之前;后半段為“兩稅法”改革直至帝國滅亡。前半段的制度,總體上比較“清明”,其變遷邏輯比較清晰,爭議也比較少,但對于后半段“兩稅法”改革則存在著諸多爭議,因而理論界關于唐代賦稅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兩稅法”改革的第二個階段。關于唐代賦稅制度尤其是“兩稅法”改革的現代研究,始于民國初期。最早對唐代賦稅制度尤其是“兩稅法”進行研究的是財政學者。胡鈞的專著《中國財政史》從財政學角度研究了唐代賦稅制度,并從五個方面高度評價了“兩稅法”改革,很多學者將這一研究視為20世紀以來最早研究“兩稅法”的著作[9]。考察既有文獻發現,有關“兩稅法”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有關改革歷史背景的研究。比如,郭建龍、劉守剛等認為,唐代土地制度的變化是“兩稅法”改革的重要背景,這是當前的主流觀點[10-11]。第二,有關改革內容爭議的研究。學術界有三種主流觀點:一是“兩稅”指戶稅和地稅[12];二是“兩稅”實際上仍然是原來的租庸調[13];三是“兩稅”由多個稅種合并或重組而成,但對具體內容仍說法不一[10,14]。第三,有關稅制設計及實施影響的研究。這類研究主要關注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兩稅法”的制度設計及其實施情況[15];二是“兩稅法”實施對經濟社會和財政運行帶來的深遠影響[11,16]。
總體來看,有關漢、唐兩代的賦稅制度研究,主要是以斷代研究為主,且集中討論稅收制度的某一方面,很少有關漢、唐兩代賦稅制度的比較研究,缺乏對兩代稅收制度的整體性觀察。而漢、唐兩代的賦稅制度在中國古代最具有代表性,其背后潛藏著一脈相承的演化邏輯,且這一制度演化進程對于現代稅收治理仍然有著很強的啟示意義。因此,比較研究漢代和唐代的賦稅制度史,從其演化過程分析其背后的制度邏輯,不僅有助于理解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制度的變遷發展,還有助于理解稅收對于國家治理的重要意義,并為以稅收現代化推進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提供歷史啟示。本文將在比較分析漢代和唐代賦稅制度基本架構的基礎上,剖析其背后的社會理想、制度設計和治理技術,并從中總結歷史經驗與教訓,提出未來推進稅收治理現代化的啟示。
三、漢唐賦稅制度的基本架構:從“稅賦役”到“租庸調”和“兩稅法”
(一)漢代賦稅制度框架:以“稅賦役”制為基礎
漢代賦稅制度因襲秦制,基本框架就是“三駕馬車”——稅、賦和役[17]。但稅、賦、役的用途有所差別,《漢書·食貨志》載:“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人也。賦共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18]簡言之,稅相當于“一般預算收入”,主要用于供給郊祭宗廟百神,天子供養百官薪俸食物及眾事的費用;賦相當于“國防預算收入”,主要供給車馬銨甲兵器士兵的勞役,充實官府儲存財物兵甲的倉庫及賞賜之用。
1.稅
由于漢代是典型的農業社會,社會財富主要體現為土地和農業產品,因而稅主要以實物形式征收。漢代的稅,大致可以分為農業稅與工商稅兩大類型。農業稅主要是田租,田租很多時候也被稱為田賦。田賦在本質上是一種地租,雖然冠以“賦”之名,卻是地地道道的“稅”。“漢世輕典,莫如田租”[19]。西漢的田租制度,總體上采取“輕徭薄賦”的方式,盡量降低全國人民的田租負擔,讓人民得到最大限度的休養生息,以解決秦末以來連年混戰、民生凋敝的問題。田租的征收標準為十五分之一,在漢文帝時朝廷曾下令減半征收田租12年、全免田租1年,但這些田租減免政策均屬于臨時性制度安排。到漢景帝時期,朝廷將“三十而稅一”的田租稅率以法令形式確定了下來,成為永久性的制度安排,后世即便面臨財政困難,也未曾改動過田租的法定稅率。東漢光武帝統治初期,為了解決征伐平亂所需軍餉,曾在短期內將田租改為“什一而稅”,即10%的稅率;到了建武六年十二月,光武帝下詔恢復自西漢景帝以來“三十而稅一”的田租制度,此后終漢室一朝田租稅率一直保持不變。此外,漢代還繼承了秦朝的藁稅制度,對民戶征收禾稈草料等實物以供獸食。工商稅主要是山澤之稅、海漁之稅和商稅三大稅種。山澤之稅,又稱假稅,即皇帝將山澤之產假與貧民,貧民獲得山澤之物后向政府繳納實物稅收。海漁之稅,就是對漁民在水域之中的捕撈收獲征稅,類似田租對土地的產出收獲征稅。西漢的商稅,主要源于國家對鹽鐵酒等商品的壟斷制度,征收的都是實物形式的產品。漢武帝為了解決開邊拓土的財政來源問題,對鹽鐵酒等商品實行壟斷專賣制度,即所謂“榷鹽鐵”。這種收益按經濟性質而論,實際上包含了國有企業上繳的利潤和稅收兩個部分。
2.賦
賦是漢代賦稅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相當于對人口征收的人頭稅,但以貨幣形式征收。漢代的賦,主要有兩個品目——口錢和算賦。西漢對人開征“賦”,有一個技術前提,即戶籍制度比較完善[19],人口統計比較準確。西漢的人口數,在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達到巔峰,約6000萬人,如《漢書·地理志》記載:“凡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20]。東漢的人口數,在順帝永和五年達到巔峰,約5000萬人,如《后漢書·郡國志》記載:“凡戶九百六十九萬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萬二百二十”[21]。在戶籍和人口數量眾多且戶籍制度比較完善的情況下,以“賦”的形式開征人頭稅,既能有效籌集賦稅收入,又能使人民直接對國家承擔責任。漢代的算賦自劉邦建國后四年開始征收,征稅的對象為成年丁口(15-56歲的國民),征收標準為每年“一算”,即120錢。口錢則是后期漢武帝為緩解戰爭支出壓力開征的人頭稅,征稅對象為未成年人(3-14歲的國民),征收標準為每年20錢。算賦和口錢的具體征收制度,在兩漢時期經歷了多次調整。在稅率調整方面,漢宣帝五鳳三年“減天下口錢”;甘露二年“減民算三十”,即算賦征收水平降為每人每年90文錢;漢成帝建始二年“減天下賦錢,算四十”,即算賦征收水平每人每年降低40文錢。當然,這種人頭稅的減免,只是減免當年的納稅義務,而非永久性減免。在征稅對象調整方面,口錢起征年齡改為7歲,算賦起征年齡改為20歲。為什么做出這一調整呢?由于口錢自嬰孩3歲起就開始征收,而未成年的嬰孩和兒童并不從事生產,且家庭還要承擔孩童撫育的成本,人民不堪重負,甚至出現了“殺嬰”等慘劇;孩童成年后將改納算賦,稅率較口錢增加了5倍,稅收負擔出現了跳躍式上升,很多家庭無力負擔,因而漢元帝時期中央下令將口錢和算賦的征稅對象做了調整[22]。上述減免都是永久性的減免。此外,漢武帝時期,政府還對車船、資產征收賦錢,即所謂的算車軺、算緡錢。
3.役
漢代除了以實物形式對國民征收農業稅、工商稅,以貨幣形式征收人頭稅(口錢和算賦)之外,還以力役形式進行勞力征收。漢代的力役之征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兵役;二是勞役。兵役源于漢代的民兵制度,主要有三種形式的兵役:一是在中央政府做“衛”兵;二是到邊疆做“戍”卒;三是在地方政府服兵“役”。這三種兵役中,以在中央政府做“衛”兵最為優待,不僅吃穿用度由中央財政保障,還相對比較輕松,且有機會接近達官貴人;到邊疆做“戍”卒最為辛苦,不僅吃穿用度得不到財政保障,還得自己承擔服役期間的衣食住行費用。勞役,則源于中國傳統的力役之征慣例,即國民有義務為國家免費勞動。根據西漢初期的制度安排,“全國壯丁按冊籍編定,每人每年一個月,替國家義務做工”[23],這種勞役比服兵役更加辛苦,干的都是一些苦差事、重體力活。老百姓按規定服役,就稱為“卒更”;如果不親自服役,可以貨幣形式折算兵役和勞役,這種貨幣性繳納就稱為“更役”或者“更賦”。三國時期如淳所注《漢書·昭帝紀》說:“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有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雇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往,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也。”[24]按如淳的注解,卒更就是服兵役、輪班值守、按期換班;踐更就是出錢代卒更;過更就是出錢代戍邊。謝宗陶對“更三品”的考證指出:“凡是踐更、過更,都要分別出二千、三百的雇費,交由官家轉給受雇者,略同于唐代的‘庸’。”[17]由此可見,更役實際上是國民為了避免兵役之征,請政府雇傭其他人代為履行義務而付出的貨幣性代價。兵役之征,可以折現征收,在稅收制度的演化歷史上,算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在整體上提升了社會運轉的效率,也避免了國民遠走他鄉的戍邊之苦。但嚴格來講,西漢的稅征收實物,賦征收貨幣,而役征收力役,踐更與過更由力役轉化為貨幣,在本質上就變成了“賦”,因而也將“更役”稱作“更賦”。
(二)唐代賦稅制度:從租庸調到兩稅法
唐代的賦稅制度,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從唐朝建國到德宗任用楊炎為相,實施“兩稅法”改革之前,以租庸調為稅收制度的基本框架;二是自楊炎主導“兩稅法”改革到唐朝滅亡,將租庸調等各項稅收進行整合,分夏秋兩季征收。[19]
1.租庸調制
唐初的稅收制度,基本沿襲自隋代的租調制度。公元619年(高祖武德二年),初步確立了租庸調制度。《新唐書·食貨志》載:“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①[25]由此可見,這一稅制的基本制度安排為:一是地租。地租以實物形式征收,征收標準為每年每丁粟2石。二是戶調。戶調也以實物形式征收,但戶調的課稅客體不是糧食,而是各類土特產品,納稅人可以上繳綾、絹、絁等產品。征收標準為:每戶每年上繳綾、絹、絁合計2丈,如果以布匹繳納,則加征20%,即2.4丈,并額外加征麻3斤;如果以絹、綾、絁繳納,則額外加征緜3兩。三是折庸。折庸其實就是以實物形式抵免勞役之征。按照唐代的規定,每丁每年必須免費服役20天,閏年加2天,但丁戶可以選擇將服役的義務折合成實物繳納,即所謂“折庸”。折庸的標準為每日三尺絹、綾、絁、布等土特產品。如果在正常服役的基礎上,加役25天可以免除戶調,加役30天則田租、戶調盡免。
2.“兩稅法”
關于唐代“兩稅法”改革的具體內容,有一些爭議,但有一點是共識,即楊炎主導的這場改革,將原來的各種稅收進行了整合,分夏季和秋季兩次征收。《舊唐書·楊炎傳》對這一改革做了以下記載:“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于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郡縣稅三十之一,度所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申報出入如舊式。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歷十四年墾田之數為準而均征之。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逾歲之后,有戶增而稅減輕,及人散而失均者,進退長吏,而以尚書度支總統焉。”[26]由此可見,“兩稅法”改革的主要內容有五個方面:第一,按居住地原則征稅,不分主戶和客戶,避免丁戶走逃、逃避納稅的問題;第二,堅持量能課稅原則,有多少地納多少稅,確保稅收公平;第三,一切稅賦和力役都并入“兩稅”,統一賦稅征收形式;②第四,一切賦役并入戶、地兩稅后在夏秋兩季分兩次征收,充分尊重農業社會生產的規律性;第五,“兩稅”稅率以改革前一年大歷十四年的田租收入為準,核定各地征斂數額。
四、漢唐賦稅制度比較分析:理想、技術與效能
漢唐兩代的賦稅制度采用不同的框架,但均是適應當時社會經濟環境的選擇,對于保障政權的正常運行起到了重要作用。盡管兩個朝代的稅制存在著先后順序,體現了動態演進的歷史進程,但二者均反映了當時歷史條件下的稅收理想,更是因應稅收治理技術的社會選擇。比較分析漢唐的賦稅制度,可以發現兩個朝代在稅收理想、征管技術和治理效能方面的共性與特性。
(一)稅收理想:稅收制度的價值觀照
所有制度均反映著一定的社會理想,一切規則均有其價值觀基礎。漢代賦稅制度反映了三大社會理想:“稅”反映的是節制資本、抑制過富、保障公平的社會理想;“賦”反映的是一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27]的社會理想;“役”反映的則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社會理想。總體上,“稅”是一種節制資本、抑制過富的制度安排[23],以實物形式征收的稅收,是帝國財政的主要來源,供養了全國的行政官僚體系。特別是在漢武帝時期,政府壟斷了鹽鐵等礦產資源的開采與銷售,逐步建立起鹽鐵專賣制度,鹽鐵專賣等形式的商稅成了財政的重要收入來源,但鹽鐵稅制度在確保低水平的社會公平之時,卻對民間資本的發展和聚集造成巨大障礙,嚴重影響了經濟效率。“賦”以貨幣形式對所有適齡納稅人口征收統一的“人頭稅”,這實際上反映了皇帝對臣民具有所有權的一種價值觀,每個國民均要向君王納稅。“役”以兵役和勞役的形式征收,每個國民均負有一定的兵役和勞役義務,體現國民對國家的責任,反映了所有人均對國家負有保衛和衛宿義務的一種國家觀。
唐代的賦稅制度最初以租庸調為基本框架,其背后潛藏著唐初的社會理想。這一理想可以概括為“為民制產,耕者有其田”[23]。從租庸調的具體制度安排來看,就是錢穆所說的“租庸調項目分明,有田始有租,有身始有庸,有家始有調”,“此制的最高用意,在有身者同時必有家,于是對政府征收此輕微的稅額,將會覺得易于負擔,不感痛苦”[23]。總體上看,租庸調制是鼓勵經濟效率的,而未過多關注公平問題,這一點與漢代輕徭薄賦的制度安排有所不同。楊炎主導的“兩稅法”改革,總體思路是將租庸調各類稅收合并,分夏秋兩季征收。租庸調向兩稅法的改革轉型,標志著“為民制產,耕者有其田”這一唐初社會理想的徹底破產,社會價值取向已經轉為公平稅負、結束藩鎮割據、實現社會安定。
縱觀漢唐兩代的稅收制度演化史發現,稅收制度反映社會理想與共同價值,并隨著社會理想的變化而變化,而社會理想變化的背后則是更加深刻的經濟政治格局變化。稅收制度的變革,在長期體現的是社會理想的變化,在短期更多源于政府財政危機。漢代稅收制度的最大變革在于,對鹽鐵等礦產資源實行專賣制度,政府從專賣稅收中獲得大量收入,滿足對外戰爭、官僚機構膨脹導致的財政支出需求;唐代稅收制度最大的變革在于,通過兩稅法改革結束田租力役土貢分項征收制度,開創單一稅制度,但其根源在于“安史之亂”及以后的藩鎮割據問題以及長期未能解決的財政危機[11]。
(二)征管技術:稅收制度的現實約束
征管技術是將稅收制度由抽象變為現實的工具與手段,但也是稅收制度的現實約束。換言之,征管技術水平直接制約了稅收制度的可操作性,也決定了稅收制度演化的上限,成為稅收制度轉化為現實的“天花板”。從征管技術手段來看,漢唐兩代盡管經濟社會比較繁榮,發展水平領先世界其他文明,但在稅收征管技術手段方面仍然十分受限,同時賦稅征收的成本很高,這兩方面的原因導致整個賦稅征收管理體系的運轉效率較低。
漢朝主要采取的是“輕稅重賦”的賦稅制度,以實物形式征收的地租稅率很低,從西漢到東漢大部分時期采用的稅率是“十五稅一”,部分時期甚至采用“三十稅一”的稅率,其稅負不可謂不輕;但口錢、算賦的稅率卻是很高的,成年丁口每年繳納人頭稅一百二十錢,在財政困難的時期還會有各種加征,其稅負可能遠高于一百二十錢。這樣的稅制設計,既有輕徭薄賦的“仁政”理念指導,也有稅收征管技術的現實制約。征管技術的限制在于:漢代的國土疆域廣袤,交通運輸條件相當不便,以實物征收的地租要運往政治中心尤其是運往首都長安,需要付出巨大的經濟代價和時間成本,運輸成本甚至高于糧食本身的價值,征收大量的糧食作為賦稅收入就顯得不那么經濟。同時,漢代雖然在中央設置了專門的財政管理機構,但并未自上而下建立專業化的稅收征收管理組織體系及配置專業化的稅收征管人員,賦稅的征收管理尤其是基層一線征收過程不得不依賴于政府行政體制之外的力量。比如,依靠地方鄉紳士族負責當地賦稅的具體征收和上解工作,這實際上是將部分稅收征管成本攤派給了老百姓。而算賦、口錢這樣的以貨幣形式征收的稅收收入,其征管成本遠遠低于實物形式的田租,且便于運輸,漢代對百姓按丁征收人頭稅的制度安排也有這方面的考慮。事實上,漢代的田租收入十分穩定,一直在40億錢左右,而算賦、口錢的收入卻達到了80億錢甚至更高。唐初以來實施的租庸調制,就有一個重要的技術前提,即賬籍(戶籍田冊)制度和均田制度有效實施,而維持賬籍制度在當時的統計技術條件下卻是政府不可實現的浩大工程,隨著賬籍制的崩壞,加之后期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導致均田制無法推行,租庸調制已經面臨著破產,帝國政府面臨著巨大的財政危機,這就是楊炎“兩稅法”改革的直接動因[28]。
從漢唐兩代的賦稅制度運行看,征管技術是制度設計和制度實施的重要制約因素。一方面,征管技術的可獲得性直接影響著稅收制度的頂層設計與具體安排。比如,漢代的征管技術水平比較落后,加之統治者秉持休養生息、輕徭薄賦的治理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支撐了漢初“輕稅重賦”的稅收制度架構。另一方面,征管技術的運作成本直接影響了稅收制度的運行效果,決定了社會理想的實現程度。比如,唐代初期租庸調制的有效實施必然有賴于賬籍制度的完善和均田制度的持續實施,無論是賬籍制還是均田制的持續實施均需要花費相當大的行政和社會成本,特別是在當時的社會統計技術條件下,精準登記、及時調整、動態更新戶籍和田冊信息沒有技術可行性,加之后期行政系統懈怠和土地兼并問題加重,最終導致租庸調制變得無法繼續維持,不得已實施“兩稅法”改革。
(三)治理效能:稅收制度的運行結果
稅收制度的最終指向是治理效能,即稅收治理的效率和效益。以歷史的眼光看,漢唐兩代的賦稅制度均有很強的合理性,其基本運行狀態好于后世絕大多數朝代,稅收治理效能也達到了當時歷史條件下的較好狀態。但從另一方面講,漢唐兩代的稅收制度遠非完善,尤其是在實際運行的各環節中,存在著諸多的阻滯,整體運轉效率偏低,這一點集中反映在稅收征管的組織體系上。
事實上,漢唐兩代均建立了一套比較嚴密的稅收征收管理組織。漢代建立了一套涵蓋“中央—地方—基層”的稅收征管組織系統,在中央政府由大司農掌管錢谷幣帛,漢初負責全國財政稅收事務的官員仍稱“治粟內史”,景帝時期改稱“大農令”,武帝太初時期改為“大司農”,王莽時期改為“羲和”(后改為納言),東漢仍稱“大司農”。此外,還有專門負責賦稅征收的機構“算府”,地方(郡國)設有管理財政、稅收事務的官吏“上計吏”,基層設有“循算使者”“嗇夫”“鄉佐”等一線崗位,專門負責征收賦稅,但他們并非“正式編制人員”,他們要承擔政府攤派的征稅的任務,卻并不從政府預算中領取薪酬,有時甚至要為未完成的稅收任務“倒貼”。地方的上計吏在國家財政制度運轉中起到承上啟下、上傳下達的作用,也保證了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有力控制。出產鹽鐵等礦產品的地方,還設鹽鐵官員。實際上,漢代稅收征管組織體系遵循的是“隨事置吏”的原則,即根據需要設置稅收征管機構、配置征管人員[29]。
唐代在中央實施三省六部制,戶部主管全國的財政事務,屬下設戶部司、支部司、金部司和倉部司四司,分別掌管賦稅貢納、計算租稅物產、庫藏出納和軍儲祿糧等事宜。戶部之外,中央掌管財物的官職是司農寺,負責領導上林、太倉、鉤盾、導官四署;上林掌管苑囿園池,太倉掌管九谷廩藏,鉤盾掌管邦國薪芻,導官掌管導擇米麥。此外,唐朝還在刑部之下設立“比部”,比部的郎中、員外郎主要掌管監督、審計事宜,是當時的財稅監督、審計管理機關。玄宗開元年以后,朝廷面臨著較大的財政壓力,開始讓其他官員來兼職管理財稅事務,稱“度支使”或“判度支使”“知度支事”“勾當度支使”,有時還根據需要臨時派遣稅收專使,如“租庸使”“鹽鐵使”“色役使”等,用以加強對租庸、鹽鐵和戶口的管理。在地方,唐代的行政組織分為道、府、縣三個層級。相應地,地方的賦稅征收管理組織體系為:道設度支、營田、轉運諸使負責賦稅征收管理;府有司庫參軍和司倉參軍,司庫參軍掌管戶籍、記賬、道路、蠲符、雜徭、逋負(逃稅)等事宜,司倉參軍掌管公廨、度量、倉庫、租賦征收等事;縣有司戶和倉督負責稅務征收管理事宜;縣以下設鄉,鄉以下設里,里管理百戶人家,設里正一人,負責核查戶口,辦理賦稅征收事務,這是賦稅征收的最前線、最基層[11]。
從漢唐兩代的賦稅征管組織體系,可以窺見兩代的稅收治理效能。總體上看,這種組織體系是比較松散的,也是非對稱的。就松散性而言,從中央到地方,雖然有負責賦稅征收的機構、官員、吏屬和非在編工作人員,但其組織架構、人員知識結構均表現出較大的差異性。中央機構和官員強調制度的程序性,更多地關注賦稅收入的上解、庫存、支出、審計等事宜,而州縣機構和吏屬注重制度的執行性,更關心如何完成上級政府下達的稅收任務,至于如何完成任務、如何執行制度并不是關注重點,因而在實際執行中可能存在攤派、提前征收、加征耗羨等問題[30]。事實上,影響漢唐兩代賦稅治理效能的主要問題在于,行政成本和遵從成本過高,導致稅收征管的社會成本過高,治理效率總體偏低,而這一問題的根源在于帝國政治治理的幅員太大,稅收治理規模前所未有,地理阻隔帶來的物流成本過高,而征管技術的有限性又造成了稅收征收成本居高不下。
五、漢唐賦稅制度的現代啟示
考察漢唐兩代賦稅制度的演化史發現,不論是漢代的“稅賦役”制,還是唐初的租庸調制,抑或唐德宗時期的“兩稅法”,在特定時期都為政權的穩定成熟和有效運轉提供了有力支撐,為社會經濟發展和科教文化繁榮作出了積極貢獻。但審視歷史又會發現,漢唐兩代賦稅制度也給我們留下了深刻教訓。這些經驗教訓,雖然是歷史的,但也是現實的,對于現代稅收治理,尤其是對于中國式稅收治理現代化,具有重要的啟示。在高質量推進稅收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中,漢唐兩代賦稅制度史至少可以提供以下四個方面的鏡鑒。
(一)稅收制度理想必須根植于社會現實的土壤,所有的制度均要在實踐中接受檢驗
稅收制度的設計乃至稅制模式的選擇,均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原則,均要放在特定的經濟社會環境、特殊的國情政情中來考慮。稅收制度和稅制模式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需要根據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發展而做動態調整。漢代和唐代初期設計的稅收制度適應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就能運行得很好,為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王朝的上升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但隨著經濟社會條件的變化,稅收制度未能適時作出變革,導致嚴重的財政危機,最終成為壓垮帝國政權的最后一根稻草[11,14]。從漢唐賦稅制度史中應當汲取的教訓是,稅收治理必須適應經濟社會環境的發展變化,尤其是稅收制度設計和稅制模式選擇,既要從理論上考慮制度的學理邏輯,還要考量中國現實的制度土壤。唯有如此,中國才能真正實現稅收治理現代化。當前,中國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理想,持續深化稅制改革[31-32],將“實現共同富裕”的制度理想深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土壤,全面推進中國式稅收治理現代化。以稅收制度設計而論,各個稅種都還有不盡人意之處,尤其是流轉稅制度,未來還有較大的改革空間。比如,自全面“營改增”以來,營業稅退出歷史舞臺,但增值稅制度在全行業實施是否最優、多檔稅率與征收率并存是否科學、七成以上納稅人為小規模納稅人是否有效率等問題,都值得反思。以稅制模式選擇而論,到底是選擇間接稅為主體稅種,還是直接稅為主體稅種,抑或所謂的直接稅間接稅“雙主體稅種”,都需要結合當下中國經濟社會發生的巨大變化來考量。同時,所有稅收制度都要放到稅收治理實踐中去檢驗,唯有經過社會實踐檢驗的制度才具有生命力,也唯有建立一套具有生命力的制度體系才能實現中國式稅收治理現代化。
(二)稅收制度體系必須有稅收治理技術配套,變通執行可能會帶來嚴重的秩序問題
稅收治理技術屬于工具理性范疇,卻是稅收制度目標實現的保障,更是稅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支撐[33]。稅收治理技術與制度體系嚴重脫節,不僅無法實現既定的制度目標,還無法回應隱藏在制度設計背后的價值理性,更不能為推進稅收治理現代化提供實踐層面的支撐。在實踐操作層面,采用變通的技術手段向現實條件妥協是沒有出路的。變通的制度執行只能帶來扭曲的制度效應,并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后果,引發嚴重的稅收秩序問題。因此,在推進稅制改革的同時,必須同步深化稅收征管體制改革,為稅收制度的正常運行提供有效的征管技術和手段,從底層邏輯上夯實稅收治理的工具理性。這一點,在未來稅制模式的轉換選擇中尤為重要。從長遠看,選擇直接稅作為主體稅種更加科學,但如果做出這種選擇,需要在實施“提高直接稅比重”的改革之前,做好配套制度建設,尤其是構建起一套數字經濟時代的自然人稅收治理體系,在技術層面突破稅源信息不對稱的問題。更具體地講,如果要以所得稅作為中國現代稅制的主體稅種,必須以外匯、金融、不動產、信息等領域制度的協同配合,充分利用第四次科技革命創造的新技術、新工具,實現稅收征管技術手段與思維的創新與突破,有效掌握“收入來源于何處、資金要流向何方、財產分布在哪里”三個方面的稅源信息。如能實現此目標,自然人稅收治理的技術手段就實現了與制度變革“適配”,并推進稅收治理向著現代化的目標邁進了一大步。
(三)稅收基礎必須建立在具有彈性的標的上,稅收治理應當隨社會條件而動態調整
一方面,整個稅收制度的基礎應當具有彈性,即主要稅種的稅基均應當具有彈性,且總體上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成長壯大。在現代國家,稅收收入是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隨著社會治理多樣化的需求日益增多,財政支出面臨著持續的剛性增長壓力,稅收制度必須具有支持財政收入可持續穩定增長的潛力。從當前中國的稅制體系來看,流轉稅尤其是增值稅在經歷了長期高速增長之后,逐漸走向緩慢增長狀態,而所得稅和財產稅則因數字經濟帶來的社會物質財富在短期內海量聚集并快速增長而具有巨大的增長空間。鑒于中國的國家治理適于“共識性大政府”[34],未來公共財政支出的需求仍將保持較快增長,中國未來的稅收改革應當考慮對既有稅制做結構性調整,進一步“提高直接稅比重”,將稅收基礎放在更具有收入彈性和增長潛力的所得與財產之上。另一方面,稅收治理應當適應社會經濟條件的發展變化。就稅收制度而言,沒有一個稅種是最優的,也沒有一種制度是完善的,稅收制度的核心要義在于適宜、適合、適應。制度實施的外在社會條件與現實土壤在不斷發展變化,原來很好的制度可能變得不再適應發展需要,因而必須做出適應性動態調整。就稅收技術而言,治理的工具與手段永遠都在追趕不斷發生的新現象、出現的新問題、暴露的新漏洞,不能寄希望于一種稅收治理工具就能夠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必須堅持創新驅動、與時俱進,借助代表先進生產力的新發明、新技術,建構適應經濟新形態、稅收新業態的征管與服務新手段、新方式。
(四)稅收治理必須考慮治理規模與治理成本,在既有約束條件下實現治理成本最小化
所有的治理實踐均有一個核心指標——治理規模,而這一問題卻往往被理論界與實務界所忽略[35-36]。治理規模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治理規模不僅會影響治理手段的效率與效能,還會帶來治理成本的巨大差異,因為在治理實踐中不僅存在著規模成本遞減的問題,還存在著規模成本遞增的問題,甚至后者是一種更為普遍的現象。稅收治理實踐亦是如此,必須考慮稅收治理規模及與之相關的治理成本問題。唐初租庸調制最終破產,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在一個超大規模的中央集權制帝國范圍內,普遍實施統一的稅法,其治理規模前所未有、冠絕中外,而統治者恰恰對這一問題未引起足夠重視甚至直接忽略了。更重要的是,由于租庸調制依賴于嚴格的賬籍統計制度和有效實施的均田制,稅收治理技術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無法勝任治理任務,至少無法以有效控制的成本完成既定的治理任務,最終造成一項飽含理想與情懷的稅收制度難以為繼。在推進中國式稅收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中,必須高度重視稅收治理規模與稅收治理成本問題。在既定的稅收治理規模下,必須科學設計稅收制度要素,合理選擇稅收治理技術,確保以最小化的治理成本實現最大化的治理收益。一些在當前階段無法實現的治理目標,可以按照“步步為營、穩扎穩打、分段實施”的原則,借助稅收治理技術的進步和稅收制度的完善逐步實現。
六、結論
本文在比較研究漢、唐兩代賦稅制度的基礎上,揭示了從漢到唐的制度演化邏輯,并從社會理想、征管技術和治理效能三個層面對二者進行了比較分析。西漢的稅收制度體系以“稅—賦—役”為基本制度框架:稅是以實物形式征收的稅種,主要包括田租、藁稅、工商稅收等;賦是以貨幣形式征收的稅種,主要包括口錢、算賦、算車軺、算緡錢等;役是以勞役和兵役形式征收的稅收,在西漢役已經可以改折貨幣征收。唐代的稅收制度體系,經歷了由租庸調向“兩稅”的轉型。租即地租,按畝征收;調即戶調,依鄉土所產,按戶征收;庸即折庸,勞役義務可以折算為貨幣繳納,折納貨幣的過程就稱為“折庸”。德宗時期實施的“兩稅”,核心含義是將所有稅收義務整合在一起,分夏秋兩季征收。漢、唐兩代的稅收制度,既有著各自的獨特時代特征,又有著共同的制度邏輯。總體上看,漢、唐兩代的稅收制度均反映了“稅收理想—征管技術—治理效能”的邏輯統一,均有著稅收制度的價值觀照,受到征管技術的現實約束,也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展現出了較高的治理效能,因而能夠歷經百年而不衰,只是此后的社會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稅收制度未能及時做出適應性調整,導致整個國家財政的失敗。
漢、唐兩代的稅收制度雖然有不盡完美的地方,但其制度設計、實踐操作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展現出了較強的生命力。與此同時,漢、唐兩代稅收制度的最終失敗,也給中國留下了很大的反思空間,這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對于現代稅收治理仍然有著重要啟示。第一,稅收制度理想必須根植于社會現實的土壤,所有的制度均要在實踐中接受檢驗。好的制度均是理想與現實有效銜接、有機融合的制度,在稅收制度的設計過程中,必須充分考慮現實條件,確保制度理想能夠切實轉化為制度現實。第二,稅收制度體系必須有稅收治理技術配套,變通執行可能會帶來嚴重的秩序失范問題。征管技術是稅收制度理想實現的上限,稅收制度的運行受制于現實的、可獲得的征管技術,因而稅收制度的設計必須配套相應的征管技術,以確保制度理想、政策目標順利實現。第三,稅收基礎必須建立在具有彈性的標的上,稅收治理應當隨社會條件變化而動態調整。稅收制度所處的社會外圍條件是處于不斷變化之中的,稅收制度也不能一成不變,因而必須根據社會環境的變化而及時做出適應性調整。第四,稅收治理必須考慮治理規模與治理成本,在既有約束條件下實現治理成本最小化。所有的治理實踐都是一個資源消耗的過程,都會產生各種不同的治理成本,因而必須考慮治理成本的問題。就現代稅收治理而言,必須在綜合考量治理規模等因素的前提下,努力以最小的治理成本實現最大的治理效能[1]。
注釋:
① 關于唐代租庸調的具體征收標準,不同的典籍記錄可能有差別,最常見的權威典籍包括《舊唐書》《新唐書》《唐會要》,但正是此三者關于“調”征收標準的記錄不一致。《舊唐書·食貨志》載:“調則隨鄉土所產,綾、絹、絁 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綾、絹、絁者,兼調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唐會要》載:“調則隨鄉土所產。綾絹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綾絹絁者。兼調綿三兩。輸布者。麻三觔。”學術界的主流觀點認為,實際征稅標準應為綾、絹、絁任意一種二丈,而非各二丈。理由有二:一是如果每種征收二丈,不符合“隨鄉土所產”的原則;二是如果每種征收兩丈,對丁戶而言負擔過重,有違唐初“輕徭薄賦、與民生息”的開國政策。因此,本文采信《新唐書》的說法。
② 關于“兩稅”到底是原來的租庸調還是其他,學術界并無定論。主流觀點認為,“兩稅”就是原來的租庸調,但也有學者考證認為,“兩稅”并不是簡單的租庸調合并翻版,而是田租、戶調。本文采信學術界的主流觀點,認為“兩稅”的主要內容還是租庸調,核心要義是分夏秋兩季征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