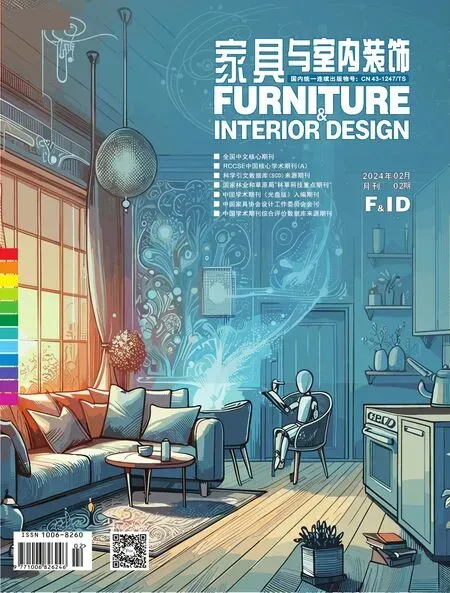家具設計的現代
■許美琪
當代國內的家具設計需要回答三個問題,一是家具設計的現代、二是家具設計的現代性、三是家具設計的現代化。“家具設計的現代”指的是現代家具設計是怎樣產生的,現在它達到了一種什么樣的狀態,還在怎樣發展;“家具設計的現代性”指的是現代家具設計所持的世界觀,即現代家具設計對世界的認知和態度;“家具設計的現代化”指的是現代家具設計的方法論,包括它的產業鏈建設、所采用工具和手段等。如果不能正確地認識這三個問題,我們就始終在黑暗的隧道中摸索,而找不到它的出口,從而不能實現真正的現代家具設計。
本文先討論什么是家具設計的現代。
1 西方家具設計的現代
先得從西方設計從古典走向現代說起:從古埃及、古希臘、古羅馬、拜占庭、仿羅馬式、哥特式,然后到中世紀至文藝復興時期,其中受到伊斯蘭的重大影響,接著是巴洛克、洛可可及以后的新古典主義風格,西方古典家具似乎走到了它的終點。隨后的復古主義風格只不過是昔日輝煌的回光返照。
但是17和18世紀資本主義的發生和19世紀的發展成熟(自從15世紀哥倫布發現美洲,歐洲向美國殖民以后,西方也就包括了美國),至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現代家具肇始了。從托耐特的彎曲木家具開始,英國最初提出了工業設計的思想及至莫里斯的工藝美術運動,直到后來一系列在設計理論方面的探索如新藝術運動、英國格拉斯哥學派和美國芝加哥學派、德國工業同盟等,最終由風格派和包豪斯在20世紀30年代確立了現代家具設計的基礎,現代家具開始形成。
在西方現代家具形成過程中,現代主義的先鋒們認識到一些淺顯而樸素的真理:
其一,是在工藝美術運動興起時,機械化與手工技巧之間的對立就是一個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1834-1896)強烈地反對機械化生產方式,工藝美術運動的建筑師和設計師查爾斯·維森(Charles Voysey,1857-1941)則認為機械化生產為現代家具設計提供了一席之地,特別是中產階級迅速崛起,對批量生產家具有迫切的要求。他爭論道,機器最終能生產出良好設計的家具,且為所有人的經濟能力所及,而不只是為精英階層所生產,所以要跳出莫里斯的“悖論”,一方面要有精致美麗的手工制品,而另一方面,這種所謂“簡樸的”家具已遠非一般大眾的財力所及。
其二,是在1905年維也納工場就宣稱:“他們的指導原則是功能,實用是我們的首要條件,我們必須強調良好的比例和適當地使用材料。在需要時,我們會去做裝飾,但是我們不會不惜代價地去做。”
其三,是1908年德國工業同盟的成員阿道夫·路斯寫了一篇題名為“裝飾的罪惡”的論文,提出這樣的觀點,過度的裝飾將敗壞社會,最終導致犯罪。稍后的1924年,該同盟的出版物《沒有裝飾的形式》圖文并茂地表述了用工業設計原理做出的更簡單、更合理的設計的好處。1928年,密斯·凡·德·羅繼而提出了“少就是多(Less is more)”的原則。
其四,是西方設計史上的一個轉折點發生在1919年,它改變了現存的全部設計教育的概念。格羅皮烏斯(Walter Gropius)在德國的魏瑪(Weimar Germany)辦了兩所藝術學校,創立了包豪斯建筑學院(Staatliches Bauhaus)。第一次真正以學術的體系來促進現代觀念。包豪斯設計哲學的一個原理是形式必須符合功能和工業化的機械生產,它成為現代運動的一項基本信條。
在這個波瀾壯闊的現代主義思潮中,涌現了一大批杰出的人物,諸如麥金托什(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1868-1928)、C.R.阿什比(C.R. Ashbee,1863-1942)、里特維爾德(Gerrit Rietveld,1888-1964)、布勞耶(Marcel Breuer,1902-1981)、阿爾托(Hugo Henrik Alvar Alato,1898-1976)、勒·柯布西耶(Le Carbusier,1887-1965)、密斯·凡·德·羅(Miss Van Der Rohe, 1886-1969)、瓦爾特·格羅皮烏斯(Walter Gropius,1883-1969)和伊倫·格雷(Eileen Gray, 1878-1976)等人,他們都以非凡的才華,各自為現代主義設計做出了偉大的貢獻。
1900年至1945年現代理念的發展塑造了這一時期西方家具設計的歷史,然而直到1945年以后,這種設計理念才與大眾市場相合拍。在幾年以后,這種技術的機械化潛力才顯示出來,但在當時既要保持這種設計理念的完整性,又要把他們的理念轉化成現實,在技術上不能做到。當代的設計師最終才把戰前的現代主義“視覺”與技術結合起來,使它們成為可能,在家具制造業中使先前的可能性成為夢想不到的現實。
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家具設計才從建筑中脫離出來,真正具有了獨立的地位,成為工業設計中的一個門類。這是家具設計的現代,它的主要理論是現代主義。1970年代第二輪全球化興起和1980年代的冷戰結束,世界格局出現了新的變化,面對深刻的經濟和社會危機,現代設計出現了多種思潮和流派,諸如后現代主義、晚期現代主義、解構主義、新現代主義等等,但對這些紛紜復雜的各種設計思潮和流派的觀念上的認識,必須從真正了解現代主義開始。
在現代主義主導設計的過程中,西方家具又經歷了重構和理性主義、有機風格、流行文化、后現代主義中的舒適主義、改革和競爭三個派別和折衷主義的一系列風格演變,到1970年代開始的第二輪全球化,東西方家具開始出現融合,西方現代家具在進一步的發展中更多地表現出全球化的特點[1-4]。
英國著名工業設計史家費耶爾(Peter Fiell)在《20世紀的設計》一書中描述了整個設計界出現的變化:“在整個20世紀,設計的產品、款式、理論和哲學一直在變化,這是由于設計過程的復雜性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不斷加大。工業生產中的設計在不斷增多,通過一系列的相互聯系的專業活動,諸如模型制造商、市場分析人員、材料學家、工程師和生產技術人員等的活動,理念、計劃和制造之間的關系被細化了,變得更復雜了。設計成為了一個多方的切磋過程,而不是單個設計師的成果,是團隊努力的結果,對于事情應該是怎樣的,他們中的所有人都有自己的理念和看法。20世紀設計中的歷史多元性也是由消費方式的變化、品味的變化、不同的銷售方式、投資者、設計師、制造商的心理需要、技術進步和各個國家在設計中的發展趨勢所決定的。
在研究設計的歷史中,必須認識到,要完整地理解產品的設計就不能夠離開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和技術之間的相承關系,正是這種關系產生了設計的概念并最終使其實現。在20世紀的不同時期,例如,西方經濟的周期對設計有著顯著的影響,有時盛行設計超越款式,有時或者相反。款式常常是設計方案中的一個補充成份,設計(design)和款式(styling)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它們有各自的準則。款式關注的是表面處理和外觀,是產品品質的表達;在另一方面,設計則主要關心問題的解決——在它的范圍里趨向于歷史性地解決問題,一般來說,是要找到最簡單和最本質的東西。在經濟滑坡時期,功能主義(設計)處于顯著地位;而在經濟繁榮時期,反理性主義(款式)則易于張揚。
在整個20世紀,對能創造具有競爭力的生意的興趣日益增加,這促進了設計的變革和多樣性,同時也使設計師的生涯改觀。一些設計師在共同的機構中工作,另一些是以咨詢或個體的方式工作。許多獨立的設計師選擇了不受工業生產束縛的方式來工作,他們設計的作品主要關心的是自己意念的表達。設計不僅是與機械化生產相聯系在一起的過程,它還是一種關于事情應該是怎樣的,是應當根據個人來做還是根據集體、機構或國家的目標來做,從而去勸說別人同意自己的觀點、看法和價值觀的手段。作為人們交流的一種渠道,設計提供了一個特殊的視角來認識一系列問題,即設計師的個性、思想;對在目標(設計所追求的)和使用者、消費者之間的關系中什么是重要的;設計過程和社會是什么關系等。
20世紀在設計上使這些概念、風格、運動、設計師、學派、公司和機構具有了特點,正是它們構成了設計理論和實踐的過程;或者說促進了造型創新、材料應用、技術手段和工藝的發展;也或者說,正是它們影響了品味、應用和裝飾藝術風格的演變、一般的文化和社會進程[5]。
這幾段文字也是對現代主義后西方的“家具設計的現代”(Modern Furniture Design)的一種客觀理性的描述,或者更貼切地說,這是對西方“家具設計的當代”(Contemporary Furniture Design )的一種客觀理性的描述。毫無疑問,它對中國家具設計也具有相當程度的借鑒價值和意義。
2 中國家具設計的現代
中國有著悠久的傳統家具設計的歷史,近代以來受到西方文化的強勢沖擊和影響也開始進行現代家具設計,清末民初的海派家具設計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但由于眾所周知的歷史原因,在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現代家具設計的創新才真正受到社會和行業的倡導和重視,到現在為止尚不足半個世紀。在我國家具業發展初期,較長時期曾追隨以意大利為代表的國際化風格,大多數企業熱衷于模仿,而較少關注創新。由于創新能力的匱乏,許多企業除了在造型上以模仿加改造之外,始終難有根本性的突破,單一思維模式導致了產品設計的同質化和家具市場的單元化。到2010年代中期,隨著中國家具業的發展壯大,開啟了“新中式”的設計探索。新中式家具有三層含義:首先,它是一種中式家具,因此它必定具有中式家具的內容,積淀了中國歷史文化;其次,它是將傳統與現代融合的中式家具;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它帶有創新性,是適合現代中國人生活方式的家具。在這種探索中,雖然出現了許多好的設計作品,也還有不少設計由于固守中國傳統家具的造型、結構和裝飾等元素而顯得繼承有余但創新不足。顯然,“新中式”還不夠成熟,尚不足以成為一種具有獨特風格的中國現代家具。
到目前為止,中國家具設計還沒有能夠建立起創新思想、體系和可操作性的運作模式。這個體系應當包括設計的創造者——大學和研究機構、設計師個人;設計的傳播者——設計教學體系、各類應用設計的企業;各類設計服務專業機構,它們包括潮流研究、市場策劃、產品設計、服務設計、工程技術、文化傳媒、信息采集與加工、知識代理和消費向導等各色人士與組織。為了保持這個體系的可持續發展,還必須有對自然和社會環境的研究、認知和宣導,政府制訂相關的政策和法規,和諧社會所具有的有序狀態,公民的自覺意識和企業的自律行為。
對于尚未實現全面現代化的中國家具業來說,這種匱乏是很自然的,但這并不等于我們無可作為。我們在建立中國自主的家具設計方面可以從以下幾點入手:
首先,要從設計教育抓起。在我們的高等院校里,最大的問題是沒有動手做的機會。在國外,學習設計之后要到實習車間做出樣品,以確保設計的東西能做出來。這對將來的工作很重要,然而國內高等院校一般都不具備這種條件,學校也沒有將實習制作作為教學中的“必要條件”。國內的家具設計教學還沒有達到“教學—實習—商業化”的水平。這種狀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亟需改變。
其次,我們急需進行自己的家具文化建設。家具既然是一個深具文化內涵的產品,它的設計就不能離開文化。一方面是西方的文化,但更重要的,是我們中國的固有文化。中國的明式家具是世界家具文明的瑰寶,它的設計思想和造型元素至今仍然具有很高的價值。現代的中國人有著現代的東方文化,它既是傳統文化的繼承,更有在不斷吸收人類文明的全部成果而發展起來的內涵。這些就是現代中國家具風格的文化基礎。問題在于我們怎樣在進行家具設計時從這種文化中發掘出創作的靈感,去吸收它的養份。設計的文化性,決定了它是一種文明的延續。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是大力培育年輕一代的設計師,這樣才能使一代一代的設計薪盡火傳。在培養中,關鍵的是訓練他們善于想象一個現實中并不存在的世界,通過他們的設計把它創造為現實。這個想象的世界正是對生活新的追求。設計是一種創造,它帶給人們的是美好的未來。
因此,對中國家具的現代設計理論和實踐提出一些基本的考慮:
(1)中國現代家具若沒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現代風格,在國際家具市場上將沒有位置,中國現代風格的家具必須具備優秀傳統和不斷創新這兩個特點才能生存發展。
家具實際上表現了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的消費水準和生活習俗,它的演變實際上也表現了社會、文化及人的心理和行為的認知。改革開放以來,西方文化和東洋文化的大量導入,現代的中國人已經開始認同多元的文化,但是中華民族有著幾千年的文化積淀,中外文化的交融和沖突更顯示出多采、復雜的一面。不管怎樣,中國已經把現代化作為走向未來的目標,而多元文化就必然成為我們的選擇。多元文化一方面以現代化作為價值導向,另一方面它的具體構建卻只能付之于特定的民族形式,這已是為世界歷史與現實所證明了的(例如歐洲與日本的現代化和美國的現代化是不同的,各有其特定的民族形式)。中國現代風格家具的文化背景要求中國的現代家具應以中國的民族形式,體現現代化的功能和藝術需求,這也是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狀態所決定的。
(2)中國的傳統家具固然留給我們豐富的遺產,但是不能簡單地認為它就可以作為現代風格的民族形式載體。中國現代風格的家具民族形式載體應該是傳統與繼承傳統的現代中國文化的結合。這就要求:一方面,要用現代的科學手段,對中國的傳統家具進行專業化、立體化和定量化的深層次研究。只有如此,才能充分揭示出其中所含的設計思想和科學精神,提煉出所謂的“中國式傳統因子”,用符號學的方法抽提出傳統的造型和裝飾的元素;并找出由于當時科技水平及其它限制條件對中國傳統家具設計的影響點,在此基礎上注入現代因子,拓展設計思想,為中國現代風格家具的開創提供比較明確的、可遵循的理論依據和操作途徑。以建筑和服裝為例,石庫門建筑是具有濃郁地方特色的上海建筑,改造后的“新天地”,更像是歐洲小城里某個溫馨舒適的小廣場,與上海人的石庫門住宅其實已經沒有什么關系,但這才是石庫門或者說上海的精髓——在中西融合的基礎上加以創新的東西。在服裝上也有類似的例子,滿清的旗袍竟可以做成如此曲線畢露又含蓄溫柔的款式;唐裝也能大顯風采,特別是在北方童裝上更顯示其民族的特色。
另一方面,現代的中華民族在文化形態、生活方式上已與傳統有天壤之別,在功能上的需求也大相徑庭。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復制優秀的傳統家具,而是深悟其道,在家具的品種、造型、功能上演衍、創造。中國的現代風格家具應深具東方的文化神韻,又具備現代生活所需的品種和功能。
3 結語
中國現代家具風格的構建是需要假以時日的,需要幾代人薪盡火傳地持續努力,而且還必須在社會轉型基本完成進入穩定時期才有可能實現。但是,現代人是站在傳統與未來橋梁上的人,既背負著過去,又展望著未來。因此,我們現在就應該做起來,而當我們倒下,兒孫們接過我們手中的工作時,會理解我們的光榮與夢想,會感嘆我們的奮斗與努力,更會感謝我們為他們鋪墊的基石。“子規半夜猶啼血,不信東風喚不回。”我深信,當中國成為世界強國的時候,中國家具業也會以同樣燦爛的家具文明為人類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