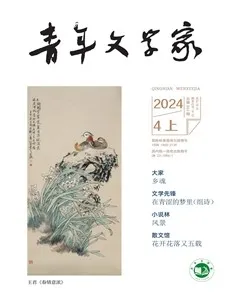炊煙,縈繞在心間
田國和
也許是在城市生活久了,也許是年齡已逾花甲,每每閑暇時,常常不由自主地透過窗戶或陽臺,眺望遠處濃濃墨綠下一個又一個的村莊,希望能看到裊裊升起的炊煙,終因距離太遠而目不能及。
天朗氣清,惠風和暢,紗窗吹進泥土氣息的風,驀然深藏的記憶隨之浮上心頭。
想到我生活過的村莊,想到房屋上粗細高矮不一的煙囪,炊煙它曾以獨特的顏色,描繪了我在故鄉的農家歲月。
半個世紀前,大多農村還沒有電,莊戶人燒水做飯都使用大鐵鍋,燒柴一般為秸稈、樹枝、樹葉,炊煙除了青白色外,還散發著一股股淡淡的柴火與樹葉味,其中還夾雜著油鹽醬醋的味道,以及蔥花、芫荽、肉菜、面食的絲絲香氣。縷縷炊煙,淳樸的故鄉,淳厚的父老鄉親,滿院悠然刨食的蘆花雞,樹上院內飛來飛去的麻雀,皆是屬于平民百姓的生活原色。
寂靜的村莊是被大紅公雞的啼鳴叫醒的,也叫醒了勤勞的莊戶人,主婦們點燃灶火,拉動風箱,燃燒的灶膛,跳躍的火苗,淡藍色的炊煙悠然升空,彌漫在鄉村的上空。晨曦中,炊煙又如同仙女的飄帶,將寧靜諧美的村莊裝點得如詩如畫。
中午和傍晚的炊煙,似乎還兼做報時的掛鐘,田中勞作的男人們一旦看到村子里屋頂上飄出縷縷炊煙,便知道飯要熟了,立馬收拾農具往家里走;那些村巷嬉戲玩耍的孩子,聞到炊煙的味道,肚子立馬咕咕叫,往往還沒等娘站在大門口呼喊,便迫不及待地往家里跑,進門直撲灶房:“娘,我餓了,飯好了沒有?”
荷塘邊幾戶小院夕陽下的炊煙,猶如碧藍色的波紋,到了橋邊,順勢拐了個彎,那河畔金柳枝條的搖曳,水面波光里的艷影,樹梢掠過的飛燕,近處蔥綠的田野,相映生輝,既有煙霧繚繞的朦朧美,又有鄉間的寧靜與和諧。戴斗笠背草筐的人,緊跟身后的小黃狗點綴其中,儼然一幅頗有江南水鄉韻味的圖畫。
逢連綿細雨或多霧天氣,氣溫偏低,尤其在早晨或者傍晚,濕濕的地氣,像是把炊煙吸住了一般,戀戀不舍地在村莊的上空縈繞,又像是頑皮的孩子,在房頂瓦片上,樹木的枝頭上,歡快地扭來扭去,等玩兒夠了才慢慢地消失,回到自己的家……
傳統節日及村里有嫁娶的喜慶日子,炊煙仿佛也在分享快樂,舞動著,跳躍著。廚房里彌漫著豐盛飯菜的香氣,久違的誘人氣息讓人不禁垂涎欲滴,街巷門口聊家常等飯熟的漢子,話語中掩飾不住對未來的憧憬和向往。平凡世界中的平凡農家,經冬復歷春,平淡生活里追光而遇,沐光而行,萬事順遂。
猛然間,我似乎找到了身居異鄉的人為什么喜歡看鄉愁文學作品的答案,不是因為作品有多么優美,而是背井離鄉的人在外不容易,想家的人太多了。特別是生于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農村的這代人,點過煤油燈,看過露天電影,看過連環畫,騎過二八大杠自行車,拿著玉米稈當甘蔗,大田里偷過瓜,小河里逮過蝦,小時候畫在手腕上的表從來沒有走過,卻帶走了我們美好的時光。小時候小賣部的東西都想買,可口袋里沒有錢;現今超市里的東西都能買,卻不知道買什么了。小時候哭著哭著就笑了,現在卻笑著笑著就哭了。
小時候期待詩和遠方,長大了才知道故鄉才是真正的詩和遠方。曾天真地以為外出謀生很風光,回到家后才明白,那些守著故土老宅,在家陪伴父母妻兒的人才是真正有本事的能人。
當我再次向外瞭望,恍惚中,仿佛看到了遠方村莊的炊煙,自然、生動、飄逸、親切、溫情。多希望在胡同的拐彎處,有年輕的父親在那兒等著童年的我放學回家。
小時候真傻,竟然盼著長大……
傳統的年夜團圓飯越來越近,漂泊在外打拼謀生的人正準備或已經走在歸鄉的路途上。回家,炊煙像一條彎彎曲曲的紐帶,指引著歸心似箭的游子,從遙遠的他鄉急速奔向魂牽夢縈的村莊,回到充滿愛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