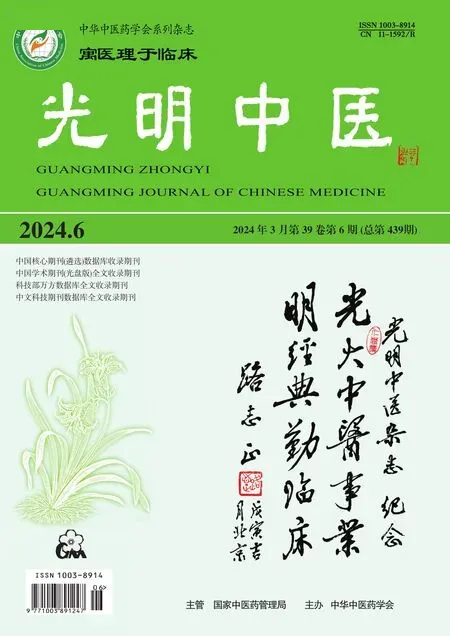升陽瀉濕法治療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初探*
李 垚 許 珂 劉亞蘭 錢彥艷 周 鑫 李美瑾 羅明麗 廖冠宇△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是指除酒精和其他明確的肝損害外因素所致,以彌漫性肝細胞大泡性脂肪變性為主要特征的臨床病理綜合征,包括非酒精性單純性脂肪肝(Non-alcoholic simple fatty liver,NAFL)以及由其演變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NASH)、脂肪性肝纖維化和肝硬化[1]。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是現代醫學病名,中醫古代文獻中并無記載,但根據其發病特點和臨床表現,可歸屬中醫學“脅痛、脹滿、積聚、肝癖”范疇[2]。一些關于該病的證候學研究觀察到,其癥狀以倦怠乏力、脘悶、納差、便溏等為主,證候也多以濕邪困阻證為主[3,4]。其病因病機,多為素體肥胖,飲食肥甘厚味,勞倦失宜,損傷脾胃,導致脾胃失于運化,濕濁內生,或為痰濕,或日久釀生濕熱,濕滯于內,阻滯氣血,甚則出現氣滯血瘀,整個病機演變非常復雜和多樣化。云南戴氏經方醫學流派為云南省自清末以來最重要的流派之一,已歷百年,該流派“經時結合”,重脾胃,思想開放,提倡包容,借鑒古今,學以致用,古為今用,繼承發明。戴氏流派在診療脾胃病方面,非常推崇李東垣和黃元御的思想,認為東垣獨辟脾胃病一門,而黃元御為古來論“中氣”最全者。筆者在長期對NAFLD患者的觀察和診療中,發現整合運用李東垣和黃元御的醫學思想來指導對NAFLD的治療,有著令人滿意的療效,分析探討如下。
1 理論源流
李東垣為易水學派的主要代表醫家,師承于易水學派的開山宗師張元素,在重視臟腑辨證的基礎上,結合《黃帝內經》《難經》探討了脾胃與疾病的關系,結合其臨床實踐總結,提出“內傷脾胃,百病由生”的觀點,開創了脾胃病學。他強調脾胃清濁升降在維持生理機能方面的重要作用,重視清陽之脾氣在疾病的病機和治療中的重要性。在治療上,運用甘溫之劑治療虛損及不足之證,繼承易老藥性“風升生”的理論[5],并運用于升發脾氣上,使“風藥”的臨床運用上升到一定高度。黃元御以中氣升降闡述疾病,以陽衰土濕,水寒木郁論述病機,治療以補火燥土,瀉水達木為大法,貴陽賤陰,反對苦寒滋膩。
上述兩位醫家的所處年代間隔較遠,東垣所在的易水學派持臟腑辨證,用藥講究臟腑歸經、四氣五味,以及“引經報使”和“風藥”。而黃元御為清代尊經醫家,尊經派的特點是崇古,以仲景及六經為宗,藥法也以仲景和《神農本草經》為正朔,斥責易水學派中的藥物運用屬“亂《本經》之旨”,思想較為偏激。但是,將這兩位醫家的脾胃理論和中氣思想進行有機整合,是中醫臨床診療的有益嘗試。
隨著現代社會民眾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飲食、工作節奏和環境的改變對人的健康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飲食不節,饑飽失度,易傷脾胃,導致脾胃納運失調,致使脾胃虛弱或脾胃不和;過逸少動,厚味肥甘,辛辣煎炸,高糖飲料,西式快餐等飲食物的攝入,損傷脾胃,致使脾胃運化失健,濕濁內生。濕為陰邪,脾為太陰濕土,同氣相招,故而濕濁之氣極易困脾,更傷脾胃。脾主升清,胃主降濁,脾以升為健,胃以降為和。脾胃為濕濁困阻,清氣不升,濁陰不降,升降失司,中氣反作,滯于中焦,造成脾虛濕困,是該病的根本病機,故見倦怠乏力、胃脘痞悶、納差;清氣不升可見便溏;“清陽實四肢”,脾虛又為濕困,脾即不主四肢,可見四肢無力、懶動,舌苔膩,脈滑。脾為太陰濕土,濕為本氣母氣,胃為陽明燥土,得燥金余氣為子氣,子氣之燥不敵母氣之濕,加之“陽明劂陰不從標本,從乎中也”,濕為陰邪,易傷陽氣,故中焦濕濁之病日久多從濕化和寒化。厥陰肝木,主疏泄,以暢達為性,如己土脾氣不升,戊土胃氣不降,中氣升降反作,亦可導致木氣不能疏達,郁而賊土,加重脾胃的損傷;木胎君火,與膽互為表里,膽藏相火,如木郁日久而化火,致使少陽相火不能降于癸水而浮于中焦,和濕濁之氣成為濕熱,使病情出現變化,產生變證,可見脅肋脹滿或痛,口干口苦,甚或黃疸。筆者認為,肝失疏泄在此病中,為中氣升降失司后的一個病理環節,屬次要的,并非主因。
2 臨床證治
臨床上,NAFLD患者常見癥狀主要有倦怠乏力,四肢無力,頭暈,不耐疲勞,脘悶,便溏,可有畏寒肢冷,或口干口苦,煩躁,尿黃,舌苔黃。部分患者可能沒有癥狀,僅見舌苔薄膩,脈滑。綜合癥狀分析,該病病位仍以中焦為主,脾胃虛弱為本,濕濁氣滯為標,有偏寒化或熱化的不同。
辨證論治上,筆者在總結臨床觀察和證治療效的評價后認為,以李東垣升陽益氣結合黃元御燥土達木的方法治療該病,可以使患者較快減輕癥狀,改善精神狀態。常根據四診所得進行辨證。
2.1 濕濁內蘊這類患者癥狀輕微或者沒有癥狀,僅可見苔膩,脈滑,精神狀態好,飲食及二便均正常,睡眠無障礙。僅在體檢時超聲波發現“中度或重度脂肪肝”,可有肝功能的輕度異常。雖然這類患者沒有太多癥狀可辨,但可根據肝臟中過多的脂質導致脾胃運化失司所致濕邪內蘊,進行辨治。治以利濕化濁。寒熱均無偏盛的情況下,筆者常用三白湯(白術15 g,白芍15 g,茯苓30 g)加味治療,酌加木香6 g,紫蘇梗10 g,陳皮6 g等以芳香之氣以利濕化濁;“風性勝濕”,稍佐防風5 g,升麻5 g,柴胡6 g等,升清勝濕。苔厚膩加厚樸10 g,藿香9 g,麩炒蒼術12 g,豆蔻6 g,薏苡仁30 g芳化燥濕;苔黃加竹茹10 g清膽化濕。
2.2 脾虛濕困患者臨床可見倦怠乏力,脘悶腹脹,食欲不振,惡心,口淡,便溏,頭暈,頭痛,四肢乏力,不耐疲勞,可有口干或苦,或有畏寒,四末欠溫等癥狀,舌淡或淡紅,苔薄膩或厚膩,或黃膩,脈細滑或弦滑。治以益氣健脾燥濕。寒熱無偏盛的情況下常以七味白術散(黨參20 g,麩炒白術15 g,茯苓30 g,葛根12 g,藿香6 g,木香6 g,甘草6 g)加味,可加防風6 g,升麻6 g,柴胡6 g以升陽勝濕;濕盛,舌胖苔水滑,可加澤瀉15 g,豬苓12 g淡滲利濕;食后腹脹加焦山楂30 g,炒麥芽15 g,炒稻芽15 g健脾助運;乏力肢軟加黃芪30 g;便溏加山藥30 g補脾止瀉;畏寒肢冷加干姜15 g溫中;或用理中湯(黨參25 g,干姜15 g,麩炒白術15 g,炙甘草6 g)加味,亦可以黃元御“黃芽湯”(黨參20 g,干姜12 g,茯苓30 g,炙甘草9 g);食欲不振加砂仁(后下)6 g溫中開胃;惡風,加黑順片(先煎)15~60 g散寒、補火生土;腹脹加烏藥10 g,紫蘇梗10 g散寒理氣;口干口苦、頭痛、煩躁、眠差,苔黃者,酌加竹茹10 g,炒黃芩10 g,蘆根30 g以清膽利濕、瀉肝疏木。
3 典型醫案
案1:鄭某某,女性,51歲。因“乏力5年余”來診。患者從事國企管理工作,10年前體檢,經彩色超聲多普勒檢查提示:肝臟脂肪性改變,近5年來,每年體檢均診斷:肝臟脂肪性改變(中-重度),三酰甘油和膽固醇均顯著升高,經降脂治療1年余,血脂檢測值在參考值上限,肝功能檢測值在參考值范圍內,但彩色多普勒仍然提示肝臟脂肪性改變為中-重度,有明顯的乏力、便溏,飲食正常,無明顯肝區不適,伴活動后頭昏、口干,易疲勞;舌淡紅,苔薄白膩,脈細滑。中醫診斷:濕阻病,證屬:脾虛濕困,治以:健脾疏木、利濕升清;方用:七味白術散加味,方藥:黨參25 g,麩炒白術15 g,茯苓30 g,炮姜12 g,葛根12 g,升麻6 g,廣藿香9 g,木香6 g,防風5 g,炒杭白芍12 g,紅景天15 g,炙甘草6 g。水煎服,每日1劑,每周服藥5 d。以此方為基礎加減治療1個月后,乏力顯著減輕,大便成形,8個月后,單位組織體檢,省級三甲醫院彩色多普勒提示:肝臟脂肪性改變(輕度),血脂檢測值在參考值范圍內,患者一般情況好,無特殊異常不適感。
案2:汪某,男性,53歲。因“畏寒,乏力10余年”來診。患者為公務員,既往無飲酒史,有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病史10余年,于2020年單位組織體檢,經彩色多普勒診斷:脂肪肝(中度),此后2次復查均提示:肝臟脂肪性改變(中度)。患者乏力、易疲勞,煩躁,怕冷、惡風,便溏,飲食減少,舌質淡胖,苔薄膩,脈沉細。中醫診斷:濕阻病,證屬:寒濕困脾;治以:培土瀉濕、補火升陽;方用:黃芽湯加味;方藥:黑順片(開水先煎4 h,煎透口嘗無麻味為度)45 g,黨參25 g,干姜15 g,茯苓30 g,澤瀉15 g,麩炒白術18 g,升麻6 g,獨活6 g,紅景天15 g,炙甘草12 g。水煎服,熱服,每日1劑,每周服藥5 d,忌生冷,避風寒。以本方為基礎,加減治療約半年后,2次于省級三甲醫院行彩色多普勒檢查均提示:肝臟脂肪性改變(輕度),患者乏力,怕冷等癥均不明顯,大便成形,精神較佳。
按語: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辨治,須四診合參,不可一味地活血、祛濕、理氣、疏肝。案1在癥狀上有乏力、活動后頭昏、易疲勞、便溏等氣虛不足之癥,舌脈提示虛與濕之象,證屬:脾虛濕困,方用:七味白術散。其中四君子湯平補脾氣;廣藿香、木香芳香化濕,醒脾理氣而不耗氣;葛根、升麻、防風皆輕用,“風升生”之品,風藥升清,升提脾氣,且風性勝濕,亦可輔助化濕;炮姜苦溫,燥濕而助脾陽升發;炒杭白芍苦瀉疏木;紅景天益氣且能改善細胞功能。諸藥并投益氣升清、健脾燥濕,脾氣旺則健運,濕氣化而氣暢,則脂肪沉積可漸消。案2在癥狀上有乏力、易疲勞、便溏等脾虛征象,又有怕冷、惡風等陽虛表現,舌脈為陽虛水濕之象,證屬:寒濕困脾,方用黃芽湯加味。其中黑順片補火燥濕;黨參、干姜、茯苓、麩炒白術益氣溫中、燥濕瀉水;紅景天益氣、改善肝細胞功能’升麻、獨活小劑量運用可升清通陽。全方共奏培土瀉濕、補火升陽之效,陽旺陰散,則肝臟脂質沉積亦可漸化。總之,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辨治,當仔細采集四診,合理分析病機、確定證候,經恰當的遣方用藥,則療效可期。
4 注意事項
中醫藥治療NAFLD,在辨證正確、方藥合理的情況下,有著良好的療效。但仍然需要注意一些方面:肝臟,作為一個腺器官,有著代謝、解毒、分泌、免疫等多方面功能,生理和病理機制復雜,目前研究尚不明確。中藥治療NAFLD具有多靶點、多通道的特點,對于改善癥狀和生活質量,有一定的優勢。但是,中藥成分復雜,在進入人體后也需要經肝臟代謝,其有效成分是藥物成分直接起效還是要在肝臟里代謝后的次產物起效,目前所知甚少,治療的機制目前也不明確,所以筆者認為,處方用藥務必精專,藥味不宜太多,藥味多,其成分也多,會不會加重肝臟的負擔?目前的試驗研究也沒有設計嚴謹的論證進行闡述,所以一定要認真進行四診采集,四診合參,在理法方藥的指導下以最少的藥物取得最大的獲益。
升陽瀉濕法和培土疏木法,是李東垣和黃元御的思想理論在診治NAFLD中的有機結合。李東垣在《內外傷辨惑論》中說:“味之薄者,諸風藥是也”,風藥質輕,性動而善行,風藥可升提脾氣又能勝濕,配合甘溫益氣之品,可使補而不滯,使氣機流暢,又能使化濕藥功效倍增,用量宜小,5~6 g即可,防風、柴胡、升麻、獨活、羌活、薄荷等藥物,可根據情況擇一二味配伍使用。中焦氣機為濕濁所困,日久亦可導致肝氣不暢而郁帶,反過來犯胃乘脾,加重中虛,使病情加重;或者患者長期熬夜,習慣冷飲空調,饑飽失度,致使中焦脾胃從濕、從寒而化,后天脾胃虛寒日久可累及先天腎氣,導致脾腎陽虛;木生于水而長于土,今脾土濕而腎水寒,亦能導致肝寒氣郁,木郁賊土,加重中虛,中虛不能運化,濕濁更盛,而寒濕益甚,導致病勢更為深重難愈。黃元御云:“風木者,五臟之賊,百病之長”[6]。立足中氣,培土疏木,使脾胃健運而濕濁不生,實土又可遠木,使木氣暢達,疏泄有度,不橫克脾胃,從而中氣升降有序,杜絕了虛者更虛要、實者更實。木氣郁而不暢,為其伴發的病機之一,臨床上可以沒有肝氣不舒的癥狀,病情輕淺時,直接以理脾胃、化濕濁治療,濕濁化,脾胃健運則木氣自舒,但是患者癥狀明顯、病情較重的時候,尚需于方藥里適當配伍制香附、杭白芍、炒柴胡等疏達肝木之品;如偏于寒者,肝寒氣郁,則配伍烏藥、桂枝或者吳茱萸等藥物以溫肝疏木;如偏于熱者,則加入龍膽草、郁金及赤芍等以清瀉肝膽。
綜上所述,在NAFLD的治療中,以升陽化濕、培土疏木為治法,可較快減輕癥狀,改善患者的精神狀態和社會功能,也能夠截斷病機,防止傳變,從而獲益更大。在該病治療時應該加強宣教,生活和飲食習慣等均應符合個體體質或狀態。今后的工作應該優化治法方藥,設計研究觀察,對相關血清學和肝臟影像學等方面進行觀察,進一步明確其療效機制和優化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