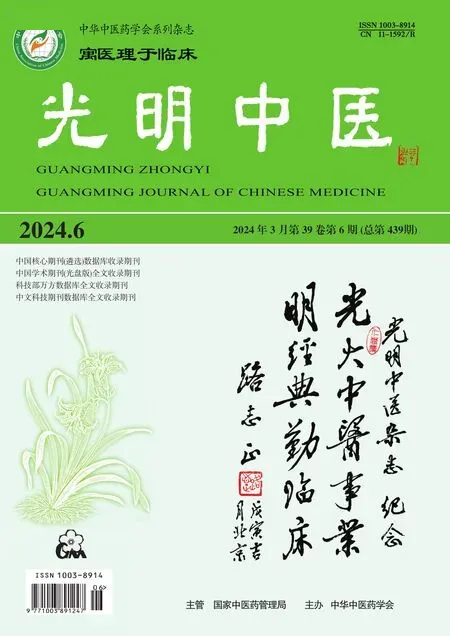抗機復法祛痛湯治療帶狀皰疹后遺神經痛116例
楊仁坤 楊冠佼 盧祖平 楊德豪
帶狀皰疹后遺神經痛(PHN)是帶狀皰疹患者最常見的并發癥,是指帶狀皰疹急性期皮疹消退后,局部持續疼痛4周以上者,是一種頑固性慢性疼痛綜合疾病,屬于難治性疼痛[1]。西醫以緩解疼痛對癥治療為主,但根治率低。中醫治療該病有優勢,古今醫家在辨證立法的基礎上選方配伍組成了不同的方劑,分型論治收到了良好效果,有些仍沿用至今。該病可分為潛伏期(皰疹前期),急性期(出疹期),恢復期(后遺神經痛期),癥狀均以疼痛為主。如何發揮中醫優勢快速治愈該病是業內急需解決之難題。對此,筆者在繼承前人經驗和現代醫家研究成果,根據PHN的發病規律及表現癥狀,推斷出該病雜合病機,采取相應復合治法,依法擬出抗機復法祛痛湯,臨床驗證,療效滿意,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選取2018年4月—2023年4月綏陽楊仁坤中醫診所收治的116例PHN患者為研究對象。男43例,女73例;年齡21~98歲,平均61.4歲;其中21~30歲5例,31~40歲3例,41~50歲18例,51~60歲26例,61~70歲32例,71~80歲19例,81~90歲11例,91~100歲2例;發病時間:1~72個月,平均2.64個月;發病部位:左右側:左側48例,右側67例,雙側1例;上中下分部:頭額眼耳21例,胸乳脅背71例,腰腹臀腳24例(包括子宮2例);疼痛到出疹:潛伏期1~26 d,平均2.82 d;服藥劑數:2~45劑,平均4.58劑;服1~5劑87例,6~10劑24例,11~45劑5例。
1.2 診斷標準西醫診斷參照《帶狀皰疹后神經痛診療中國專家共識》[2]:分散和局部皮膚的疼痛,常表現為某神經分布相關區域內瘙癢性、灼燒性、針刺樣、刀割樣、點擊樣或搏動樣疼痛;間歇性和慢性疼痛;有明確記錄的皰疹史。體格檢查可見局部有遺留的瘢痕或色素沉著;局部可有痛覺過敏或痛覺減退;局部可有痛覺超敏;局部可有汗多等自主神經功能絮亂表現。中醫辨證標準參照《蛇串瘡中醫診療指南(2014年修訂版)》[3]擬定。
1.3 納入與排除標準納入標準:符合上述西醫診斷標準及中醫辨證標準者;病程1~72個月;依從性良好。排除標準:有嚴重的心腦血管疾病;合并惡性腫瘤、血友病;凝血功能異常有出血傾向;處于妊娠期及哺乳期。
1.4 治療方法(1)口服自擬抗機復法祛痛湯。方藥組成:金銀花30~50 g,連翹20~30 g,黃連10~60 g,黃芩20~30 g,黃梔子10~50 g,土茯苓40~200 g,三棱30~100 g,莪術30~100 g,川芎30~100 g,木香10~30 g,白芍30~200 g,甘草10~80 g,醋延胡索100~200 g,黨參20~50 g,麩炒白術20~100 g,茯苓30~80 g。據癥加減:①便秘者減麩炒白術,加山藥150~200 g,生白術60~80 g。②火熱瘙癢者,加板藍根30~80 g,蒲公英30~50 g,槐花30~40 g,大青葉30~40 g。③皮損針刺痛者,加白及15~30 g,三七30~60 g,丹參30~50 g。④隱隱痛久不愈者,加枸杞子30~50 g,山萸肉30~50 g,鹽杜仲30~50 g,巴戟天20~30 g,淫羊藿30~150 g。⑤失眠者,加炒酸棗仁30~70 g,柏子仁30~70 g,熟地黃100~170 g,肉桂10~20 g。⑥病位在上半身者,加升麻20~30 g,柴胡20~30 g。⑦病位在下半身者,加牛膝30~50 g,木瓜20~30 g。⑧厭食者,加焦三仙各20~30 g,牡蠣20~30 g。⑨泄瀉者,加炒訶子(去核)30~50 g,麩炒芡實30~50 g,蓮子30~50 g。煎服法:飲片加水淹過藥面,首次淹過飲片7 cm,余次5 cm,煮沸20 min,濾凈藥液盛于大容器中,如法連煎4次,混合服用。每日3~4次,每次50~200 ml。(2)口服西藥方:安乃近片[遠大醫藥(中國)有限公司,國藥準字 H42021303,規格:0.5 g×1000片/瓶],1片;氨芐西林膠囊(重慶科瑞制藥集團有限公司,國藥準字 H50021651,規格:0.25 g×12粒×2板),2粒;維C銀翹片(貴州百靈企業集團制藥股份有限公司,國藥準字 Z44022230,規格:30片/袋),3片;醋酸潑尼松片(浙江仙居制藥股份有限公司,國藥準字 H33021207,規格:5 mg×1000片/瓶),1片;維生素C片(西南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國藥準字 H50020036,規格:100 mg×1000片/瓶)1片。(注:此5種藥合為1包,即1次量)。加減:劇痛加雙氯芬酸鈉腸溶片(四川依科制藥有限公司,國藥準字 H51020298,規格:25 mg×24片/瓶)1~2片;食欲不振加多酶片(四川依科制藥有限公司,國藥準字 H51020247,規格:100片/瓶)2~3片;無發熱則減安乃近片。疼痛緩解則停服西藥,只服中藥。
1.5 療效判定標準參照《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試行)》[5]擬定,結合尼莫地平法以VAS評分進行判定,療效指數=(治療前VAS評分-治療后VAS評分)/治療前VAS評分×100%。痊愈:疼痛癥狀消失或基本消失,療效指數≥90%;顯效:疼痛癥狀明顯改善,90%>療效指數≥70%;有效:疼痛癥狀好轉,70%>療效指數≥30%;無效:疼痛癥狀無變化,甚至加重,療效指數<30%。總有效率=(痊愈+顯效+有效)例數/總病數×100%。
1.6 統計學方法根據收治先后,按出院小結或患者自述的姓名、性別、年齡、病程、合并病種、治療經過、住院與否、次數和時間、刻下癥、就診次數、用藥味數、劑量、服藥劑數、治愈時間等項,逐一登記、建檔,通過復診和電話采訪形式進行客觀列表統計。
2 結果
臨床療效統計:116例患者中,痊愈110例,占比為95%(110/116);顯效6例,占比為5%(6/116);無效0例;總有效率為100%(116/116)。
3 典型醫案
田某,女,68歲,四川合江人。2022年4月12日經其親人推薦遠程診治。自述:患有高血壓病(5年)、類風濕病(7年)、淋巴結核(1年半),均在服用相關治療藥物。2021年9月又患帶狀皰疹,諸病合攻,多次因痛欲輕生。患帶狀皰疹后,在當地三甲醫院住院9 d,出院后每日服3次西藥,至今未斷。期間服過6劑中藥,痛劇難忍即往當地醫院輸液止痛,現請專人護理。刻下癥:頭痛,左側乳下及背部皮膚紫色疹斑,面積長寬26 cm×16 cm(讓子女量)。痛如針刺、火燒、刀割、電擊,衣擦更痛,夜不能眠。口干苦、食可、二便可。舌紅苔微黃、舌下脈瘀紫(觀視頻)。近日又在輸液。據其病史及表現綜合分析,西醫診斷:帶狀皰疹后遺神經痛及三種基礎病;中醫診斷:蛇串瘡。治法:西醫:解熱鎮痛、抗病毒、營養神經、抗感染等;中醫:祛風利濕、清熱解毒、化痰行瘀、健脾補腎、養血通絡、復損止痛等。予中藥口服抗機復法祛痛湯:銀花30 g,連翹20 g,黃連50 g,黃芩20 g,黃梔子20 g,土茯苓60 g,三棱50 g,莪術50 g,醋延胡索180 g,川芎100 g,木香20 g,黨參30 g,麩炒白術30 g,茯苓50 g,枸杞子20 g,山萸肉50 g,杜仲50 g,板藍根50 g,白芍150 g,甘草50 g。6劑,每劑水煎4次混服。西藥:基本方,去安乃近,加雙氯芬酸腸溶片,30包。
5月25日—8月11日二~四診:疼痛減1/3,效不更方,繼服一診原方中、西藥。
9月20日五診:頭稍昏欠清醒、自覺視物不清、口干不苦、進食后感胃脹氣約1 h、燒心、便溏,每日排便3~5次。右乳下及背部的皰疹皮膚稍痛。處方:人參(打吞)30 g,麩炒白術30 g,茯苓50 g,甘草20 g,熟地黃50 g,白芍120 g,當歸20 g,川芎50 g,黃芪100 g,肉桂10 g,陳皮30 g,砂仁20 g,木香20 g,枸杞子50 g,山萸肉50 g,杜仲50 g,桑椹50 g,淫羊藿100 g,檳榔30 g,黃芩20 g,百部20 g,丹參50 g,柴胡20 g,升麻20 g,醋延胡索180 g,土茯苓100 g。5劑,煎服法同前。
11月1日六診:頭不悶、視物較前清晰、口微干、食可、胃稍脹、精神、睡眠、二便可,右乳下神經偶有痛感,生活自理,體質量由原來的80斤增加到90斤。為其調整抗癆藥,中藥同五診。
2022年12月26日—2023年4月24日七診、八診:西藥已停服40 d,近日右乳下及背部又有痛感,偶有刀割痛,晚上8點到早上8點有點目劄、惡寒怕冷、四肢僵硬、麻木。處方在五診原方上加甘草30 g,白芍30 g,川芎10 g,三七50 g,延胡索20 g,淫羊藿20 g,去砂仁、檳榔,連服8劑。
2023年4月25日九診:中藥已停4 d,除右乳下皮膚稍有點熱痛,眼癢時流淚外,余無異常。處方:人參(打吞)50 g,麩炒白術30 g,茯苓50 g,甘草80 g,熟地黃150 g,白芍200 g,當歸20 g,川芎60 g,黃芪100 g,肉桂10 g,陳皮20 g,枸杞子50 g,山萸肉50 g,桑椹50 g,淫羊藿150 g,土茯苓100 g,醋延胡索200 g,三七(打吞)50 g,龍膽草20 g,木香20 g,野菊花(后下)20 g,3劑水煎服。
近日隨訪,除仍服降壓藥外,余藥已停,做家務無恙。
按語:據患者病史病程表現,尋找出其系統病機。針對病機采取相應的復合治法。運用銀翹散、黃連解毒湯、芍藥甘草湯、四君子湯等數方化裁即抗機復法祛痛湯。該方金銀花、連翹辛涼透邪、芳香辟穢,共為君藥。臣以黃連、黃芩、黃梔子瀉火解毒、清利三焦濕熱;土茯苓能解毒除濕、化痰,治惡瘡、筋骨拘攣;三棱、莪術可破血祛瘀、行氣止痛;川芎、木香、延胡索活血祛風、疏肝行氣止痛;白芍、甘草可養血柔肝、緩急止痛;黨參、麩炒白術、茯苓能健脾益氣、培土生金、補虛復損,共為佐使。因患者基礎病多,病久必致正虛,故方中加枸杞子、山萸肉、杜仲補腎之陰陽,以板藍根助其清熱解毒涼血之力,以除痼疾。全方各藥針對靶點,發揮協同作用;首劑見效后,連續三診守方,到五診時痛減九成,再改用大補氣血、調補肝腎之法協同舒經活血、行氣止痛藥治療,直至治愈。
4 討論
帶狀皰疹(HZ)患者在急性期之后可經歷數月甚至更久的持續性疼痛,即PHN[6],其發病與年齡增長及機體免疫力下降有關[7]。該病屬中醫學“蛇串瘡、蛇丹、纏腰火丹;甑帶瘡”范疇。首見于《諸病源候論》曰:“甑帶瘡者纏腰生……狀如甑帶,因以為名”。此后,《外科正宗》將其分為“干”“濕”兩型論治,其言:“干者……治以涼血清肝,化斑解毒湯是也。濕者……宜清肺、瀉脾、除濕,胃苓湯是也。腰脅生之……曰纏腰丹,柴胡清肝湯”。《醫宗金鑒·外科心法要訣》則提出其病重易亡之觀點,言:“纏腰火丹蛇串名……纏腰已遍不能生”。傳統多為分型論治,用龍膽瀉肝湯、逍遙散治療,都取得了較好療效。面對HZ急性期后9%~34%的PHN患者[8],現代醫家也進行了深入研究,如謝文明等[9]提出,鄭則敏教授從肝、脾論治PHN,擅用蟲藥以止痛,如全蝎、蜈蚣等。劉志強等[10]總結了張炳厚教授診療PHN以活血止痛為重,自擬方“疼痛三兩三”,均從不同角度取得了滿意療效。對于中醫究竟用什么方藥(通用方)才能快速治愈該病則鮮有報道。
筆者在長期臨床實踐中發現,PHN可致發于頭部患者失明,或致發于腳及小腹部患者難以行步,甚者因諸痛聚身而欲輕生,并非個案。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此難題,必先尋找該病的系統病機,針對病機采取相應的復合療法,大方重劑,十者圍之[11],即“錯節盤根,必求利器”,方能止痛復康。據其病史病程表現癥狀,尋找出系統病機。針對病機采取相應的復合治法。
目前,關于該病病機的研究方面,張博文等[12]認為,PHN的病機離不開肝郁、脾虛;病理產物涉及濕、痰、瘀、毒;劉剛等[13]報道,PHN多由濕熱火毒耗散正氣而致虛損。此2項研究均證明了其病機的真實性。方藥研究方面,張婷等[14]報道,黃連解毒湯在抗炎、降血壓、抗腫瘤、免疫調節及保護心肌等方面具有一定作用。羅亞敏等[15]報道,芍藥甘草湯為臨床緩急止痛之名方,其對中樞和外周神經末梢均有鎮痛作用。魯春梅等[16]研究表明,延胡索的主要活性成分為異喹啉生物堿,其中的延胡索乙素鎮痛作用最為顯著。楊建宇教授認為,疼痛可因免疫能力降低,通過補充氣血,用四君子湯等方,提高免疫力,疼痛自然可消[17]。以上研究均證明了抗機復法祛痛湯的有效性。由上可知,從傳統病機到現代藥理研究結果,都對該方的有效性、真實性提供了有力的依據。
綜上,抗機復法祛痛湯經臨床實踐和現代藥理證明,療效顯著,可操作、重復性強,是治療PHN的通用方,值得臨床推廣。但要注意幾點:①疼痛劇烈時可輔服西藥,緩解后則停服西藥,只服中藥。②疼痛減至80%時,可在該方中加益氣養血、補腎之品,愈后亦鞏固。③女生經期服藥,應視經量而定,經少宜少服,經多宜停服。④該方加減可治療HZ的各階段,只需根據痛之輕重調整藥味和藥量。⑤有基礎病患者,可在該方基礎上加藥兼治。⑥該方方大量重,由于個體差異,仍需因人因癥,由輕到重施量。因該研究樣本量偏小,故還需進一步總結完善,以便為該病患者減少痛苦貢獻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