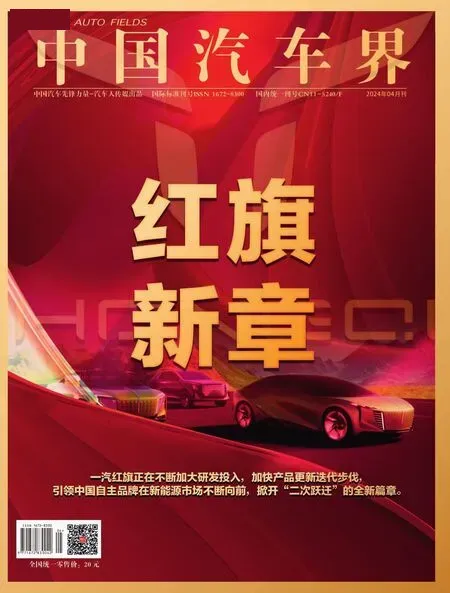新能源不賺錢 供應商動搖
文 / 齊策
近日,繼奔馳CEO康林松宣布推遲新能源2025、2030計劃之后,博世CEO史蒂凡·哈通也出人意料地對德國媒體表示,實現全球車輛電氣化至少需要30到35年,德國必須繼續提供內燃機技術,因為強制其他地區的客戶放棄內燃機不切實際。
新能源業務不賺錢
表面上看起來,哈通在為德國的海外市場擔憂。因為除了中美歐,其他區域市場既缺乏意愿,也缺乏必要的資源,能夠跟住全球新能源浪潮的發展。
博世作為全球最大、影響力最強的一級供應商,其業務方向的調整舉足輕重。哈通作為博世掌舵人,一向謹言慎行。他雖然“只有“57歲(對于一個超級企業的CEO來說相對年輕),但像很多老派的德國汽車經理人一樣,公開講話總是字斟句酌,和公司戰略步調保持高度協同。
這一次,言論貌似脫韁,釋放了不同尋常的信息。《汽車人》猜測,哈通很可能代表其大客戶的看法。
哈通不斷稱中國是博世最大單一客戶。中國業務大概占博世集團20%,而汽車業務大概占25%,確實很重要,但還沒達到BBA中國業務那種權重。
2021年,哈通還在候任CEO,博世在時任CEO鄧納的主持下成立了XC智能駕駛與控制系統事業部,將橫跨各域的域控制集中在一起。這是一次由業務變化帶動的事業部級調整。

2023年,博世進行了138年歷史上最徹底的一次架構重組,占整個集團業務量60%的汽車業務獨立運營,名為“智能出行集團”。
根據2023年財報,博世汽車業務收入增幅7%,隨后憑借匯率漲跌,戲劇性實現11%增長;息稅前利潤率只有5%,雖然較上一年(4.3%)小漲,但仍未能打到哈通樹立的目標(7%)。
博世煞費苦心地迎合了中國客戶電動化需求,和其他供應商一樣,能夠接受年降3%-5%。但2023年的價格戰,博世被要求降價15%;而今年一開年,很多主機廠要求一級供應商在去年基礎上降價20%。
博世中國總裁徐大全表示:“我們關門不做了,可能比降20%更好。”雖然不清楚他講這句話的情緒,但這么卷下去沒出路,是肯定的。
歐洲業務收縮近在眼前
站在全球業務的角度,哈通在2月份表示:“一些尖端技術訂單情況并不像公司預期那么強勁。”他沒有講如何應對訂單疲軟。
現在,歐洲大的供應商基本上有同感。收購了海拉的佛吉亞一方面宣稱2023業務有14%增長,利潤率5.3%,看上去中規中矩,但另一方面動手裁員1萬人。
大陸、博世、佛吉亞都是一邊賺錢一邊裁員。當然,歐企裁員不是IT企業風格,HR跑到工位上宣布,給卡上打N+1賠償,然后注銷工卡,下午人抱著紙箱子就被趕出來了。
歐企講究一個慢條斯理,用提前退休、買斷工齡、安置分流、減少招聘等柔性手段應對。
新能源業務不賺錢,依靠匯率漲跌賺錢是很滑稽的。匯率能緩解利潤減少的不適,也能補上一刀。強烈的危機感,讓供應商們不斷調整戰略節奏。他們預感到,至少在歐洲,業務收縮將很快到來。
歐盟監管信號含混不清
信號是主機廠直接給的,單子少了,價值低了,老客戶跑了,任何人都能看出來。而市場監管方傳遞的信號,就比較散亂和耐人尋味。
這兩年,雖然有2023年6月的個別放水(允許合成燃料在2035年之后繼續使用),但歐盟理論上并未放棄新能源的推進節奏,一個是碳排逐年加嚴的要求沒有取消;另一個是新能源投資沒有放緩。
根據國際能源署的數據,2023年全球碳排增長了1%。這和主要工業國(中美歐)大刀闊斧的清潔能源投資是相悖的。
中美歐新建的光伏和風力發電,占全球90%;新能源車占了全球95%(中國一家占了全球60%)。中美歐作為全球經濟的發動機,碳排往下走,但仍然沒能抵擋住全球碳排上升。
目前,全球清潔能源投資1.8萬億美元。其中,中國投資6760億美元,美國投資3000億美元,歐洲投資4180億美元。中美歐投資額占全球總投資78%。日本新能源投資只占中國的5%,不是主要投資力量。

這個投資力度表明,中美歐的能源轉型都沒有中止。但是從商業角度衡量,新興業務允許虧損,但時間長了,看不到盡頭,就難免產生撤退的想法。
美國和歐盟都間接承認在商業上競爭不過中國電動車,因此都打算或者正在祭出非商業防御手段。《汽車人》在《智能網聯存“風險”,美國欲對中國汽車采取行動》一文中有所闡述。即便歐盟、美國能防得住,但跨國企業不想放棄全球業務,即還得想辦法從商業上應對。
新能源業務不賺錢,強烈的危機感讓跨國供應商們不斷調整戰略節奏。他們預感到,至少在歐洲,業務收縮將很快到來。

有沒有勝負手
對于新能源產業發展,初期中美歐的思路其實差不多,就是用補貼拉動產業鏈發展,逐步形成完整“自持”的新能源供應鏈。
當然,除了正面激勵,還有負面懲罰,就是燃油車碳排標準的逐年提高、燃油車停售的時間表。后者由于爭議的聲音比較大,都停留在愿景階段。中美歐(除了一些歐盟小國)等大工業國,都沒有進一步推動成為強制性法律法規。
但是10年前開始的這場競速游戲,到2020年就產生了分化。中國從上游到下游,實現了一體化控制,由自我革命欲望非常強烈、技術積累深厚的企業率先激活并引領了全供應鏈發展。
中國十幾年前在澳洲和非洲、南美的收購行動,在后兩者長期堅持的緊密捆綁的政經戰略,收到了奇效。引入特斯拉也成為一個漂亮的激活手段,德國對這一策略復制成功,但效果遠不如中國。
有一個因素很難否認,就是燃油車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苦哈哈忍受新能源的虧本生意。作為企業長期戰略的執行者,他們即便制定了適應未來的戰略、調整了組織架構,但指望的收獲期,不能是遙遙無期。
雷諾為了應對即將到來的中國車競爭浪潮,打算推出2.5萬歐元的小型電動車(5E-Tech)。這款還在PPT上的車如果現在投放中國,會被打得沒有還手之力。但在歐洲,它成了救命稻草。
斯特蘭蒂斯和大眾汽車分別加入了這個計劃,三家創紀錄的合作模式,并未減少面臨的競爭壓力。雷諾CEO因此提出創建“歐洲空中客車”式的大聯合企業,應對即將到來的競爭。架構上如此大膽的創新,各家需要讓渡很多利益,可見威脅多么迫在眉睫。
現在看,這更可能是一個勝者通吃的游戲。
現在歐洲一些主機廠只說要放緩(新能源),但很可能演變成一場潰退,新投入的新能源資產毀于一旦。另一些主機廠還在咬牙堅持,但已經產生肉眼可見的動搖。監管方先是變得不堅決(德國斷崖式撤銷新能源消費補貼,歐盟只甩鞭子不給甜頭),市場的即時反饋理所當然是非常負面的(當月新能源銷量大跌)。
連鎖反應,就像燃燒的導火索,一路燒到供應商那里,結果就是大家一起動搖。雖然給人的印象是歐企害怕中企不要命的競爭,但重拾用著順手的舊武器,生存需求毫無懸念地戰勝了臉面需求。
過幾年回過頭來看,今天的格局可能意味著國家新能源戰略競爭,勝負已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