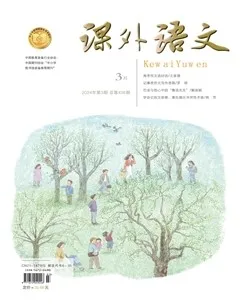香雪的困境
蘭學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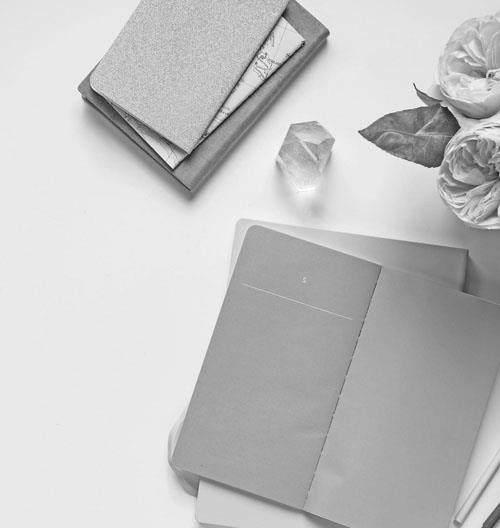

《哦,香雪》是當代著名作家鐵凝寫于20世紀80年代初的代表作品之一,被選入了部編版高中《語文》必修上的教材中,排在了第一單元的“青春吟唱”模塊里。教參對它的解讀是“通過對香雪等鄉村少女的生動描摹,表現了山里姑娘淳樸、善良和美好的心靈,表達了姑娘們對山外文明的向往與追求”,并對此賦予了更深刻的意義——“寫出了改革開放后中國從歷史的陰影下走出,擺脫封閉、愚昧和落后,走向開放、文明與進步的痛苦與喜悅。”基于此,“香雪”也就成了封閉山村中向往現代文明的代表人物形象之一,不足8000字的小說還被改編成了長達102分鐘的電影,而小說中香雪用雞蛋換回的“鉛筆盒”也成了知識的載體與現代文明的象征物。
鉛筆盒到底喻指什么呢?
讓我們從小說文本中尋找答案,并借以來探尋小說的主旨。
香雪由于在離村15里的公社讀初中,所以才從同桌那里見到了以前不曾見過的那種塑料的、帶有磁鐵開關能自動開合的鉛筆盒,因而對自己那個父親特意打造的“獨一無二的”木制鉛筆盒不喜歡,擺在課桌上也讓她感覺“羞澀”;再加上她生活的山村一天吃兩頓飯,而她的公社同學家里一天吃三頓飯,她才忽然意識到自己雖然是全村唯一考上初中的孩子,但家鄉臺兒溝的貧窮卻讓她覺得“不光彩”,并且,因為自己出身山溝,她的同學常常一遍一遍盤問她家里一天吃幾頓飯。這些,讓香雪覺得似乎受到了同學的“歧視”(雖然文中沒有出現這個詞)和不公正對待,機緣巧合之下,在村頭只停靠一分鐘的火車讓她萌生了用雞蛋換鉛筆盒的想法,并且很快就付諸了實施。其間雖經歷了一系列的小波折,好在結局圓滿,她終于擁有了一個和同桌一樣的鉛筆盒,雖然它是別人曾經用過的,雖然換取的代價是40個雞蛋和30里的夜路。
因貧窮給香雪帶來的心理不適,靠換來的鉛筆盒得到了暫時的緩解,她甚至急切盼望第二天上學時同學們會“再三盤問”她,會用“驚羨的目光”看她的“新”鉛筆盒(這種心理,與《項鏈》里的瑪蒂爾德從借來的項鏈中獲得的滿足感非常相似),到時,她可能會驕傲地大聲宣布:鉛筆盒是她用雞蛋換的,自己終于也有了和同學們一樣時髦的鉛筆盒了。那么,然后呢?她的同學們真的就會對她刮目相看了?她自己身處貧困臺兒溝的現狀就得以改變了?同學們就不會對她一天只吃兩頓飯報以“輕輕的笑”了嗎?當然,對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十六七歲的初中生,我們不該惡意揣測他們像《祝福》中魯鎮的村民那樣,有一遍一遍聽祥林嫂講述自己悲慘遭遇的所謂茶余飯后的“消遣”,但對身處貧困山區的同學香雪,她的同學們卻缺少了最起碼的善意、包容和理解,否則,他們就不會一遍一遍地明知故問香雪家一天吃幾頓飯。這些公社初中里的同學,明知香雪來自山溝,卻誅心似的不停“盤問”,這種帶有明顯嘲諷的行為,真的只是在開善意的玩笑嗎?相較于走了30里夜路回到家鄉臺兒溝,卻一直站在鐵軌旁等香雪的伙伴鳳嬌她們,山溝的孩子是多么善良和淳樸啊。盡管時已夜半,伙伴們卻沒有丟下香雪選擇各自回家,而是像等待凱旋的戰士一樣耐心地等待著她。這場夜色中的等待,才是同學間該有的溫情吧?
在那樣的學校環境里,一個并不嶄新的鉛筆盒,真的能為香雪贏得該有的尊重和理解嗎?筆者看未必,說不定他們還會嘲笑鉛筆盒并不新,而香雪家一天吃兩頓飯的事實依然存在,短期內也并不能得到解決。因此,即使同桌沒有那個自動鉛筆盒,書包、鉛筆、橡皮或者其他臺兒溝沒有的東西也同樣會給香雪帶來困擾,火車的到來不是給她帶來了文明,只是給她提供了一個獲得鉛筆盒的契機,因為鉛筆盒的困擾是她初中的同桌帶給她的。
所以,總體來看,香雪的困擾有兩個:一是貧窮的原生家庭,二是周圍不太善意的同學,或者說不太友好的學校環境。因此,只要生存環境不變,困擾就必然存在,而香雪的見識或者格局都讓她想不到或找不到解決這個問題的最佳途徑(當然,不只是香雪,作者鐵凝當時或許也沒找到),因此,單純的香雪只想到了最容易解決的辦法:得到一個鉛筆盒。因此,把這篇小說定義為“姑娘們對文明的向往和追求”筆者覺得并不準確,甚至有刻意拔高之嫌。
回到文本,香雪得到期盼已久的鉛筆盒之后呢?當她拿著用四十個雞蛋換回的視若珍寶的鉛筆盒,回家后該如何面對自己的父母呢?父親辛勤做木工活給她交學費去公社讀初中,香雪卻用母親辛苦攢下的雞蛋換回了一個徒有其表的二手鉛筆盒,父母是支持還是反對?雖然香雪在路上就已想好如何應對父母的質疑:她要把鉛筆盒說成“寶盒子”,“寶盒子”能讓自己“要什么有什么”,這個 “從來不騙人”的姑娘因為這個鉛筆盒要第一次對母親撒謊了。可是,這樣的說辭真的足以說服她的母親嗎?如果不憚以最庸俗的想法來揣測樸實善良又貧困的香雪的雙親,筆者想,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定然是免不了的,她的父母雖然說不出賈政批評寶玉那樣“學了一肚子精致的淘氣”之類的話, 但是,用40個雞蛋換回的鉛筆盒真的會讓她樸實的父母覺得物有所值嗎?在父母或輕或重的批評里,香雪會不會冷靜下來,思考自己這次行動的代價呢?當時過境遷,她的熱情沉淀下來,又或者某一天,當她終于認識到擁有了鉛筆盒并沒有改變她的處境之后,她可能會說:“我這是做了一件什么樣的傻事啊!那個鉛筆盒并不比木制的好用,甚至一點也不實用啊。”
那么,這個用40個雞蛋和30里夜路換回的鉛筆盒,在我們看來,是香雪為了融入環境或者說是希望獲得外在認同的“媒介”,香雪希望通過它,能夠換得同學們的認同,或者憑借這個鉛筆盒讓自己在班級里找到精神上的歸依,不至于讓自己顯得“格格不入”,為此,香雪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在那個相對“愚昧、封閉和落后”的時代,40個雞蛋可能是一個三口之家一個月的柴米油鹽,雖然,我們不能只從物質角度來評價一個物品的價值,但在父母眼里,40個雞蛋真的不是一筆小數目啊。這個青春時光中的不菲代價,如同歌里唱的那樣,它是年少時的夢,是永遠不凋零的花,陪伴青春的你我走過那些風吹雨打;或者,它也是人在面對困境或困擾時的一個出口,佛教上說,“因上努力,果上隨緣”,意思是說,世間皆苦,人要靠自我探尋找到前行的力量,這個力量既可以是精神的,也可以是物質的,雖然它不一定能讓我們徹底擺脫困境,但至少可以成為我們的一個夢想。而在探尋的過程中,付出一些代價是必然的,而換回來的那些“鉛筆盒”,看似美好卻并不一定實用,可它是成長中常常要付出的,甚至是一定會付出的,哪怕它曾經像火炬一樣照亮她的夜路,裝點她的青春。我們設想,在香雪長大之后,回想起那一晚辛苦走過的夜路,她可能會莞爾一笑,并說:“我的青春時光,也曾經那樣單純而瘋狂,執著而沖動。”
在我們明晰了“鉛筆盒”的意義之后再來看它,它其實和“鳳嬌”們喜歡的發卡與紗巾并無本質上的區別。因此,我們不能因為鉛筆盒是學習用品就刻意回避了現實生活環境帶給她們的困擾與痛苦以及她們為緩解這些痛苦而付出的努力,從而也就不能簡單地把鉛筆盒定性為知識或文明的象征。
因此,課文《哦,香雪》的主旨,我們不妨解讀成“青春·時代·成長”,應該比“知識”“文明”更貼近文本,也更貼近生活本身和當時的社會現狀。雖然鐵凝的這篇文章風格淡雅別致,意境回味悠長,具有詩情畫意之美,但依然掩蓋不了那個時代生活的沉重和“香雪”們的實際生活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