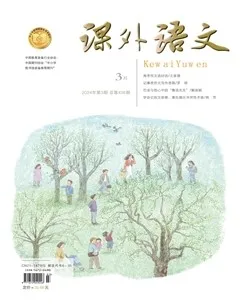無奈的帝王:這般才情,卻命運多舛
潘紅云


人人都羨慕帝王生活的多姿多彩,都認為他至高無上,但誰又知道帝王其實可能很悲慘?尤其戰爭時期的帝王們,分分鐘都有被“滅”的可能。歷史上,有一個帝王是真悲慘:
他是南唐國主,有愛國救民之心卻不能守土護疆,最終被北宋所滅,淪為階下囚;
他是一名藝術家,精通書法,擅長繪畫,通曉音律,在詩詞和散文方面均有一定造詣,尤以詞的成就最高,可惜卻被賜毒酒。
他就是五代十國時期最著名的詞人——李煜。
作為一個帝王,他也有力挽狂瀾的勇氣,但無奈大勢已去。李煜的詞有前后期之分。前期,作為一名帝王,他的詞里面有描寫宮廷豪華生活的,有描寫男女情愛的,有抒發離愁別緒的傷感,更有對歸隱生活的向往……后期,作為一名階下囚,由于經歷了國破家亡的悲傷,他的詞作多了一份怨恨和惆悵。但不管是怎樣的題材,“真”貫穿他的全部詞作。因為“真”,他的詞作總讓人看到他充沛的、真摯的情感,他也因此成為一個多情的帝王。
讓我們從他的千古名篇《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來看這位帝王的“多情”。
一、詞作前瞻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是李后主的絕筆詞。他因為這首詞而被賜毒酒。在這首詞里,他抒發了自己亡國后的寂寞、希望落空后的絕望心境。我們先看看此詞的創作背景。
當時的李煜投降北宋之后,一直被幽囚在汴京(今河南開封),某個晚上,他喝酒喝得酩酊大醉。也許是寂寞無奈的傷感,也許是無可奈何的心傷,他讓歌伎唱這首詞。本來這首詞表達的是傷心和無奈,但是對于宋太宗而言,它就是“反動”。宋太宗認為,詞中的“小樓昨夜又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表達的是對故國的懷念。因此,李煜有“謀反”的跡象——想重拾河山。在宋太宗看來,這簡直就是“大逆不道”,于是,宋太宗順勢賜牽機藥將他毒死。
那么,這首詞具有怎樣的“偉力”呢?“偉力”居然大到讓皇帝動了殺心?
二、詞作中蘊含的情感
(一)上闋——表達故國之思
此詞上闋是:“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上闋體現了李煜的悔恨和傷感之情,更有對故國的思念。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前文提及,李煜投降北宋之后,就一直被幽囚在汴京,他每天的活動空間就在高高的圍墻之中,而且還在刀斧手的嚴密監視之下。自由、向往對于他來講都是奢侈的愿望。他可能有這樣的疑問:外在的世界是怎樣的?他曾經的臣民是怎樣安置的?他們的生活過得怎樣?……李煜一無所知。春暖花開、人月兩團圓的美好時光,對他來講都是奢侈——這美好的情景很快會消散吧?“春花秋月”象征著一年又一年的輪回,對他來講,何時才是個頭呢?他的生活沒有期盼,沒有希望,沒有了做帝王時期的那份歡欣。幽禁的歲月里面,李煜也會回想過往的歲月,但又有多少能夠回憶得起呢?可能,淪為階下囚的李煜也會總結自己失敗的原因——不理朝政、不管百姓、不問前景,每天過著聲色犬馬的生活。此時此刻,想必他的心中不但有無奈和悲哀,更有無限的悔恨之情。
“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自己現在被幽囚,昨晚小樓吹來暖暖的東風。東風吹來了春天的氣息,那份暖意、那份生機象征著新一年的開始。但對于被囚禁的李煜來講,又有什么意義呢?詞中的“又”字別具深意,它意味著這樣的夜晚(聽著東風看著明月,卻有幽暗令人驚慌)已經很多次了。又一個晚上,他聽風望月,觸景生情,愁緒萬千。夜不能寐之際,想起已經被滅的李氏王朝。故國歲月,在李煜看來是“不堪回首”的,但是對于這種境況,自己卻什么也做不了。在被幽禁的日子里,每天都倉皇度日。字里行間透露著作者無限的傷感。
(二)下闋——抒發國破之愁
下闋是:“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是順接上闋的“故國不堪回首”,這里的“雕欄玉砌”說的是南唐宮殿雕花的欄桿和玉石砌成的臺階。但疑問由此而來。上闋明明說“不堪回首”,但為什么又牽扯出前朝的“雕欄玉砌”呢?可見,李煜時時刻刻都在懷念故國。但想歸想,“朱顏改”一句揭示出自己曾經住過的宮殿已經物是人非,可能變成了北宋王公貴族的府衙,也可能被大火付之一炬。可謂人生短暫,可謂變幻無常。“往事”也好,“朱顏”也好,都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這里暗含著李煜這位帝王對國破家亡、國土更姓、山河變色的無限感慨。
“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詞的前面部分全然回顧了昔日和今日、景物和人事,并將它們放在同一個時空展開對比,暗含對時過境遷的傷感和人事變幻的失意。李煜心中的郁悶和悲傷最終凝成了千古之絕唱—“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李煜其實是借用別人的提問來自問自答:您的愁緒有多少啊?“愁”本來是不能計算的,既然不能計算,不如就用比喻來回答吧。有的人將愁緒比喻成丁香,唐代詩人李商隱在《代贈》中寫道:“芭蕉不展丁香結,同向春風各自愁。”有的人將愁緒比喻成雨水, 元代的楊顯之在《瀟湘雨》中談及:“雖然道姻緣不偶,我可一言難就,有多少雨泣云愁。”有的人將愁緒比作麻,像成語“愁緒如麻”……但李煜將自己的愁緒比作滿江的春水,它就像一江緩緩流淌的江水延綿不盡。用滿江的春水來比喻滿腹的愁恨,這個比喻極為貼切、極為生動、極為形象,不僅顯示了李煜愁恨的悠長深遠,而且顯示了李煜心中的愁恨就像江水一樣無限翻滾,似乎這滿江的春水就如同李煜的真實心境一樣,更如李煜的人生一樣跌宕起伏。
一個新王朝不容許舊帝王對前朝有任何幻想。或許后世的人覺得李煜是被冤枉的。他已經被幽囚了,哪里還有什么能力“光復”南唐呢?而且“愁恨滿懷”的他已經被磨滅了心境。但是,宋朝統治者可能這樣想——李煜作為被幽囚之人,應該低聲下氣,應該是毫無尊嚴,應該是感激不盡;留下了你李煜的性命,已經是仁至義盡了,這樣的待遇對于亡國君主而言已是優待。所以,詞中的“故國”“雕欄玉砌”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就是李煜光復故國的“莫須有”罪名。“寧枉勿縱”——可憐的李煜就因此詞而死。可惜、無奈!
三、后記
唐代詩人白居易的《后宮詞》中寫:“最是無情帝王家。”確實,在帝王家,為了皇權,父殺子、子弒父,兄弟相殘、叔侄相殘的現象比比皆是,所以才有了“無情帝王家”的說法。這種無情可能并不適合李煜,因為他是一個多情的人。
作為晚唐五代詞人中造詣最深、成就最大的帝王詞人,李煜命運悲慘。《虞美人》飽含情感,為我們呈現了多情的他。我們雖不是帝王,但是李煜的悔恨也讓我們唏噓。他明明可以選擇振興國家,但他荒廢政事,最后國破人亡。我們唯有珍惜每一天,才不至于渾渾噩噩,最終悔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