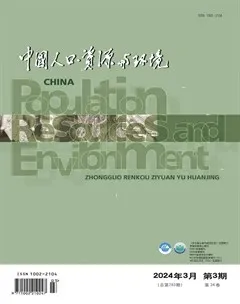農村數字化發展對農業全要素碳生產率的提升效應
王鳳婷 王浩 孔凡斌



摘要 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數字化轉型的綠色效益受到關注。農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亦是第二大溫室氣體排放源,如何借助數字化同時實現農業降碳和增產是中國實現“雙碳”目標的關鍵問題。基于2011—2020年中國30省份面板數據,遵循“發展基礎-發展動力-發展結果”的邏輯構建農村數字化綜合指標,運用EBM?GML方法準確量化農業全要素碳生產率(ATFCP),采用歷史農村公路密度和上一年農村互聯網用戶數作為工具變量,研究農村數字化和ATFCP之間的因果關系。研究發現:①農村數字化能夠提升ATFCP,經過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和內生處理,這一結論仍然成立。②農村數字化通過促進技術創新、規模經營、結構升級、產業集聚和非農就業,進而實現對ATFCP的提升。③異質性分析結果表明,農村數字化對ATFCP的正向影響表現為邊際遞減,在綠色發展水平較高或較低地區均能發揮顯著提升作用。此外,農村數字化存在金融門檻,在農村金融發展水平較高地區的提升作用更強,這是制約農村數字化促進ATFCP提升的主要原因。④空間計量分析結果表明,農村數字化和ATFCP之間存在顯著的空間效應,短期和長期的間接影響均顯著為正,農村數字化不僅能夠提升本地的ATFCP,還能通過技術擴散正向影響鄰近地區的ATFCP。基于此,要進一步強化農村數字化降碳增產的紅利效應,通過加大資金投入,完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推動要素流動和技術落地,提升農村數字化發展潛力;要實施動態化和差異化數字鄉村發展戰略,完善區域間合作機制,促進各地區之間數字經濟的協調發展。
關鍵詞 數字化;碳生產率;超效率EBM模型;動態空間杜賓模型;空間溢出效應
中圖分類號 F205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24)03-0079-12 DOI:10. 12062/cpre. 20230707
農業碳排放總量與工業碳排放總量相比并不突出,但農業碳排放源更加復雜,農業生產高位增長伴隨的農業碳排放增量不斷增加[1]。2021年農業溫室氣體碳排放占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比例已達到20%~25%[2]。據預測,2050年全球農業溫室氣體排放量可能會增加58%,成為最難以控制的碳排放源[3]。中國推進實現“雙碳”目標,農業碳減排迫在眉睫。當前,農業碳減排面臨嚴峻挑戰:一方面,強制性減少農業碳排放,勢必影響農業生產活動,不利于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另一方面,中國農業生產仍然存在嚴重依賴化肥和農藥投入的問題[3-4],單純通過改變耕作方式實現降碳不僅作用有限,并且這一方式也受到快速增長的糧食需求的阻礙[5-6]。因此,農業經濟發展和農業碳減排需要納入統一框架下進行統籌考慮。隨著數字化深入發展,其強行業滲透性和邊際收益遞增性特點日益凸顯,在糧食生產、耕地保護和工業技術等方面發揮著顯著的改善作用[7-8]。那么,農村數字化能否協同提升“農業經濟增長”和“農業碳減排”的雙重目標效應,其影響機制是什么?該效應在不同異質性條件下有哪些差異?上述問題的回答對于豐富數字化轉型的綠色效用理論,進而提出實現農業降碳增產雙重目標的政策建議,兼具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1 文獻綜述
農村數字化和農業全要素碳生產率(Agriculture TotalFactor Carbon Productivity,ATFCP)的研究本質是數字化與生產效率的因果關系探究,同時額外考慮了碳要素。因此,文獻綜述主要沿著以下脈絡展開:一是梳理已有碳生產率的測度方法;二是梳理數字化對農業生產效率影響的研究;三是梳理數字化對農業碳生產率影響的研究。
1. 1 關于農業碳生產率的測度
關于碳生產率的測度,當前主要有單要素和全要素兩種評價方法。第一種是單要素評價方法。該方法以碳排放總量與某一要素比值作為碳排放績效衡量指標,但問題在于忽略了其他投入要素的影響。第二種是全要素評價方法。該方法將農業碳排放和投入要素均納入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測算框架,進而得到農業全要素碳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的測度方法主要包括SFA 和DEA 兩種方法。其中,DEA方法可以有效避免方程形式的設置錯誤,使其更易于操作,應用更普遍[9]。此后,為了克服傳統DEA 方法無法區分環境因素等缺點,非徑向非角度的SBM模型被提出[10]。為進一步進行動態效率分析,SBM模型與ML指數結合已成為衡量全要素生產率動態變化的最常用方法[11-12]。目前,較為有效的做法為EBM?GML方法,同時,結合超效率DEA 模型將EBM 超效率化[13]。其優勢在于超效率EBM 模型包含徑向與非徑向兩類距離,該模型是SBM模型的優化,同時該模型考慮了全局的GML指數,也克服了ML指數無可行解的問題。
1. 2 數字化對農業生產效率的影響
數字化發展推動農業生產方式的變革和生產效率的提升[14]。中國數字化轉型開始轉向深化應用、規范發展、普惠共享的新階段,關于數字化發展與農業生產效率關系的研究也隨之展開。例如,數字化與農產品技術進步率的關系[15]、數字經濟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關系[16]、數字經濟與農業企業生產效率的關系[17]、數字金融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關系[18]等。這些研究均認為,數字化能夠有效提升農業生產效率。上述研究成果為深入探索兩者間的因果關系提供了理論和方法借鑒。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碳要素被納入生產效率范疇,但數字化和碳生產率的確切關系尚未有定論。
1. 3 數字化對農業碳生產率的影響
從已有研究的結論來看,如同硬幣的兩面,數字化對碳生產率的影響通常具有雙重效應。一方面,數字化對碳生產率具有抑制作用。例如,已有研究基于澳大利亞的長時間序列數據發現,數字化的發展刺激了電力消費的增長,但電力效率卻未提升,反而增加了本地的碳排放[19]。另一方面,數字化對碳生產率具有改善作用。數字化通過改善能源強度和能源消費規模提升城市碳生產率[20],還可賦能工業碳生產率,且具有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21]。
就數字化對農業碳生產率的影響研究而言,已有文獻仍存在一些局限。Zhong等[22]研究了數字經濟和農業碳強度之間的關系,但農業碳強度作為單要素碳生產率指標,難以反映真實的農業生產效率。此外,其數字經濟指標是基于城市互聯網發展的數據,難以影響到農業農村的生產生活。Jiang等[23]和Xu等[24]基于農業農村數據構建了類似的農村數字化指標,嘗試探討農村數字化和農業綠色發展之間的關系。但前者的重點在于面源污染,且農村數字化指標并未考慮數字化轉型對農村產值的貢獻,因而指標的可靠性較弱。而后者僅考慮了種植業的碳排放,忽視了養殖業碳排放。鑒于農業活動的溫室氣體中有43%來自腸道發酵和糞便管理[25],因而養殖業碳排放不可忽視。此外,上述3篇文獻均未考慮內生性問題。
綜上,為克服已有文獻不足,有必要進一步基于中國數據,全面準確地構建并測度農村數字化指數和農業碳生產率,分析農村數字化和ATFCP之間的因果關系,探討內在影響機制、多維度異質性和空間溢出效應,用以解決“農業經濟增長和農業碳排放”這一矛盾的現實問題,助力實現農村數字化對農業的降碳增產效應。具體而言,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做出探索:第一,研究視角上,立足數字鄉村和“雙碳”背景,探討農村數字化影響農業碳生產率這一議題,以嘗試回答如何實現“農業經濟增長”和“農業碳減排”雙重目標。第二,研究方法上,一是為處理內生性問題,構建了歷史農村公路密度與中國農村互聯網人數的交乘項作為農村數字化的工具變量;二是為解決徑向模型和非徑向模型的固有問題,采用考慮非期望產出的全局Super?EBM 模型,改進了效率測量方法。第三,研究內容上,基于Grossman等[26]提出的經濟增長和環境質量的分解效應理論,并結合中國農村數字化轉型實踐,從技術、規模、結構、集聚和就業5類效應對影響機制進行驗證,結合地理區位、農業生產條件和農村發展環境進行多維度的異質性分析和空間效應分析,即通過提供多層次的實證分析視角,解構二者間的內在邏輯關系。
2 理論分析和研究假說
2. 1 農村數字化對ATFCP的影響機制
農村數字化通過作用于技術創新、規模化、結構升級、產業集聚和勞動力轉型,進而影響農業生產數量、效率和結構,最終影響ATFCP。
技術效應。新經濟增長理論認為,推動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是技術進步,農村數字化所帶來的關鍵技術裝備創新能夠提升農業生產績效。廣泛的研究表明,經濟增長與碳排放存在倒“U”型關系,即存在“環境庫茲涅茨曲線”[27-28]。而隨著農業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農業經營主體和政府追求環境效益。農村數字化助推數字技術在田間地頭落地,能夠盡早達到這一拐點,從而實現降碳和增產的雙贏。
規模效應。農村數字化借助數字技術實現規模經營,提高化肥、農用機械等利用效率,有助于降碳。一方面,依托農村數字化的信息資源整合功能,搭建土地要素流轉平臺,提供規模化經營基礎。另一方面,依托農村數字化的大數據管理功能,構建農業物聯網系統,提供規模化經營技術。
結構效應。根據Grossman等[26]關于經濟增長和環境質量間的3個分解效應,除技術和規模效應以外,農村數字化帶來的結構效應不可忽視。農村數字化以數字技術為紐帶,通過創新賦能實現數字技術與農村產業的融合,促進產業鏈攀升,實現產業結構高級化,因而農村數字化可以實現在提升產品附加值的同時直接減少碳排放。
集聚效應。農村產業集聚主要表現為電子商務催生出產業集群,以“淘寶村”為代表。淘寶村是地理集聚和虛擬集聚的結合體。首先,虛擬集聚本身就是數字化的表征。虛擬集聚的跨時空特征降低了信息獲取成本,有利于資源流向效率更高的部門。同時,虛擬集聚主要基于線上網絡開展經濟活動,本身具有低碳特征。其次,地理集聚帶來規模效應、內部專業化分工效應以及同產業技術溢出效應,進而也能夠極大地提升農業生產效率和緩解資源錯配。
就業效應。隨著數字化在農村的深度應用,電子商務和數字媒體為農村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創收渠道,促進了非農就業[29]。非農就業能夠推動兼業和土地流轉,分別影響農戶投入行為和實現土地規模經營,亦能有效促進農業經濟增長和農業碳減排。
假說1:農村數字化發展能夠提升ATFCP。
假說2:農村數字化的發展通過促進技術創新、規模經營、結構優化、產業集聚和非農就業,進而提升ATFCP。
2. 2 農村數字化對ATFCP的空間溢出影響
農村數字化對ATFCP 的影響可能存在空間溢出效應。根據托布勒第一地理定律,鄰近事物的相關性更為密切,對于農村數字化而言,數字化轉型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它通過高效的信息傳輸壓縮了時空距離,增強了區域間經濟活動的廣度和深度[20]。因此,當地農村數字化發展的經驗和成果可以通過區域合作流入周邊地區,提高周邊農村數字化水平,其空間相關性得以存在[30-31]。對于ATFCP而言,由于CO2等溫室氣體的流動性以及每個地區間的地理聯系,一個地區的農業碳排放亦將影響相鄰地區。Zhong等[22]利用中國30省份面板數據研究數字經濟和農業碳強度之間的關系,發現數字經濟對碳強度的抑制作用具有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這一效應來自技術進步的擴散。因此,農村數字化發展帶來的數字技術擴散,往往能夠對ATFCP產生空間溢出影響,假說3由此提出。理論分析框架圖如圖1所示。
假說3:農村數字化對ATFCP 的影響存在空間溢出效應。
3 材料和方法
3. 1 模型設定
3. 1. 1 基準回歸模型
為考察農村數字化對ATFCP的影響,構建如下計量模型:
3. 1. 2 機制檢驗模型
為避免傳統三步法中介效應模型的缺陷,機制檢驗部分僅進行核心解釋變量rd 對機制變量Mit 的回歸,至于Mit 對被解釋變量atfcpit 的影響,擬采用文獻佐證和道理闡述的方式解決。模型設定如下:
3. 1. 3 動態空間杜賓模型
為探究農村數字化對ATFCP的空間溢出效應,同時考慮農業碳生產率的變化可能存在時間依賴效應以及潛在的內生性問題,將滯后一期的ATFCP引入普通的靜態空間面板杜賓模型,建立動態空間面板杜賓模型,見公式(3):
3. 2 變量選取和說明
3. 2. 1 被解釋變量:農業全要素碳生產率(ATFCP)
采用EBM模型和GML指數測算,分為投入、期望產出和非期望產出3類指標:①投入指標為土地(農作物播種面積)、勞動力(第一產業從業人數)、資本(農業資本存量)、農藥、化肥、農膜使用量、農業用水用電和農業機械總動力。其中,資本存量首先通過縮減指數構造方法,得出第一產業投資數據的價格平減指數[32]。然后根據永續盤存法得出各省份第一產業資本存量數據[33]。②期望產出指標為第一產業實際增加值和農業碳匯量[34]。③非期望產出指標為農業碳排放總量,依據農地利用、畜禽養殖、水稻種植和農村生活碳排放4類碳排放源計算。農地利用為化肥(氮肥、磷肥、鉀肥和復合肥)、農藥、農膜、柴油、翻耕和灌溉。畜禽養殖為生豬、家禽、牛、馬、驢、騾、山羊、綿羊等8種(由于畜禽飼養周期的不同,計算前需對畜禽平均飼養量以出欄率進行調整)。水稻種植為早稻、中季稻和晚稻。農村生活碳排放為農村生活能源碳排放,具體而言:首先,構建農村生活能源消耗數據庫,包含原煤、洗精煤、汽油、柴油、電力等32種能源;其次,將上述32種能源消耗量轉化為標準煤;最后,通過標準煤的碳排放折算系數(0. 68)計算。
3. 2. 2 核心解釋變量:農村數字化
從數字基礎設施、數字創新水平和數字產業發展3個維度構建農村數字化指標體系,見表1。在此基礎上采用熵權法確定各指標權重。相關文獻已建立較為完整的農業農村數字經濟指標體系[30-31],表1中指標體系的改進之處在于:一是根據“發展基礎-發展動力-發展成果”的邏輯,分別對應數字基礎設施、數字創新水平和數字產業發展3個維度,建立了農村數字化指標體系。二是聚焦農村層面的數字化發展,剔除了與農村數字化關聯不強的指標(例如傳統農業技術人員和傳統涉農貸款等)。三是借助省級投入產出表,通過區分涉農數字行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和其他電子設備;儀器儀表;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核算了農村由數字化發展帶來的額外收益。
數字基礎設施。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是農村數字化發展的基礎,其中,互聯網的接入和信息化設備的持有是支持農村數字化運行和發展的基礎[31]。因此,將數字基礎設施作為一級指標,其下設置3個二級指標:①從行政村村級層面和農民個體層面的寬帶接入水平來衡量農村互聯網普及率。②從彩色電視機、移動電話和計算機3個方面衡量農村信息化設備。③農業氣象服務作為數字鄉村建設的基礎生產設施,已在農業生產中發揮愈加重要的作用。因此,也將其納入農業數字基礎設施,具體以農業氣象觀察站數量來衡量農業氣象觀察業務。
數字創新水平。數字創新的水平是農村數字化發展的動力。針對中國農村地區的數字服務水平現實情況設置4個二級指標:①農村數字化的發展應當服務于農村居民,體現為技術驅動。以農村營業網點服務人口衡量信息技術在農村的應用情況。農村營業網點服務人口越多,說明服務網點分布密度越小,因此為負向指標。②農村數字產品與服務消費,該指標用于衡量農村居民對于數字產品的消費水平,體現為消費驅動。以農村居民家庭人均交通通信消費支出來衡量。③農村數字金融體現農村的數字金融能力,體現為金融驅動。以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來衡量。④農村生產投資能夠體現農村數字創新發展的經濟基礎實力,體現為投資驅動。以農村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的投資額來衡量。
數字產業發展。數字產業的發展是農村數字化發展的成果。設置4個二級指標:①生產方面。利用第一產業中的數字經濟規模占比衡量農業生產數字化程度。引入數字經濟調整系數[35],借助省級投入產出表測度第一產業中數字經濟增加值[31]。②流通方面。由于中國物流代表性企業,如順豐和三通一達等快遞業務數據的不可得性,農村物流業務指標用農村郵政業務總量衡量,以體現農村電商、快遞進村的能力。③運營方面。利用農村電子商務銷售額和采購額之和衡量農業數字化運營的能力。④農業數字產業基地能夠有效反映地區農村數字產業化發展的環境優劣,以淘寶村數量來測度。
3. 2. 3 控制變量
為盡可能地緩解遺漏變量偏誤,進一步控制了影響ATFCP的其他變量。①農業經濟發展水平(pgdp),以第一產業增加值與第一產業從業人員比值表示。經濟增長對農業碳排放具有重要影響[28]。②農業產業結構(stru),以種植業和畜牧業增加值之和與農林牧漁增加值之比表示,種植業和畜牧業為農業碳排放的主要來源行業。③農業財政支持(afs),以農林水事務支出和財政支出之比表示。政府的外部政策干預能夠影響碳排放[36]。④環境規制強度(er),以污染治理投資額和GDP的比值來表示,以盡可能反映當地的環境監管強度。⑤農村人力資本(edu),以農村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通常來說教育水平的提升能夠影響邊際減排成本。⑥農業技術投入(tech),以農經機構的專業技術人員數量表示。
3. 3 數據來源
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樣本范圍為2011—2020年中國的30省份(未涉及西藏、香港、澳門和臺灣)。數據主要來自相應年份的《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農產品進出口統計月報》《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和各省級年鑒。數字普惠金融數據來自已有研究成果[37]。此外,為了減輕異方差對模型估計結果的影響,在進行實證分析時所有連續變量均取自然對數。全部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2。其中,農經機構的專業技術人員數據僅統計到2018 年,2019—2020 年通過插值法補齊,因此,存在非整數數據。
4 實證結果
4. 1 基準回歸結果分析
表3報告了農村數字化對ATFCP影響的基準回歸結果。根據Hausman檢驗,固定效應模型是合適的,結果見表3中列(1)和列(3),農村數字化對ATFCP的影響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從列(3)中可以看出,農村數字化水平每提升1%,ATFCP能夠上升0. 629%。據此,假說1得到驗證,即農村數字化能夠提升ATFCP。具體提升作用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農業要素使用效率得以提高,驅動粗放型傳統農業轉型精細化高效農業;二是催生低碳新業態,從產業結構層面實現農業產值增長和農業碳排放的相對減少。因此,在兩個方面作用下實現農村數字化對ATFCP的提升。
控制變量方面,農業產業結構對ATFCP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說明種植業和養殖業作為主要的兩大農業碳排放來源,這兩類行業比重的上升往往帶來更大的農業碳排放,不利于ATFCP提升。農業財政支持和農村人力資本對ATFCP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前者的原因在于發展低碳農業勢必需要政府財政支持,政府財政對低碳生產的經營主體給予補貼,引導經營主體進行更加有效的低碳農業生產,而政府財政對“雙碳”技術研發機構的支持,鼓勵經營主體研發低碳農業技術。后者的原因在于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通常更傾向選擇更為低碳的農業生產方式,從而影響邊際碳投入,帶動ATFCP的提升。
4. 2 穩健性檢驗
采取3種穩健性檢驗方法:一是自變量滯后。在時間層面,考慮到農村數字化對ATFCP的影響存在滯后影響,將農村數字化的一階滯后項和二階滯后項作為核心解釋變量進行回歸。二是控制區域時間趨勢項。在區域層面,中國長期以來受到區域發展政策和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響,各區域發展存在明顯的差異。這些差異可能隨著時間的變化影響結果的正確估計。為此,構造區域虛擬變量(東中西部)和時間趨勢變量的交互項。三是剔除直轄市。考慮到樣本選擇偏差問題,直轄市具有政策和經濟天然優勢,數字經濟基礎好。因此,剔除北京、天津、重慶和上海4個直轄市樣本。結果見表4。在3種穩健性檢驗下,農村數字化均能顯著提升ATFCP,證明了基準回歸結果的穩健性。
4. 3 內生性討論
為緩解模型可能的內生性問題,采用IV?2SLS方法處理。以往相關研究多選用1984年的郵電歷史數據作為數字化指數的工具變量。但是,農村數字化的發展不同于城市。由于農村數字化起步晚、發展慢,其發展程度往往與當地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水平密切相關。區域層面的郵電發展水平難以影響農村層面的數字化發展,不滿足“相關性”條件。此外,郵電指標不能完全脫離經濟體系,不滿足“外生性”條件[20]。鑒于此,遵循農村基礎設施和農村數字化具有緊密關系這一邏輯,同時,鑒于樣本中重慶于1997年正式設為直轄市,選擇1998年農村公路密度作為工具變量。由于截面數據無法進行面板數據的計量回歸,參考已有做法[38],增加一個時變的變量進行交互。具體而言,以上一年全國農村互聯網用戶數分別與1998年各省農村公路密度構造交互項。
工具變量的選取需要滿足相關性與外生性兩個條件:一是相關性。農村數字化的發展有賴于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數字基礎設施的“數字”相對于傳統基礎設施而言,其本質仍然是基礎。根據農村基礎設施發展的歷史和延續性,中國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史上最關鍵的項目是“村村通”,主要指通公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村村通”項目的重點逐漸轉向通寬帶,從傳統基礎設施建設向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推進。因此,歷史農村道路密度會影響后續農村發展[39],這對農村數字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二是外生性。通常來說,公路并不會影響當前農業的碳生產率[40]。但農村公路會影響農村經濟的發展,這可能會導致內生性,即工具變量不是因變量受到影響的唯一路徑,從而影響工具變量的排他性約束。為了解決這一問題,采用了以下3種方法:①選擇歷史數據,1998年的數據與當前的樣本數據相對較遠,因此,很難與當前的因變量和擾動項相關聯。②根據中國的“農村公路建設規劃”,到2010年,所有符合條件的建制村基本上都建立了油路(水泥)公路連接(樣本期為2011—2020年)。因此,農村公路的差異至少不會成為影響各省份ATFCP 的重要因素。③已將農村經濟水平作為控制變量納入實證模型,以更好地控制和觀察農村經濟對因變量的影響。此外,盡管構建了1個交互項,但國家層面的農村互聯網用戶數量不會直接影響每個省份的農村互聯網用戶數量。總體而言,工具變量的選擇是合理的。
表5中2SLS模型的列(1)和列(2)結果表明:第一階段中,工具變量和自變量滿足相關性,農村公路密度大,歷史基礎設施條件越好,越有利于后續農村數字化發展;第二階段中,農村數字化對ATFCP的影響依然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且均通過工具變量有效性檢驗。此外,由于構造的工具變量本質上為地方層面的信息與國家層面的信息相結合,因此,進一步構造了一個Bartik 工具變量[41]:rdi,t - 1 × △rdt,t - 1 即一階滯后農村數字化指數與農村數字化指數在時間上的一階差分的乘積,將其加入2SLS模型中,結果依然成立。
4. 4 機制分析
為驗證假說2,對農村數字化影響ATFCP 的作用渠道進行檢驗。根據前文理論分析,農村數字化能夠通過技術創新、規模經營、結構升級、產業集聚和非農就業等路徑影響ATFCP。
第一,技術效應。為了實證考察農村數字化對技術創新的影響,構造了技術創新指標。通常來說,專利被認為能夠較好捕捉技術創新能力。但由于申請意愿和制度保護等因素,專利數量實際上并不能正確反映技術創新水平[42]。為客觀準確反映中國農業技術創新現狀,手工整理了中國農業科學院發布的農業知識產權報告。以報告中的農業知識產權創造指數來衡量技術效應,結果見表6列(1)。結果表明,農村數字化水平每提升1%,技術創新水平提升0. 647%,說明農村數字化顯著促進了技術創新。現有研究基本證實了技術創新和ATFCP之間的正向關系。例如,Liu等[40]基于省際數據,發現技術溢出作用體現在農業研發投入的增加,以及綠色低碳技術的采用和應用,提升了生產效率和減少了碳產出,由此提升了ATFCP。Huang等[43]通過對ATFCP 進行生產分解發現,技術進步亦是ATFCP提升的關鍵驅動力。
第二,規模效應。為了實證考察農村數字化對規模經營的影響,構造了規模經營指標。使用規模化經營水平(農作物播種面積和農村戶數的比值)衡量規模效應。原因在于,農業的小規模經營往往是與家庭經營組織相匹配的。因此,以家庭為單位的測度,較個體勞動力更為準確,即農村每戶人家所經營的農地面積,結果見表6列(2)。結果表明,農村數字化水平每提升1%,規模經營水平提升0. 254%,說明農村數字化顯著推動了規模經營。現有研究基本證實了規模經營和ATFCP之間的正向關系。例如,Zhu等[44]結合微觀截面和宏觀面板數據,發現規模經營能夠有效降低農業生產要素的使用強度,從而實現ATFCP的提升;魏夢升等[45]以糧食主產區政策為例,發現該政策的糧食增產和碳減排效益主要得益于規模經營效應,表現為通過規模經營以提升農資的利用效率,最終提升ATFCP。
第三,結構效應。為了實證考察農村數字化對結構升級的影響,構造了結構升級指標。使用基于余弦法計算的農業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數衡量結構效應[46],結果見表6列(3)。結果表明,農村數字化水平每提升1%,結構升級水平提升0. 033%,說明農村數字化顯著促進了結構升級。現有研究基本證實了結構升級和ATFCP之間的正向關系,例如,田云等[47]利用脫鉤模型研究了農業碳排放的效率和公平,發現產業結構的優化能夠有效改善農業增長和農業碳排之間的矛盾,從而提升ATFCP。
第四,集聚效應。為了實證考察農村數字化對產業集聚的影響,構造了產業集聚指標。使用區位商(agg =Ei /EtAi /At,Ei 為一省份的農業就業人數,Et 為一省份全部就業人數,Ai 為全國農業就業人數,At 為全國就業人數)衡量產業集聚水平,結果見表6列(4)。結果表明,農村數字化水平每提升1%,產業集聚水平提升0. 273%,說明農村數字化顯著促進了產業集聚。現有研究基本證實了產業集聚和ATFCP之間的正向關系,例如,Liu等[40]指出集聚能夠充分發揮集聚規模經濟效應,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農業生產效率和碳減排,最終有助于提高ATFCP。
第五,就業效應。為了實證考察農村數字化對非農就業的影響,構造了非農就業指標。使用非農就業收入(農民工資性收入、資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之和)衡量非農就業水平,結果見表6列(5)。結果表明,農村數字化水平每提升1%,非農就業水平提升0. 235%,說明農村數字化顯著促進了非農就業。現有研究基本證實了非農就業和ATFCP之間的正向關系,例如,Chang等[48]利用分位數回歸模型研究了非農就業和農業化學品使用之間的關系,發現非農就業能夠有效降低包括化肥在內的各類化學品使用,有效減少了邊際碳產出,從而提升ATFCP。
4. 5 異質性分析
進一步討論農村數字化在不同地理區域、農業生產條件和農村發展環境下對ATFCP的影響。
4. 5. 1 區位條件
農村數字化對ATFCP增長的帶動效應,可能由于區位條件不同而產生差異。因此,將樣本分為東、中、西和東北4組,不同區位條件異質性結果見表7。結果表明,農村數字化能夠顯著提升東部和西部的ATFCP,尤其是東部地區的回歸系數(1. 396)顯著大于基準回歸的系數(0. 629)。其可能的原因在于兩個方面:一是東部地區經濟發達,數字基礎設施較為完善,網絡化程度較高,較其他地區相比本身數字產業發達;二是東部地區農村普遍現代化程度高,其中,浙江省更是常年位于中國農村人均收入首位,數字經濟易于向農村下沉、農民接受程度高。兩方面因素有利于實現農村數字化。在中部和東北部地區,農村數字化對ATFCP的提升作用并不顯著。可能的原因在于兩類地區城鄉差距大、數字基礎較弱,就城鎮化率而言,中部6省只有湖北省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對農村的支持能力相應偏弱,城鄉“數字鴻溝”難以彌合。
4. 5. 2 碳生產率水平
為分析農村數字化對不同分位點ATFCP的影響,進一步采用雙向固定的分位數模型驗證,結果見表8。結果表明,在5個分位點上,農村數字化對ATFCP均存在顯著正向影響,隨著ATFCP水平不斷提升,提升作用逐漸減弱,表現為邊際效益遞減。
4. 5. 3 農業綠色發展水平
因政策支持、經濟發展和資源稟賦差異,中國各省份農業綠色發展水平不盡相同,在此差異下,農村數字化對不同農業綠色發展水平地區的ATFCP的影響可能產生差異。參考《中國綠色發展指數報告:區域比較》(2011—2019)獲取30省份綠色發展水平數據,重新進行參數估計,結果見表9列(1)和列(2)。結果表明,農村數字經濟對ATFCP均顯著為正,說明數字化的綠色效應并不會受到當地已有綠色發展水平的限制,驗證了數字化的包容性,亦符合表8中分位數回歸的結果。
4. 5. 4 農村金融發展水平
自從數字技術融入農村金融業態以來,數字金融在農村得到了廣泛應用和推廣。實際上,數字金融的嵌入會受到農村自身金融發展水平的約束,因此,農村數字化對ATFCP的提升作用可能會受到傳統金融發展的影響。為此,以農村金融發展水平(農民貸款與農林牧漁總產值的比值)作進一步異質性分析,結果見表9列(3)和列(4)。結果表明,農村數字化僅在高金融水平地區表現出顯著的正向影響,說明農村數字化與農村金融之間存在一個“金融門檻”,金融水平低的農村不僅存在物理排斥,較低的金融水平通常意味著數字基礎設施的不完善,而且還存在自我排斥,農戶金融素養的匱乏導致數字金融的難以普及。綜合作用下,農村金融水平較低的地區會制約農村數字化的發展。
5 進一步討論:空間效應分析
為檢驗農村數字化和ATFCP 的空間自相關,使用Moran's I 指數來測試,結果見表10。結果表明,2011—2020年農村數字化的Moran's I 均在1% 或5% 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說明農村數字化具有顯著的空間自相關。ATFCP的Moran's I 雖然只有2020年顯著為正,但是總體Moran's I 仍然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因此,仍有必要作進一步的空間效應分析。
LM檢驗、LR檢驗和固定效應選擇項檢驗結果表明具有時空雙重固定效應的SDM模型是合適的。表11顯示了農村數字化對ATFCP的空間效應估計結果。同時給出了空間回歸模型在經濟距離、地理距離和嵌套3個權重矩陣下的估計,以驗證其穩健性,結果見表11 列(1)—列(3)。結果表明,空間自回歸系數(ρ)均顯著為正,證明了空間效應的存在。由于空間相互作用項(w×rd)的回歸系數不能直接用于討論空間邊際影響。因此,為進一步測量相鄰區域間復雜的空間相關性,通過計算偏導數得到系數,用總效應、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來描述相鄰區域的空間邊際效應,結果見表11列(1)。結果表明,短期和長期的間接影響分別在1%和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農村數字化對ATFCP存在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假說3得到驗證。可能的原因在于數字技術的跨時空信息傳播和共享增強了區域間的農村經濟活動,即農村數字化的發展能夠突破經濟距離差異,不僅提升本地ATFCP,同時起到示范和引領作用,從而提升鄰近地區的ATFCP。在地理距離矩陣下,農村數字化對ATFCP仍具有正向的空間溢出效應,但間接效應并不顯著。在嵌套矩陣下,結論和經濟距離矩陣下的結果基本一致。
6 結論和啟示
6. 1 結論
基于2011—2020年中國30省份的面板數據,構建農村數字化綜合指標,運用EBM?GML方法量化ATFCP,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分位數模型和動態空間杜賓模型等方法探索農村數字化對ATFCP的影響,得出如下研究結論。
第一,農村數字化能夠顯著提升ATFCP,在經過工具變量等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該結論依然成立。
第二,農村數字化通過推動技術進步、規模經營、結構升級、產業集聚和非農就業,進而實現ATFCP增長。
第三,農村數字化對ATFCP的提升作用存在區域異質性,東部地區因其經濟基礎優勢,農村數字化能夠發揮更大的積極效應。總體來看,農村數字化表現為邊際效益遞減的正向影響,在綠色發展水平低或高的地區均能發揮顯著提升作用,在農村金融發展水平高的地區農村數字化的影響更為顯著。
第四,農村數字化對ATFCP具有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短期和長期間接效應均顯著為正。
6. 2 啟示
以數字技術和傳統農業的融合為代表的農村數字化將是實現“農業經濟增長”和“農業碳減排”雙重目標的重要工具。據此,結合上述結論,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鑒于農村數字化在提高農業碳生產率方面具有紅利效應,未來應加大數字農業領域新技術、新產品和新模式的應用推廣力度,盡快將農業傳感器、智能裝備等納入農機購置補貼。堅持推進“寬帶下鄉”和“數字鄉村”戰略,實現農村4G或5G網絡覆蓋,保證農村居民基礎的信息服務。同時,嘗試設立數字經濟示范村和農業大數據試點縣,推動數字成果盡快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第二,鑒于農村數字化通過技術、規模、結構、集聚和就業效應提升農業碳生產率,未來需加快推進覆蓋農業全產業鏈條的數字農業試驗區建設,促進產業集聚和加強農業綠色技術的創新,由此發揮規模經營和技術進步的協同作用。同時,調整農村產業發展重點,借助農村數字化推進農業與數字產業的融合,助力農特產品搭上“數字快車”和農文旅融合插上“數字化翅膀”,實現農業結構升級和就業多元化。
第三,鑒于農村數字化對農業碳生產率的影響具有顯著區域異質性,未來應總結和提煉東部地區成功經驗,實施動態化和差異化的數字鄉村發展戰略。對于農業綠色低碳發展已取得較好成效的地區,進一步鞏固農村數字化的降碳增產紅利,注重技術擴散,對低數字化水平的地區進行幫扶。對于低金融水平地區來說,優先發展農村金融機構,弱化物理排斥與自我排斥,發揮傳統金融對農村數字化發展的支撐作用。
第四,鑒于農村數字化對農業碳生產率的影響具有顯著空間溢出效應,未來應重點完善區域間的合作機制,借助數字化能夠突破經濟距離限制的優勢,打造一體化的數字經濟智慧服務平臺,建立龐大的數字經濟服務數據庫,實現數據資源和平臺共享,加強農業生產環境信息公開和技術擴散。
參考文獻
[1] 于卓卉,毛世平. 中國農業凈碳排放與經濟增長的脫鉤分析
[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22,32(11):30-42.
[2] FUGLIE K,RAY S,BALDOS U L C,et al. The R&D cost of climate
mitigation in agriculture[J]. Applied economic perspectives and
policy,2022,44(4):1955-1974.
[3] ALEKSANDRAL A, EMILY M, YOU L, et al. 5 Questions about
agricultural emissions, answered[EB/OL].(2019-07-29)[2023-
03-16]. https://www. wri. org/insights/5?questions?about?agricultural?emissions?answered.
[4] KARKACIER O,GOKALP GOKTOLGA Z,CICEK A. A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energy use in agriculture[J]. Energy policy,
2006,34(18):3796-3800.
[5] TILMAN D,BALZER C,HILL J,et al. Global food demand and the
sustainable intensification of agriculture[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11,
108(50):20260-20264.
[6] LITVINENKO V S. Digital economy as a factor in th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of the mineral sector[J].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2020,29(3):1521-1541.
[7] LIOUTAS E D,CHARATSARI C,DE ROSA M. Digit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a way to solve the food problem or a trolley dilemma[J].
Technology in society,2021,67:101744.
[8] XIE Y,CHEN Z,BOADU F,et al. How do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ased Measure (SBM) approach[R]. Tokyo:National Graduat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2004.
[11] CHUNG Y H,F?RE R,GROSSKOPF S. Productivity and undesirable
outputs: a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approach[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1997,51(3):229-240.
[12] LI Y,CHEN Y Y. Development of an SBM?ML model for the measurement
of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he case of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J].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2021,145:111131.
[13] ANDERSEN P,PETERSEN N C. A procedure for ranking efficient
units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J]. Management science,
1993,39(10):1261-1264.
[14] 孔凡斌,程文杰,徐彩瑤. 數字經濟發展能否提高森林生態產
品價值轉化效率:基于浙江省麗水市的實證分析[J]. 中國農村
經濟,2023(5):163-184.
[15] 楊入一,孔繁濤. 數字化發展與農產品批發市場技術進步:兼
論農產品電商渠道的中介效應[J]. 中國流通經濟,2023,37
(3):3-16.
[16] 孫光林,李婷,莫媛. 數字經濟對中國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
響[J]. 經濟與管理評論,2023,39(1):92-103.
[17] 王菲,劉天軍,宋經翔. 數字經濟發展能提高農業企業加成率
嗎:基于全國53196家農業企業的微觀證據[J]. 山西財經大學
學報,2022,44(11):15-27.
[18] 唐建軍,龔教偉,宋清華. 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
基于要素流動與技術擴散的視角[J]. 中國農村經濟,2022(7):
81-102.
[19] SALAHUDDIN M,ALAM K. Internet usage,electricity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ustralia:a time series evidence[J].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2015,32(4):862-878.
[20] ZHANG W,LIU X M,WANG D,et al. Digital economy and carbon
emission performance:evidence at China's city level[J]. Energy
policy,2022,165:112927.
[21] 任曉松,孫莎. 數字經濟對中國城市工業碳生產率的賦能效應
[J]. 資源科學,2022,44(12):2399-2414.
[22] ZHONG R X,HE Q A,QI Y B. Digital economy,agricultural technological
progress,and agricultural carbon intensity:evidence from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2022,19(11):6488.
[23] JIANG Q,LI J Z,SI H Y,et al.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evidence from China[J]. Agriculture,
2022,12(8):1107.
[24] XU N,ZHAO D S,ZHANG W J,et al. Do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mote agricultural carbon productivity in China[J]. Land,2022,
11(11):1966.
[25] 翟鄖秋,張芊芊,劉芳,等. 我國畜禽養殖業碳排放研究進展
[J]. 華南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22,54(3):72-82,2.
[26] GROSSMAN G M, KRUEGER A B.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R]. Combridge: National
Bureac of Economice Research, Inc, 1991.
[27] LIU D N,XIAO B W. Can China achieve its carbon emission peaking:
a scenario analysis based on STIRPAT and system dynamics
model[J]. Ecological indicators,2018,93:647-657.
[28] ZHANG L,PANG J X,CHEN X P,et al. Carbon emissions,energy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evidence from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of China's main grain?producing areas[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019,665:1017-1025.
[29] ZHOU D, LI B. How the new media impacts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n empirical study[J].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2017, 9(2): 238-254.
[30] 朱紅根,陳暉. 中國數字鄉村發展的水平測度、時空演變及推
進路徑[J]. 農業經濟問題,2023,44(3):21-33.
[31] 慕娟,馬立平. 中國農業農村數字經濟發展指數測度與區域差
異[J]. 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20(4):90-98.
[32] 徐現祥,周吉梅,舒元. 中國省區三次產業資本存量估計[J].
統計研究,2007,24(5):6-13.
[33] 宗振利,廖直東. 中國省際三次產業資本存量再估算:1978—
2011[J]. 貴州財經大學學報,2014(3):8-16.
[34] 田云,張俊飚. 中國農業生產凈碳效應分異研究[J]. 自然資源
學報,2013,28(8):1298-1309.
[35] 許憲春,張美慧. 中國數字經濟規模測算研究:基于國際比較
的視角[J]. 中國工業經濟,2020(5):23-41.
[36] GALINATO G I,GALINATO S P.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 spending
on deforestation due to agricultural land expansion and CO2 related
emissions[J]. Ecological economics,2016,122:43-53.
[37] 郭峰,王靖一,王芳,等. 測度中國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指數編
制與空間特征[J]. 經濟學(季刊),2020,19(4):1401-1418.
[38] NUNN N,QIAN N. US food aid and civil conflic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4,104(6):1630-1666.
[39] WANG Z, SUN S.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J].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2016, 8
(3): 516-525.
[40] LIU H, WEN S, WANG Z.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gglomeration
and total factor carbon productivity: based on NDDF?MML index
analysis[J].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2022, 14(4):
709-740.
[41] 易行健,周利. 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是否顯著影響了居民消費:
來自中國家庭的微觀證據[J]. 金融研究,2018(11):47-67.
[42] FUNK J. Beyond patents: scholars of innovation use patenting as
an indicator of both innovativeness and the value of science, it
might be neither[J]. 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8, 34
(4): 48-54.
[43] HUANG X Q,FENG C,QIN J H,et al. Measuring China's agricultural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its drivers during 1998-
2019[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022,829:154477.
[44] ZHU W,WANG R M. Impact of farm size on intensity of pesticide
use:evidence from China[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21,753:141696.
[45] 魏夢升,顏廷武,羅斯炫. 規模經營與技術進步對農業綠色低
碳發展的影響:基于設立糧食主產區的準自然實驗[J]. 中國農
村經濟,2023(2):41-65.
[46] 付凌暉. 我國產業結構高級化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
[J]. 統計研究,2010,27(8):79-81.
[47] 田云,吳海濤. 產業結構視角下的中國糧食主產區農業碳排放
公平性研究[J]. 農業技術經濟,2020(1):45-55.
[48] CHANG H H,MISHRA A K. Chemical usage in production agriculture:
do crop insurance and off?farm work play a part[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12,105:76-82.
(責任編輯:李琪)
affect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pro?land behavior: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gnition and cross?border search[J]. Technology
in society,2022,70:101991.
[9] SUEYOSHI T,GOTO M. World trend in energy:an extension to
DEA applied to energy and environment[J]. Journal of economic
structures,2017,6(1):13.
[10] TONE K. Dealing with undesirable outputs in DEA: a Sla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