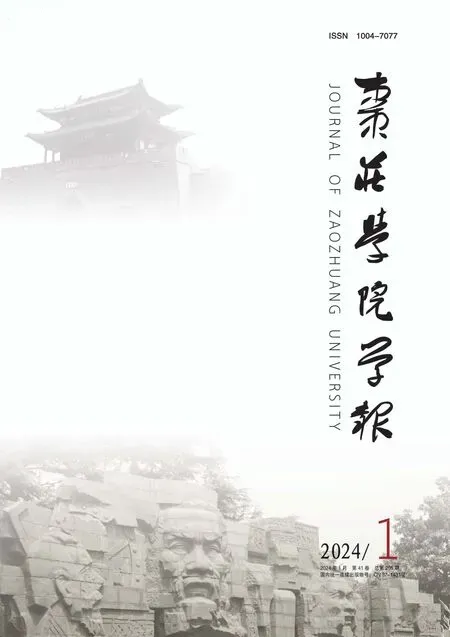《長恨歌》:自戀、主體性缺失及匱乏需求的關系
孫凡迪
(1.北京語言大學 文學院,北京 100083;2.中國氣象局 華風氣象,北京 100081)
自戀情結緣起于古希臘神話中那個相貌出眾的少年喀索斯。在中國文學中,自戀情結的大規模亮相是在20世紀90年代的女性小說中,這既是個人自戀的情結氤氳了文學中大片的自戀氛圍,也是多元化快速發展的時代催生了個人和文學中相互傍依的自戀因子。自戀包含三個特征:一是夸大、積極的自我概念;二是為維持這種積極自我概念所采取的自我調節策略;三是低共情、低親密度的人際關系。[1](P199~210)
20世紀以來,許多學者從不同角度闡述了自戀的含義。1914年,弗洛伊德(SigmundFreud,1856~1939)在《論自戀》(OnNarcissism)中首次系統地論述了自戀,并把其納入精神分析領域。自戀是一個具有多維結構的概念,表現為浮夸、自愛和膨脹的自我,就其功能而言,自戀“既好又壞”。自戀者與人交往之初多能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但這種人際關系的虛假性會在長期的互動中暴露出來;從決策的角度來看,自戀者的過度自信、高度冒險以及對回報的短視常常導致其決策偏差。艾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在1941年發表的《逃避自由》(EscapeFromFreedom)中認為,適當良性自戀可以對人的精神活動有積極意義,自戀是自我認同的主要機制,在建構主體過程中具有必要性。他同時還討論了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應付孤獨感的幾種心理機制,稱之為性格的動力傾向性。過于自戀的人往往具有接納傾向性,這類人沒有生產或提供愛的能力,他所需要的一切完全尋求別人幫助、依賴別人,是接受者而不是給予者。而具備創造性傾向性的人卻可以主動創造可能、構建關系,讓自體在關系的流動中逐漸強大,從內心主動覺知、思索、體察愛與被愛,繼而創造出有價值意義的思想和行動。
西方自戀理論伴隨著西方女權主義漂洋過海,來到了渴望突破男權社會、重塑真實自我的中國女性作家面前。在自戀理論影響之初,有不少女性作家推崇追求自我、體認和肯定自我的價值論,把過分理想和膨脹的自我奉為一切成長的內在動力。自戀在90年代的文學中更多地體現在女性作家把對自我的欣賞和本土文化的偏執熱愛,轉嫁到小說女主人公的身上和故事里,表現為對她們不分對錯的同情、明目張膽的偏愛和光明正大的抬高。本文以《長恨歌》為例,探討自戀、主體性缺失及匱乏需求的關系問題。
一、自戀:海派文化的優越感和原生家庭自卑感的怪異產物
《長恨歌》中王琦瑤的悲劇是過度自戀導致的,但首先是作者的自戀賦予了她這份自戀的權力,從而揭示了90年代女性作家的某種身份焦慮和精神危機。50~70年代的小說對女性人物的敘事是以祛除女性獨特的性別特征、生命體驗為指征的,對歷史驅動和革命理想的書寫湮沒了對女性主體性和差異性命運的思考。但是,90年代以來女性書寫呈現出日益繁雜的樣態,女性的成長又被簡單粗暴地扭曲為與男權意識的對抗、欲望化敘事,這種激進化態度似乎讓90年代的女性文學走向了與建構自足、自立、自強的女性生命主體和生存空間的反面。女性的成長敘事、感性經驗、世俗人性或者日常生活,與女性自我主體的建構,往往有著一種對立、緊張和互峙的關系。[2](P164)
《長恨歌》對女性的書寫,假借了新舊海派文化交織變遷的幌子,對小說中人物的同情與贊美很多時候影響了我們客觀理性的判斷。通篇看到的是對王琦瑤命運充滿憐香惜玉般的同情,并唱起了因同情發酵出來的悲愴贊歌,而王琦瑤也順遂地成了一個因過度自戀而步步喪失女性主體性的人。在一段段自我的糾結踟躕,以及與男人的情愛糾葛和女性的明爭暗斗中,王琦瑤鈍化著覺知,撕裂著意識,加劇著匱乏,最終導致其徹底拒絕成長,更引發了她無休止的自戀,直到在自戀的幻影中死去。王琦瑤的40年人生,在自戀的視域下或許是跌宕起伏的一生,而客觀審視之后,充其量只是始終走不出弄堂的深閨怨婦靜滯沉淪的40年,同情用錯了地方,也是自戀的體現。
她們漫長一生都只為了一個短促的花季,百年一次盛開。她們是美的使者,這美真是光榮,這光榮再是浮云,也是五彩的云霞,籠罩了天地。那天地不是她們的,她們寧愿做浮云,雖然一轉眼,也是騰起在高處,有過一時的俯瞰。虛浮就虛浮,短暫就短暫,哪怕過后做他百年的爬墻虎。[3](P233~234)
無論是浮云還是爬墻虎,似乎都看得出作者內心是深知這些“王琦瑤們”的結局會是多么不幸,但她還是給與了“王琦瑤們”足夠的同情和理解。小說對王琦瑤原生家庭描述不多,但可以看出她和母親關系的冷淡,而且從不同角度的描述對比中,也能感覺到王琦瑤的家庭是很一般的小市民家庭。在上海這種物欲橫流的城市氛圍下,她內心希望依仗姿色成名成媛的強烈欲望,使她對現實生活越來越不滿。后來,她有機會和家境優越的蔣麗莉成為朋友,并被邀請住進蔣麗莉家。那個夜晚,王琦瑤內心的自卑和自戀再一次不可遏制地交織在一起噴涌出來:
她聽著靜夜里的聲音,這聲音都是無名的,而不像她自己家的夜聲,是有名有姓:誰家孩子哭,奶娘哄罵孩子的聲;老鼠在地板下賽跑的聲;抽水馬桶的漏水聲。這里只有一個聲音有名目,像是萬聲之首的,那就是鐘聲。它凌駕于一切聲息之上,那些都是它的余音,是聲的最細小的筆觸,是夜的出聲的冥想。[3](P131)
不滿卻又無法改變的自卑,讓自己的自戀像無根而又肆無忌憚的浮萍,隨便抓住一點可以攀上的高枝,就可以傾注一切,所以遇到高官李主任的時候,王琦瑤骨子里那股媚勁兒和處理人情的老道世故就顯現出來了。她其實很懂這類男人,用自己無條件的“乖”迎合他們的一切需求,從而讓自己獲得躍龍門的機會。為了實現這一人生理想,王琦瑤急得連婚紗也沒來得及穿就 “獻”了身。
在男權社會,女人要想活得錦衣玉食、高人一等,只有王琦瑤式的倒貼才是最快和最省力的捷徑,但王琦瑤選擇的這條路只能讓自己一輩子被人戳脊梁骨,很難再有抬頭之日。海派文化就算再包容,再進步,也無法脫離中華民族根上的美德標準,王琦瑤走到這一步既違背孝道,也毫無操守德行可言。還待字閨中的時候,家人就對她保持著一種不正常的疏離和生分,父母很多時候也要把她當客人款待,不敢得罪。在作者筆下,原生家庭帶來的自卑,海派文化對“美”的盲目偏愛,導致很多女性的價值失衡,并助長了一大批“王琦瑤們”病態的自戀情結暗潮涌動。“情結”一詞是榮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最早使用的,他認為“情結是個人潛意識中一組組心理內容的聚集,有似完整人格中彼此分離且獨立自主的一個個小人格;它有自己的驅力,并可以強有力地控制與支配一個人的思想與行為”[4](P9),情結大多是心靈分裂的產物。王琦瑤的自戀情結,就源自對名利世俗的貪婪和對現狀生存的強烈不滿,這兩種情緒是在“無意識色彩的自發內容”沖擊下,一點點吞噬主體意識而形成的,自戀情結變成了王琦瑤內生的基因。在病態生長的自戀中一次次敗下陣來的王琦瑤,如果將自戀的勁頭放在自我主體性的覺醒和成長上,也不會落得如此悲慘的下場。
二、自戀導致女性主體性的缺失
女性主體性,是女性認識到自身作為主體而存在,通過不斷地反思和行動,超越自身處境,在現實社會實踐中追求自身在生活方式、知識技能、社會地位、人格塑造等方面不斷提高的自覺能動性。在小說中,王琦瑤一直自以為主體意識明確,卻始終活在對客體的依附中而不自知。愛的缺失導致愛的能力缺位,沒有愛的能力,就只能用日益膨脹的自戀來獲取縹緲的希望和虛假的安全感。一直假裝冷漠地對待世界的王琦瑤,其實內心比誰都更強烈渴望被關注、被疼愛。自戀為何導致了其主體性的缺失,可以從與自己的關系、對男性的依附和對女性的態度這三個層面看出緣由。
(一)自戀:讓美成為一切的免死金牌
在與自己的關系中,王琦瑤始終認為靠美可以擁有一切。小說開頭先是用了四個章節描摹海派文化中的弄堂、流言、閨閣、鴿子,然后才是王琦瑤的登場。王琦瑤的自戀,就源自上海這座城市給予美人們的天生優越感,以及在優越感里夾帶著的清冷和迷惘。小說對王琦瑤的描述用了兩個“典型”:其一,“王琦瑤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兒”;其二,“王琦瑤是典型的待字閨中的女兒”。“她們夏天一律疰夏,冬天一律睡不暖被窩,她們需要吃些滋陰補氣的草藥,藥香彌漫。這都是風流才子們在報端和文明戲里制造的時尚,最合王琦瑤的心境,要說,這時尚也是有些知寒知暖的。”[3](P53)小說中的價值觀都是圍繞美與丑進行的,長得美的人即便作態也是可愛的,而長得丑的人活該要比別人低一等。吳佩珍的出場和王琦瑤形成鮮明對比,只不過作者這樣對“美”的一味縱容和對“丑”的慣性歧視,雖然給予王琦瑤一塊免死金牌,卻最終把她送上黃泉路。
《長恨歌》中人物間的直接對話很少,而作者的轉述很容易帶著立場和情緒。王琦瑤和吳佩珍都不再只是小說中的人物,更像是作者價值觀附帶下的女性符號。美就是王道,丑就是卑微。王琦瑤因自戀而夸大自己的美,又因為美而深深陷在狂妄可笑的自戀中,所以從未清醒的她一直沒有真正的主體概念。從最初去片場,到后來坐在程先生的相機前,再到成為上海選美的“三小姐”,她無時無刻不惦記著這份美給她帶來所渴求的一切,雖然有時有些故作姿態。作者或許意識到了這份美的單薄,因此也想讓這份美有更深的厚度,想賦予這種美一種內在的智慧。
王琦瑤卻是個不犯錯誤的例外。她比較聰敏,天生有幾分清醒,片廠的經歷又增添了見識,這就使她比較含蓄和沉著。要說作態,她也有,是不作態的作態,以抑代揚,特別適合照片的表現。……她心情很明凈,拍過的照片她不再去想,當它是樁沒結果的事情。[3](P88)
可是她真的不在乎嗎?她是太在乎自己的美貌了,所謂的不去想,只是怕自己對美貌的自戀贏不過世俗的評判和權錢的交易而已。因此,王琦瑤的這份美,毫無人生智慧可言,世俗的小聰明倒比比皆是。她的這種美是在女性價值觀尚未成熟前極其危險的誘餌,她會把美當做攀上高枝的資本。單純的美,讓王琦瑤因自戀而走向危險,夾雜著世故的美和自戀,讓王琦瑤步步淪陷,直至徹底丟失自我。跟著李主任住進“愛麗絲”公寓的日子,讓她迅速飛上云端,又瞬間跌至地獄。而王琦瑤從未反省過當初錯誤的選擇,只是逃離到外婆住的鄔橋,一味自憐自艾。
因為丟失自我主體性,拒絕成長,所以王琦瑤對有限肉身和生命長度極為關注,她擔心時光會帶走美賦予她的一切權利。“她想,老這東西真可怕,逃也逃不掉,逼著你來的。走在九曲十八彎的水道中,她萬念俱灰的只有‘老’這一個字刺激著她。”[3](P302)從愛麗絲公寓跌回人間的王琦瑤感到絕望,而更大的絕望還在等著她,沒有了李主任這棵大樹之后,最大的恐懼就是接下來找誰攀附,小說又借著外婆的話,再次把王琦瑤的美兜售一遍,但這里面竟然還是充滿了深深得同情,絲毫沒有怒其不爭。
從作者對王琦瑤的塑造中,我們也逐漸認識到王琦瑤真實的自我認知。她一味回避自己失了德行和操守,覺得最初的選擇并沒有錯,只是因為李主任的突然死去,自己從天上掉到地下,自己一直都是受害者。這就是王琦瑤搬進平安里之前,由美和無知而產生的過度自戀所導致的悲劇根源。她從來沒有過“自我”的主體意識。筆者認為,《長恨歌》傳遞了一種錯誤且帶有迷惑性的價值觀所滋生的文化優越感,這種優越感恰恰為那些因自戀而喪失主體性的女性拒絕自體的成長,提供了一個錯誤的精神向度。其實,除了沉溺于自己的美,自戀更可以也更應該是源于自體的成熟與強大。
(二)自戀:導致寄生
王琦瑤一生都在尋找可以令自己高枕無憂而寄托終生的男人。太過自戀的王琦瑤,不僅對自我的態度上從未清醒,而且她的夢還一直纏繞在所有和她有交集的男人身上。適度的自戀可以促使女性主體性的增強,但是過度的自戀就會抹殺主體意識。女性主義哲學的起點是波伏娃的《第二性》,波伏娃認為“男性是外在的、超越性的自我;女性則是自在的、內在性的自我”[5](P39~40)。女人的“他者”地位總是和她的總體“處境”息息相關的,是存在主義的。女人不是生來就是客體,而是被男權社會規訓和壓抑成客體的。
可憐可悲的王琦瑤,一直心甘情愿地成為毫無主體意識的客體。40年代末自愿被李主任金屋藏嬌,避亂鄔橋時與少年阿二不切實際的精神意淫,50年代與康明遜、薩沙不合時宜的情欲糾葛與互相欺騙,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和老克臘舊夢重溫,都是在自以為尋找女性主體性的道路上,堅定不移地淪為了客體。似乎只有在60 年代初為人母,與程先生精打細算、隱忍妥協的那段生活中,王琦瑤才短暫地感受到了女性主體萌生的別樣體驗。很可惜,這短短的自我覺醒也隨著程先生的自殺以及和女兒的爭風吃醋而再度灰飛煙滅。
王琦瑤希望依附的主體,本身都是虛弱的客體。王琦瑤早年披金戴銀的“繁華”和余生被棄的“落寞”,其實也觀照出每一個走進她世界的男人也是落寞的,這些男人都是王琦瑤強大的自戀思想中幻生出來的一種對殘缺的愛的鏡像。李主任高處不勝寒的落寞,阿二追夢無蹤的落寞,康明遜自私逃避的落寞,薩沙逃之夭夭的落寞,程先生縱身一躍的落寞,老克臘沒趕上高潮只趕上結局的落寞。這些都是王琦瑤曾經以為深愛或者深愛著她的男人們,但所有的這些也恰恰是王琦瑤不同人生階段自戀情結的實體投射。你是什么樣的人,就會吸引來什么樣的人。每一次和男人關系中的勇敢和擔當,其實都是王琦瑤龐大而又脆弱的自戀個體在作祟。和李主任在一起時從未有過的乖,和康明遜在一起要獨立生下孩子的孤勇,對程先生付出多年愛意的理所當然,以及最后對老克臘低三下四的強行挽回,這一系列的清晰主體性的缺位,都是王琦瑤骨子里病態的自戀所導致的。
適度的自戀,會讓個體在關系中更加強大;而過度的不加反省的自戀,會讓自體的覺醒和成長徹底瓦解。“內聚性”是美國心理學家科胡特(Heinz Kohut,1913~1981)提出的概念。內聚性是指自我有一種向心力,可以保證心靈各個組成部分向內聚合,從而構成一個整體。在情緒的驚濤駭浪中,內聚性自我穩穩地在那里。王琦瑤的內聚性自我從未形成,但是全能型自戀卻從原生家庭中時就如影隨形。因為家中沒有所謂的溫暖和想要的財富,所以她在一元索取型關系中畸形地生長起來。所謂的一元型關系,就是要么你們都要愛“我”,要么你們都是魔鬼。因此,王琦瑤在年齡增長、心智停滯的時光里,她有一個龐大的潛意識:你們必須承認“我”是美的,繼而給“我”想要的一切,不然你們就是罪孽的。
如果內聚性自我足夠穩定強大,適度的自戀會讓王琦瑤們學會不斷地突破重生,在認知迭代的過程中,會有更強大的意識層面以外的東西來摧毀小我,讓一切認知、理念正向流動,最終在破碎后修復進化成一個更強大的全新自我。但是王琦瑤在自體價值觀都未成熟的時候就急于讓自己自戀包裹的欲望野蠻生長,因此她沒有一個內核穩定的內聚性自我,以后也談不上由內而外地成長,只是在原地重復地做一些簡單的肢體動作來證明生命的原始意義。
(三)自戀:導致個體迷失
如果說王琦瑤對自己、對男人的態度,讓她的自戀由內而外地涌現出來,淹沒了自己的主體性,那么在她與女性的相處中,則是由作者賦予了其特權,可以自外向內地把自戀進行到底。
作者想把王琦瑤塑造成一個不被動地等待命運安排的人,賦予了她很多“自主”性以及改變命運的選擇。比如,競選“上海小姐”、做李主任偏房、隱居平安里,以及為康明遜生下沒有名分的孩子,等等,都是出于她的自主選擇。可這恰恰是因果倒置,她正是完全服從于命運的推波助瀾,讓自己憑借美貌獲得了其他女孩得不到的一切,才被命運安排了和這些男人相遇。如果懂得自我成長、主體性選擇,王琦瑤壓根不會遇到他們,更不至于覆水難收。從這個角度看,自戀情節滲透到王琦瑤生命的各個環節,作者想要體現海派文化的包容,卻恰恰把海派文化“做小”了。小說中提到和王琦瑤同時代的女性還有吳佩珍與蔣麗莉,在作者的筆下,這兩個女性都是來襯托相信“美就是王道”的王琦瑤的,她的一生不僅值得被羨慕,而且又必須被同情。
吳佩珍的存在就是為了顯示:美就可以肆無忌憚,丑就該退避三舍。面對王琦瑤的頤指氣使與忽視冷淡,吳佩珍始終拋開自己的一切自尊,站在王琦瑤的角度替她考慮。在拋棄一切女德成為別人情婦的王琦瑤面前,吳佩珍一直那么卑微。吳佩珍對王琦瑤的崇拜和望塵莫及的內心定位從未搖擺過,反倒因為王琦瑤“靠自己”住進了愛麗絲公寓,更覺得自己低人一等。這是王琦瑤輻射出的強大自戀直接導致了身邊女性的主體性缺失的典型說明。多年后,真正靠自己努力成為中產階級的丑女吳佩珍,還是在做了小三的美女王琦瑤面前怯懦自卑。小說將價值觀簡單地鎖定在對美丑的錯誤定位上,導致一個個出場的女性被王琦瑤強大的自戀情結席卷過去,丟掉了自我對真正價值的評判。“這時,娘姨送茶來,說聲:小姐請用茶。王琦瑤厲聲道:分明是太太,卻叫人家小姐,耳朵聽不見,眼睛也看不見嗎?”[3](P278)驕縱病態的王琦瑤,雖然借高官上位,但內心深處依然無法欺騙基本良知,這又是面子上的自戀,進而加重了芯子里的自卑。因此,當聽到吳佩珍結婚的消息時,王琦瑤更加深了對自己當下處境的哀嘆和痛苦。一方面,王琦瑤希望借外在形象抵消曾經的自卑,希望展現一個獨立、美麗、自強而又智慧的女性形象,可這只是她的外顯人格;另一方面,她潛意識里也清楚本不該屬于自己的一切更加吞噬著殘喘的靈魂,撕裂感會越來越強,直到瓦解掉她所有的主體性,在分裂中心甘情愿成為無意識的客體,與宿主的關系變成了單純的索取與交換。
蔣麗莉算是陪王琦瑤時間最長的女性了,但是她和程先生也是失去主體性,并臣服于王琦瑤強大的自戀,喜怒哀愁都是為了王琦瑤而產生和消失。程先生是王琦瑤一生的備胎,蔣麗莉一生都對程先生無法放下。就這樣,“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兩人,在王琦瑤自戀的光環籠罩下,成了兩個毫無主體意識的客體。最后,一個病死,一個自殺。蔣麗莉一生都未得到愛情,雖然后來有了婚姻,但是她卻一直嫌棄對方。在海派文化的沖擊下,作者把其他一切文化歷史都描寫得有些低人一等,蔣麗莉的丈夫和他的家人雖然一直對她照顧有加,但是在蔣的眼中,口音以及本分的處事方式都讓她心生厭煩。
王琦瑤周邊的女人是如此,海派文化周邊的文化亦是如此。沒有主體性,沒有自己的地位,一切都要仰望著那具有包容力和魅力的上海,以及無論做什么都值得保護和同情的“王琦瑤們”。這再次說明,自戀已經不單單是王琦瑤對自己偏執的認知,更是周圍女性對她失焦的評價。
三、主體性的缺失導致匱乏需求增加,再次加重自戀
馬斯洛(Abraham H.Maslow,1908~1970)將人的需求分為七個層次,最主要的是基本需求和成長需求。基本需求是由于心理和生理上有某些欠缺而產生的,所以又稱為“匱乏性需求”。當人的基本需求出現匱乏時,心理能量就會一直集中在追求這些基本需求上。主體性缺失導致匱乏需求變本加厲地生長,進而碾壓成長需求,使心智不再成長,退行到孤獨的全能自戀中,并如“銜尾蛇”般再度加重自戀情結。
自戀一般分為兩層。第一層是“我”是對的,“我”說了事情會怎樣,事情就會向那個方向發展;第二層是“我”比你強,“我”在關系中要高過你,“我”地位高、你地位低的格局才能讓“我”舒服和自在。王琦瑤基本上處在自戀的第一層,她總是認為自己應該無條件地得到上天眷顧、男人垂涎、女人羨慕,所以蒙蔽了對自我的真實認知。而她和周邊人相處的過程中,體現了自戀的第二層,就是“我”一定要高過你,強過你。除了第一次在李主任面前裝出的“乖”,其他的一切都是伏筆和鋪墊。在自體和關系中的過度自戀,導致王琦瑤主體性缺失,使她一直都處在心理和生理上的低級匱乏層面,而匱乏需求又導致成長需求處在永遠斷裂的狀態,所以她到死都無法完成自我的成長。
(一)主體性缺失到匱乏需求增強
王琦瑤的心理出現明顯變化是在她競選“上海小姐”之后,在此之前,她一直有意強行壓制自己的潛意識,不愿意承認自己是一個要等待男人救贖才能擁有理想生活的低俗女人。從她第一次去片場的態度以及在程先生的相機前故作驕傲和清冷的姿態可以看出,自戀的膨脹最初激發的是她虛假的自尊。直到李主任出現后,王琦瑤潛意識里強烈渴望擺脫平庸生活的欲望爆發出來,欲望讓她僅有的一點理智喪失了,甚至是急不可待地跳進了沒有名分卻享盡繁華的愛麗絲公寓,這就是命運。住進愛麗絲公寓的那一刻,王琦瑤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順從和依附可以讓她暫時獲得想要的一切,因此主體性在她的身上沒有任何價值。但是主體性的消亡會直接導致自我構建的坍塌、內心匱乏,從而外化出更貪婪的索取,所以王琦瑤對李主任也由最初僅乖乖地止步于物質的滿足,到慢慢迫切地想抓住李主任這個人,求得感情的認同和歸屬。在王琦瑤生命中有兩個極端的男人:一個是李主任,另一個就是程先生。一個是一手遮天,可以為王琦瑤重造命運,讓她從真匱乏到假清醒;一個是一元型好人形象,始終提醒著她在真匱乏中保持真清醒。
但是李主任突然死了,這種索取鏈條的突然斷裂并沒有讓王琦瑤清醒過來,反倒使其一直沉浸在遇到第二個李主任并把自己拯救出來的幻象中。當然,這個人一定不能是程先生。王琦瑤太過自戀,對于程先生這份毫無攻擊性的好與善,她躲在自戀的軀殼里駕輕就熟地免疫了一輩子,因為和程先生在一起就會提醒自己曾經不光彩的過去、那些跌落神壇的慘敗。王琦瑤因為太過自戀,始終把自己架到一個高處不勝寒的地方,俯視著人間最該被珍視、卻一直被忽視的愛情,而“匱乏”的程先生卻只能給與王琦瑤“貧乏”的愛情。
(二)因匱乏而自戀升級,拒絕成長
在平安里的那段日子,是王琦瑤試圖自我拯救,嘗試尋求主體性,但最終還是敗下陣來、拒絕成長的一段復雜時光。跌下神壇后,王琦瑤開始重新尋找人生方向,通過自己的勞動賺得基本的生存需求,這是因匱乏而開始和過往的自己較勁,要尋得新的成長的開始。但是,當在爐邊夜話的美好時光里再度遇到康明遜和薩沙這樣對她有吸引力的男人時,之前那個自戀又不切實際的王琦瑤又卷土重來了。
王琦瑤之前始終停留在匱乏需求這個層面,無法進階到成長需求,以至于她一直禁錮在匱乏認知層面,這樣的人會根據自己的想象行動而不是根據現實行動。如果一個人有了正確的成長需求,那么她的認知也會進化為存在認知,就是說,以現實為基礎來正確客觀看待世界,而絕不自欺。這段時間里,王琦瑤就是拎不清現實,并和自己較勁,她覺得自己命不該如此。先是傍上李主任,李主任死了,又愛上康明遜,卻依然無法獲得名分和安全感。但此時經歷過溫柔鄉的王琦瑤并不想再用“乖”來依附男人了,她決定生下和康明遜的這個孩子。這次的姿態是故作獨立和堅強,這也是王琦瑤經歷前期巨大匱乏后產生的自戀進階版。不得不說,還有一部分是她在半覺醒邊緣想尋找主體性的表現,但更多的還是強大的潛意識,就是過分自戀導致了極度不自信。不是由內而外地成長,而是試圖從外向內在男人面前證明自己。她在和自己較勁的過程中,內聚性自我還是沒有形成,否則就不會有一個李主任,又接二連三地有了康明遜和薩沙以及最后的老克臘。這些都是王琦瑤骨子里的自戀吸引來的愛情殘次品,是王琦瑤奴性基因在真實生活中投射的實體。
意識層面越自戀,潛意識深處就越覺得自己不配被好好愛,這種較勁就會導致思想扭曲。越是得不到,越能激發她內心巨大的不安被觸碰后的變態狂喜。她內心深處就是喜歡這種由不安引發的關注,被更多人疼愛、佩服的那種變態快感。所有表象的愛,都是因為對匱乏的恐懼,在不斷索取中,又一點點增加自戀,丟掉主體性。
自戀到主體性缺失,再到匱乏,最后又回歸到自戀加重的惡性閉環,在王琦瑤身上展現得淋漓盡致。她覺得平凡的生活配不上自己,不愿意承認自己掉落人間,但又沒有能力回到天上,所以對著鴿群,一遍遍不厭其煩地描述,它們是最洞若觀火的生靈,自己就在人世間上空高不成低不就般存在。她就是不能從對愛的匱乏中走出來,走到成長的需求層面,去看看這個城市40年風卷殘云后,剔除了什么,留下了什么,迎來了什么。雖然王琦瑤有膽量做外室,名不正言不順地生孩子,編造一個莫須有的父親,但是她不敢學會成長,不敢學會去愛和付出。
(三)自體成長的停滯反過來加重自戀
王琦瑤的一生,從做女兒到當母親,一直拒絕成長,在匱乏中投射出一個巨嬰般的自己。到1976年,王琦瑤的女兒微微已經15歲了。成為母親的王琦瑤,自戀的泛濫沒有那么理直氣壯和洶涌澎湃了。在女兒面前,她作為獨立女性的自主意識在不斷完善;但是,作為一個呵護女兒、疼愛女兒的母親,她又總是在尋找那種能彌補年齡代際的心理安慰。很多默契和交流不是發生在母女之間,而是發生在微微的好朋友張永紅和王琦瑤身上,因為張永紅又是微微那個時代的美人,這在作者的價值觀里,都是海派文化中的“優等人”。王琦瑤面對張永紅有很分裂的兩種情緒:一方面是對那么像自己且擁有大把青春的女孩的嫉妒和痛惜;另一方面是女兒姿色平庸,只有和張永紅相處時才能找到自信和昔日光環,這讓年事漸高的王琦瑤自欺欺人地認為沒有被這個城市徹底拋棄。
日本女作家上野千鶴子《厭女》一書中曾提到母女之間微妙的關系:
母親一方面期待著女兒,可當女兒真的實現了自己未能達成的欲求,卻又不會是單純的高興,而會懷有更復雜的心情。但兒子無論實現了什么,母親都無需與他競爭,性別在這個時候起到了便利的緩沖作用。但女兒不同,因為同為女性,母親無法為自己找到借口。[6](P126)
王琦瑤潛意識里覺得自己是要一輩子被疼愛的,包括女兒的出現也不能把她的這份特權奪走。王琦瑤也試圖做一個好母親,但在微微去美國以后就徹底放棄了這方面的想法。她每一次和自己抗爭,都在強大自戀的控制下完敗。女兒走后,王琦瑤再次“活回了”自己,尋找寄生的宿主,又和老克臘牽扯出了一段有些讓人反胃的姐弟戀。男人對她的垂涎,是她得以生存在自戀幻覺里的氧氣。看似一直要獨立自尊的王琦瑤,從來不懂獨立和尊嚴為何物。到最后,長腳夜半闖進她的房間時,她本來可以通過失去財產來保住性命,但是太過自戀的王琦瑤怎能讓自己受盡這樣的侮辱,那可是李主任當年對自己真愛的唯一見證了,然而她以為拼命保護的是對愛情的守護和殘存的尊嚴,但是到最后呵護的卻恰恰只是一個幻影和執念。
王琦瑤的40年,從來不會主動付出愛,投射到她身上的愛也都被一點點掐滅,更別說很多人對她根本談不上愛,只是出于好奇感和征服欲。最虛妄的東西卻被她攥得最緊,并視為證明自我價值的重要籌碼。只有主體性的增強,才能讓自己快速成長,才能真正懂愛、會愛。在一味被動等待的過程中,自戀會扭曲變形,唯有主動走到真實世界,真正為一份值得的愛獻身的時候,身上那種變態的自戀才會土崩瓦解,才會由內而外成長出一種自信和智慧的力量,自體也會因成長而變得更豐盈。不需要自戀,而且能迎來更多人真正的愛戀,這才是一個獨立的個體,一個有明確主體意識,敢于寬恕并無畏付出,也依然可以嫉惡如仇的獨立完整的生命。
王琦瑤的一生是可悲又墮落的,她自戀而不自愛,以至于看不見女性該有的廣闊天空。她的一生都在尋找宿主,卻自我欺騙在尋找真愛,其實她從來就沒有愛的能力,也沒有接受愛的資本。她只是試圖通過外在的變量來尋找心靈安定的“錨點”,卻從不懂如何由內而外地成長,找到內生力量的“聚點”。她因自戀而迷失自我,又因主體性缺失而始終滯留在生命的匱乏層面無法成長,反過來加重病態的自戀,困在這個因果倒置的畸形閉環中,一生都從未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