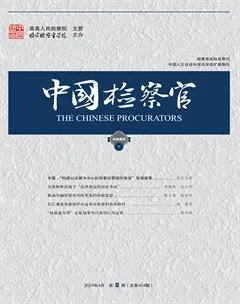“兩卡”網絡詐騙案件中幫助行為主觀明知的級層化證明思路
謝文翼 高葉 向柯翰

摘 要:對電信網絡詐騙中的幫助行為所涉幫信罪、掩隱罪、上游共犯三種罪名的主觀明知之證明,應建立級層化的證明框架。以“犯罪行為客觀存在”為第一層次幫信罪的明知,在此基礎上若能吻合“在犯罪既遂后對資金性質明知”則上升到第二層次掩隱罪的明知,再若還能符合“在犯罪既遂前對共同性明知”則上升到第三層次上游共犯的明知。在具體證明思路上,對于幫信罪的明知若無直接證據則可以推定明知條款為核心進行證據搜集,對于第二層次掩隱罪的明知可以行為的“異常性”為方向結合推定條款進行證據收集,對于第三層次的共同犯罪,可以從一般共犯與片面共犯兩種角度進行證據收集。
關鍵詞: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 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共同犯罪 犯罪主觀要件
一、問題的提出
在“兩卡”犯罪幫助行為中,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以下簡稱“幫信罪”)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以下簡稱“掩隱罪”)以及上游犯罪的共同犯罪(以下簡稱“上游共犯”)三罪的主觀“明知”要素上的區分在司法實踐中難以處理[1],導致了“明知”標準模糊化、證明思路混雜化的問題。[2]要解決“兩卡”犯罪中所涉三類罪名主觀要件的證明問題,就應從司法實踐的具體認定中總結基本方法,并在此基礎上構建解決思路。
(一)參考案例
[案例一]陳某誼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案。2022年7月13日至8月26日,陳某誼明知他人進行信息網絡犯罪活動,仍將自己名下在本市某某區某某支行辦理的交通銀行卡及工商銀行卡出借他人使用并進行轉賬操作。法院認為現有證據不足以認定陳某誼幫助不法分子轉賬時上游犯罪已既遂和其明知是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陳某誼構成幫信罪而非掩隱罪。[3]
[案例二]沈某某等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案。2021年6月,沈某某等人在上海市青浦區多處公寓據點非法從事跑分業務,使用沈某某2張銀行卡、“卡頭”王某某及其招攬而來的 “卡農”銀行卡、支付寶或微信等支付賬戶用于收取、轉移多人被騙資金。后在取保候審期間再次伙同他人進行跑分。法院認為沈某某與負責與上頭對接的楊某某構成掩隱犯罪,而其余人構成幫信犯罪。[4]
[案例三]陳某等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案。2020年12月份左右,李某甲、李某乙組織陳某使用銀行卡轉移犯罪所得。陳某提供了自己的三張銀行卡,并頻繁將不同賬戶內的錢款轉移到特定賬戶或者通過購買虛擬貨幣等方式參與轉賬,并通過李某甲等與上線組建的聊天群記對賬。2021年2月20日,李某甲等人被公安機關抓獲后,陳某仍舊組織他人使用銀行卡轉移犯罪所得,負責和上線聯系、記賬和找轉賬地點、接人。法院認為陳某轉賬、套現的“手續費”具有高度異常性,以此認定其構成掩隱犯罪。[5]
[案例四]李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案。2021年3月至11月間,被告人李某陸續購買大量未實名注冊的手機卡,又安排王某、陳某等人對手機卡進行實名認證后注冊微信賬號,之后李某將采用前述方式獲得的100余個微信賬號以每個人民幣170元出售給他人用于實施違法犯罪活動,并致一名相關人員向虛假賭博網站投注,被電信詐騙受損100余萬元。法院以李某交易行為的異常性為基礎,認定其構成幫信犯罪。[6]
(二)司法活動中證明工作的基本特征與借鑒價值
1.對幫信罪與掩隱罪主觀要素的區分呈現模塊化與層次化特征
在案例一中,法院指出幫信罪的明知對象在于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的存在,掩隱罪的明知則是知道他人的犯罪所得或犯罪所得收益,而本案中的被告人雖明知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的存在,但并不明知所涉金額屬于犯罪所得,故被告人不構成掩隱犯罪。案例二中,法院指出行為人明知他人涉嫌犯罪,其所經手的資金應系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仍用本人或收集來的銀行卡為他人“跑分”,構成掩隱犯罪。行為人明知他人涉嫌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僅向他人出租、出售銀行卡用于“跑分”的,構成幫信犯罪,并以此對不同被告人區別定性。
可以看出,幫信罪與掩隱罪在“網絡犯罪行為存在”這一點上具備相同之處。而掩隱罪的行為人在主觀上另有在犯罪既遂后對卡內資金性質的明知。這一觀點也符合2020年12月21日“兩高一部”《關于深入推進“斷卡”行動有關問題的會議紀要》中第5點將幫信罪“情節嚴重”定義為“信用卡內流水金額超過30萬元,其中查證3000元系詐騙資金”,而掩隱罪則不存在對一般流水的規定,僅要求系犯罪所得或者掩隱次數達標。因此,掩隱罪的明知等同于幫信罪的明知加上行為人對犯罪既遂后資金性質的明知。這樣的處理和區分方式體現出一種模塊化、級層化的特征,能夠指導司法實踐進行具有針對性的證據收集。
2.“異常性”證據和推定條款的積極運用
以掩隱罪為例,司法機關在行為人主觀明知的認定上較為強調對資金流動、交易方式、行為“異常性”的判斷參考。[7]例如案例三中,法院就以行為人實施轉賬、套現等手續費的“異常性”為基礎認定了明知。而在幫信犯罪里,案例四中法院對“異常性”證據的組合使用也是認定幫信罪明知要件的主要方法。
“異常性”的證明標準具備相關的法律依據。2019年10月“兩高”《關于辦理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幫信解釋》)第11條第(三)(五)項規定,交易價格或者方式明顯異常、頻繁采用隱蔽上網加密通信、銷毀數據等措施或者使用虛假身份逃避監督或者規避調查的可以明知認定。2009年11月最高法《關于審理洗錢等刑事案件具體運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掩隱解釋》)第1條第(二)到(五)項也指出,沒有正當理由通過非法途徑協助轉換轉移財物、以明顯低于市場價收購財物、協助轉換轉移財物收取明顯高于市場價手續費、協助他人將巨額現金存于多個銀行賬戶或在不同賬戶間頻繁轉劃的,可以認定明知。
上述案件中在難以通過直接證據證明明知的前提下采用的以推定明知條款指導偵查并綜合認定明知的方式,可以成為今后“兩卡”犯罪中對主觀“明知”證據收集的指導。
二、級層化證明框架的構建
我國的司法實踐所表現出來的以推定條款為指導的取證方向具有一定的科學性,但仍舊較為簡陋和不成體系。例如,幫信罪與掩隱罪的明知認定雖存在一定的級層特征但尚不十分明確,上游共犯的明知也并未被納入這一體系,且“異常性”證據在具體的適用方式上也尚不明確。筆者認為,應當針對幫信罪、掩隱罪和上游共犯的明知構建級層化、模塊化的判斷框架,并針對不同級層、模塊的明知要件提出具體的證明方法,從而掃清“兩卡”案件幫助行為主觀要件的認定窘境,規范司法實踐的證據適用。
(一)對上游共犯主觀要件的理論解構
要針對上游共犯、掩隱罪和幫信罪主觀明知要件建立判斷框架,具體需要解決兩個方面的理論問題。一是要成立上游共犯,行為人應當在主觀要素上達成何種內容,二是如何將司法實踐中級層化的區分思路運用到共同犯罪的明知要素中。
1.上游共犯主觀要件具體內涵之釋明
最高檢在2018年發布的《檢察機關辦理電信網絡詐騙案件指引》(以下簡稱《指引》)第二部分第五款關于犯罪事前通謀審查中指出,對于共同犯罪也包括無共謀但明知他人實施犯罪提供幫助的情況。對于幫助者明知的內容和程度,并不要求其明知被幫助者實施詐騙行為的具體細節,其只要認識到對方實施詐騙犯罪即可。《指引》一方面強調共同犯罪的成立必須具備對犯罪存在的明知和幫助意志,另一方面并不要求行為人對上游犯罪具體細節進行了解,甚至并不要求行為人與上線犯罪者存在意思交流。從這一論述來看,《指引》采取了部分共同說的觀點。
一方面,在認識因素上,不需要二人以上具有相同的犯罪故意,只要行為人具有和他人共同實施行為的意思即可,即使二人的犯罪故意不同也不阻卻共犯的成立。另一方面,雖不用和上游犯罪者的犯罪故意完全相同,但是也要求行為人明知行為的“共同性”與“犯罪性”,所謂“共同性”即是行為人在犯罪既遂前對自己和他人存在共同、分工、幫助的認識,所謂“犯罪性”即是對犯罪行為客觀存在的認識。[8]
2.對上游共犯主觀要素的模塊化與級層化處理
首先,正如前文所舉案例一、案例二法院的說理,掩隱罪與幫信罪在主觀明知層面具有共通之處。而對上游共犯、掩隱罪和幫信罪三者的主觀要素進行分析可以發現,雖意志因素有所不同,但是其認識因素上具有共通性,即均有對犯罪行為客觀存在的明知。掩隱則是在這基礎上增設了在犯罪既遂后對獲利性質的明知,共犯則是在此基礎上增設了在犯罪既遂前對行為“共同性”的明知。[9]
其次,分析法律和規范性文件規定可以發現,掩隱罪與幫信罪在法律條文設定中均存在“實施本罪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以處罰較重的定罪處罰”的規定,而幫信罪的法定最高刑為3年以下,掩隱罪則為7年以下,相較于幫信更高一級層。而對于上游共犯而言,以詐騙為例,詐騙罪最高法定刑為10年,明顯高于掩隱罪和幫信罪。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無論是幫信罪還是掩隱罪,均存在“若有事前通謀就以共犯論”的規定,而“事前通謀”可以說是高精度地證明了行為人對“共同性”與“犯罪性”的明知。實際上,從立法原意上來看,幫信罪的設立是因為對于信息網絡犯罪的幫助行為往往無法查證共同故意,無法適用共同犯罪處理,才設立幫信加以處罰。[10]而對于掩隱犯罪而言,該罪同樣是針對相關上游網絡犯罪事后贓物處理的共犯認定不足而予以“兜底”性質的立法。[11]
最后,分析行為人主觀認識可以發現,三者在主觀認識難度上存在層層遞進的關系,在一般犯罪中,行為人對于幫信罪的明知是最容易也是最先達成的,無論是上游共犯還是掩隱罪的明知,都需要首先知曉上游犯罪客觀存在,幫信罪的明知是后兩者成立的基礎。而相較于必須限定在犯罪既遂前,而且要求對行為“共同性”明知的上游共犯,在犯罪既遂后僅要求知曉資金性質即可的掩隱罪明知更加容易判斷。需要指出的是,若掩隱的明知發生在犯罪既遂前,此時若足以明知“共同性”,則以上游共犯論處,若不足以達成共犯的明知,則以幫信罪處理,故掩隱的明知實際上是介入在幫信與共犯明知中間的。至此,可以發現三者的主觀認識在證明難度和包容性上表現出一種以“幫信罪、掩隱罪、上游共犯”為順序的層層遞進、上層包容下層的邏輯關系。
綜上所述,可以將上游共犯的明知解構為“行為人對犯罪行為的客觀存在具備明知”和“行為人在犯罪既遂前對自己與他人的共同性存在明知”兩個模塊。而在級層設定上,應當高于幫信罪與掩隱罪的明知,這種處理方式也符合行為人的一般認識邏輯和法律適用規定。
(二)級層化判斷框架的搭建
根據上述分析,可以以幫信罪、掩隱罪、上游共犯為基本順序,建立級層化判斷框架:
以幫信罪作為第一級層,考量“對犯罪行為客觀存在的明知”這一模塊,以掩隱罪作為第二級層,考察“犯罪既遂后對資金性質明知”這一模塊,以上游共犯作為第三級層,考量“犯罪既遂前對共同性明知”這一模塊。其中在判斷完第一級層后,即使不符合第二級層中“資金性質的明知”模塊,也應當考量第三級層中“共同性”的明知。在這種級層思路的指導下,也更能清晰地說明前文案例中法院的認定原理。
三、級層化判斷框架中具體模塊的證明方法
前文將幫信罪、掩隱罪和上游共犯的主觀要素進行了模塊化,并創設了級層化的判斷框架。在此邏輯框架下,證據的收集審查就可以模塊為中心進行組合考察。
(一)“對犯罪行為現實存在的明知”模塊的具體證明思路
1.以“明知”推定條款為取證方向
《幫信解釋》第11條第3、5款的規定應當著重考察行為人在上網方式、交易價格、虛假身份、逃避監管等客觀表現上的異常性,從而綜合推定行為人的明知,前文所舉案例四中的法院便對交易活動的“異常”進行了具體認定。實際上,除了前述規定的情形外,其他條款也均可以作為證據收集的指導。例如本條第1、2款規定的告知、舉報一般均在政府、相關機關單位的后臺留有數據,行為人自身也無法消除,取證較為容易。除此之外,第4款的適用也較為重要,其規定為“提供專門用于違法犯罪的程序、工具或者其他技術支持、幫助的”,主要是針對“并非社會正常活動所需,而系為違法犯罪活動提供幫助的專門服務”的活動。[12]對于此類在規范意義上已經存在禁止性規定,或者在日常生活中根本不會存在的某些特定的提供行為,若滿足“非正常生活所需,并專為違法犯罪而生”的標準,則也可以使用第4款的規定推定明知。
綜上所述,對于幫信罪明知模塊的證明,在沒有直接證據加以證明的情況下,可以《幫信解釋》第11條各款的規定為指導,集中進行證據收集。
2.對推定條款適用的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司法實踐活動在符合《幫信解釋》中某一款的情況下,往往還采取了其他足以證明“異常性”的要素進行補強,例如在前文所舉案例三、案例四中,法院均是在證明其中一種推定條款的情況下,結合了其他能夠進行相互印證、強化證明力的證據進行綜合認定。因此,筆者認為應當從兩個方面對推定條款的適用進行限縮,一是不能僅符合《幫信解釋》第11條中其中一款就直接予以推定,而應當在此基礎上強調其他要素的綜合性認定,二是對推定條款的適用必須建立在窮盡直接證據徹底無法證明的前提下,以恪守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則。
(二)“對資金性質的明知”模塊的證明思路
參考前文所舉案例二、案例三的處理方式,對于掩隱罪中“對資金性質的明知”模塊的證明思路則應當強調對資金流動、提示警告、行為方式等諸多因素“異常性”的考察。對于“異常性”的理解,一方面可以參考《掩隱解釋》中“沒有正當理由”的規定,主要考察針對于大額、大宗轉賬,畸高、畸低買入賣出行為,巨額現金散存等行為中行為人的辯解是否符合一般人的正常生活邏輯,是否具有合法事由,能否在客觀上加以印證等。另一方面可以參考金融機構的警示通知或者其他規范文件、國家反詐app短信信息等發送情況和銀行交易、流水、轉賬時間、次數等能否與其他同案犯或者其他涉案財物相互印證。
另外,對于掩隱罪中推定條款的適用,一方面也應當受到如同幫信推定條款一樣的限制,在符合其中一款的情況下結合其他證據綜合認定。另一方面,應當將第二級層的明知產生時間嚴格限制在上游犯罪既遂之后,掩隱犯罪針對的行為是犯罪行為結束后對非法獲利進行隱瞞、切割聯系的行為,核心在于事后隱瞞。[13]關于這一點,前文所舉案例一中的法院也提出了“幫助不法分子轉賬時上游犯罪已既遂”的要求。若這種明知產生在犯罪尚未既遂、非法獲利尚未產生之前,則要么以上游共犯論、要么以幫信罪論。
(三)“對共同性的明知”模塊的證明思路
對上游犯罪共犯中“共同性明知”證明的問題,應當以是否具備“事前聯系”為標準區別為“事前共謀”和“片面共謀”,也就是一般共犯和片面共犯。而因“事前聯系”形式標準的有無,對一般共犯和片面共犯中“共同性明知”的證明要求也不同。
1.一般共犯中“共同性明知”的證明
一般共犯要求“事前共謀”的存在,要求二人以上為了實施特定犯罪行為,以將各自的意思付諸實現為內容進行策劃謀議,或者說各犯人就何種犯罪以及犯罪的目標、方法、時間進行了策劃、商議。[14]行為人只需要在實施犯罪上具有共同故意即可,而進行的謀劃商議也不需要完全知曉犯罪的全部細節,只需要針對犯罪行為存在分工、商量即可,即使僅透露商議了整體犯罪行為的一部分,只要這種溝通商議行為存在,且行為人具有與他人共同實施犯罪的故意,則符合“事前共謀”的認定。
故對于一般共犯而言,一方面需要判斷行為人與上游犯罪者之間是否就犯罪的具體內容進行過聯系溝通,另一方面需要判斷行為人是否對犯罪行為客觀存在、自身與他人之間的輔助分工或其他共同關系以及自身在整體犯罪中所起到的價值地位存在明知。級層判斷思路中,則應當組合現有證據,一方面證明行為人知曉自己與他人實施犯罪行為間的關系,另一方面證明行為人對自己犯罪行為在他人犯罪行為中地位、價值存在明知。
2.片面共犯中“共同性明知”的證明
《指引》第二部分第五款認為,雖無共謀但明知他人實施犯罪而提供幫助的情況,也應當認定為共犯。由此看來《指引》認可了片面共犯的存在,并認為此種行為應當以共犯定罪處罰。故有必要將片面共犯納入“兩卡”犯罪中共犯的成立范圍。[15]值得一提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增設幫信罪之前,相關司法解釋規定單方明知的信息網絡犯罪幫助行為幾乎全部能夠以被幫助的網絡犯罪的共犯論處。[16]
片面的幫助,即正犯者沒有認識到另一方對自己的幫助行為,但幫助者知道自己在幫助正犯實施構成要件行為。[17]片面共犯與一般共犯的區別在于缺乏“聯系溝通”的形式,其并不存在雙方行為人之間的交流合意,僅存在一方對于他人實施犯罪行為的認識,故有必要對片面共犯中“共同性明知”進行單獨判斷。
首先,片面共犯的明知應當在具體罪名上與上游犯罪一致。與前述一般共犯不同,上游的犯罪分子并不知道自己與行為人之間的共同關系,也并未與行為人進行謀劃,并未就共同實施某一犯罪行為達成合意。[18]故對于片面共犯應當要求行為人準確地知曉上游犯罪所觸犯的具體罪名,因為若行為人與上游犯罪者對于行為罪名的認識不一致,加之二者之間并未對實施犯罪達成合意,那么行為人單方的幫助行為也就很難被評價為“幫助者知道自己在幫助正犯事實構成要件行為”。
其次,片面共犯中的行為人應當對上游犯罪的基本流程、行為模式具備明知。因為在片面共犯中幫助的犯意是行為人單方產生的,上游犯罪者不可能通過聯系溝通幫助行為人知曉共同關系,故僅有在行為人原本就對上游犯罪的基本流程、行為模式具備明知的情況下,才可能了解與上游犯罪者之間的分工、共同、輔助關系以及自身在整體犯罪中的價值。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片面共犯中同樣不需要行為人知曉上游犯罪的所有細節,只需要對犯罪性質、犯罪流程和模式具備明知即可。例如在提供信用卡型幫助行為中,在沒有交流合意的情況下,行為人要成立片面共犯,則需要知曉上游在實施電信詐騙行為和上游詐騙犯罪的基本流程和行為模式,例如何時詐騙、取現、使用自己的信用卡等。而對于上游詐騙犯罪的具體細節,例如何人實施詐騙、采用何種理由實施詐騙、信用卡轉賬的錢將被用于何處等細節則并不需要明知。
故對于不具備“溝通聯系”形式特征的“共同性明知”模塊,應當考量如下內容:(1)行為人是否明知上游犯罪的具體罪名(2)行為人是否對上游犯罪的基本流程具備明知(3)行為人是否對上游犯罪的基本行為模式存在明知。
3.對“共同性明知”模塊的階段限制
我國并不存在事后共犯的問題,若行為人在上游犯罪結束后才與犯罪分子共謀,為其犯罪所得進行掩飾隱瞞,就不能以上游犯罪的共犯定罪處罰,而應當以掩隱罪定罪處罰。《指引》第二部分第五款也明確提及行為人的主觀明知應當在犯罪行為既遂之前。
四、結語
本文圍繞“兩卡”電信網絡詐騙中的幫助行為主觀要件的認定困境,針對幫信罪、掩隱罪和上游共犯主觀要件的區別與證明提出了級層化的判斷框架,并將三罪復雜的主觀要素模塊化,從而對司法實踐認定區分“兩卡”相關罪名的活動進行指導,也為相關罪名的證據收集提供了基本引導。但不可忽視的是,級層化判斷框架仍舊有待于進一步的補全和完善。
一方面,“級層化”判斷邏輯框架仍舊停留在學理構架上,其對于證據的收集僅能提供方向性的指導,而對于證據具體內容、證明標準的把控仍舊會給司法者帶來較大負擔。另一方面,本文的探討僅止步于相關犯罪的構成與否,如何把握入罪后處罰幅度的均衡,還有待于司法者進一步的研究。[19]
* 四川天府新區人民檢察院第三檢察部一級主任科員[610213]
** 四川天府新區人民檢察院第三檢察部副主任、四級高級檢察官[610213]
*** 華東政法大學刑事法學院[201620]
[1] 參見曹化:《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司法適用的異化與歸正》,《青少年犯罪問題》2023年第3期。
[2] 參見莫洪憲、呂行:《論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司法擴張與規范適用》,《貴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1期。
[3] 參見《陳某誼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案》,《人民法院報》2023年12月14日。
[4] 參見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2022)滬02刑終607號。
[5] 參見河南省焦作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2022)豫08刑終50號。
[6] 參見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22)滬0106刑初118號。
[7] 參見李立眾編:《刑法一本通》,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791頁。
[8] 參見張明楷:《刑法學》(第六版),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534頁。
[9] 在網絡犯罪語境下,幫信犯罪行為人與被幫助的對象(一般是上游犯罪的正犯或實行犯)之間往往缺少雙向意思聯絡更不存在事先通謀,在實施犯罪前基本上沒有接觸互不認識。參見王聚濤:《準確把握涉“兩卡”犯罪的罪名和罪數》,《檢察日報》2023年4月26日。
[10] 參見喻海松:《網絡犯罪二十講》,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05頁。
[11] 參見趙擁軍:《“斷卡”行動中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及其從犯的認定與限制》,《人民法院報》2023年3月16日。
[12] 參見喻海松:《網絡犯罪黑灰產業鏈的樣態與規制》 ,《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21年第1期。
[13] 參見謝棟、陳月月:《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與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的定性爭議》,《人民法院報》2021年10月21日。
[14] 參見單成林:《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共犯明知的認定》 ,《中國檢察官》2022年第9期。
[15] 參見閆雨:《網絡黑惡勢力犯罪技術幫助行為的刑法規制》,《社會科學家》2021年第6期。
[16] 參見歐陽本祺、劉夢:《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適用方法:從本罪優先到共犯優先》,《中國應用法學》2021年第1期。
[17] 同前注[8] ,第597頁。
[18] 參見林鈺雄:《新刑法總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59頁。
[19] 參見喻海松:《涉非典型“兩卡”案如何實現罰當其罪》,《檢察日報》2023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