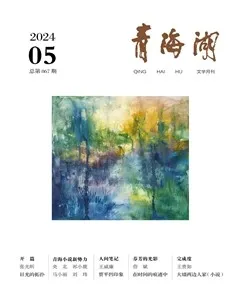始于“智力”,終于“郊區”
胡亮
1990年,姜濤考入清華大學醫學工程專業。1994年,又考入同校中文系。1997年,他寫出長詩《畢業歌》,計有十節二百二十八行。此詩成敗于何種企圖或風格?借來周偉馳的話,就是“巴洛克式的修辭”;借來姜濤的話,就是“對智力、想象力的雙份貪婪”。修辭的滑雪,智力的沖浪,想象力的蹦極與跳傘——即便以很挑剔的視力去看,三者都已經玉成了此詩;而以更挑剔的視力去看,三者有可能玉碎了此詩。所謂成敗,每在分毫。來讀第一節:“宣布開始,你的獨白便如一支分叉的樹干/伸展、盤曲、逐漸推出了結論:/書生甲聞雞起舞,為治愈梅毒而投筆從戎;/書生乙披星戴月趕奔延安/在中途卻偶感一場小布爾喬亞的風寒。”這是寫什么?論文答辯。來讀第五節:“那些能夠上晚自習的人是有福的/在星球涼爽的窗口下準備下一周的力學考試/‘給你一個支點,能否將一條企鵝版的彩虹撐起/而花前月下,那些合理的撫摸/已使一株椿樹滿面羞慚”。這是寫什么?愛情自習。來讀第七節:“求職途中你拜訪過一位二等文官、一只博學的海鷗/所謂的前程會像一架電梯駛向高處的玩具城:/狐貍當道,小熊請客/那些靜悄悄敞開在半空的單位里/新到的打字員提早穿上了鮮花堆簇的緊身陽臺”。這是寫什么?求職歷險。可見此詩之最高價值,在很大程度上,系于修辭、智力與想象力的“本身”,而非三者共同圈定的“語義單元”。周偉馳獨拈出“熱鬧”來評此詩,那就高明得讓我們分不清“褒貶”。《畢業歌》乃是一個分水嶺,作者清算了理想主義的傻氣、浪漫主義的神氣,喚醒了沉睡在體內的奇喻小妖精。而所謂傻氣與神氣,就密切相關于海子。姜濤之少作塞滿了“亡靈書寫”,兜售了“復活信仰”,積壓了“數字迷戀”,周偉馳認為,三者都緣于海子,而海子則緣于《圣經》——先來讀姜濤的《平原之歌》:“三只小鳥 三個青春的主詞 三個夢想的謂詞”,再來讀海子的《夜色》:“我有三次受難/流浪 愛情 生存/我有三種幸福/詩歌 王位 太陽”;姜濤的“數字迷戀”緣于海子,或兩者的“數字迷戀”均緣于《啟示錄》,正如姜濤的“哀慟有時”(一個詩題)來自《傳道書》,“×××是有福的”(一種句式)來自《福音書》。稍早于《畢業歌》的《廂白營》與《旅行手冊或死亡札記》,雖在急轉彎,仍然充盈著《圣經》式的“亡靈書寫”和“復活信仰”,正如《畢業歌》依然殘留著《福音書》式的“句式”。可見姜濤的清華大學時期,大體上就是他的“海子時期”;他畢業于清華大學,便也畢業于“海子大學”。《畢業歌》終于銷毀了海子式的單純、清澈和熱烈,轉而升級了西川式的博喻、反諷和龐雜。1997年,姜濤畢業后謀生于某報。1999年,又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2002年,他畢業后任教于該校。他在這個階段的部分作品,似乎,可視為《畢業歌》的N次方——變本加厲,履險如夷,他已速成為一個身懷絕技的文體家。來讀《三姊妹》:“從倒掛枝頭的會議室到退休部長/蔭涼的臂彎,三姊妹口銜釣鉤/藏身有術,仿佛機關舌尖上/一個輕輕卷起的袖珍支部”。來讀《機關報》:“宴罷歸來,苦苦思忖分身術/早聽說一根老練的舌頭可以由三岔口/伸向金水橋,舔盡體制/胯下濃密的樹蔭”。然而詩人卻認為——本為反對“俗套”,沒想卻自成“俗套”;本為挑戰“局限”,沒想卻自曝“局限”。對此,他有過哪吒式的反省:“看似表達對社會生活的不滿,實際是貪戀詞語的享樂,這既滿足了智力的驕傲,也補償了小知識分子內心的花花公子渴念。”所謂“剔骨還父”,所謂“割肉還母”,無非便是這樣的“痛法”吧?可見姜濤的北京大學時期,大體上就是他的“西川時期”;他畢業于北京大學,便也畢業于“西川大學”。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眼看著,他就要得到精鋼。那么,詩人意欲何為?“世界駁雜萬有可以被悉數吞下,終結于也是服務于一首詩的成立。”這里的“一首詩”,相當于“數首詩”。2010年,姜濤寫出短詩《海鷗》:“我站著拍照,鏡頭像漩渦吸入了萬有/你展翅追蹤,向世界吐露惡聲/海水不平,山木也嶙峋/油炸食品沿曲線低空拋出/卻吻合了大眾口味,也包括你我/相逢瞬間各取了需要”。這首短詩,寫著寫著,成了一首元詩(metapoem)——它從兩匹肋骨之間,長出了一根枝指,提醒我們要注意作者的陰轉晴。什么陰轉晴?推己及人,以物驗我。比如,《教育詩》寫及的“她”,比如,《家庭計劃》寫到的“我們”,《我的巴格達》寫到的“我”和“她”,難道只是“自傳”意義上的“夫妻”嗎?比如,《罪中罪》寫到的“小區”,《郊區作風》寫到的“郊區”,難道只是“居住地”意義上的“封閉域”嗎?非也!詩人說,“學會了自我收縮,把握分寸,玩弄手段,半是偽裝半是心酸地把個人生活的失敗,寫成自嘲的詩篇”;又說,“從身邊的瑣碎困窘寫起,最好的狀況下,也能聯動他人、家庭、社會,保持一點語言中的日常政治性”。詩人似乎已經深陷于“家庭”“小區”和“郊區”,其身份,就從“先知、情種、斗士或莽漢”校正為“智者”,又從“智者”校正為“雜文詩人”或“社區洞察者”。為了遙繼“海子時期”和“西川時期”,周偉馳很勉強地把這個階段稱為姜濤的“面具時期”。是啊,他傳不過是自傳的“面具”,小區不過是郊區的“內衣”。回過頭來卻說——如果詩人越出“社區”,成了“游客”,他就會深陷于“沉默”。來讀《周年》:“萬物伸出新的援手,卻不能解釋/我至今遲遲不能開口的原因”。那么,詩人真能如其所愿發明出一座“遠山”、一個“遠景”,并從“遠山”和“遠景”蹇回到作為此時此地的“現場”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