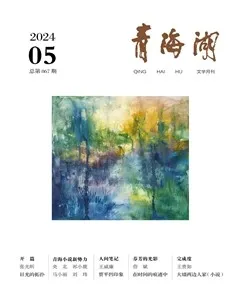在時間的痕跡中
詹斌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是蘇聯電影大師,一生電影作品很少,只拍了七部半,但質量很高,每一部都是經典。其質地與數量有些像文學界的墨西哥作家胡安·魯爾福,“他的作品不過三百頁,但是它幾乎和我們所知道的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一樣浩瀚,我相信也會一樣經久不衰。”(加西亞·馬爾克斯)塔可夫斯基的電影充滿詩意,特別是關于電影就是“雕刻時光”極具想象性的描述,讓許多觀眾、文青、知識分子欣喜并著迷。讓我哀傷和喟嘆的是,塔可夫斯基與我剛剛寫過的電影導演基耶斯洛夫斯基、萬瑪才旦一樣,都是人生走到第54年,就告別人世,但留下的“浩瀚”作品,千古流芳般滋養著喜愛他電影的觀眾。大師易老,作品永恒。讓我們走近塔可夫斯基的影像,在時間的痕跡中,去感受他的熱愛,他的信仰,他的精神性。
一
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深入地考察了宇宙的時空問題,其提出的“二律背反”用同一思維方法,論證了無論時間有無開端,都是無限存在的。從宇宙大爆炸(宇宙的起源)模型和現有的科學理論和認識來看,時間確實客觀存在。對于人類,我們是從主觀視角來理解、感知和看待時間的。在從猿到人演化發展的歷程中,人作為萬物之靈長,創造了燦爛的文化,既有創世神話,又有科學文明。但每當反躬自省時,我們仍然困惑,這是如何發生的奇跡?并可能會以某種形式追問:“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要到哪里去?”這一切,假如拋開復雜的終極哲學探析,其都指向人類主體在時間長河中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塔可夫斯基非哲學家和文化學者,并不關心大尺度的人類歷史文化及演變的時間地圖。作為導演,他專注的是已成為其生命一部分的電影,并以此來探討和激發觀眾對生命、存在和人性的深刻思考。問題是,他為什么認定,電影就是“雕刻時光”的藝術?
從時間與生命的關系看,塔可夫斯基認為,“時間是我們的‘我存在的一個條件……死亡的那一刻,也正是個別時間消失的時刻”(塔可夫斯基:《雕刻時光》)。時間作為生命載體,還包含著自己的人格存在。可見,塔可夫斯基所講的時間,并非線性的物理時間,它意味著發生的某種事情、表演的某些動作。在他眼里,時間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無比生動的一種存在狀態。
塔可夫斯基認為文學、音樂、繪畫等藝術作品中的時間,僅僅是為記錄時間而采取的一種藝術方法。在論述的過程中,他自然列舉了普魯斯特。不難想象,“雕刻時光”這一概念的命名,或許明顯受到了《追憶似水年華》中關于時間描述的影響。不過,塔可夫斯基真正感興趣的不是文學時間,而是“時間與生俱來的道德特質”。是的,你沒看錯,當物理時間的意義被摒棄的時候,塔可夫斯基就將時間賦予了更豐富和特別的內容,并將它注入了人類的元素:“其中的烈焰正是人類靈魂元神存活的所在”(塔可夫斯基:《雕刻時光》)。問題是,時間何來道德的質素?是因為,時間中流淌著人類的精神,而“人類的良知存在完全依賴時間”。
“時間永遠分叉,通向無數的未來”。博爾赫斯從生命意義上講出了人生(時間)小徑分叉的復雜多變和不確定性,并以指向“未來”的描述明確地道出了時間的單向性。的確,在人類的認知常識里,時間是單向而不可逆的,人死不能復生,或者“我們無法讓過去回到現在”。
顯然,塔可夫斯基并不想討論和呈現人們常識中的“時間”。如果他僅僅只看到常識的“時間”這些深度,顯然還不足以成為電影史上具有顯著個性、備受贊譽的大師。事實上,他用影像反復不倦地提醒人們,時間并非只指向未來,它要復雜、豐富和有魅力得多。在他看來,時間與記憶重疊交織(這在《鏡子》中表現得非常典型),或者從本質上講,就是兩個性質相同的介質,猶如“一枚勛章的兩面”,相互融合,相互依存,互為表里。當時間消逝,記憶將不復存在;當失去記憶,人將淪為幻像的“囚徒”,變成一具行尸走肉,或者墜入癲狂。關鍵是,如果說時間與記憶相伴相生,那么假如記憶存在,消失的“過去”,就是不死的,并且可能比現實更加真實、穩定。為什么呢?因為現實混亂無序,人生無常,但在因果循環的世界里,時間猶如魔法,憑借記憶,就可以召喚“道德意涵”和靈魂從死去或消隱的生命中重返現場,從而實現可逆或復活。
《潛行者》表面看是一部科幻片,本質上,它也是一部關于時間的電影,雖然在影片中沒有任何關于時間的提示,但潛行者宣稱有一個“區域”,問題在于,那是一個什么地方呢?“潛行者自己創造了他的潛行區域。他之所以要創造這個區域,為的就是把一些不幸的人帶入其中,并給他們灌輸某種希望”(羅朗絲·科塞:《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訪談錄:詩人、僧侶、導演》)。尋找“區域”,就是回到“潛行者”現在之前構造的時間現場。科幻經典《索拉里斯》(又名《飛向太空》)仍然也是將尋找作為源頭,將視域空間轉向了太空。尋找主題的起源和確定,來自于宇航員波頓完成任務返回后,其接近神秘星球拍攝的短片留下的空白而引起的“謎團”。這是一種貪婪的好奇心,凱爾文就肩負著這一使命。當他經過漫長的太空旅行,到達索拉里斯星,見到廢棄的空間站,科學家的自殺,還有海洋的波動讓幻覺與記憶的重生。他意外地回到過去,在床邊見到了死去的妻子哈莉。其實,對她的組織的分析表明,在一定的微觀水平之下,沒有東西,只有虛空。《索拉里斯》看似是講科幻與未來,實際上是講人類自己,展現的是人類心靈的一次“太空”探索和精神歷險(哈莉不過是凱爾文自己內心深處的創傷幻想的物化),使主人公見證了記憶或逆向時光的震撼。不難看出,尋找的過程,就是充滿情感地對時間痕跡的回溯,既有傷感的情景,又有溫暖的氣息。或許,正是基于這種認識和理解,塔可夫斯基在接受約翰遜訪談回答死亡問題時才會這樣說:“我相信一件事:人類精神是永恒不朽、無堅不摧的。那里可能千姿百態,但不管是什么樣子都不重要。我們所說的死亡不是生命的終結,而是重生。”(約翰·吉安維托:《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訪談錄》)《犧牲》中,亞歷山大與他的兒子,用水澆灌枯樹而重新長出樹葉的隱喻,深刻地詮釋了塔可夫斯基式生命的再生、復活的奇跡。
在闡述時間的痕跡時,塔可夫斯基引用蘇聯記者對時間的描寫,準確而生動。歲月的記號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種“銹”:“一種自然的腐蝕、舊時代的魅力、時間的印記。”在他看來,這是把時間作為了一種藝術的材料。擁有這樣的啟示,當面對普魯斯特構建的“一個巨大的記憶架構”時,年華就可供追憶。雖然文學等其它藝術形式也依靠記憶或時間進行自由創作,并遵循自己的準則,但在塔可夫斯看來,文學與電影卻差異巨大:“因為文學使用文字描述世界,電影卻不需要借用文字,它直截了當呈現自己。”因而,他堅定地認為,時間不能被文學獨占,而這是一個全新素材,恰恰正是電影的應有之義。電影自誕生之日起就如此與眾不同,其無與倫比的優勢在于,在文化藝術史中,人類得到了真實時間的“鑄型”,擁有了留存時間的魔盒,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在銀幕上復制、觀看,并長期地保存。在此,電影就開始了以“事實”為原料來印制時間。正如塔可夫斯基指出:
時間,復印于它的真實形式和宣言中:此乃電影作為藝術的卓越理念,引導我們思考電影中尚未被開采的豐富資源,以及其遠大的前景。我的實際工作和理論假設都是建立于此一理念之上。(塔可夫斯基:《雕刻時光》)
那么,在這一理念的照耀下,作為一個把拍電影當作信仰的人的認知里,導演工作的本質是什么呢?塔可夫斯基給出了明確和生動的描述:
我們可以將它定義為雕刻時光。如同一位雕刻家面對一塊大理石,內心中成品的形象栩栩如生,他一片片地鑿除不屬于它的部分——電影創作者,也正是如此:從龐大、堅實的生活事件所組成的“大塊時光”中,將他不需要的部分切除、拋棄,只留下成品的組成元素,確保影像完整性之元素。(塔可夫斯基:《雕刻時光》)
的確,塔可夫斯基驚喜并篤定時間在影像中的新發現,認定“電影是唯一可以銘記時間的藝術”,以導演之名,先后雕刻出《壓路機和小提琴》《伊萬的童年》《安德烈·盧布廖夫》《索拉里斯》《潛行者》《鏡子》《鄉愁》《犧牲》等七部半電影,以獨特優異的作品奠定了他作為世界電影大師的奇跡。
二
客觀而言,無論是客體的物理時間,還是主體的心理時間,都不會孤立地存在。時空從來都是一體的,不可分割。作為時光雕刻師的塔可夫斯基,他面對的質料,首先就是空間中的大地。“很多人不知道,我們犁的土都是星塵,隨風四處飄散;而在一杯水中,我們飲下了宇宙”(伊哈布·哈桑,轉引自科特·施塔格:《詩意的原子》)。這就是人類與大地和宇宙的關系。用影像來展現大地,本質上是雕刻停留在大地上的人和物,特別是那些時間的痕跡。我認同這樣的判斷:“塔可夫斯基是一位大地導演、祖國大地的導演”(安托萬·德·貝克:《安德烈·塔可夫斯基》),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發生在蘇聯或與俄羅斯大地有關的故事。
在沉默的或風吹的大地,最常見的無疑就是土。在《安德烈·盧布廖夫》最后一節中的一幕,從年輕的鑄鐵工人鮑里斯主觀鏡頭里,他的視線從樹干、樹枝移動到樹葉,最后落在大地。另一幕,鮑里斯在傾盆大雨中,欣喜若狂地發現了合適的黏土,而這種黏土正是他們苦苦尋找的鑄造大鐘模子的必需。不難感到,在盧布廖夫與眾人腳下的泥濘大地,大鐘不僅是信仰的警醒與召喚之源,更是美好的事物和希望。在《安德烈·盧布廖夫》中一開始,就是農民飛行家葉菲姆借熱氣球飛上了天,在飛行中,主觀鏡頭意味著他注視著大地上的一切:縱橫交錯的水泊、奔騰的群馬、沉默的沙丘和劃著小船的人們,最終,當動力失能,他就只能墜落大地。
在電影學者安托萬·德·貝克看來,塔可夫斯基的影片中有三種大地:
《犧牲》建立在三種層面之上,將一系列自然的影像聯結在一起,而這一聯結也使影片具有循環反復的特征。第一層面是原生的大地;第二層面恰好相反,是災難后的大地;最后一個層面則是“變形的自然”,即經過人類之手主動改造后的大地。(安托萬·德·貝克:《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在《犧牲》中,事實上是說,原生的大地來自最初“未經觸碰的大自然”,猶如亞歷山大面對的綠色原野、廣袤土地。災難后的大地在時間的影像中一再閃現,核戰的威脅、荒涼的街景、頹廢的人們、廢墟的房屋等。變形的自然,即人們對大自然精心的“野蠻”改造等,這三種大地的概括或許并不完全準確,當然也并非導演的本意,但至少表現出塔可夫斯基對當時世界現狀不滿,并對人類的未來充滿了憂慮。電影以同一的鏡頭開始,即亞歷山大和他的兒子在大地上種下的一棵枯樹;并以相似的同一個鏡頭結尾,不同在于,枯樹卻長出了樹葉,這既是水的滋養,更是信仰的力量,意在表達他者無私的付出和“犧牲”,暗含了固執的不死的希望。當然,讓人感嘆和崇敬的是,最后的鏡頭在亞歷山大燒毀自己的房子后,是他的兒子躺在那棵長出葉子但稀疏的樹下面,然后畫面消隱,導演給小安德烈的獻詞:“帶著希望和安慰。”然后鏡頭又逐漸意味深長地閃回到那棵樹。
從另一個視角看,在大地的時間塑型中,“三種空間支配了塔可夫斯基的所有電影:大自然、家、神廟或教堂”(羅伯特·伯德:《安德烈·塔可夫斯基:電影的元素》)。可以說,這三種空間就是塔可夫斯基眼中的世界和肉身與靈魂的安居之所。大自然在很大程度上與土地同義,人類的一切活動都發生在此。而在土地上建筑的家,承載了人類的生存、幸福或苦難。《鏡子》的主題是記憶和情感,雖然父親作為缺席的形象,但母親、妻子、孩子,構成了家的底色。回憶中、想象中和照片中的母親,在蒙太奇的影像循環中更加典型地強化了家的氛圍。當時間被擊碎、空間遭解構,就必然需要警示和重建。在《鄉愁》中,意大利的教堂,先知式的瘋子多梅尼克如傳教士式的布道,以及《安德烈·盧布廖夫》的修道院、圣愚形象的塑造,特別是第四集“最后的審判”,借鑒了《圣經》故事。正如安托萬·德·貝克所言:
“在這位俄國導演的內心深入,世界是《圣經》的倒影;對于《圣經》故事,每個人的心中都有著無法釋懷的記憶。”
不難看出,在塔可夫斯基的電影中,大地是生命及一切事物的容器。在這一容器中,水就顯得尤其重要。水土交融,其本身就是大地的一部分,甚至成為塔可夫斯基的一種獨特電影元素及影像風格。《安德烈·盧布廖夫》開場的一幕,就是葉菲姆在湖泊中劃著小船急行,他正要前去試飛熱氣球。湖泊中的水是靜止的水,本身并無特別意義,但出現在鏡頭中,作為船的承載物,使時間流動了起來。《伊萬的童年》中,小伊萬在月黑風高的晚上,與其他護送的戰士劃著小船在湖泊和沼澤中行進,要到對岸德軍陣地收集情報。鏡頭中的水幾乎與夜晚一般黑,在樹林的深處,時而傳來零星的槍聲,預示著行動十分危險。水在這里并非是行船的簡單載體,讓人感到緊張、壓抑和不安,暗黑的水隨時都可能吞噬伊萬弱小的身體。因而,在這里,水不僅代表著時間的流動,明顯影響著觀眾的情緒,充滿了寓意和象征。故事最終表明,伊萬隨時間一同消失在了黑暗的沼澤中,而后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安托萬·德·貝克指出,“在塔可夫斯基的作品中的大地倘若沒有水,便什么也不是”。可見,水在塔可夫斯基雕刻時光的藝術中有多么重要。那些不同性質的水:湖泊的水、河流的水、天空的雨水、海里的水、洼地的水、大海的水等,幾乎都成為他影像情感表達最好的原液,我愿意相信,他就是一位“吟誦沉重的水的詩人”。
塔可夫斯基為什么那么沉迷于水?因為“水是一種非常神秘的元素,在鏡頭下,一個水分子是魅力無窮的”。他說“它能展現運動,以及變化和流動之感”。(約翰·吉安維托:《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訪談錄》)在詩意的鏡頭中,比如《索拉里斯》中清澈溪流中如水流般變動的水草,有包裹著家園翻騰的海洋。在《潛行者》中,作家、教授和潛行者在“區域”尋找“欲望小屋”的過程中,他們三人疲憊地躺在被水包圍的中央,討論著人類的福祉、靈感、幸福以及個人的價值,特別是水洼中躺著潛行者與他的狗的畫面,充滿了頹廢的詩意,讓人印象深刻。《鄉愁》與《安德烈·盧布廖夫》中,有很多雨和水在流淌,無論是《鄉愁》中詩人戈爾恰可夫走過霧氣彌漫的池塘,以及他與多梅尼克在四處滴水、遍地水洼的破敗房間,還是《盧布廖夫》中的三個僧侶在雨中行走,或大鐘鑄造者鮑里斯在暴雨中跌落,意外發現膠泥土,在多數時候,雨或者水都成為大地的時間敘事的重要成分,沉默地調和著情緒的氛圍,也讓故事變得柔軟和流暢。
三
在英格瑪·伯格曼看來,“塔可夫斯基是偉大的,捕捉生命一如倒映,一如夢境”。顯然,這是從電影的維度中肯的高度評價。事實上,塔可夫斯基電影必然受到現實的深刻影響。我們知道,他將人生中的夢境分為兩類:預言式的超驗之夢和與現實接觸碰撞產生的雜亂無章的夢境。在他用影像雕刻時光的敘事結構中,作為生命中最神秘的痕跡,他幾乎完美地將生命之夢流暢完善地編輯植入,使記憶和夢境成為其極為重要的元素。在安托萬·德·貝克看來,“塔可夫斯基主要根據三種活動構建他的電影:尋覓、回憶和夢境”,可以說,這也是作為影像詩人的他最重要的創作特征之一。
《鄉愁》講述的是俄國詩人戈爾恰科夫到意大利采寫俄國音樂家的傳記并最終客死異鄉的故事,雖然其中大量充斥著歐洲的古典建筑、美術和音樂,但塔可夫斯基鏡頭中戈爾恰科夫俄羅斯的家及家人在記憶中反復出現。其中最為詩意的一幕是,雨滴敲打著詩人的窗戶,改變了時間的節奏和方向,預示著夢境的來臨,使他慢慢沉浸其中。隨之出現的是他的愛人、母親、孩子,狗、馬,山坡上的房屋,以及那條河流,一幕幕向他涌來。當良知潛入靈魂,一切都是有關魂牽夢繞家鄉的回憶:從妻子開始,鏡頭緩慢移動,掠過一個更年輕的女人(可能是他妹妹),然后年邁的母親進入記憶和夢境,母親輕輕地轉頭,看見他年輕的愛人與孩子出現在畫面,狗和馬一起跑來,他們的身后就是沉寂的樹木和家的房屋,隨后是更年輕的女人和母親,讓人驚奇在于,他們都看見了自己,時間在這里實現逆轉,生命形成一個循環,戈爾恰科夫在記憶和夢境中反復吸吮了鄉愁,完成了良知的安撫。
其實,電影《鄉愁》開始的一幕就是,潮濕的霧氣、寧靜的原野、孤單的汽車。當詩人戈爾恰科夫與情人兼助手尤金尼婭被這樣的環境包圍時,女主角觸景生情:初次見到這景象我淚流滿面,這光線讓我想起俄羅斯的秋天。這個開篇是詩意的,更是具有暗示和引導性的,它讓觀眾迅速地隨鏡頭進入想象與回憶。而隨著女主步行到霧氣彌漫的遠景,在戈爾恰科夫的眼里,此時隱約出現一條鄉間小道,與故鄉味道太相像了,直奔主題的鏡頭,讓我們很自然就進入塔可夫斯基或戈爾恰科夫抑制不住、波濤起伏的內心世界。
塔可夫斯基說:“導演分為兩類,一種專注描摹自己所生活的世界,另一種致力于創造自己的世界。”(約翰·吉安維托:《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訪談錄》)在他看來,后者包括電影界的詩人,如布列松、伯格曼、布努埃爾、黑澤明等電影界的重量級人物。如詩人父親阿爾謝尼一樣,塔可夫斯基也十分鐘情詩歌,在影像天空,顯然他屬于這一行列的代表。所謂詩的本質,如德理達所言,就是記憶和心靈。夢境恰恰是這兩個詞最真實直接的反映。
如果說,《索拉里斯》和《潛行者》反映的是尋找的主題,那么,在此基礎上鑄刻的《鏡子》,無疑就是時間的回溯——記憶和夢境。沿著這一思維脈絡,不難發現,《鏡子》反射的光影,在某些時候可能非常清晰,有時可能變形或虛化,但不可否認,它是一部充滿情感精心構建的、復雜的關于如何“雕刻時光”的證明書與宣傳冊。
從塔可夫斯基的訪談和一些文獻中可看到,《鏡子》的拍攝經歷了許多混亂和痛苦,以及呈現的主題都發生了重大轉變,“原本設想為一部關于塔可夫斯基母親的電影,最終卻成為了自傳性的研究”(羅伯特·伯德:《安德烈·塔可夫斯基:電影的元素》)。作為具有過去和現在雙重時間結構的電影,其中混雜了童年記憶、歷史事件、過去的夢境以及婚姻現場等等,鑒于回憶與夢境的交織、主觀意識的介入、蒙太奇的剪輯,使影片表達內容和指涉有著相當的不確定性,具有現代詩歌的特點,往往故事性很弱,讓觀眾難以從邏輯上去理解。對此,塔可夫斯基在《雕刻時光》一書中,還列舉了一些觀眾在觀看《鏡子》后寫信給予的怒氣沖沖或嫌惡的質問。當然,他也列舉了真誠贊美的信件,如“謝謝你的電影《鏡子》,我的童年就是那樣……”“我無法用言語形容,因為我生活在其中”。時間中為數不多的縫隙,那正是光照進來的地方,用夢境和想象填充,使內心生活更為豐富,生命感受更為溫暖。在巴赫曼關于《游走在兩個世界之間》的訪談中,他詳細解釋了他的創作與想法:
我希望找到一種形式,它源自人類的處境和心理狀況,也就是說,來源于人類行為的因素,這是再現心理真實的首要前提。因此,在我的電影中,故事永遠不是最重要的,作品的真正意義從來不是通過情節傳達的。我試圖在不受阻的情況下,去表達最關鍵的內容,去展現邏輯上并不必然相關的事物,用思維的流動把它們從內容串聯起來。
在塔可夫斯基看來,“只有一種旅程是可以實現的,那就是通過我們的內心之旅”。換句話說,就是內心真實可經由記憶和夢境來抵達,通過時光的回溯、停滯以及流動來實現,“所有的藝術作品都依托于記憶”,《鏡子》就是這樣一部非常典型的作品。
塔可夫斯基說,《鏡子》這一片名并非隨意所取。仔細想想,的確意味深長,既含有映照的含義,又具倒影的意思,它看上去虛幻,卻又無比真實。在《鏡子》中,出現了幾次母親坐在家外面的木柵欄上,吸著煙,望著遠方有樹和長滿小草的大自然發呆的鏡頭,或許是在沉思冥想,或許在等孩子或丈夫的歸來。這就是塔可夫斯基的童年的記憶。
“大自然在我的電影中隨處可見,這不是風格問題,這是真實的情況。當父親在戰場廝殺之時,我的母親每年春天都會帶我們去鄉野間。母親覺得這是她的責任,從那時起,我就把自然和母親聯系在了一起。”(約翰·吉安維托:《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訪談錄》)
塔可夫斯基三歲時,他父親就離開家了。在他的記憶中,上學時,他與妹妹都已入睡,父親與母親還在廚房爭吵,他就意識到不能與父親共同生活。“我和我母親、外婆、妹妹生活在一起。家里沒有男子漢。這顯然影響了我的性格……”(馬克西姆·古列耶夫:《塔可夫斯基父子:阿爾謝尼與安德烈》)后來,他父親腿受重傷,被截肢,加之由于觀念不同等因素,沒在一起生活,見面很少,使他父親的形象在他的童年記憶中是非常缺失的。而母親是完全不同,基于此,在《鏡子》中,講述者把妻子視為母親的延續。其實,《鄉愁》的夢境中,在大自然的家,往往反復出現的也是妻子與母親。
在《伊萬的童年》中,伊萬的家人在戰爭中喪生,他對家人的記憶總是在敘述中不斷閃回并進入伊萬的夢中,母親和妹妹、陽光和海灘反復出現,精神追憶與客觀真實經常混為一體,塔可夫斯基以此來完成對記憶的重建。而在塔可夫斯基的現實中,他常常揮之不去的往往也是關于童年的記憶:“昨天我又做了一個關于戰爭的夢,這種夢經常出現。”(約翰·吉安維托:《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訪談錄》)可見,最美的記憶往往來自童年,最大的傷痛也常常可能是童年在時光中留下的浸潤式的穿透性陰影。
塔可夫斯基將童年最美的記憶與最可怖的夢境交織在對時光雕刻的敘事中,創作出一部部杰出的作品。伯格曼也是一個對記憶和“夢”情有獨鐘的電影大師,他對塔可夫斯基推崇備至,他在《魔燈》中寫道:
“在所有人當中,塔可夫斯基是最偉大的導演,因為他的影片除了忠實紀錄之外,就都是夢。他在夢境空間四處游走,那么自如。……而我畢生都在敲門,很少能進入其中,大部分有意識的努力都以令人尷尬的失敗而告終。”
可見,讓伯格曼僅能偶爾一窺其堂奧的影像夢幻,塔可夫斯基卻宛如魔術師,以尋覓性與回溯性的流暢記憶,穿越神秘性和神圣性的時間之流,達到表達內心世界的至高境界。
四
塔可夫斯基用影像雕刻時光,如果說大地和雨水是敘述的依托,記憶和夢境是重要的途徑,那么精神性與信仰就是牽引著時間之流的最根本的內在動力,假如失去了這種源頭,人就如同盲人,沒有前行的目標。
在塔可夫斯基看來,當今世界,我們已經丟掉了精神性,人們已經不再需要。從政治、精神和社會各方面來看,我們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在回答觀眾“為什么在我們這個時代,大眾尤其想要缺乏精神性的藝術?”問題時,塔可夫斯基說:“大眾不是想要缺乏精神性的藝術。總體而言,他們什么樣的藝術都不想要。……他們想要的是娛樂。”雖然精神空虛幾乎存在于大多數人當中,藝術家則必須肩負責任,從自身做起,追求精神性。藝術家作為人民的心聲,應該用自己的語言去表達人民的內心和精神狀態,特別是傳達出“沉默的大多數”的感受、想法和希望,“他們必須樹立起某些關鍵的典型,精神和道德上的典范,幫助自己和人們取得精神上的進步”(約翰·吉安維托:《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訪談錄》)。
可以想象,沒有精神和信仰作支撐,人類很容易沉湎現實,及時行樂,而難以克服困難,抵達心中的彼岸。
《潛行者》中,雖然主人公潛行者只是一個普通弱勢的個人,為什么能夠帶領作家和教授,進入神秘莫測的“區域”,在泥濘的道路前往欲望之屋?在塔可夫斯看來,因為“他擁有一種讓人無堅不摧的特質,就是信仰”。潛行者是一個善良樸實、心底純凈的最后的理想主義者,他獨創了在“區域”中的欲望之屋。吊詭的是,潛行者、作家、教授三人經過艱難跋涉,抵達目標,可最后誰也沒有進入那房間。他們害怕進入房間,因為他們不確定自己的真正欲望(愿望)是什么。作家推斷,房間不是讓人的欲望得到滿足,而是實現每個人深埋內心的真實念頭,他不相信自己。科學家根本就不想進去,他甚至想炸掉那個房間,因為“欲望”會擾亂人們的心智。潛行者唯有嘆息,他不能進去,因為這與他的信仰相悖。為什么會這樣?潛行者在謎中悟道:“只有自己相信,虔誠的信仰能讓人類獲得幸福。”
雖然,精神性與信仰在生活中往往比較抽象,但當它變成被雕刻的時間影像時,甚至可能“過去比現在更真實”(塔可夫斯基),這一缺乏心理學深度的表達,并非在講客觀現實的真實,而意在突出強調“即時間不僅是一個基本尺度,而且是人生甚至是精神的重要方面”(雅克·奧蒙:《電影導演論電影》)。更為關鍵的是,在流淌在時光的精神性領域中,信仰尤其重要。在塔可夫斯基看來,只有信仰才能拯救人類。
《鄉愁》中,塔可夫斯基一再表述著這一信念。戈爾恰科夫站在水池中央,耳旁回響這首動人的詩行:當夜幕降臨,我的身后//哪里有微微閃亮的翅膀/我是那蠟燭,在盛宴中消亡……沒想到,這詩意的詩詞竟一語成讖,預示著他人生最后的盛宴即將來臨。
“偉大的作品誕生于藝術家表達其道德理想的掙扎”。塔可夫斯基的電影幾乎都源于這種自身認同的踐行。最震撼人心的敘事來自于尾聲的畫面:戈爾恰科夫遵照多梅尼克的請求,擔負起他的使命(大意是:如果有人能持燭火,涉水走過酒店旁邊的凱瑟琳溫泉而不熄滅,那么全世界將得到拯救。多梅尼克做不到,他的行為被視為“瘋子”,而被人強行從水池中拉起)——點燃手中的蠟燭,走下早已干涸的溫泉池,手捧著它凝神屏氣、小心翼翼向前。燭光在微風中搖曳,當蠟燭熄滅,他回到起點,再次點燃蠟燭,雖用衣領遮擋,但沒走幾步又被風吹熄滅。就這樣,他再次從原點重新出發,最終,蠟燭點燃,他輕輕地放在了對面墻壁的沿上。遺憾的是,當抵達終點,蠟燭點燃之后,戈爾恰科夫終于心力交瘁,突然倒下。戈爾恰科夫與多梅尼克實現了同一,回望兩人的交集,你分不清誰是誰的影子、誰是誰的記憶。隨后鏡頭是,童年,母親,故土。他與狗一起側臥在水塘邊,家鄉的房子背后是意大利建筑,然后大雪紛飛。這段長達9分鐘的長鏡頭,塔可夫斯基拍得沉靜、舒緩、肅穆,猶如一場宗教儀式,點睛般地濃縮了戈爾恰科夫(或自己)面對良知和信仰苦苦追尋卻不被理解的心路歷程。
《鄉愁》給我們的啟示,在塔可夫斯基看來即是“在分裂的世界,我們如何找到達成一致的途徑?唯有相互作出犧牲”。
既然都講犧牲,那么作為電影《犧牲》究竟意在闡述什么?正如郵遞員奧托所言:“我們都在等待著什么……希望,希望,再生。”如何才能獲得這一拯救的密碼?奧托像上帝的信使或預言者一樣,在亞歷山大耳邊秘語“愛上一個脆弱而且受人鄙視的人”,其實所有獻給他人的饋贈本質上都是犧牲。不過,愛與尋找不能迷失方向,必須依靠信仰的指引。亞歷山大遵從神的暗示,愛上了瑪麗亞,點燃了房屋,獻出了自己,他如多梅尼克一樣,都被視為“瘋子”,但卻儀式般地得救了。的確,在塔可夫斯基看來,“就總體效果而言,這不止是一個關于犧牲的寓言,也是一個人如何得救的故事”。他們都似圣愚,難道都是“瘋子”?《鄉愁》中,“瘋子”多梅尼克站在羅馬廣場上,像傳道士般大聲呼告,當《歡樂頌》響起,當眾自焚。多梅尼克為何要自焚?面對所謂的殘垣斷壁、四處漏風的現代文明,他精神錯亂,其悲劇性在于他內心與周遭現實的深刻分裂。在他看來,人類已經走向迷途,喪失了信仰,他無法接受精神與信仰被玷污,因而要以自我犧牲的精神、“殉道”的姿態、活火炬的燃燒,十字架一般倒地來喚醒大家、警示世人。
如果說,在犧牲和救贖之間,多梅尼克和亞歷山大的故事充滿隱喻的話(塔可夫斯基喜歡隱喻不喜歡象征),那么,《安德烈·盧布廖夫》就是塔可夫斯基關于用時間雕刻信仰的歷史敘事的一部典范。塔可夫斯基深知,13—15世紀的俄羅斯圣像畫,從來沒有哪幅以哪個藝術家署名的,圣像畫家也從不把自己當藝術家,在他們眼里,他們有機會為圣人作畫,那是上帝的慈悲,他們覺得自己是用專業技藝侍奉上帝。安德烈·盧布廖夫就是圣像畫家。其同名電影分為兩部分,八個片段,大致以時間順序,講述了畫師安德烈·盧布廖夫跌宕起伏,為信仰而追尋求索的一生。
故事開始于《流浪藝人》一章,安德烈·盧布廖夫、達尼爾·喬爾內和基里爾三位畫圣像的修道士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道路。開篇就是放熱氣球展現俄羅斯底層嘈雜混亂的場景,而后面對流浪藝人,基里爾鄙夷地說:“上帝創造了神父,魔鬼創造了小丑。”盧布廖夫的目光卻表現出仁慈和友好。可惡的是,基里爾接著就告發了小丑,使之身陷囹圄,這一行為對盧布廖夫內心造成巨大不安和痛苦,其影響使他無法繼續創作。后面的故事波瀾壯闊,盧布廖夫經歷了迫害、鎮壓、無措,基里爾出走,慘痛的災難與才藝的枯竭,以及在信念的召喚中繼續創作,其肉身受苦與心靈磨難的過程,如同《圣經》故事,這自然是他抵達信仰之路的洗禮。鮑里斯對大鐘的鑄造正是一個寓言,相當于創世紀。盧布廖夫靜靜并驚奇地審視著這個創造性的作品,猶如源頭之水,滋潤了他枯竭的才能,使他對自身的藝術創作得到重新認識和新生。
史詩性的《安德烈·盧布廖夫》是以主人公受難(犧牲)的方式進行自我救贖,以靈魂復活的主題,肯定了苦難的價值,謳歌了信仰的力量。當鏡頭在教堂中安德烈·盧布廖夫的《三位一體》圣像畫緩緩落幕,并且由黑白漸漸變成彩色時,回望盧布廖夫的一生,或許,這正是用影像雕刻時光的神跡。
總體而言,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電影以充滿開創性的雕刻時光的整體考量,著眼于大地和雨水,依托記憶和夢境,執著于精神性與信仰來編織故事。他常常以長鏡頭的方式、緩慢而寧靜的節奏,深入捕捉電影主人公細膩的表情和內心的變化,傳達深度的內在情感,表達良知的鄉愁。注重從文學經典中借用,以非線性的敘事結構,通過時間的交疊、跳躍和循環等錯綜復雜的剪輯與融合,營造出時間之流詩意的夢幻感覺,使影像的敘事更具有豐富性和美感。當然,我們必須看到,塔可夫斯基對俄羅斯充滿深情,深諳人物內心的復雜描繪,特別對于隱喻和象征的運用、歷史文化的挖掘、母親與童年的回憶、宗教典故的引申,以及對自然的個性表達的呈現。這些特點共同構成了他獨有的電影語言,并使其作品在世界電影之林獨樹一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