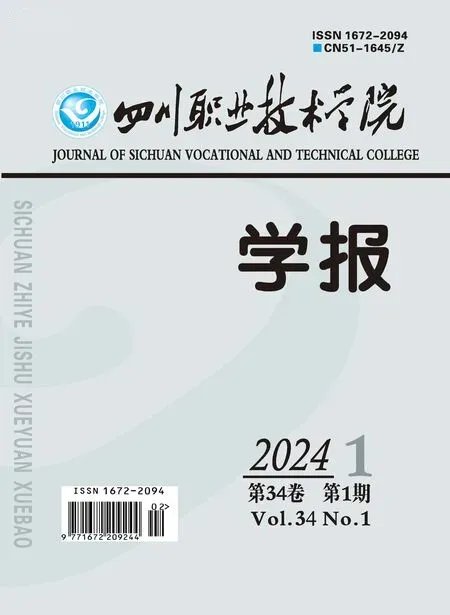新時(shí)代“兩個(gè)中心論”統(tǒng)一的內(nèi)在邏輯
周 成,王 沁
(南京旅游職業(yè)學(xué)院 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江蘇 南京 211100)
以人民為中心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xí)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新概念,集中體現(xiàn)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政治立場和價(jià)值追求。自提出以后,學(xué)界展開了廣泛深入的研究,包括以人民為中心的理論基礎(chǔ)、生成邏輯、豐富內(nèi)涵、時(shí)代價(jià)值、踐行路徑等,其中如何認(rèn)識(shí)“以人民為中心”和“以經(jīng)濟(jì)建設(shè)為中心”的關(guān)系,是學(xué)界關(guān)心的又一個(gè)重點(diǎn)議題。有的學(xué)者認(rèn)為,“以人民為中心”的提出是對“以經(jīng)濟(jì)建設(shè)為中心”的取代,意味著黨的工作重心再次轉(zhuǎn)移,進(jìn)而提出了“中心取代論”。還有的學(xué)者依據(jù)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提出了兩個(gè)中心并立的“雙中心論”等等。那么,“兩個(gè)中心”之間究竟有著什么樣的關(guān)系?在實(shí)踐中我們又應(yīng)該如何處理“兩個(gè)中心”之間的關(guān)系?回答好這一問題,有利于促進(jìn)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和人的全面發(fā)展良性互動(dòng)。
一、“兩個(gè)中心”統(tǒng)一于馬克思主義理論邏輯
處理好“兩個(gè)中心”的辯證關(guān)系,歸根結(jié)底是要處理好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和人的全面發(fā)展之間的關(guān)系,馬克思、恩格斯對此早有論述。唯物史觀認(rèn)為,社會(huì)是人的社會(huì),人是社會(huì)歷史的起點(diǎn),是構(gòu)成社會(huì)的基本要素,是推動(dòng)社會(huì)發(fā)展的根本動(dòng)力。“創(chuàng)造這一切、擁有這一切并為這一切而斗爭的,不是‘歷史’,而正是人,現(xiàn)實(shí)的、活生生的人。”[1]作為社會(huì)歷史的主體,人民群眾是物質(zhì)財(cái)富和精神財(cái)富的生產(chǎn)者,是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變革者,在實(shí)踐中認(rèn)識(shí)并改造著自然,按照自己的想法構(gòu)建出一個(gè)理想的社會(huì)。換言之,社會(huì)是人的實(shí)踐活動(dòng)的產(chǎn)物,是人與人相互作用的結(jié)果。人民群眾既是“劇作者”,也是“劇中人”。離開了人,社會(huì)就不能稱其為社會(huì);同樣,社會(huì)的進(jìn)步也離不開人的健全發(fā)展。人民群眾在社會(huì)歷史中的主體地位決定了一切活動(dòng)必須圍繞人民群眾的需要和發(fā)展展開,始終做到以人民為中心,堅(jiān)持人與社會(huì)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相互促進(jìn)。
然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追求剩余價(jià)值成為資本主義生產(chǎn)的唯一目的。資本家占據(jù)著大量生產(chǎn)資料,在生產(chǎn)中占主導(dǎo)地位,擁有產(chǎn)品的所有權(quán)并決定著產(chǎn)品的分配。工人為了生存,不得不將勞動(dòng)力出賣給資本家,實(shí)現(xiàn)與生產(chǎn)資料的結(jié)合,以此取得低廉的工資,維持生存和發(fā)展的需要。工人愈是努力工作,生產(chǎn)的產(chǎn)品越多,他占有的就越少,越貧困。勞動(dòng)本應(yīng)是“自由的生命表現(xiàn)”,是“生活的樂趣”。但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工人的勞動(dòng)是被迫的強(qiáng)制勞動(dòng),是“滿足勞動(dòng)需要以外的需要的一種手段”[2]159。由于舊式分工的存在,機(jī)器的使用,使工人成為機(jī)器的附庸,重復(fù)著極其簡單的動(dòng)作,壓抑人的個(gè)性,使工人變得畸形,使人的發(fā)展片面化。“勞動(dòng)越機(jī)巧, 工人越愚鈍, 越成為自然界的奴隸。”[3]因此,如何實(shí)現(xiàn)人的解放,實(shí)現(xiàn)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就成為馬克思窮極一生所追求的夢想。即使是“遭受國家驅(qū)逐,飽嘗顛沛流離的艱辛和貧病交加的煎熬,他依然初心不改、矢志不渝”[4]。
馬克思立足于現(xiàn)實(shí)的人,從多方面探討了人的解放的可能性,其中一個(gè)重要的現(xiàn)實(shí)條件就是生產(chǎn)力的高度發(fā)達(dá)。他認(rèn)為物質(zhì)生產(chǎn)是人類社會(huì)存在和發(fā)展的第一個(gè)前提,也是一切社會(huì)歷史活動(dòng)的起點(diǎn)。“當(dāng)人們還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質(zhì)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應(yīng)的時(shí)候,人們就根本不能獲得解放。”[2]527人類社會(huì)只有在滿足最基本的物質(zhì)生活條件后,才會(huì)產(chǎn)生新的更高的需求。這些需求會(huì)推動(dòng)人類的實(shí)踐,促進(jìn)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而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出豐富的物質(zhì)財(cái)富,使人們擺脫貧困狀態(tài),擺脫物的奴役,社會(huì)發(fā)展不再以多數(shù)人的犧牲為代價(jià)。同時(shí),由于生產(chǎn)力的高度發(fā)達(dá),勞動(dòng)生產(chǎn)率的提高,生產(chǎn)滿足社會(huì)成員生活資料的時(shí)間大大減少,人們將享有更多的自由時(shí)間,能夠去從事感興趣的活動(dòng),追求更高層次的精神活動(dòng),人的各方面能力將得到極大提升,人的個(gè)性將得到充分發(fā)揚(yáng),人的社會(huì)關(guān)系將得到全面發(fā)展。
與馬克思所設(shè)想的不同的是,社會(huì)主義革命并沒有首先在生產(chǎn)力高度發(fā)達(dá)的資本主義國家取得勝利,而是在東方經(jīng)濟(jì)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率先成功。由于資本主義發(fā)展的不充分,生產(chǎn)力不發(fā)達(dá),以及面臨嚴(yán)峻的國際形勢,決定了無產(chǎn)階級在奪取政權(quán)后,必須“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chǎn)力的總量”[5],消除貧困,避免“陳腐污濁的東西死灰復(fù)燃”[6]256,以此達(dá)到消滅私有制的目的,為共產(chǎn)主義的實(shí)現(xiàn)奠定堅(jiān)實(shí)的物質(zhì)基礎(chǔ)。列寧在領(lǐng)導(dǎo)俄國十月革命和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過程中,進(jìn)一步深化了對這一觀點(diǎn)認(rèn)識(shí)。他認(rèn)為高度發(fā)達(dá)生產(chǎn)力是鞏固蘇維埃政權(quán),恢復(fù)和發(fā)展國民經(jīng)濟(jì),防止敵人反撲,增強(qiáng)國家實(shí)力,鞏固社會(huì)主義制度的重要手段。“無產(chǎn)階級奪取政權(quán)和鞏固政權(quán)的任務(wù)完成后,必然要把一個(gè)‘根本的任務(wù)’提到首位,這個(gè)根本的任務(wù)就是提高勞動(dòng)生產(chǎn)率。”[7]在實(shí)踐中,他也對如何提高生產(chǎn)力的途徑也進(jìn)行了有效的探索,包括實(shí)行租讓制,恢復(fù)小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實(shí)現(xiàn)電氣化,發(fā)揮科技的作用等。既然解放和發(fā)展生產(chǎn)力是社會(huì)主義的根本任務(wù),那么以經(jīng)濟(jì)建設(shè)為中心就是其應(yīng)有之義。
盡管社會(huì)主義和資本主義都強(qiáng)調(diào)發(fā)展生產(chǎn)力,但兩者的目的具有根本區(qū)別。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是“以物為本”的發(fā)展,人只是作為經(jīng)濟(jì)增長、社會(huì)財(cái)富增加的手段。“是一種‘客體為中心’的發(fā)展、‘沒有發(fā)展的增長’和‘沒有幸福的富裕’”[8]。馬克思對此早已作出批判。在《論猶太人問題中》就曾指出:“實(shí)際需要、利己主義是市民社會(huì)的原則。”“金錢是人的勞動(dòng)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異化的本質(zhì);這種異己的本質(zhì)統(tǒng)治了人,而人則向它頂禮膜拜。”[9]而社會(huì)主義發(fā)展生產(chǎn)力的目的在于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最終實(shí)現(xiàn)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人既是發(fā)展的手段,更是發(fā)展的目的。它把人的發(fā)展作為衡量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的最核心的指標(biāo),一切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自覺圍繞著人的發(fā)展展開。既突破了見物不見人的以物為本的發(fā)展的缺陷,又彌補(bǔ)了“人本主義”離開現(xiàn)實(shí)的人來抽象地、空洞地談人的發(fā)展的弊端。
人的發(fā)展和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都是一個(gè)動(dòng)態(tài)的歷史過程。馬克思把人的發(fā)展過程劃分為三個(gè)階段,即人的依賴階段、物的依賴階段和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階段。在第一階段,由于生產(chǎn)力的不發(fā)達(dá),“在這種形式下,人的生產(chǎn)能力只是在狹隘的范圍和孤立的地點(diǎn)上發(fā)展著。”[10]在第二階段,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生產(chǎn)方式的變革,物質(zhì)財(cái)富的迅速增加,開始“形成了普遍的社會(huì)物質(zhì)交換、全面的關(guān)系、多方位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體系。”[6]107但也使人為物所奴役。由于社會(huì)主義脫胎于舊社會(huì),是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的第一階段,不可避免地依然保留著某些舊社會(huì)的痕跡。只有在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勞動(dòng)不再是謀生的手段,人們“可能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干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6]85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成為客觀現(xiàn)實(shí)。
二、“兩個(gè)中心”貫穿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黨的全部奮斗歷程
雖然“以經(jīng)濟(jì)建設(shè)為中心”和“以人民為中心”兩個(gè)概念在提出時(shí)間上有先后之分,但從實(shí)踐上看,“兩個(gè)中心”指導(dǎo)思想一直貫穿于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全部奮斗歷程。
在全國革命勝利前夕,中國共產(chǎn)黨對革命勝利后的工作重點(diǎn)就有了清醒的認(rèn)識(shí)。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huì)第二次全體會(huì)議上就提出革命勝利后的所有工作“都是圍繞著生產(chǎn)建設(shè)這一個(gè)中心工作并為這個(gè)中心工作服務(wù)的”[11]1428。他進(jìn)一步把經(jīng)濟(jì)發(fā)展、人民生活改善和革命政權(quán)鞏固聯(lián)系起來,指出如果“不能使生產(chǎn)事業(yè)盡可能迅速地恢復(fù)和發(fā)展……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quán)”[11]1428。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由于長期戰(zhàn)爭的破壞,國家積貧積弱、一窮二白,社會(huì)生產(chǎn)遭到嚴(yán)重破壞,民生凋敝,人民生活困苦。有關(guān)資料顯示:“1949年與1936年中國歷史最高水平相比,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值下降20%以上,工業(yè)總產(chǎn)值減少一半,其中重工業(yè)減少70%,輕工業(yè)減少30%。”[12]“1949年全國鋼產(chǎn)量僅15.8萬噸,比1943年減少82.9%,原煤產(chǎn)量由6188萬噸降到3243萬噸,下降47.6%,糧食產(chǎn)量從 3000 億斤下降到1949年的2263億斤,下降24.5%。”[13]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共產(chǎn)黨人把恢復(fù)和發(fā)展經(jīng)濟(jì)作為中心工作,繼續(xù)完成民主革命遺留任務(wù),推進(jìn)社會(huì)主義改造,建立社會(huì)主義制度,為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提供了制度保障。在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期間,毛澤東多次強(qiáng)調(diào),“現(xiàn)在的中心任務(wù)是建設(shè)”[14],要大力發(fā)展生產(chǎn)力,把滿足人民群眾利益作為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價(jià)值目標(biāo),改善人民生活條件,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zhì)生活和文化生活。
“文革”結(jié)束后,早在1978年9月,鄧小平在“北方談話”中就指出,社會(huì)主義制度的優(yōu)越性就在于生產(chǎn)力快速發(fā)展,使人民群眾物質(zhì)文化生活需要不斷得到滿足。“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速度比資本主義慢,那就沒有優(yōu)越性,這是最大的政治,這是社會(huì)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zhàn)勝誰的問題。”[15]172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ì)正式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diǎn)轉(zhuǎn)移到社會(huì)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shè)上來,實(shí)現(xiàn)了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又一次轉(zhuǎn)移。1979年10月,鄧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區(qū)委員會(huì)第一書記座談會(huì)上再次強(qiáng)調(diào):“經(jīng)濟(jì)問題是當(dāng)前最大的政治,經(jīng)濟(jì)問題是壓倒一切的政治問題。”[15]194要求把經(jīng)濟(jì)工作作為當(dāng)前和今后工作的重點(diǎn)。改革開放新時(shí)期,鄧小平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我國人口數(shù)量多,經(jīng)濟(jì)基礎(chǔ)薄弱,還處在社會(huì)主義初級階段,生產(chǎn)力不發(fā)達(dá),遠(yuǎn)遠(yuǎn)不能滿足國家和人民的需要。現(xiàn)階段我國社會(huì)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zhì)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huì)生產(chǎn)之間的矛盾,解決這個(gè)矛盾的辦法就是大力發(fā)展生產(chǎn)力。各項(xiàng)工作必須服從和服務(wù)于經(jīng)濟(jì)建設(shè),決不能再離開這個(gè)重點(diǎn)。1992年,在“南方談話”中,他又從社會(huì)主義本質(zhì)的角度來闡述生產(chǎn)力的極端重要性,提出要把“三個(gè)有利于”作為檢驗(yàn)一切工作成效的標(biāo)準(zhǔn),告誡全黨同志“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dòng)搖不得”[16],號(hào)召黨員干部學(xué)習(xí)經(jīng)濟(jì)理論、經(jīng)濟(jì)工作和科學(xué)技術(shù),抓住機(jī)遇,發(fā)展經(jīng)濟(jì),在發(fā)展中改善人民生活。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huì)以來,以江澤民同志為代表的共產(chǎn)黨人接過歷史的接力棒,繼續(xù)統(tǒng)籌推進(jìn)經(jīng)濟(jì)建設(shè)和人的全面發(fā)展。江澤民指出,人的全面發(fā)展和經(jīng)濟(jì)文化發(fā)展是互為前提與基礎(chǔ)的。一方面,人的全面發(fā)展是經(jīng)濟(jì)文化發(fā)展的出發(fā)點(diǎn)和落腳點(diǎn)。從人類社會(huì)發(fā)展歷程來看,奴隸社會(huì)、封建社會(huì)、資本主義社會(huì)都是建立在少數(shù)人對多數(shù)人的剝削和壓迫基礎(chǔ)上的。尤其是資本主義社會(huì)在資本邏輯主導(dǎo)下,把實(shí)現(xiàn)利益最大化作為根本目的,人只是作為賺錢的工具而存在。盡管資本主義帶來了工業(yè)文明,創(chuàng)造了比過去一切世代還要多,還要大的生產(chǎn)力,但也導(dǎo)致人的異化,造成人的畸形片面發(fā)展。而社會(huì)主義社會(huì)以實(shí)現(xiàn)人的全面發(fā)展為根本目的,協(xié)調(diào)推進(jìn)物質(zhì)文明與精神文明建設(shè),促進(jìn)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在發(fā)展中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質(zhì)和科學(xué)文化素質(zhì),促進(jìn)人的全面發(fā)展。另一方面,人的發(fā)展又是經(jīng)濟(jì)文化發(fā)展的重要前提條件。江澤民指出:“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17]進(jìn)入新世紀(jì)以來,隨著知識(shí)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人才在綜合國力的競爭中的重要性愈加凸顯。我國作為后起的發(fā)展中國家,要建設(shè)富強(qiáng)、民主、文明的社會(huì)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實(shí)現(xiàn)由追跑到并跑甚至領(lǐng)跑的跨越,既要靠社會(huì)主義制度的優(yōu)越性,充分借鑒吸收世界各國的優(yōu)秀成果,也要靠人才,發(fā)揮人的主動(dòng)性和創(chuàng)造性。必須高度重視人才培養(yǎng),大力發(fā)展教育事業(yè),努力把人口數(shù)量優(yōu)勢轉(zhuǎn)化為人才質(zhì)量優(yōu)勢。總之,經(jīng)濟(jì)文化發(fā)展和人的全面發(fā)展是一個(gè)相互結(jié)合、相互促進(jìn)、逐步提高的過程。既要?jiǎng)?chuàng)造豐富的物質(zhì)文化財(cái)富,努力為實(shí)現(xiàn)人的全面發(fā)展創(chuàng)造條件;也要著眼于人民群眾的現(xiàn)實(shí)訴求。貫徹“三個(gè)代表”要求,發(fā)展生產(chǎn)力和社會(huì)主義先進(jìn)文化,最終要落到實(shí)現(xiàn)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來。在經(jīng)濟(jì)社會(huì)不斷發(fā)展的基礎(chǔ)上,切實(shí)保障人民群眾的合法權(quán)益。
在實(shí)踐中,由于對發(fā)展的認(rèn)識(shí)不夠,簡單地把經(jīng)濟(jì)發(fā)展和GDP等同起來,一段時(shí)間內(nèi)“唯GDP論英雄”盛行,盲目地追求發(fā)展速度,導(dǎo)致資源浪費(fèi)嚴(yán)重,環(huán)境污染加劇,不協(xié)調(diào)、不可持續(xù)問題更加突出,這些都制約著我國經(jīng)濟(jì)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胡錦濤同志提出科學(xué)發(fā)展觀,回答了擺在我們面前的“實(shí)現(xiàn)什樣的發(fā)展、怎樣發(fā)展”這個(gè)難題。強(qiáng)調(diào)以經(jīng)濟(jì)建設(shè)為中心是興國之要,是保證國家興旺發(fā)達(dá)、長治久安的根本要求。要緊緊抓住發(fā)展這把關(guān)系全局的金鑰匙,不斷解放和發(fā)展生產(chǎn)力。同時(shí)也指出發(fā)展是科學(xué)的發(fā)展,是以人為本的發(fā)展。在發(fā)展過程中既要關(guān)注經(jīng)濟(jì)指標(biāo),也要注重人文指標(biāo)。要著眼于人的全面發(fā)展這個(gè)終極目標(biāo),以改善民生為重點(diǎn),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fā)謀劃發(fā)展,深入群眾,了解民情,集中民智,使黨的各項(xiàng)決策更好地實(shí)現(xiàn)人民群眾的利益,更好地保障人民群眾在經(jīng)濟(jì)、政治、文化、社會(huì)等各個(gè)方面的權(quán)益,讓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fā)展的成果。
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國內(nèi)外形勢的新變化,習(xí)近平總書記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只要國內(nèi)外大勢沒有發(fā)生根本變化,堅(jiān)持以經(jīng)濟(jì)建設(shè)為中心就不能也不應(yīng)該改變。同時(shí)根據(jù)人民群眾的新要求和新期待,堅(jiān)持以馬克思主義人民觀為指導(dǎo),批判吸收中國傳統(tǒng)民本思想的精髓,總結(jié)中國共產(chǎn)黨治國執(zhí)政的歷史經(jīng)驗(yàn),立足于新時(shí)代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的偉大實(shí)踐,創(chuàng)造性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強(qiáng)調(diào)要堅(jiān)持人民主體地位,發(fā)揮人民首創(chuàng)精神,時(shí)刻心系群眾,永葆對人民的赤子之心,始終把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我們的奮斗目標(biāo)。要求把黨的群眾路線貫穿到治國理政的全過程,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lián)系,讓人民群眾成為檢驗(yàn)黨的工作成效的裁判員和評判者,帶領(lǐng)全國人民向全面小康的目標(biāo)前進(jìn)。不斷增進(jìn)人民福祉、促進(jìn)人的全面發(fā)展,讓人民群眾過上更加體面更有尊嚴(yán)的幸福生活,進(jìn)一步深化了對“三大規(guī)律”的認(rèn)識(shí)。
三、正確處理好“兩個(gè)中心”的關(guān)系
以經(jīng)濟(jì)建設(shè)為中心和以人民為中心是我們黨在建設(shè)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的不同階段提出的,但兩者并不是對立矛盾的,而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jìn)的,既各有側(cè)重,又密切相關(guān)。首先,以經(jīng)濟(jì)建設(shè)為中心和以人民為中心兩個(gè)范疇并不是處于同一層面的,直接比較沒有意義。以人民為中心更加側(cè)重于思想層面,不僅僅是一種發(fā)展思想,更是一種價(jià)值追求。不僅體現(xiàn)在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而且是黨和國家其他事業(yè)所遵循的重要原則。如習(xí)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宣傳思想工作要“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dǎo)向”[18]“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必須堅(jiān)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研究導(dǎo)向”[19]78“網(wǎng)信事業(yè)發(fā)展必須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20]等。以經(jīng)濟(jì)建設(shè)更加側(cè)重于實(shí)踐層面,旨在創(chuàng)造出豐富的物質(zhì)財(cái)富,為社會(huì)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shè)奠定堅(jiān)實(shí)的物質(zhì)基礎(chǔ),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其次,從時(shí)間上看。以人民為中心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價(jià)值追求,貫穿于黨的奮斗歷程的全過程。以經(jīng)濟(jì)建設(shè)為中心則是階段性的,是無產(chǎn)階級政黨取得政權(quán)后的一項(xiàng)根本任務(wù)。最后,以經(jīng)濟(jì)建設(shè)為中心和以人民為中心是發(fā)展手段與目的的統(tǒng)一。正如習(xí)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追求的發(fā)展是造福人民的發(fā)展。”[19]35經(jīng)濟(jì)發(fā)展是人的發(fā)展的前提和基礎(chǔ),是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的手段,是發(fā)展生產(chǎn)力的必然選擇,是堅(jiān)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實(shí)踐要求;以人民為中心體現(xiàn)了中國共產(chǎn)黨治國理政的價(jià)值目標(biāo),是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目的和歸宿,為經(jīng)濟(jì)建設(shè)提供價(jià)值指引。我們要正確認(rèn)識(shí)和處理兩者的關(guān)系,既要堅(jiān)持以經(jīng)濟(jì)建設(shè)為中心不動(dòng)搖,又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貫徹到經(jīng)濟(jì)建設(shè)的全過程,在發(fā)展中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地推動(dòng)社會(huì)發(fā)展。
第一,堅(jiān)持以經(jīng)濟(jì)建設(shè)為中心的地位不動(dòng)搖。以人民為中心的提出不是對以經(jīng)濟(jì)建設(shè)為中心的否定,而是對它的超越,內(nèi)在地包含了以經(jīng)濟(jì)建設(shè)為中心。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堅(jiān)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dòng)搖,把發(fā)展生產(chǎn)力擺在首位,緊緊扭住不放,經(jīng)濟(jì)建設(shè)成效顯著,綜合國力顯著提升,躍居成為世界第二大經(jīng)濟(jì)體;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基礎(chǔ)設(shè)施不斷完善,各項(xiàng)社會(huì)事業(yè)蓬勃發(fā)展,中華民族、中國人民的面貌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實(shí)現(xiàn)了由“站起來”“富起來”到“強(qiáng)起來”的偉大飛躍,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進(jìn)入新時(shí)代,我國發(fā)展進(jìn)入新的歷史起點(diǎn)。盡管成就巨大,前途光明,但是我國發(fā)展仍面臨著許多問題,大而不強(qiáng)、臃腫虛胖體弱問題突出、區(qū)域發(fā)展不平衡不協(xié)調(diào)、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不合理、貧富差距大、社會(huì)保障水平總體比較低等。同時(shí),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huì)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也沒有變。解決我國一切問題還要落實(shí)到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上來。必須貫徹新發(fā)展理念,始終堅(jiān)持以經(jīng)濟(jì)建設(shè)為中心,統(tǒng)籌推進(jìn)“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為實(shí)現(xiàn)中國夢奠定堅(jiān)實(shí)的物質(zhì)文化基礎(chǔ)。
第二,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貫徹到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的全過程。馬克思指出:“一旦有了生產(chǎn),所謂生存斗爭不再單純圍繞生存資料進(jìn)行,而是圍繞著享受資料和發(fā)展資料進(jìn)行。”[21]也就是說,人的需求具有多樣性和發(fā)展性,在基本生存資料得到滿足后,會(huì)不斷追求新的更高的需要。美國心理學(xué)家馬斯洛也認(rèn)為人的需求具有層次性、階段性和上升性等特點(diǎn)。經(jīng)過70多年的不懈奮斗,我國逐步實(shí)現(xiàn)了由溫飽到小康的跨越,正在向共同富裕邁進(jìn)。進(jìn)入新時(shí)代,我國社會(huì)的主要矛盾已經(jīng)轉(zhuǎn)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fā)展之間的矛盾。人民群眾的需要呈現(xiàn)出差異化、多樣化、個(gè)性化的特點(diǎn),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強(qiáng)烈,需要更加廣泛。不僅對物質(zhì)文化有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wěn)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huì)保障……。”[22]而且在民主、法治、生態(tài)環(huán)境等方面的需要與日俱增。我們必須緊扣社會(huì)主要矛盾的變化,解決好不平衡不充分這個(gè)制約我國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的短板,積極回應(yīng)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在發(fā)展中更加注重解決人民群眾關(guān)心的就業(yè)、醫(yī)療、教育、住房等問題,補(bǔ)齊民生短板,確保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落實(shí)到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的全過程,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幸福感獲得感滿足感。
第三,扎實(shí)推進(jìn)共同富裕。貧困問題是世界各國發(fā)展所面臨的共同難題,尤其是在一些發(fā)展中國家,貧困帶來嚴(yán)重的社會(huì)問題,甚至影響國家政權(quán)的穩(wěn)定。社會(huì)主義就是要消除貧困,實(shí)現(xiàn)共同富裕。馬克思通過長期對資本主義社會(huì)的觀察、研究發(fā)現(xiàn)指出:“工人階級處境悲慘的原因不應(yīng)當(dāng)?shù)竭@些小的弊端中去尋找,而應(yīng)當(dāng)?shù)劫Y本主義制度本身中去尋找。”[23]新中國的成立,社會(huì)主義改造的完成,社會(huì)主義制度的建立,為我們國家消除貧困奠定了制度基礎(chǔ)。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扶貧的新形勢新特點(diǎn),習(xí)近平總書記提出了精準(zhǔn)扶貧戰(zhàn)略,作出了打贏脫貧攻堅(jiān)戰(zhàn)的重要部署,堅(jiān)持黨對扶貧工作的集中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健全專項(xiàng)扶貧、行業(yè)扶貧、社會(huì)扶貧的“三位一體”大扶貧格局,統(tǒng)籌推進(jìn)“五個(gè)一批”和“六個(gè)精準(zhǔn)”,變大水漫灌為精準(zhǔn)滴灌,變輸血式扶貧為造血式扶貧,堅(jiān)持扶貧和扶志扶智相結(jié)合,增強(qiáng)脫貧的內(nèi)生動(dòng)力。在精準(zhǔn)扶貧戰(zhàn)略的指導(dǎo)下,我國“現(xiàn)行標(biāo)準(zhǔn)下9899萬農(nóng)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gè)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gè)貧困村全部出列”[24],困擾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告別歷史舞臺(tái),得到徹底解決。習(xí)近平總書記指出,脫貧摘帽不是終點(diǎn),而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diǎn)。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永無止境,黨和國家為人民謀福祉也永不停歇。在后扶貧時(shí)代,要繼續(xù)鞏固好脫貧攻堅(jiān)的成果,加快構(gòu)建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jī)制,扎實(shí)推進(jìn)共同富裕,實(shí)現(xiàn)共同富裕的目標(biā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