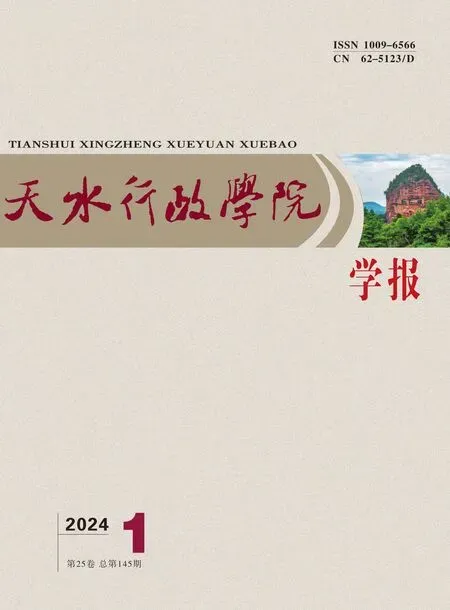德里達對馬克思批判精神的繼承及其當代價值
——基于《馬克思的幽靈》的文本研究
張卓璐
(天津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天津 300382)
雅克·德里達的解構主義思想內容龐大,他的解構性閱讀十分廣泛,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文本,到胡塞爾、海德格爾的哲學文本,再到文學、精神分析學、政治哲學等領域的文本,這其中也包含著馬克思及馬克思主義的文本。20世紀90年代之后,德里達的研究視角開始由文本向政治、宗教、倫理等現實社會領域轉移,在這期間,德里達集中出版過幾本經典著作,特別是《馬克思的幽靈》給學者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德里達在《馬克思的幽靈》發表之前就已經開始關注馬克思主義,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不斷的思考,為他日后對馬克思主義的解構式閱讀奠定了基礎,且相關思想成果集中體現在《馬克思的幽靈》之中。
德里達在《馬克思的幽靈》中運用其早期的解構理論及獨特的“幽靈學”解構邏輯對馬克思主義作了新型的解釋,以解構主義的立場捍衛了馬克思主義,在構建“幽靈學”的基礎上凸顯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法的合理內核。在此基礎上,德里達指出世界上每個人都是“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繼承人”[1],并強調了馬克思批判精神的重要地位,認為馬克思的批判精神是人類必須繼承的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遺產。德里達在《馬克思的幽靈》中關于繼承馬克思批判精神遺產的觀點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現實性與當代價值的充分肯定,不僅在當時特殊的歷史背景下捍衛了馬克思主義及其精神的重要地位,而且在今天對于正確認識當代資本主義世界以及推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也具有重要的價值。
一、德里達對馬克思主義的“幽靈化”解讀
(一)馬克思“幽靈”的到來
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隨著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潮,社會主義國家發展模式及馬克思主義的現實價值遭受質疑。福山等人所聲稱的“歷史終結論”籠罩著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它企圖使人們相信,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將不再是相對立的歷史局面,資本主義新世界秩序將成為人類的未來。德里達以《馬克思的幽靈》批判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對其提出的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終將滅亡的論斷進行了駁斥,認為當下社會主義實踐遭遇的挫折不僅無法預示馬克思主義的消亡,反而為馬克思主義及其精神遺產的“幽靈化”顯現提供了條件。德里達希望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的解構式閱讀實現對馬克思主義的捍衛,他認為只有將馬克思主義“幽靈化”才是實現這一目的的唯一出路。
德里達在東歐劇變之前從來沒有態度明確地發表過關于馬克思主義的看法,或與其建立某種聯系,然而,他卻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頗受質疑的時刻,走近馬克思主義并為其辯護。可見德里達的《馬克思的幽靈》并不是簡單地對馬克思主義的一種匆忙的整合,而是經過深思熟慮后向馬克思的致敬。德里達深刻批判了發達工業社會的諸多問題,指出其仍然處于危機之中,并沒有實現歷史終結論者們所聲稱的那樣完全的正義與公平,實現成為世界未來的目標。因此德里達認為,在這樣一個脫節的時代,人類看到的不應是馬克思主義的看似失敗,反而應當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馬克思“幽靈”的復歸與指引。
德里達指出,東歐劇變使得共產主義作為整體在西方已經瓦解,隨之而來的便是馬克思“幽靈”的降臨。蘇聯社會主義體制的首次建立承載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希望,但蘇聯社會主義的最終解體使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形式寄托隨之喪失,只能成為一個四處游蕩的鬼魂。而鬼魂的特點正在于,它可以再次寄托于形體。因此,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和不斷繼承與創新的內在要求,使得馬克思主義的“幽靈”能夠隨著時代和現實的變化不斷轉換理論形態,在未來不斷呈現新的出場形式,在不在場與在場之間不斷轉換。
(二)馬克思“幽靈”的內涵
德里達指出自己所呼喚的馬克思的“幽靈”并不是純粹的幻象,而是具有深刻內涵的,并在《馬克思的幽靈》中詳細闡述了“幽靈”的內涵。德里達的“幽靈”一詞來自《共產黨宣言》,然而“幽靈”在德里達和馬克思口中的含義卻完全不同。《共產黨宣言》中的“幽靈”是共產主義的“幽靈”,意在表達共產主義終將會如幽靈一般降臨在全世界;而德里達所說的馬克思的“幽靈”指的則是曾經存在,而現在已經無法顯形、失去肉身的馬克思和馬克思的精神。
德里達認為,馬克思的“幽靈”是一個復數,他用馬克思的“幽靈們”來表示,他認為馬克思的“幽靈”不是一個,而應當是“一小撮”。而且馬克思的“幽靈”的形式也不是單一的,而是各不相同的。德里達意在凸顯馬克思“幽靈”的多樣性和異質性,他指出,對馬克思主義進行解構就是為了給馬克思的“幽靈們”呼吁多樣性,呼吁異質性,為他們的未來作出預示[1]。德里達這里所說的“異質性”,是指馬克思主義理論既有價值又有局限,呈現矛盾性,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價值就在于馬克思的批判精神,而其局限性主要指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等理論。德里達呼吁異質性就是要求對馬克思主義進行多元化的解讀,既要彰顯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又要拋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局限性內容。由此,他通過復數的馬克思的“幽靈們”來證明蘇聯社會主義體制的失敗并不能代表馬克思主義的末日,同時,馬克思的“幽靈”所內含的異質性使得馬克思主義在當下和未來依然具有無限的活力。
此外,德里達還說明了馬克思“幽靈”的展現形式。他認為,馬克思“幽靈”的顯形在時間上沒有確定的日期,既不是現在,也不是將來,但它預示著某種復歸,而這種復歸也無法確定;在空間上它沒有具體的形態,它既存在于每個空間,又不在任何一個空間,它不能被稱作一個靈魂,也不能算作肉體,但他又可以既是靈魂,又是肉體[1]。馬克思的“幽靈”既在場又不在場,既有形又無形,它四處徘徊卻又無處不在。
二、德里達對馬克思批判精神的繼承
德里達呼喚馬克思主義的異質性,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局限性內容應當被拋棄,但任何人都無法忽視馬克思的批判精神。歷史已經證明,馬克思徹底的批判精神是審視資本主義各種問題的有效工具,是批判當代發達工業社會弊端的有力思想武器。并且在未來,馬克思主義也將繼續指引我們的生活,現實世界中的一系列社會問題都必將求助于馬克思主義,馬克思的“幽靈”呼喚著我們,每個人都是馬克思主義批判精神遺產的繼承人。
(一)繼承馬克思的“異質性”遺產
德里達首先論述了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所具有的異質性,正是這樣的異質性特征,其內部呈現的矛盾性為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不斷發展的條件。這樣的異質性使得馬克思主義能夠不斷被重新閱讀和解釋,使其擁有不斷前進發展的源泉和動力。基于此,德里達進一步對馬克思精神的異質性進行了論述,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精神也具備異質性的特征,馬克思主義具有各不相同的多種精神,而不是只有一種。由此,德里達呼吁我們繼承馬克思的遺產,馬克思的“幽靈”本身及其精神都是我們要繼承的“異質性”的遺產,而其中最重要的遺產就是馬克思的批判精神。
德里達將馬克思主義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為“好的馬克思主義”,也就是馬克思的批判精神,他強調馬克思的批判精神是我們必須繼承的馬克思遺產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并且要將其與具體的現實相結合,才能顯示出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價值和力量[2];另一部分則是“壞的馬克思主義”,是喪失了活力的部分,是導致馬克思主義逐漸僵化、教條化的因素,應當與馬克思的批判精神區分開來,并且加以拋棄。此外,德里達還強調了馬克思“異質性”遺產中除了批判精神,還有另一種精神——“彌賽亞”精神。德里達在《馬克思的幽靈》中對“彌賽亞”精神作了詳細的闡釋,并區分了彌賽亞主義和彌賽亞性,闡述了他所要繼承的“彌賽亞”精神的內涵,在這里我們可以理解為是馬克思的解放精神。德里達認為,馬克思的解放精神值得我們繼承的是它的某種允諾,馬克思以分析分工和所有權制度的發展為基礎,從理論上建立了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構想。這種解放精神能夠使人們對未來充滿希望,更重要的是它能夠在現實中為改造社會的行動創造動力。
在闡明人類所要繼承的馬克思的“異質性”遺產后,德里達進一步思考了應當如何繼承馬克思的遺產。他首先強調了,反復閱讀和討論馬克思主義是繼承馬克思遺產的前提,必須要不斷對馬克思主義進行重新解讀和過濾篩選,批判地繼承馬克思主義。其次,德里達反對以中立化的立場繼承馬克思的遺產,他認為將馬克思主義置于純粹的哲學學術研究而不討論繼承的立場,將導致對馬克思主義理解的偏差。對于否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關聯性的觀點,德里達指出,他們是想僅在學術層面毫不費力地就對馬克思主義作出評判,在理論內部利用馬克思來反對馬克思主義,以達到自己企圖抑制政治律令的目的[1]。最后,德里達強調繼承馬克思的遺產,應當與現實政治相結合。政治性和意識形態性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寶貴的理論特質,離開現實政治談馬克思主義必然導致無效解讀。因此德里達認為必須以與現實政治相結合的方法繼承馬克思的“異質性”遺產,繼承馬克思的批判精神,由此才能使馬克思的“幽靈”在現實和未來中發揮真正的力量。
德里達關于繼承馬克思批判精神的觀點雖然在極大程度上肯定了馬克思批判精神對于資本主義現實社會的深刻揭露作用,凸顯了馬克思主義的現實性,但是他對于馬克思主義的這種解構式閱讀方式應當引發我們的思考。
(二)德里達繼承馬克思批判精神的實質
從德里達對馬克思主義的解構式閱讀來看,馬克思主義的全部理論內涵的核心就在于其批判精神,這顯然是有失偏頗的。馬克思的徹底的批判精神是馬克思思想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它絕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理論批判也從來不是馬克思認識世界的目的。馬克思認識世界最終是為了改造世界,理論批判只是理論創新的途徑,不斷為改造世界提供行動指南。伊格爾頓指出德里達解構后的馬克思主義其實是“一種沒有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這樣的馬克思主義只是符合其自身需要而被他利用、改造并占有了的馬克思主義[3]。由此我們應該看到,德里達只保留馬克思批判精神的觀點可以說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一種片面化、激進化的解讀,這在客觀上消解了馬克思主義以及馬克思批判精神的最為重要的實踐性特征。
德里達將馬克思的批判精神與自己的解構理論結合起來,形成對馬克思主義的解構性解讀,客觀上來看有兩點考慮。一方面,德里達注意到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批判理論對資本主義現實問題的深刻揭露,認為馬克思的批判精神與自己的解構理論具有契合之處,在當時的特殊時代背景下都能夠對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展開有力的駁斥,但德里達不能贊同馬克思所提出的共產主義社會目標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的其他內容,因此他對馬克思主義展開解構,將馬克思的批判精神與解構理論相結合,提出了自己對未來社會的“新國際”構想;另一方面,德里達的解構理論旨在反對一切形式的邏各斯中心主義,對經典文本的解構是其內在需要,那么在馬克思主義面臨邊緣化危機的特殊時代條件下,對馬克思主義文本的解構式閱讀就成為了必然,在這一過程當中,德里達也十分注重馬克思批判精神與解構主義的契合之處,“對于德里達來說,保衛馬克思就是保衛解構主義,因為解構主義也是要批判,對現實和可能性給予永不停息的質疑”[4]。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德里達以“幽靈學”的邏輯將馬克思主義與解構主義結合起來,認為只有將馬克思主義幽靈化才是拯救馬克思主義的唯一途徑,并且在解構的過程中過濾掉了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許多至關重要的理論內容。因此,德里達所要繼承的馬克思的遺產與我們所要繼承的馬克思的遺產具有很大的區別,幽靈化的馬克思主義已經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
三、德里達繼承馬克思批判精神的當代價值
德里達在“幽靈學”解構邏輯的基礎之上,結合關于馬克思主義的解構式閱讀,對其主張繼承馬克思批判精神的觀點以及繼承馬克思批判精神的方法作了詳細的闡述,彰顯了馬克思主義強大的生命力,特別是馬克思批判精神的重要地位和價值。
(一)正確認識當代資本主義世界的思想工具
德里達對馬克思主義的重新解讀是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潮、馬克思主義面臨重大挫折的特殊歷史時期展開的,其中蘊含著他對于當代資本主義現實狀況的深刻批判。德里達對發達工業社會的批判既是其解構邏輯之上的馬克思的“幽靈”出場的時代背景,又是其解構精神與馬克思批判精神的契合之處,是德里達對馬克思批判精神的一種致敬。在《馬克思的幽靈》中,德里達深刻分析并批判了當代發達工業社會的各種不合理現象與問題,為我們今天正確認識當代資本主義世界提供了重要啟示。
發達工業社會聲稱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理想已經破滅,而資本主義社會依舊呈現出充滿自由與正義的一派繁榮景象。德里達卻敏銳地發現,這種繁榮只是一種表象,而隱藏在其背后的貧乏單調的日常生活秩序、現實世界的不公與黑暗的深刻危機才是發達工業社會的真實景觀。他指出,這樣的時代是“脫節的時代”,“這個世界出毛病了”[1]。德里達認識到,在全球化的世界背景和工具理性的時代之下,人類并沒有在工業社會的全球化運動中走向富足美好的理想社會,反而陷入了資本引發的種種危機與災難之中。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是消費社會,資本通過消費實現增值,而工具理性的時代下消費活動呈現為符號編碼式的虛擬化形式,由此進一步刺激了消費,擴張了資本,過度的物質消費也導致了人精神的缺失,資本主義社會的“繁榮”不過是消費的異化和人性的扭曲。因此,德里達強調正是在這樣一個脫節的時代,召喚馬克思的“幽靈”才顯得尤為迫切,必須在它的指引下繼續采用并發展馬克思的資本批判。
德里達還指出,資本令社會高度集約化,它通過生產實現對人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控制,資本的控制不僅表現在經濟、政治領域之中,更延伸至意識形態、思想觀念等領域。歷史終結論者們宣稱集體主義式的暴力與專制的意識形態已經被自由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所取代,資本主義社會正在走向勝利,然而在德里達看來,資本主義社會并沒有勝利,而是正在衰敗。發達工業社會看似自由、正義與公平的面貌,實則是被資本掩蓋了的另一種形式的專制與暴力。資本的高速運行帶來的是人們被迫接受著鋪天蓋地的受資本利益驅動的虛假宣傳,符號化的消費社會所制造的需求并不是人的真實需求,它所激發的消費欲望已經與人本身發生分離。高度發達的科學技術帶來的不僅是人類自然限制的解放,還有人類思想觀念的一次次被顛覆,人類的思想觀念看似不斷更新與進步,實則只是資本與利益操控下的一次次迷失。德里達正是在這樣的現實批判中凸顯了繼承馬克思批判精神遺產的重要意義。
對社會現實的批判是馬克思批判精神的內在要求。在德里達對發達工業社會現實的深刻批判中,我們不難發現,德里達所指出的發達工業社會中的許多問題與危機,在當代資本主義世界中依然存在。因此,雖然德里達的資本主義批判更多地是一種理論批判,其目的是為了闡述他對于未來的“新國際”構想,他對于馬克思批判精神的繼承也拋棄了馬克思實踐的品格,但德里達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現實問題的深刻揭露與批判,他堅持呼吁繼承馬克思批判精神的觀點,依然能夠幫助我們今天正確地認識當代資本主義世界,進而與時俱進地豐富與發展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批判理論。
(二)為推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提供重要啟示
德里達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潮、馬克思主義遭受質疑的時代條件下走近馬克思,一方面是在將解構主義與馬克思批判精神相結合的基礎之上,通過批判當代發達工業社會的現實問題,提出建構“新國際”的未來構想并進一步豐富和發展其解構主義理論,另一方面,德里達也想喚起人們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反思。在德里達看來,馬克思和他的繼承者們以充滿正義與美好的共產主義理想社會為目標,最終卻孕育出了高度個人集權制的斯大林模式,這值得人們深思。因此,德里達呼吁人們反復閱讀和討論馬克思主義,隨時代的發展不斷反思社會現實,在歷史的困境中繼續尋求馬克思主義的幫助,在向馬克思的回歸與致敬中繼續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這為我們推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啟示。
德里達強調了馬克思批判精神的重要地位和價值,也肯定了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不斷創新的理論品質。但作為當代真正的馬克思精神的繼承者,我們絕對不能拋棄的是馬克思主義實踐的品格。因此,在合理借鑒德里達繼承馬克思批判精神觀點的基礎之上,為進一步推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更好繼承馬克思的批判精神,我們必須要立足于當下新時代的現實,與時俱進地促進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
馬克思主義只有在創新中才能緊跟時代步伐,始終保持活力并發揮強大的生命力。推進馬克思主義的時代化,既是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內在要求,也是當代中國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然要求。馬克思主義理論形態在歷史發展進程中一直呈現著鮮明的時代特色,馬克思主義在與各個時代的具體情況相結合的過程中不斷豐富,不斷發展出符合時代條件的新的理論。馬克思曾指出,時代的問題也同其他所有合理的問題一樣,“主要的困難不是答案,而是問題”,批判的重點也應當是問題[5],所以只有在對時代問題的不斷批判與否定中才能實現馬克思主義的時代創新。更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不僅是一種批判理論,更是一種改造世界的運動,馬克思主義時代化也是一個從繼承到創新的社會實踐活動。因此,馬克思的批判精神只有在實踐基礎上才能推動創新,只有在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中才能促進馬克思主義的時代化發展。
新時代,我們要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是兼顧各國現代化共同特征與鮮明的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因此,我們必須緊跟時代前進的步伐,結合實踐活動中新的問題與挑戰,繼承以實踐為基礎的馬克思的批判精神,在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統一中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建設,以新時代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引領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前進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