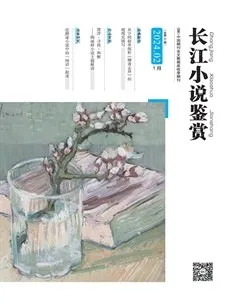重章疊句,一唱三嘆
葉芳
[摘? 要] 《秋天的懷念》是當代散文家史鐵生的名篇,歷年來讀者對其細膩動人的刻畫、質樸凝練的語言、真摯深沉的母愛和睿智的人生思考贊許有加,卻往往忽視了隱藏在故事和細節背后的反復藝術。無論是情節的建構、人物的刻畫、細節的呼應還是詞語的運用,反復藝術無處不在,正是這種多重反復藝術的巧妙運用,將母親的愛和作者的懷念沉淀成意蘊深長的歌,讓文章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關鍵詞] 反復? 重章? 錯位? 留白 見微知情
[中圖分類號] I106? ? ? ?[文獻標識碼] A? ? ?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02-0121-04
史鐵生是當代著名作家,也是一名特殊的作家。錢理群先生對其評價:“他是一個真正的作家,一個用生命寫作的人。”他將自己有限并且殘缺的生命與無限的人類生命相結合,以獨特的視角和深沉的情感,探討深刻的人生和宇宙的哲學問題,創作了《我與地壇》《務虛筆記》《病隙碎筆》等廣為傳頌的作品。其實對于生命的理解,史鐵生也曾迷惘過,尤其是在他21歲因病癱瘓時,曾經忍受不了生命的厄運而三次試圖結束自己的生命。在這段令史鐵生痛不欲生的日子里,他的母親用自己最真摯而樸實的愛和堅忍不拔的精神引領史鐵生走出了人生的苦難,完成了生命的重大轉折,從而也鑄就一篇感人至深的散文小品——《秋天的懷念》。
《秋天的懷念》最初發表在1981年廣州的《南風報》上,篇幅不長,只有800余字,語言簡練質樸,筆墨細膩深沉。如果說更受大家關注的長篇哲思抒情散文《我與地壇》是一條波瀾壯闊、奔騰不息的大河,那么《秋天的懷念》如同一汪澄澈而深邃的清泉,流淌吟唱著人間至真至純至善的親情小調。讀者(在閱讀這篇散文時)往往會沉浸在被母愛的感動和對細膩而質樸的語言地品味之中。但是,如果過度關注細節的刻畫容易讓人物形象支離破碎,如果只關注文章語言的質樸雋永又會讓人忽視文章的謀篇布局,從而缺乏對文章架構的整體領悟以及其他表現手法的重視。例如文章所采用的“反復”藝術就被眾多讀者忽視。多重“反復”手法的獨特運用,使這篇散的建構更加精美,使人物形象在反復渲染中更加立體和鮮活,從而深化了文章真摯情感和深刻思想的表達,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
“反復”這種藝術表現手法源自《詩經》中的“重章疊句”。所謂“重章疊句”,指上下句或者上下段用相同的結構形式反復詠唱以更好地表情達意。在漫長的文化流傳與演變過程中,“重章疊句”這一概念通俗化,成為大家耳熟能詳的“反復”,并作為常見的藝術表現形式被文學創作者繼承和發展。
首先要明確:“反復”不等于簡單的重復,而是為了意旨的沉淀和深化。凌煥新先生在《微型小說藝術探微》中指出:“重復,是藝術上的大忌,特別是情節上的大段重復,往往標志著藝術上的單調和貧乏。然而,有意的重復,重復中顯出不重復,重復處見出作者獨特的藝術匠心,表現出異乎尋常的藝術魅力,則是藝術技巧的嫻熟與高超。”[1]《秋天的懷念》無論是在謀篇布局、人物刻畫還是細微的句子乃至詞語的表達,都巧妙地運用了“反復”這一藝術手段。
一、“重章”敘事,娓娓道來
《秋天的懷念》是一篇寫人記事的散文,它不是按照完整的時間脈絡來構建故事情節,而是采用《詩經》的“重章”(情節的反復)手法來構建文章,實現鏡頭“三重奏”。
正如《詩經》中名篇《關雎》《蒹葭》等作品反復選取男子追求女子的經典鏡頭一樣,《秋天的懷念》截取生活中的三個片段來進行構建,圍繞著“看花”二字來反復展開:“天上北歸的雁陣”時(春天),母親勸我去北海看花;“樹葉‘唰唰啦啦地飄落”時(秋天),母親勸我去北海看菊花;“又是秋天”時,我和妹妹去北海看菊花。三個情節不是單純的重復,它在時間上實現了跳躍,從第一年的春天跳到了秋天,然后跳到第二年秋天;它在人物上實現了轉換,前兩個情節是母親勸我去看花,第三個情節是我和妹妹去看花;它在結局上出現了變化,春天時母親勸我去看花沒有成功,秋天再次勸我時我答應了,可母親因病去世。這種同中有異的情節反復,構建了一位偉大母親用自己的愛使癱瘓的作者走出人生“癱瘓”的動人故事。閱讀這篇散文,我們的情感隨著作者構建的三個鏡頭不斷升華:作者癱瘓的痛苦讓我們憂慮憐憫,母親逝去的悲哀讓我們深切同情,“我”對母親的深切懷念讓我們感傷,執著的母愛扭轉人生的偉大力量讓我們嘆服……
《秋天的懷念》在情節上所采用的“重章”手法,串起了一段段生命的記憶,打破了傳統敘事結構的桎梏,使文章的節奏更加獨特,文中人物形象更加鮮明,文章的情感表達更加深切,對生命的思考更加厚重,從而使這篇文章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與讀者產生強烈的共鳴。
二、反復“錯位”,母愛無私
孫紹振先生的“錯位理論”認為:“藝術的感染力在于審美價值與科學認識和實用價值之間拉開距離,三者之間產生‘錯位,才能有審美情感的自由可言。”[2]《秋天的懷念》首先存在情感與理性的錯位。
從理性的角度來看,任何人面對自己身體的疾病都會予以足夠的關注,這屬于每個人的本能。母親重病纏身,卻完全不顧自己生命的“憔悴”,只是全身心投入到對兒子的照料和激勵之中,她的心里完全沒有自己,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只掛念著“那個有病的兒子和我那個還未成年的女兒”。在對待自己的疾病這一方面,母親情感與理性出現“錯位”,理性完全讓位于情感,而恰恰是這種“錯位”,塑造出一位母親忍痛前行、舍己愛子的光輝形象。
在對于人生的態度方面,母親和兒子都出現了情感與理性的“錯位”:兒子雖然癱瘓,但并未面臨生命的終結,可是兒子“狠命地捶打這兩條可恨的腿,喊著,‘我可活什么勁兒!”在兒子看來,雙腿殘廢就等于人生的終結,因為他失去了生的希望;母親呢,面對自己的不治之癥,卻說“咱娘兒倆在一塊兒,好好兒活,好好兒活……”在母親心中,不管生活有再多的磨難,只要娘兒倆在一起,他們就一定能“好好兒活”,因為她有面對苦難的堅韌。可仔細一想,這“好好兒活”四個字是針對自己嗎?完全不是,因為母親的心里只有孩子,只有千難萬難也要讓孩子“好好兒活”的人生信念,甚至孩子“好好兒活”才是她生命的終極意義,才是她能“好好兒活”的唯一標準。正是這種無堅不摧的信念和對“好好兒活”的獨有理解支撐著母親陪著孩子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也正是這種對人生苦難不屈的精神最終感染了史鐵生,讓史鐵生戰勝了人生的苦難,走出頹廢,活出了璀璨的人生。
正是因為情感與理性的“錯位”,也導致了母子身份的“錯位”。從中華民族傳統道德倫理上看,孩子本應是孝順尊重父母的,可是作者因為癱瘓而“暴怒無常”,甚至對母親病情的嚴重性一無所知。母親呢,沒有任何埋怨,只是小心翼翼地照料兒子。母親這時候的身份是非常卑微的,單單是第二次勸告兒子去看花時“臉上現出央求般的神色”一句中的“央求”二字就可見一斑,這種“錯位”的卑微更是讓人心疼而又充滿敬意。
多角度“錯位”手法的運用,凸顯了文中人物性格的多個方面,讓母親的形象更加立體,字里行間充斥著作者對母親深深的感念和對自己行為的懺悔,時刻調動了讀者的閱讀體驗,讓讀者對文章所表達的母愛和人生的思考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認識。
三、反復留白,隱顯相生
留白是中國藝術作品創作中常用的一種手法,指書畫藝術創作中為使整個作品畫面、章法更為協調精美而特意留下相應的空白,留有想象的空間。在文學創作中,留白也是一種常見的表現手法。讀者欣賞文學作品是以自己的人生體驗和情感為基礎的再創造過程,留白手法的運用給讀者提供了廣闊的想象和聯想的空間,能夠以“空白”為載體給讀者創造出更美的意境。
《秋天的懷念》中處處存在著留白。首先是故事情節的大片留白:文章截取的是第一年的春天、秋天和“又是一年秋天”三個時間節點,而對第一年的夏天、冬天和第二年的春夏兩季的故事進行了留白。查閱資料可以得知:北海公園養荷育荷的歷史悠久。從春天和秋天的兩次勸說兒子去看花的情節來推理,在夏天荷花盛開的時候,母親也一定有再次勸說兒子去看花的言行。作者為何不寫呢?因為一來容易有贅筆之嫌,二來更是為了留給讀者以想象的空間:不僅能讓讀者想象母親在夏天荷花盛開時再次勸我去看花的言行和我的回應,還能讓讀者想象母親悉心照料孩子的情景。而對于母親去世后的冬天到第二年夏天這一段時間的留白,客觀上是因為母親已經逝去,接下來就是作者直面人生“好好兒活”的故事。從相關資料來看:母親病危時,26歲史鐵生在母愛的激勵下,已經能堅強地面對生活。他不僅自己搖著輪椅四處尋藥同時還照看10歲的妹妹。這些故事在讀者閱讀了文章最后一段我和妹妹去北海看菊花的情節后也不難猜想出來。朱光潛先生認為“無窮之意達之以有盡之言,所以有許多意,盡在不言中。文學之所以美,不僅在有盡之言,而尤在無窮之意”[3]。一千個讀者就會想象出一千種劇情,這種劇情的留白既簡潔了文章,又激發了讀者綿綿無盡的想象和創造,給人以“無言之美”的感受。
其次,文章在細微之地也處處留白。“當一切恢復沉寂,她又悄悄地進來,眼邊紅紅的,看著我”一句中的“眼邊紅紅的”意味深長,我們可以由此猜想母親躲在外面偷聽兒子動靜的情景。俗話說:“痛在兒身,疼在娘心。”史鐵生在后來對母親的追憶中曾說過:“兒子的不幸在母親那兒總是要加倍的。”兒子雙腿癱瘓、痛苦壓抑在心里,母親何嘗不想痛哭一場,卻怕自己的哭聲被孩子聽到會更加刺激孩子,她或者選擇了輕輕啜泣,或者選擇了強忍淚水。這種全力壓制自己,全心呵護孩子的細節是多么令人震撼!“鄰居的小伙子背著我去看她的時候,她正艱難地呼吸著,像她那一生艱難的生活”中“她那一生艱難的生活”也語焉不詳,留給讀者去想象的空間和查閱相關資料的興趣。
省略號的運用是一種常見的留白方式,文中共有四處采用了省略號:
(1)母親撲過來抓住我的手,忍住哭聲說:“咱娘兒倆在一塊兒,好好兒活,好好兒活……”
(2)她也笑了,坐在我身邊,絮絮叨叨地說著:“看完菊花,咱們就去‘仿膳,你小時候最愛吃那兒的豌豆黃兒。還記得那回我帶你去北海嗎?你偏說那楊樹花是毛毛蟲,跑著,一腳踩扁一個……”
(3)她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話是:“我那個有病的兒子和我那個還未成年的女兒……”
(4)我倆在一塊兒,要好好兒活……
第一處省略了母親后面所說的話。母親當時一定有千萬句想安慰的話,但是面對兒子拼命捶打自己的雙腿時也不知道用什么樣的語言來表達,只能強忍哭聲重復“好好兒活”。讀者雖然不知道母親重復了多少次,但是這個省略號可以讓我們想象母親的悲痛欲絕和深深的無奈。第二處省略號是母親因說出“踩”字生怕觸起兒子內心的悲傷而戛然而止,這里包含了母親對過去與健康的兒子相處的點點滴滴美好時光的諸多追憶。然而就是這一點暫時美好的追憶也不能延展,因為一個詞的忌諱又回到殘酷的現實,讀起來是多么悲愴!第三處省略號也許是病危的母親沒有說完,也許是母親說了很多話作者沒有寫出來,但不管哪一種,都包含著母親對兒女無盡的牽掛。第四處省略號是我和妹妹去北海看菊花時想起了母親的話而對生活充滿了信心。這一省略號在文章結尾,可以讓讀者想象作者和他的妹妹如何按照母親的期待“好好兒活”的情景,使文章有“余音繞梁”的效果。
綜上可見,《秋天的懷念》的留白藝術可謂運用得登峰造極,無論是整體情節的布局,還是細微之處,乃至標點符號的運用,可謂胸中有丘壑,眼中有草木,不僅層次分明,而且因前后呼應而顯得渾然天成。
四、細節反復,見微知情
《秋天的懷念》成為經典,大家都認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文中的細節刻畫。其實更絕妙的是多次細節前后反復,反復之中又彼此呼應,如同一點點漣漪在靜謐的湖泊中泛開,然后又彼此交融,在交融中展現人間真情,創造了絕美的意境。
文中反復出現了“花”這個意象,分別出現在以下四處:
(1)“聽說北海的花兒都開了,我推著你去走走。”她總是這么說。
(2)母親喜歡花,可自從我的腿癱瘓后,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
(3)“北海的菊花開了,我推著你去看看吧。”
(4)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黃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潔,紫紅色的花熱烈而深沉,潑潑灑灑,秋風中正開得爛漫。
這四處“花”有所不同,第一處是北海春天開放的花,是母親希望孩子能走出房間,讓美麗的春光驅散兒子內心的悲傷。第二處是母親喜愛并侍弄的花都死了,這是因為母親全身心投入到對兒子的照料之中而完全拋棄了自己的愛好。第三處是北海的菊花,母親殷切地希望兒子去看看,隱藏著母親的心思:希望兒子能感受菊花傲霜的精神從而也能像菊花一樣堅強地面對生命的挑戰。這就與第四處我和妹妹去北海所看到的菊花熱烈爛漫開放形成呼應,暗示我理解了母親的期望,走出了人生的陰霾。仔細品味這四朵“花”,母親耗盡心力反復勸導孩子走出心理困境的執著是多么令人敬佩,而這份執著所產生的力量又是多么令人震撼!
再仔細研讀第一處和第三處的兩次勸解,我們會發現“北海的花兒都開了”前面有個“聽說”二字,而“北海的菊花開了”沒有。大概第一次母親是聽別人所說,也未必能完全確定;而第二次勸說卻如此肯定,也許母親是完全打聽清楚了甚至是親自前往過。這個細微的變化可以看出母親為了讓兒子走出心理的頹廢而時時關注并尋找最恰當的時機,這種無微不至的關懷是多么深沉。再比較后面的言語,第一次勸說中的“走走”在第二次勸說時變成了“看看”。這是為什么?因為“走”字是一種忌諱,“看”是更低的央求,后面還有個“吧”字,真是一字傳情,把母親字斟句酌的謹小慎微和苦苦央求的卑微展現得如此真切,每個讀者都會為之心痛不已。
文章中還有兩處容易被人忽視的細節:
(1)可我卻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經到了那步田地。
(2)我沒想到她已經病成那樣。看著三輪車遠去,也絕沒有想到那竟是永遠的訣別。
這兩處都是作者不知曉母親病情的“反復”。“一直都不知道”強調自始至終都不知曉,“沒想到”“也絕沒有想到”反復強調自己沒有任何預料,這三個短語的意思一層比一層更深,仔細揣摩,我們一方面能感受到作者寫這篇文章時內心無比的愧疚和自責,另一方面我們也能感到母親在孩子面前隱瞞自己病情的苦心和偉大。
文章中有一個詞反復出現了三次,更是一絕。
(1)母親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見的地方偷偷地聽著我的動靜。
(2)當一切恢復沉寂,她又悄悄地進來……
(3)她又悄悄地出去了。
母親“悄悄”地進來,又“悄悄”地出去,一切都是那么的小心翼翼。這種無聲的呵護更顯張力,深刻地表現了一位母親對孩子的精心呵護,正所謂“潤物細無聲”也莫過于此。
《秋天的懷念》是一篇愛的樂章,它沒有驚天動地的豪言壯語,只有最樸素的言與行的反復綻放,而正是這種多角度、多層次地反復積淀、反復醞釀,才讓這篇文章成為淡遠雋永的酒,永遠氤氳著母愛的醇香,成為流傳的經典。
參考文獻
[1] 凌煥新. 微型小說藝術探微[M].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
[2] 孫紹振.美的結構[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
[3] 朱光潛.朱光潛美學文集(第二卷)[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
(責任編輯 羅?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