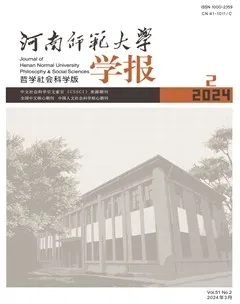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監獄經費芻議
DOI:10.16366/j.cnki.10002359.2024.02.16
摘要: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司法獨立為時代所倡導,人們圍繞監獄經費來源問題展開了爭論,人們期望監獄經費由中央政府統一撥付,但因為財政困難,這一愿望最終難以實現。就江蘇監獄而言,其經費主要來源于省財政劃撥,在江蘇省財政狀況持續惡劣的環境下,減折、拖欠發放成為常態。盡管地方司法部門積極采取了社會募捐、法收項下截留及監獄自身收入補貼等應急措施,但監獄經費拖欠發放及打折發放并未有較大改觀。地方負擔司法經費籌集,極易導致地方司法系統對于地方行政權力的依附,司法的公正獨立性受到嚴重消解。
關鍵詞:南京國民政府;江蘇;監獄;經費
作者簡介:李風華(1970—),男,河南固始人,歷史學博士,河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中華民國史、社會史、監獄史研究。
中圖分類號:K26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2359(2024)02011407收稿日期:20221228隨著史學研究者視野的下沉和史學研究的深入發展,近年來監獄史研究漸受學界重視。在此氛圍下,民國監獄史研究成果臘逐漸豐富,其中監獄經費問題也引起了不少學者的關注。但綜觀既有成果,學者們較多討論了司法經費短缺、經費由地方劃撥引起的司法腐敗及其之于司法改革的影響等內容,而對于司法獨立語境下各省監獄經費劃撥的實然狀況及其對監獄改良之影響層面則論之較少。鑒于此,筆者主要依據江蘇省檔案館所藏“民國江蘇高等法院檔案”材料,試圖對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江蘇監獄經費來源及劃撥實際狀況展開考察,借以管窺中國司法近代化發展歷程。
一、南京國民政府監獄經費政策體系
監獄作為國家暴力機關的一部分,對于維護社會秩序、保護國家既有政權統治具有重要的作用。因而,由國家財政提供經費以維持其正常運作,為近代較多國家所遵循之慣例。民國政府也認為監獄經費理應由國家統一編制預算,并由國庫按時足額劃撥。但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作為司法經費一部分的監獄經費,其來源及劃撥實態并非如此。
監獄作為司法系統的一個分支,其經費為司法經費中的一部分。司法經費往往涉及兩個方面,即政府部門撥付的經費和司法實踐中產生的司法收入經費(即“法收”)。一般而言,司法經費來源有兩個可供選擇的路徑。其一,各級司法部門的司法收入依法上繳,而其各種開支經費則由中央政府全數撥款,這常被稱為“收支兩條線”。“收支兩條線”的經費模式因收支涇渭分明,便于經費管理和監督而備受司法改良者和政府部門青睞。其二,沿襲清末以來形成的慣例,即從法收中截取一部分作為司法部門運轉經費。但是地方截留具體數額、使用明細等須先行上報司法最高管理部門,待其核定經費數額后,地方司法部門方可在法收項內截留,然后劃撥至各部門使用。這兩種方式,無論執行哪一種,皆以司法獨立于地方政府運行及司法權統一為前提。清季晚期司法改良已起步,其經費來源采用的是由法收中截留的方式。民國北京政府時期,各省司法經費一般歸地方開支。為了安撫地方政府情緒和減輕地方司法機構向地方政府索要經費的阻力,北京政府同時賦予地方行政長官監督司法之權力。到了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司法獨立得到政府和社會的進一步認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表現為,在政府行政體系的構建上,實現了由中央司法行政部門到各省高等法院直至基層司法部門的系統垂直,且取消了北京政府時期關于“地方政府長官監督司法之權”的規定,賦予了省級司法部門獨立于地方政府職責之外的權力。但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之后,國家真正大一統的局面在短期內并未得以實現,加之中央財力的薄弱,政府只得頒行“劃分國家支出、地方支出標準案”,祭出“在承審制度未廢止之前,地方司法經費,暫由地方經費內支出”的政策。但是,關于包括監獄經費在內的司法經費當屬中央財政撥付的呼聲,一直在司法部門和國民黨中央政府之間傳遞,并經歷了一段時間的爭論。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初始,關于地方司法經費來源問題,亟欲變革北京政府的做法,提出地方司法經費例由國庫開支者,均要列入各省預算。為此,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在各省增設司法廳機構,并規定司法廳廳長由省政府派員兼任,參與省級財政預算。新的司法行政機構的設立,顯然有利于各地司法經費的落實。但由省政府派員兼任司法廳廳長的舉措,顯然與“司法獨立”之精神相悖,于是不久南京國民政府旋又裁撤司法廳建制,改為省級司法行政權歸各省高等法院管轄,以將司法職能與權力獨立于省政府之外,監獄管理則依舊遵循民國北京政府時期“委托法院監督”舊例。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司法機構得以垂直,司法權力得以“獨立”,但司法經費卻依然按既定“暫由地方經費內支出”的方針行事。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地方司法經費撥付出現問題。且各省經濟狀況不同,能夠提供給該省包括監獄在內司法部門經費的能力各異,導致了各地司法改良和監所事業發展的不平衡,故而質疑司法經費由地方財政負擔的政策,呼吁變革既有制度,改歸中央政府統一劃撥的呼聲日漸強烈。
各省司法部門要求變革司法經費定制的呼聲此起彼伏,其中江蘇省的聲音尤為響亮。1927年10月,江蘇司法廳根據南京國民政府擬定成立五院制方案,認為“現在司法既列于五權之一,行政上有其重要之任務,自應擴張經費”。并提出兩種操作途徑:“(一)司法經費應確定為全省政費之重要支出,除固有之經常費外,應按期依照所需之額數增加之;(二)在司法廳可能范圍內整頓司法收入,以為補充。”江蘇省司法廳鑒于司法經費不足以維持司法實踐所需,提出了增加司法經費數額,部分借鑒晚清及北京政府時期以法收補助的舊制。1928年,江蘇省政府更是向國民政府提出“撥照軍政外交事例,將司法經費,概由中央支出之請”。
各省變革司法經費劃撥的呼吁引起了國民政府的重視,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回應。1928年6月,全國經濟會議議決司法經費“均由國家經費內支出”。翌月,全國財政會議繼而審查“寬定司法經費案報告書”,并議決“由財政部查酌辦理”。全國經濟會議的議決以及全國財政會議的“查酌辦理”,并未改變司法經費依然由地方政府支出的現實,且各省司法經費因無中央統一劃撥而日趨緊張的程度日漸加重,但是司法行政部對此卻無能為力。1929年司法行政部制定的司法改造計劃,雖然列出經費議題,卻并不存在中央撥款的奢望,甚至抱著所需經費“為數甚巨”,不太好提,又不得不提的心態。于是,該計劃曲折隱晦地表示出“指望各省自籌司法經費改組司法是不可能的”。
1930年,時任司法院院長的王寵惠在國民黨三屆三中全會上的法院工作報告中,宣讀了司法改革的十三項計劃,其中司法經費變革為其重要一項。“將改革主張直接提上國民黨三中全會,可見問題已十分嚴重”。王寵惠等司法部門上層也清楚中央政府的財政難處,感覺提出各地司法經費概由中央統一負擔的建議不合時宜。于是只能提出不切實際的解決司法經費的三種方法:第一,土地登記由法院辦理,即以登記收入擴充司法經費;第二,庚子賠款撥一部分;第三,增加訴訟費。
1934年5月,南京國民政府第二次財政會議召開,大會一度出現原則上應由國民政府中央負擔司法經費的動議。但國民黨中央在審視財政收支實際狀況及經過通盤籌劃之后,最終決議“各省司法收支原則上應歸中央,惟于中央財政未充裕以前,司法經費暫由地方負擔,其法收除印紙等工本費外,悉數歸地方,并由財政部與司法行政部會商辦理”。隨后的幾年,“盡管國家經濟狀況日漸好轉,但司法經費較之北洋政府時期僅有少量增加”,司法經費緊張的狀況一如既往,因而變革司法經費劃撥來源,期望由中央政府統一撥付的主張,依然被各省司法部門認為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所在。
1935年9月,南京國民政府召開第一次全國司法會議,司法經費再次成為熱門話題。湖南省高等法院院長徐聲金、首席檢察官曹瀛提議監獄經費應“擬照教育經費由中央支出、鹽稅項下撥發之例,所有各省新監獄經常費一律指由中央稅收機關按月撥付”。河北第一監獄典獄長吳峙沅也建議“監獄經費須仿教育經費成例,指定的款按月發放”。另外,福建、江西、山東等省參會的司法界人士亦都針對監獄經費改革提出了議案。由國庫統一劃撥監獄經費,是大多數與會代表一致的看法。最后大會做出了司法經費“改由國庫負擔”,“以所得稅、遺產稅及其他稅收款為撥付來源”等決議,但旋而又對此進行了否決,把“改由國庫負擔”修正為“各省所有一切司法經費,在國庫未完全負擔前,仍歸各省負擔”,且“國庫負擔應以所得稅、遺產稅及其他確定稅收之款為源,其細則由司法院與財政當局商定之”。修正案不提國庫負擔之責,而一味強調國庫未負擔前“各省負擔”的責任,且一定要有“確定稅收”為保障,說明盡管會議代表皆有司法經費從速實現由“國庫負擔”的愿望,最終卻連一個實行國庫負擔期限的議案也未形成,更遑論實際落實了。
此后,雖然司法經費依然由地方撥付的實際未有絲毫改變,但“司法經費應由國庫負擔”的呼聲卻并未停止,并在監獄、法院、司法行政部及南京國民政府的各種高級會議之間繼續喧囂、爭論與博弈。1939年2月,參政員周鯁生與其他21位參政員,在第三次國民參政會上再次將此話題提到南京國民政府的議案上。周鯁生等提議“改進司法之基本問題,首須由國庫負擔經費”,“各省司法經費,應與一般中央行政費視同一律,以改由國庫直接支給為原則”。該提案最終獲得大會通過。南京國民政府為了掌握地方“法收”款項以及探究其中真相,同時為了試圖扭轉當時十分嚴重的地方司法腐敗,加之迫于國內各界團體民主建國的輿論壓力,最終確立了自1940年始,在其所轄非戰區省份,如西北區域陜西、甘肅、西康、寧夏、青海等省和西南區域廣西、貴州、云南、四川等省份,其所屬法院、監所經費,除了原有收支外,概由國庫負擔。至此,司法部門夢寐以求、爭論已久的變革司法經費由地方負擔,改由國庫支出的期望終得以實現。而此時全國原有絕大部分監獄,連同其所處的大片國土已經淪陷,處于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鐵蹄蹂躪之下。
二、江蘇監獄經費來源
由上文可知,1940年之前,南京國民政府各省監獄經費事實上皆來自地方財政,江蘇省也不例外。江蘇省監獄經費實際來源,主要有地方政府劃撥、民間募集、法收和監所自身收入等四種路徑。
其一,地方政府劃撥。根據南京國民政府司法經費由地方負擔政策的指引,江蘇各監獄經費的來源主要由江蘇省政府負擔,而各監獄經費數額則由省高等法院核定。如1928年8月10日,江蘇高等法院核定江蘇第二監獄、第三監獄、第四監獄和第三監獄分暨高等法院看守所7月份監經費數量分別為4330元、2729元、1712元和2476元。
監獄經費由省高等法院直接核定,然后由省財政部門開具經費領取通知書,并指定該省各地政府部門或其下屬財政機關給予撥付。各監獄需派員持經費領取通知書,到省財政廳指定的機關辦理經費領取事宜。如1928年8月20日,江蘇第二監獄派員持7月份經費通知書,至太倉縣政府領取經費4330元。而該監八月份的經費,則于1928年9月9日由南匯縣政府領取。其后,江蘇司法廳應江蘇第二監獄請求,又咨商江蘇財政廳,要求嗣后該監經費改由寶山縣撥付《江蘇司法廳咨財政廳嗣后第二監獄經費請改指寶山縣撥付文》,王尹孚:《國民政府現行公文程式詳解》,上海法學編譯社,1930年,第11頁。。由此可見,監獄經費最終由各縣財政負擔,具體撥付單位由財政廳指定,且各監經費具體撥付單位不具確定性。
由地方政府負擔監所經費,其發放常受地方經濟形勢掣肘。作為刑罰執行部門的監獄,與政府其他職能部門相較具有較明顯的特殊性,因而為了保證其正常運轉,省政府特別強調“司法監獄等費按月必須發放”。但由于各縣面臨“行政費收不敷支,有每年虧短一、二萬至五、六萬元不等”的局面,因而監獄經費撥付“往往東挪西墊,借用各種專款應急,致引起無數糾紛”。同時,隸屬各級法院的看守所,其獄政經費也由地方政府負擔,但與監獄不同的是,看守所經費常由其所在地方政府財政撥出。如1932年5月,上海地院看守所、吳縣地院看守所、無錫縣院看守所、武進縣院看守所、南通縣院看守所、江都分院看守所經費皆由其各自所在地地方政府撥付。
其二,民間募集。正常情況之下,江蘇監獄經費主要來源于政府部門的劃撥。但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長時期持續的戰亂時局制約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破壞著社會的穩定性,導致各地政府財政收入并不理想。因而,財政狀況日益艱難的地方政府往往不能按時、足額撥付監獄經費。因而,為了維系監獄日常運轉和獄政改良,借助政府以外的社會力量來彌補監獄經費不足,已為客觀必須。
鑒于此,1929年前后,各省紛紛相繼出臺《捐款改良監所獎勵暫行章程》。江蘇高等法院也擬定《江蘇省捐款修建監所獎勵暫行章程》,并經司法行政部批示通過。該章程內容共有七條,其重點聚焦于給予捐款者及組織募捐者同等榮譽及嘉獎的詳細規定。由此可見,社會募捐已成為江蘇籌集監所經費的重要渠道之一。該章程頒布不久,江蘇高等法院即通過第5543號、6427號訓令,通令全省施行,并要求江蘇省民政廳和各縣商會協助辦理。但江蘇各地對此反應不一。1930年初,江蘇高等法院總結說:“現據各縣呈報,有已組織募捐委員會及正在組織者;有已擬有整個修建計劃者;亦有呈俟冬防后舉辦者;而未報各縣及已報而未積極進行者尚多。”針對這樣局面,江蘇高院不得不“再令催仰即遵照迭次訓令,克日召集各法團暨承審員、管獄人員依照本院前訂募捐等級,克日組織募捐委員會”。
為了監獄改良順利推進,多方籌資和妥善管理經費已為時需。為此,江蘇高等法院推行了一項《募捐修監管理辦法》,要求各地將所募款項按月匯報。
其三,法收。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各地監獄雖名為歸屬司法行政部下屬監獄科統一管理,但又明確規定各省監獄由各省高等法院代為監督。因為有此責任,所以各省高等法院針對監獄經費短缺局面,為了維持所轄各監獄的正常運行,常常在法院收入經費中抽取一部分為監獄所用。
各級法院法收項目主要為民狀費、審判費、執行費、民事抄錄費、登記費、罰金、印紙費等,這些法收項目收入較為可觀。如,鎮江地方法院“每月約收審判費一千余元,掛號費三四元,執行費十數元,鈔錄費一百五六十元,送達費五十余元,非訟事件費八九元,登記費二三十元,罰金五六百元,民刑狀費三百余元,由二十年七月至本年四月,共收法收二萬二千余元”。面對日益嚴峻的監所經費短缺狀況,江蘇省高等法院劃撥部分法院法收款項以維系監獄運行,雖屬無奈之舉,但漸為常態。
由于各級法院自身經費也常常不敷,為了維系監所運營和繼續推動監獄改良,于是地方政府以法院增加訟費、訟狀印紙費,以及變通運用所收罰金,甚至以增加法收額度等方式為監獄提供經費。如1929年,江蘇高等法院致函司法行政部監獄司,擬在鎮江另建能容一千人的新監,其建設經費來源就是增加訟狀印紙費,“將民刑各種狀紙一律加價五成。預計年可收銀六萬元,備作改建舊監基金”。又如1932年11月24日,司法行政部為改良江蘇監獄,決定加征訴訟狀紙費用,“司法行政部監獄司長王新之視察句容、六合、江浦等縣監獄狀況后,擬對江蘇全省監獄加以改良,并提出的籌集改良監獄經費及改良步驟的指導意見:于江蘇訴訟狀紙項下加收改良監獄費五成,預計每年可收五萬元左右,先將高淳、溧水、句容、六合、江浦五縣監獄著手改良。第二年收入,再改良其他縣監”。再如1934年11月23日,司法行政部訓令江蘇省高等法院籌備銅山縣監獄建設經費,其地價及第一期建設費,擬從江蘇高等法院1939年度預算所列的睢寧、宿遷兩縣建筑以及設備費三萬元內挪用。此后每年再加征五成“狀價”項下撥支二萬元,列入預算,至1937年該監建完為止。
其四,監所自身收入的補充。作為刑罰執行機構,監獄自身也有部分收入,這些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舒緩經費緊張的措施之一。各監獄自身收入項,主要體現在監獄作業收入金上。
為了管理好監獄作業收入金,司法行政部制定了嚴格的收入金使用規范。按照法律規定,監所作業勞役收入“概歸國庫”,除賞與金可從中劃撥外,監獄其他開支不得挪用作業收益。為了避免作業收入挪用,《監獄作業規則》特別強調“作業費應與經常費劃清界限”。但是面對經費的緊張局面,挪用作業收入為他用,成為當時各省監獄解決燃眉之急的普遍做法,江蘇亦不例外。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江蘇監獄作業成績較為突出,收入也較為可觀。如1936年,江蘇第一監獄9月作業收入達7000余元,是年江蘇第二監獄10月作業收入甚至超過萬元。監獄經費持續緊張,挪用作業收入補充監獄經費的缺口,已成為江蘇各監獄維系自身運轉的無奈之舉。如無錫縣監獄,1933年9、10月“作業盈余項下,每月補助分駐所經費六十元外,及歷年撥修工場房屋及添建瞭望臺等經費,現已沒有積存”。以作業收入補充監所經費,在江蘇各新監獄中亦為常見。據檔案資料,江蘇第三監獄于1930年第7、9、10、11四個月份的監獄作業開支中,除了作業“材料及雜支”“賞與金”兩項為符合監獄法規的必須開支外,均包含“辦公費及工資”和“撥補經常費”兩項,而且四個月內后兩項款額平均占作業全部開支比例高達22%左右。江蘇第三監獄的相關做法并非個案,江蘇其他新監也常采用同樣的手段。以作業收入補貼監獄經費已成常態、慣例,成為補充監所經費來源的又一個渠道。
另外,除了以上四種途徑,江蘇地處南京國民政府首府之地這種得天獨厚的政治地理優勢,有時也會為其監獄建設帶來額外的經費劃撥“驚喜”。如1932年,因王元增司長就近視察江蘇地方舊監,溧水、高淳二縣就能得到中央財政贊助“三分之二”的舊監改良經費。此等“福利”,或江蘇僅有,或江蘇較多。這是江蘇省所獨有的政治地理優勢的體現。
綜上可知,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江蘇監所經費的來源,主要有政府撥付、社會募捐、法收補助及作業補充四個方面。但是,隨著日本對中國侵略的日益嚴重,國內政治、經濟形勢日趨惡化,監獄經費來源日漸減少,到了全面抗戰爆發前后,江蘇較多監所經費僅靠地方政府財政廳撥付和法收補助進行維系。
三、江蘇監獄經費發放實態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之后,由于長期戰亂、地方勢力分割、官僚資本對社會經濟侵蝕等因素疊加,導致舉國長期政治不穩、經濟蕭條、社會動蕩。這不僅加重了國民政府中央財政困難,同時嚴重影響了包括江蘇省在內各地方財政的收支。江蘇省政府財政常態化拮據,引發政府各機構經費跟著緊張,監所也不能幸免,經費發放異常困難。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初期,江蘇省新舊各監所經費撥發還較平穩,但好景不長,時隔幾年之后,形勢越來越糟。特別是20世紀30年代以后,經費減折發放,拖欠發放,甚而減折后依然拖欠發放的事情,在江蘇各監所中時常發生,且漸為常態。
其一,減折發放。1932年6月9日,江蘇第二監獄呈文江蘇高等法院:“案查蘇省核減政費一案,司法部分前由本院通盤籌劃,將各級法院及各縣兼理司法經費一律按八折核減;監所經費除囚糧、薪餉、雜費循舊支給外,其余薦委俸給亦照八折減支開單,送請江蘇省政府查照轉行財政廳按數核發在案,所有該減核減后,實發經費數目合予摘錄令知,仰即遵照此令。”由上文可知,司法經費“八折”核減發放,主要針對“各級法院及各縣兼理司法經費”,監獄經費當然位于減折之列。不過監獄方面,減折發放多集中于“薦委俸給”,而監所經費中如囚糧、雜費及一般監所管理職員的薪餉則“循舊支給”。1932年,江蘇第二監獄“減折”后經費發放實況為:“經費省庫原系月發五千一百五十四元,核減后將薦任長官一員月俸二百元,委任長官三員月各八十元,委任待遇官二員月各五十元,合計月俸五百四十元。按八折減除一百八元,實發五千四十六元。”
在各級法院經費減折的同時,其所屬看守所的經費當然也會減折發放。如1932年5月,吳縣地方法院看守所接到江蘇高等法院根據該院第九八四三號令而核發“減折經費支付命令一紙”,領取了減折后的該年4月份經費“計銀壹千肆百肆拾陸元”,該所是年5月份經費依然保持減折后的4月份的額度。
其二,拖欠發放。隨著國民黨政府加強維護其獨裁統治投入的增加,特別是其企圖消滅國內革命力量而發起的軍事行動的擴大,中央財政已負擔不起龐大的軍事費用。于是國民政府要求各省分擔軍費支出,致使原本緊張的各省地方政府財政更為舉步維艱,監獄經費撥付自然更為艱難。同時,各監所犯人數量不斷攀升,監所經費需求增加與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下滑的逆向落差日益擴大,最終監所經費開始拖欠發放,有些省份甚至面臨斷供局面。20世紀30年代以后,江蘇監所經費拖欠發放日趨嚴重。如1932年4月,江蘇省財政廳致函江蘇高等法院,提出江蘇第三監獄分監三月份經費只能先行撥給2500元。5月4日,江蘇省財政廳又通過決議,補發該監三月份經費1628元,并要求由吳縣財政局劃撥。但是最終該監并未從吳縣順利領到此筆經費。
位于國民政府首府南京的江蘇第一監獄,其經費拖欠發放也十分嚴重。1932年,該監“每月經費共五千五百二十四元”,而至是年5月卻“積欠二萬三千余元”,維持監獄運轉“全仗部院墊借”。江蘇第一監獄作為模范監獄,且地處顯要之地,其監獄經費積欠多達四個月之久,“全仗部院墊借”的日子十分艱難。當然,亦有個別監獄經費能夠如期足額發放,如同期鎮江監獄經費“每月經費七百十九元”,經費發放“當不拖欠”。
江蘇各級法院及其看守所經費積欠也十分嚴重。1932年開始,各縣地方法院經費劃撥出現斷裂。如鎮江地方法院至1932年5月22日,共計“積欠一萬九千余元”,積欠金額相當于該院四個月經費的總和。江寧地方法院看守所至1932年經費積欠已達“一萬四千元”,其日常運轉所需只能由“法院設法移墊”。
因經費拖欠發放,監獄為了維系運轉,只能向司法行政部或省高等法院借款生存。如1932年11月,江蘇第一監獄因該監經費“財廳懸欠恒在二個月左右,計款則達壹萬七千余元”,以致“所有每日千余人犯之囚糧及緊急開支,純系東挪西湊,勉為支撐”,且“瞬交冬令,囚人棉衣被、看守制服急待添置”,該監典獄長鈕傅錡在是年2月至4月已向高院借入囚糧款1309.65元及作業基金3000元的情況下,再次致函江蘇高院院長林彪“肯乞撥借三千元,俾資救濟”。但由于高院自身經費也十分緊張,在收到第一監獄請援呈文半月之后,最終只“應準酌借壹千元,以資維持”。
江蘇監獄經費積欠并非一時一地之問題,而是漸為常態。如1935年,江蘇各新監獄依舊靠借款維系運轉。至是年3月,江蘇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監獄、第三監獄分監、監獄臨時收容所及高等法院分院收容所曾向高院分別借維持費17500元、7100元、5500元、3300元、10500元、4300元和1000元。另外一監、二監、三監、三監分監及收容所又曾借作業基金分別為3000元、2000元、1400元、1000元和400元。以上借款,各監至是年3月皆未歸還。
結語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其政權建設和法制建設是依據孫中山的“權能分治”“五權憲法”“建國三時期”等理論展開的。孫中山的“權能分治”說認為,“政權”和“治權”組成了國家權力的兩個部分。其中治權為政府的權力,它包括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項權力,這五項權力由政府五個獨立的機構分別行使。司法制度若欲得到獨立高效運行,司法經費的充足和統一則為前提和保障。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戰亂不斷,國民黨當局不僅要面對軍閥內部的混戰和國內土地革命戰爭,而且還需應對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這就導致國民政府不僅財力有限,而且有限的財力主要集中于軍事之撥付,因而司法經費長期嚴重不足。其時,即使為司法高級部門,如司法院下屬司法行政部、最高法院及行政法院等機構,維持其運營的辦公費用亦必須完全依賴司法行政部的“法收”解決王用賓:《司法會議后本部之責任》,《現代司法》,1935年第1卷第2期。。分布于各省內的地方司法機構,其經費來源和劃撥只能如江蘇監獄經費一樣,延續民初以來司法經費由地方負責的舊制。
地方負擔司法經費籌集政策的弊端是顯而易見的。首先,由于各省地方財政收入普遍不能滿足支出所需,司法經費拖延發放、縮減發放漸為常態。其次,長期截留地方司法部門“法收”項下資金為司法經費,極易導致“監獄、法院等部門更為腐敗”。最后,司法經費由地方提供,極易導致地方司法系統對于地方行政權力的依附,司法的公正獨立性受到嚴重消解。在這樣的經費撥付環境下,地方司法機關“在財政上依賴地方政府”,必然會“失其獨立與權威”。。由此可見,通過經費發放的制約,各省地方政府牽制、削弱、消解了地方司法機關的部分獨立性,阻礙了監獄改良步伐,遲滯了中國司法近代化的進程。
[責任編校解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