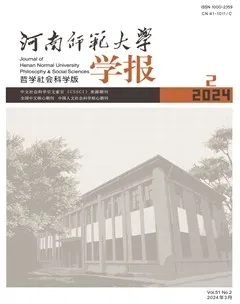古典詩歌中“河清”意象的內(nèi)涵累積及文化意義
王立 胡全章
DOI:10.16366/j.cnki.10002359.2024.02.17
摘要:黃河澄清是一種自然現(xiàn)象,在古代多被賦予人文意蘊,形成中國古典詩歌中的“河清”意象。先秦至唐,“河清”被賦予情感表達與政治祥瑞兩種意涵。唐以后,意象疊加的形式使“河清”彰顯古人的生存智慧,推動河流文學書寫的發(fā)展。宋以來,“河清”進入河患書寫,開始具有黃河安瀾之意,其文學功用被進一步放大,以人文關(guān)懷實現(xiàn)心靈療救,以批判精神指刺時弊。在清末民初思想轉(zhuǎn)型中,“河清”的祥瑞意涵得以重構(gòu),展現(xiàn)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清遺民詩人筆下的“河清”也體現(xiàn)出該意象的復雜性與多義性。“河清”意象的內(nèi)涵累積,不僅豐富著古典詩歌表達,反映古典文學中民族意象的演進機制,更成為啟迪現(xiàn)代社會的重要民族文化基因。
關(guān)鍵詞:河清;內(nèi)涵累積;祥瑞;河患;民族意象
作者簡介:王立(1993—),女,河南遂平人,文學博士,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xù)發(fā)展研究中心博士后,主要從事元明清文學研究;胡全章(1969—),男,河南鹿邑人,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xù)發(fā)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近代文學研究。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22JJD750022);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青年項目(2022CWX038)
中圖分類號:I207.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2359(2024)02012109收稿日期:20230621
黃河向有“濁河”之稱,《后漢書·溝洫志》載“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但在詩歌中,時見“河清”書寫,且多被賦予人文意蘊,不僅拓展了詩歌的表達空間與審美意蘊,而且形成了其對于民族精神的建構(gòu)。目前,“河清”意象尚未得到學界充分關(guān)注,研究大多只提及“河清”具有祥瑞內(nèi)涵,其實作為民族特色的文學意象,“河清”并非只有單一意涵,而是在逐漸生成與發(fā)展的過程中,被賦予了豐富的內(nèi)涵。故而,本文將“河清”意象置于動態(tài)的古典詩歌演進中,在探討自然黃河、人文黃河與中國文學淵源關(guān)系基礎上,揭示“河清”具有的多重意涵及文化意義,也為探討中國文學中民族意象的生成與演變提供一個研究視角。
一、雙線生成:作為情感表達與政治祥瑞的“河清”
先秦以后,“河清”從自然現(xiàn)象轉(zhuǎn)化為文學意象,與中國的水文化密切相關(guān)。水是萬物之源,中國文化中就具有“水原”思維與“水鏡”玄鑒等意識,促進了民族“尚清”思想的產(chǎn)生,正是在這樣的契機中,黃河偶爾變清的現(xiàn)象得到了文化層面上的關(guān)注。唐及唐以前的社會從“河清”承載的情感表達與政治祥瑞兩方面論起,也由此奠定了“河清”意象的兩種文學闡釋方向。
“河清”是詩人情感表達的重要載體,承載著他們的人生況味與處世心態(tài)。中國歷史上關(guān)于黃河澄清的記載有六十余次,這在歷史長河中寥寥可數(shù),但對于壽命有限的個體而言,終其一生也未必得見,是故《拾遺記》云:“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這種難以實現(xiàn)的事件為詩人提供了新的創(chuàng)作思路,《左傳》中“襄公八年”記載了最早出現(xiàn)“河清”的詩歌:“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以河清之難見對比生命的有限。后世詩人將這種自然的不可抗拒與自身的渺小形成鮮明對比,由此營造出情感落差的闡釋空間,用來表達他們的生命哲學理念。
“河清”意象應用于社會人生的表達,通過比興手法得到了極大的擴展。詩人對“河清”的解讀與中國文化對水的理解一脈相承,“流水每每被中國古人用來聯(lián)想與表現(xiàn)時間、機緣、功業(yè)乃至年華、生命的不可復返性,使人在懷古悼今、懷舊自傷中,生發(fā)出對生命、愛情、事業(yè)等價值追求及其不如意的無限感嘆”。故而詩人也以“河清”表達他們在紛繁世事中的復雜情緒。詩人常采用比興手法,先列出黃河澄清的現(xiàn)象,以其難見作為標準,后引出他們所經(jīng)歷與思考的社會百態(tài),囊括萬千。東漢趙壹《刺世疾邪詩》說明生命有限:“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唐代白居易《潛別離》則是感慨比河清更難實現(xiàn)的是永不分離的愛情:“河水雖濁有清日,烏頭雖黑有白時。惟有潛離與暗別,彼此甘心無后期。”孟郊的落第詩《寄張籍》以天上銀河清朗對比地下黃河渾濁:“清漢徒自朗,濁河終無澄。”孟郊以黃河經(jīng)年不可更改污濁的特征,對比自己在當下的落第遭遇。當“河清”依托于比興手法出現(xiàn)在詩歌中時,這種婉轉(zhuǎn)表達不僅豐富了詩歌的情感層次,而且基于黃河難清已經(jīng)作為常識被普遍接受,詩人將其引入與其他事物的對比中,消解了讀者對作品的陌生感,“使讀者能夠?qū)υ姼柚懈邪l(fā)之生命有所體會和認知”,比興也成為“河清”意象可資借鑒的書寫范式。
“河清”意象具有政治祥瑞內(nèi)涵,這是其獨特之處。在古代,異象常因無法解釋而被賦予超自然的神秘色彩,故而“河清”在尚清意識影響下有了升平之意,《易緯·乾鑿度下》中提到:“天之將降嘉瑞應,河水清三日。”雖然同時出現(xiàn)了災異說法,如《后漢書》就記載襄楷認為“河清”是不祥的:“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但官方在維護統(tǒng)治的基礎上大力推崇“河清”,“河清”代表政治清明、國泰民安的觀念始終占據(jù)主流,詩人也以之為基本立場,傳達他們對時代政統(tǒng)與文化精神的體認。
魏晉南北朝是“河清”作為政治祥瑞意象的定型時期。先秦兩漢時期,張衡《歸田賦》的“徒臨川以羨魚,俟河清乎未期”,以“河清”代指清明之世,但此期并未形成“河清”祥瑞文學的書寫氣候。在魏晉南北朝,因戰(zhàn)禍連綿、政權(quán)更迭,統(tǒng)治者頗為重視祥瑞現(xiàn)象,將之作為神功圣化與受命于天的標志,以維護統(tǒng)治政權(quán),“河清”具有的祥瑞意義被普遍接受。沈約撰《宋書》就首設《符瑞志》,所列歷代祥瑞之一就有河清現(xiàn)象,書中記載元嘉二十四年(447)“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美瑞”,并稱贊鮑照因此創(chuàng)作的《河清頌》“其序甚工”。到了北齊太寧元年(561),武成帝就因青州地界黃河部分河段澄清,次年改元“河清”以求吉祥。
此期重視“河清”祥瑞的文化風氣極大地推動了相關(guān)詩歌的創(chuàng)作。但詩人并非基于河清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才進行創(chuàng)作,而是在應制詩中自覺使用“河清”的祥瑞意義,強調(diào)王朝統(tǒng)治的正統(tǒng)性。齊梁時期“竟陵八友”的應制詩即是如此,他們以“河清”為蕭梁政權(quán)頌德,王融受竟陵王之命作《齊明王歌辭》,其六《長歌引》云:“紫煙四時合,黃河萬里清。”描繪永明時期“百姓無雞鳴犬吠之警,都邑之盛”的景象。沈約應梁武帝之詔作《華山館為國家營功德》:“丹方緘洞府,河清時一傳。”有著裝點王朝太平盛世的用意。任昉《九日侍宴樂游苑》疊加“河清”與“溫洛”兩種祥瑞意象,認為正是梁武帝有圣德偉業(yè),才使“時來濁河變,瑞起溫洛清”。魏晉南北朝的亂世局面促使詩人格外珍視和平歲月,雖是出于應制目的而使用“河清”意象,卻也是他們對時代深沉美好的祝愿。
在唐代,“河清”進一步彰顯盛世氣度與功業(yè)理想。唐代官方將“河清”認定為祥瑞,《舊唐書》記載貞觀十四年(640)“景云見,河水清”,大臣也紛紛上表祥瑞,有長孫無忌的《賀河清表》、張文收的《景云河清歌》等,唐太宗作《答長孫無忌等上河清表詔》回復群臣,并借此契機表露對王朝盛世的自豪,宣揚功績:“乃天地表祥,宗社垂祐,欲使四海隆平,八荒褆福。”
唐代詩歌中采用“河清”表達祥瑞,但因統(tǒng)一王朝推涌著詩人的事功之心,他們以“河清”贊譽時代,強調(diào)當下正是施展才華抱負、積極入世的絕佳機會。初盛唐時期,張說《東都酺宴》以東都洛陽的繁華引入:“喜氣連云閣,歡呼動洛城。人間知幾代,今日見河清。”詩中洋溢著對玄宗即位后國家升平的贊許,也是對自己能夠大展宏圖的期待。李白《西岳云臺歌送丹丘子》則以華山高峻與黃河奔流進一步襯托盛世華彩:“榮光休氣紛五彩,千年一清圣人在。”還有薛逢《九日曲池游眺》云:“正當海晏河清日,便是修文偃武時。”張九齡《奉和圣制經(jīng)函谷關(guān)作》云:“函谷雖云險,黃河已復清。圣心無所隔,空此置關(guān)城。”這些詩歌中的“河清”飽含著詩人的治世建議與襟懷抱負。及至晚唐,崔鉉《進宣宗收復河湟詩》仍然展現(xiàn)出大唐戰(zhàn)功與王朝的震懾力:“煙塵永息三秋戍,瑞氣遙清九折河。”詩人對于唐王朝統(tǒng)治高度體認,將盛世激發(fā)出的積極進取精神與功業(yè)理想傾注于“河清”中,使其兼融國家命運與個人際遇的雙重意義,代表著他們強烈的時代使命感。
從魏晉南北朝到唐代,“河清”已成為建構(gòu)統(tǒng)治權(quán)力的話語,而后世詩人在此基礎上的使用更具有多樣性,如將“河清”疊加其他祥瑞意象“海晏”等,作為詩歌中的固定搭配。清初查慎行作“地久天長運,河清海晏期”;康熙朝君臣效柏梁聯(lián)句亦有“河清海晏禹績彰”之句,祥瑞意象的雙重疊加表示政通人和,而且詩歌作為重要的傳播媒介之一,推動“河清海晏”深入到社會日常生活的通俗表述中。又如清初遺民詩歌中的“河清”頗耐人尋味。屈大均《新年》中“河清終已矣,難俟奈君何”;顧炎武《五十初度時在昌平》中“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終自望河清”;毛奇齡《和秋日閑居詩》中“徒吟王粲賦,安得俟河清”等詩中的“河清”在輿圖換稿的思想沖擊下,究竟是懷念勝朝還是贊譽新朝,只有詩人心中明了,不過“河清”表達的始終是他們對于家國太平的祝愿。經(jīng)過歷代詩人在不同時代語境下的應用,“河清”已成為寄托美好祝愿的民族文化符號,直至當下,依然是國人話語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再度疊加:“河清”融合其他河流意象
唐以來,“河清”意象不斷被疊加。“在詩學世界中,意象并非孤立存在的,而是在相互聯(lián)系中顯示其象,深化其意”。“河清”本就由黃河與清疊加而成,隨著航運發(fā)達,唐以后河流文學書寫呈現(xiàn)蓬勃發(fā)展趨勢,詩人將天下河流納入個體生命表述中,也將“河清”與其他河流意象進行疊加。但詩人帶著藝術(shù)創(chuàng)造力及對水之清濁的視覺感官,對“河清”進行意象疊加的形式是分解與重構(gòu),即在加入濟水、淮水、渭水等基礎上,形成清濟與濁河、清淮與濁河、清渭與濁涇的對比搭配。雖然“河清”具有的政治祥瑞之意深刻于民族文化基因中,但是相關(guān)疊加意象較少表示這種意義,詩人主要基于“尚清”意識,借助清濁的對比來傳達處世觀念。
其一,清濟與濁河。作為四瀆之一的濟水有“清濟”之稱,如《戰(zhàn)國策》中曾記載“齊有清濟”。濟水發(fā)源于河南濟源王屋山,流經(jīng)山東后匯入渤海,水質(zhì)清澈,與黃河中下游河段的渾濁有著明顯對比。故而當濟水與“河清”進行疊加時,形成清濟對濁河的客觀視覺基礎。而且又因濟水雖細微但能獨行入海,“瀆之言獨也,不因馀水,獨能赴海者也”,人們也將之理解為高潔堅守精神的象征,白居易就稱贊濟水堅毅品格:“至清遠外濁,有本其何修。朝宗未到海,千里不能休。”這種文化意義也被帶入疊加意象的內(nèi)涵建構(gòu)中。唐代大歷二年(767),杜甫在夔州為狄仁杰曾孫狄博濟所作《寄狄明府》,便采用“濁河終不污清濟”之句,贊狄仁杰出淤泥而不染能夠堅持本心、剛正自守,也是以此優(yōu)良品格勸誡與鼓勵狄博濟。北宋梅堯臣的長詩《次韻答黃介夫七十韻》直接以“清濟”剖白心志:“肯為濁河濁,愿作清濟清。”朱東潤評此詩“提出一生的遭遇并揭露自己的人生觀”,此句揭示了他在慶歷、嘉佑時期政變中的立身處世觀,表達自己不肯隨波逐流,愿學“清濟”的獨立品格。此后還有明末清初黃淳耀《會稽隱》說“曹馬自爭儂自隱,濁河清濟不同流”,清末鄭孝胥《贈郭秋屏》中的“濁河方滔天,伏濟清自貫”等,均是以清濟與濁河的對比表達處世觀念,已經(jīng)斷流的濟水就在意象的演變中永久流傳。
其二,清淮與濁河。淮河亦是四瀆之一,發(fā)源于河南桐柏山,是中國南北方的地理分界線。先唐詩歌中較少書寫淮河,但當其出現(xiàn)時有著頗為明顯的特征,一是水流清澈,二是作為地域分界而被賦予漂泊、離別、思鄉(xiāng)等意味。南朝何遜《望新月示同羈》寫到“月映清淮流”,清澈的淮水承載著他細膩的離愁情思,唐代淮河也“主要被描寫成偏僻之地,是一個催生旅愁和思鄉(xiāng)情緒的消極空間”,如孫遜《淮陰夜宿》云:“水國南無畔,扁舟北未期。”隨著河運發(fā)達以及南北方溝通的便利,淮河的價值得到重視,相關(guān)詩作增多,書寫形式更為多樣,與“河清”意象的疊加即是其中一種形式。清淮與濁河的對比既有針對性的社會批判,元代宋褧《河淮曲》中的“河水濁,淮水清”,便是以濁河代指治河弊政,如官員對百姓的肆意盤剝等,清淮則代表與之相反的積極行為,結(jié)尾寄語“愿君莫學河水學淮水”,則是規(guī)勸官吏在治河中要行為規(guī)范,以民為主。又有針對個體行為處事的感悟,如明清鼎革之際錢謙益的《舟發(fā)泇溝》賦予淮水超脫世俗的用意:“濯纓自與清淮約,不用臨流嘆濁河。”清代梁佩蘭《送周梨莊歸江南次留別原韻》中以“清淮”稱贊友人品行:“清淮不入黃河濁,高人好似云中鶴。”同時也是他晚年皈依佛教,崇尚平淡自然生活的自我寫照。隨著與“河清”進行疊加,淮水意象的內(nèi)涵也得以豐富。
其三,涇渭清濁。渭水與涇水作為黃河的兩大支流,以清濁分明聞名,但在不同歷史時期,渭水與涇水的清濁現(xiàn)象并不固定。故而歷代對《詩經(jīng)》中“涇以渭濁”的解釋可謂眾說紛紜,《毛詩鄭箋》持涇清的說法:“涇渭相入而清濁異。”《毛詩正義》則認為涇濁:“涇水以有渭,故見其濁。”但具體到詩歌創(chuàng)作領(lǐng)域,詩人并沒有執(zhí)著于涇渭孰清孰濁的問題,將之與“河清”的疊加也頗為自由,或是渭清涇濁,如唐代杜甫《秋雨嘆三首》中的“濁涇清渭何當分”;或是涇清渭濁,如明代邊貢《分韻得岳字送邢侍御出按秦中》云:“渭水清清涇水濁,須君激揚無憚數(shù)。”疊加意象的形式雖多樣,但均賦予了人格化的理解。北宋黃庭堅有《閏月訪同年李夷伯子真于河上,子真以詩謝次韻》云:“白璧明珠多按劍,濁涇清渭要同流。”亦有《次韻楊明叔見餞》云:“楊君清渭水,自流濁涇中。”黃庭堅借涇渭分明的道理勸告友人,世事雖有污濁,但要像涇水與渭水那樣同流卻不合污,在紛繁世事中保持初心,這是黃庭堅處世智慧所在,也是他久經(jīng)宦海沉浮后的心志剖白。作為黃河的支流,渭水與涇水在清濁分明前提下與“河清”疊加形成的意象,也在豐富著“河清”意象系統(tǒng)。
“河清”與河流意象的疊加立足于清濁之辨,目的是激濁揚清。因為“在中國古代的文化闡釋中,‘清與‘濁,是關(guān)系到社會政治和道德倫理的重要范疇”,所以“河清”的疊加意象均折射出了倫理道德的色彩。詩人帶著尚清意識對清濟、清淮的贊揚,對濁河的貶斥,體現(xiàn)出他們激濁揚清的處世態(tài)度與道德品格。不僅如此,詩人將在生活浮沉中堅持的激濁揚清態(tài)度,以詩歌的形式和水之清濁的比喻發(fā)散出來,是人生反思與情緒抒發(fā)的機會,而在詩歌的傳播與接受過程中,這些帶有正向?qū)б脑捳Z無疑具有道德教育的功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讀者的價值觀。意象疊加為“河清”的演進開辟了新方向,不僅豐富其內(nèi)涵建構(gòu),增添其應用的范疇,也推動了中國文學中河流書寫及其意象的發(fā)展。
三、詩題拓展:河患書寫進入“河清”
宋以來,河患書寫進入“河清”意象的內(nèi)涵累積,“河清”開始代表黃河安瀾的意義。面對巨大災害,文學何為?這是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關(guān)于文學價值的深刻發(fā)問。從古至今,人們都在與災害進行艱苦卓絕的斗爭,文學是其中重要的參與者,以在場視角記錄與反思災情,從人文關(guān)懷層面給予災民創(chuàng)傷后的心靈慰藉。黃河水患是困擾古代的大問題,河患文學作品自不在少數(shù),東漢王景治河后,黃河維持了數(shù)百年的穩(wěn)定局面,故而河患詩比較少見。宋以后河患始多,黃河又南下奪淮,河道淤積導致濁流橫溢,造成了巨大的社會破壞,河患詩遂在北宋“由前代極少的零星現(xiàn)象蔚然而成一代詩風”,“河清”也在此期進入河患詩創(chuàng)作中,在其營造出的特有詩歌空間中,寫盡洪災之下的苦難與抗爭,揭露災難背后的真實與黑暗,在治河過程中發(fā)揮著多重功用,與河患主題的綰合也助推了“河清”意涵的拓展。
河患詩中的“河清”代表河患平息的社會共同愿景,也承載著慰藉心靈的情感目的。從視覺表象來看,詩人對河患與“河清”的聯(lián)想是妥帖的。宋以來,黃河奪淮入海造成黃河流域水災頻發(fā),災患的顯著表征是渾濁的黃河水洶涌而來,詩人對黃河之濁既有著敏銳的色彩感知,又有著情感上的恐懼,因傳統(tǒng)文化中有包含國泰民安意涵的“河清”存在,他們遂將對河患的焦慮與無助投諸其上。如元代迺賢《新堤謠》的“但愿皇天念赤子,河清海晏三千秋”,清代潘耒《汴河行為方中丞歐余作》的“且為公歌汴河詩,洗眼坐待河清時”。而張永銓《悲淮民》卻寫到“不愿俟河清,但愿堤無傾”,面對洪災,他不愿河清的情感抒發(fā)則是一種沉痛的無奈。總體來看,詩人借助“河清”并非空泛表達黃河安瀾的期望,緩解他們的情緒,詩人也在思考如何遣詞排句,使讀者進入由“河清”營造出的與現(xiàn)實參照的平行空間,使讀者緩解在洪災中的悲痛與創(chuàng)傷,實現(xiàn)河患詩主旨的升華,促使情感最大限度地釋放,最終實現(xiàn)心靈療救的文學價值。
元代至正年間水患頻發(fā),貢師泰的《河決》對黃河決溢下的社會景象做了全方位描述。貢師泰先以宏大夸張的手法營造洪水傾襲的壓迫感,“初疑滄海變,久若銀漢連”,接下來用紀實的語言描述面對洶涌的洪水,百姓根本無法應對。然而在后續(xù)防洪與家園重建中,官吏的盤剝與對民生的漠視,更使百姓陷入無盡的黑暗,在一番悲憤控訴之后,詩人采用議論的形式將批判矛頭直指治河策略與官員弊政。在詩歌中,讀者跟隨詩人的指引回到了不忍再見的洪災生活,接著又被帶入到深層次的河患思考中,此時悲愴與痛恨的情緒達到了一定程度,但詩歌卻進入到了尾聲,“平成諒有在,更獻河清篇”,假如應對河患的諸種策略都安排妥帖,便可迎來太平光景。讀者累積的情感還未來得及爆發(fā),即被詩人美好的設想打破,痛苦的極致是無聲勝有聲,讀者在此時獲得了自由的情感空間與沉思空間。詩尾出現(xiàn)的“河清”與其說是盛世期許,不如說是詩人在殘酷洪災與混沌世態(tài)中帶來的人文溫情,這正是詩歌中“河清”書寫的關(guān)懷精神所在。
除了突顯“河清”的情感功用外,詩人也以其表現(xiàn)他們比較焦慮的治河問題。如何治理黃河是社會普遍關(guān)注的問題,詩人通過如何實現(xiàn)“河清”的討論,既警醒當政官吏,又給出了言之有物的建議。北宋黃庭堅《流民嘆》中“投膠盈掬俟河清,一簞豈能續(xù)民命”,借用《抱樸子》中“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的說法,批判朝廷未能及時有效治河,造成“疏遠之謀未易陳,市上三言或成虎”的混亂狀態(tài),破壞正常的社會秩序;清代李漁《黃河篇》寫作“千年一清斯其時。寄語官人浚勿遲,主德無虧孰承疵”,也是在強調(diào)治河事務的緊急性,以避免損害政權(quán)統(tǒng)治;吳以諴《觀黃淮交匯糧艘競渡感而有作》所說實現(xiàn)“河清作頌聲摩空”的前提是采取適當?shù)闹魏硬呗裕壳皢渭儾捎媒椟S濟運的方法顯然是缺乏全局考慮。詩人對于治河的勸誡與批判來源于對現(xiàn)實弊端的深入思考,具有一定的現(xiàn)實反思價值。自宋以后,這些不斷出現(xiàn)在河患詩中的“河清”聲音,已匯聚成強大而有聲的力量,成為治河過程中不可或缺的理念指引之一,時刻提醒著治河者。
明代黃哲《河渾渾》的創(chuàng)作即是典型事例。洪武四年(1371),黃哲任東平府通判負責治河時作《河渾渾》,詩序云:“無所施其功,故議者欲上聞,有復堰黃陵岡之舉。噫,此季元之覆轍,何足與議哉。”由此可知,該詩是黃哲為反對當時所議治河措施而作,但他并沒有停留在單純的批評層面,而是以實踐經(jīng)驗針對如何實現(xiàn)“河水渾復清”進行建議。詩歌開篇渲染了百姓在洪水中的悲慘生活,而后詩人筆鋒一轉(zhuǎn),開始批判有司治水不顧現(xiàn)實情況,仍要沿襲元代賈魯治河舊策筑塞黃陵岡,并直接提出自己的看法,認為這樣不符合當下的治河實際,恐怕是毫無功效的,接下來給出了自己的解決方案,需要在梁山疏通洪水:“龍門一疏鑿,亙古功巍巍。”這是黃哲作為主政者的治河態(tài)度,也是在詩歌流傳的公共空間中傳達的治河策略。黃哲詩歌中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言說方式,與其治河行動相得益彰,也有助于推行自己的治河措施。此外,正如余嘉錫所說:“洪武四年浚河通漕之事,《明史·食貨》《河渠》兩志皆不載。然哲時方官東平府通判,躬董其役,則其言固足補史之闕矣。”黃哲以第一人稱視角敘寫現(xiàn)場實況,填補了史實空缺,無疑也為后人治河提供了寶貴的經(jīng)驗借鑒。
從詩歌史來說,在由“河清”意象生成的河患書寫空間中,詩歌創(chuàng)作視角得以擴展,黃濁色調(diào)的突顯使得洪災紀實描寫具有畫面感與真實性,基于如何實現(xiàn)“河清”生發(fā)出的議論則增添了詩歌的書寫層次。更值得注意的是,詩歌的文學功用也被積極調(diào)動起來。詩人作為災難的經(jīng)歷者與記錄者,展現(xiàn)出百姓面對洪水的無助與命運掙扎,是對生命悲憫與關(guān)愛的文字見證;帶有批判精神的治河言說,拓展了詩歌介入社會生活的深度與廣度,也積極發(fā)揮了文學的現(xiàn)實作用;而“河清”所具有的國泰民安意義作為河患詩的文化底色,則更代表了民族面對災難時堅強樂觀與不屈不撓的精神品質(zhì)。
四、近代新聲:世變中的“河清”
清末民初的世變既是古典詩歌中“河清”書寫的背景,又推動其祥瑞內(nèi)涵的重新建構(gòu)。當西方的堅船利炮打破天朝上國的迷夢,在失敗恥辱中崛起的國人開始尋求救亡圖存與民族復興之路,詩歌是他們采用的方式之一。詩人頻頻使用“河清”意象,目的是借助其代表的已取得民族共識的國家祥瑞意涵,為國難中的民眾帶去心靈的慰藉,同時也為自己倡導的救國新思想、新理念提供傳統(tǒng)文化支撐,“河清”即在這種創(chuàng)作氛圍中融入革新救弊、革命救國等具有時代特征的話題,發(fā)揮時代轉(zhuǎn)型中的文學使命,也反映著世紀之交的人文情懷與思想演變歷程。
鴉片戰(zhàn)爭后,在經(jīng)世致用思潮激蕩下,詩人筆下的“河清”從盛世頌揚轉(zhuǎn)向憂患表達。此期類似高心夔《中興篇》贊頌同治中興“鳳鳴河清莫虛致,普天率土還耕織”,以“河清”為清朝歌功頌德的詩歌已不多見,取而代之的是以其痛批時弊、抒發(fā)忠憤。尤其在時事詩中,如楊子恂緣事而發(fā),在《津門感事》中記錄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的情況,開篇“三輔名區(qū)帝股肱,建瓴勝勢據(jù)滄瀛”,以豪邁的語言突出天津占據(jù)有利防御條件,下文卻說此地官兵無力阻擋外敵入侵,國家最終被迫簽下屈辱的《天津條約》,出乎意外的失望與無計可施的國難痛苦交織在一起,詩人卻只能呼喚“愿留人壽待河清”,通過“河清”表達救國期望的同時以之寬慰心靈。湘軍將領(lǐng)的彭玉麟在太平天國戰(zhàn)爭中所作《肅清長江》,并非只是通過“河清”感慨國家命運,也寄寓振衰救弊責任與建功立業(yè)志向:“河清海晏消烽火,浪靜潮平息鼓鼙。”即便在傳統(tǒng)的士不遇主題詩歌中,“河清”依然承載著憂患意識。皮錫瑞雖然因科舉未第無法施展抱負,但他的憂國憂民之心并未因困頓科場而消磨,由《行路難》中“黃河一千年一清,安得躬逢圣人生”,以及《旅館夜》中“櫪伏非無志,河清豈可要”等可以感知,為生計奔波的疲敝沒有磨滅皮錫瑞的經(jīng)世抱負,當面對晚清家國零亂與民生多艱,他將不遇的苦痛與國家憂患融合在一起,依然要為實現(xiàn)“河清”努力,并將之化為最為純粹的人生驅(qū)動力,積極加入時代變革的進程。因處于封建傳統(tǒng)語境下,詩人通過“河清”依然表達鞏固王朝統(tǒng)治政權(quán)的愿望,其中的憂患意識與救弊抱負,正是晚清經(jīng)世文學思潮的寫照。而彼時出現(xiàn)在詩歌中的“河清”,不僅是詩人表達處世焦慮與理想信念的恰當載體,更豐富了晚清詩歌憂患書寫的情感層次。
甲午戰(zhàn)爭后,“河清”意象又出現(xiàn)轉(zhuǎn)向,反映著匡救時弊中的駁雜心境,以及為國家上下求索的艱難過程。“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經(jīng)歷了甲午戰(zhàn)爭的有識之士愈加認識到清王朝的腐敗與無能,將救國救民的希望轉(zhuǎn)向西學新知,提倡反清排滿與民族革命。光緒二十五年(1899),章太炎作《臺北旅館書懷寄呈南海先生》,他在回顧了自己的思想變化過程后感慨:“斗轉(zhuǎn)空憑眺,河清動夙悲。”“河清”代表著章太炎對國家安定的期盼,但在當時的局勢下,他之前所作的種種努力皆化為泡影,如何找尋挽救國家頹勢的“河清”之路,成為他當時最為焦慮的問題。但由于此時他正經(jīng)歷思想斗爭,批判維新保皇與主張社會改革思想交織在一起,“河清”也進一步承載著他立志掙脫維新改良范疇,重新探索解救國家于危局的決心。
光緒三十年(1904),黃節(jié)、嚴復、黃遵憲三位詩人不約而同地書寫“河清”,著意從傳統(tǒng)文化中尋找精神支撐,訴說著他們在世變中的命運沉淪與堅韌斗志。是年,距黃節(jié)在清王朝最后一場科舉中落第已有兩年,此時的黃節(jié)接受了新文化洗禮,積極投身到革命潮流中,他于年初生日作《甲辰生朝拍照自題一律》云:“世界無窮愿無極,寸心留得俟河清。”該句化用梁啟超《自厲》中的“世界無窮愿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也在延續(xù)梁詩中救助國難的精神意志,以突顯自己“不肯虛度年華的積極進取精神”,此后,黃節(jié)與同道以救世扶危為重,為激發(fā)民眾的愛國思想,籌辦國粹學社,創(chuàng)辦《國粹學報》,以昂揚的斗志與革命追求為實現(xiàn)“河清”努力。同年三月,嚴復辭去京師大學堂附設譯書局總辦一職,在去往上海前與福建同鄉(xiāng)聚于陶然亭,作《甲辰出都呈同里諸公》云:“但恐河清不相待,法輪欲轉(zhuǎn)嗟吾衰。”為民族救亡奔波的嚴復使用“河清”,是因救國事業(yè)未竟而生發(fā)出時不我待的感慨,怕不能踐行“乾坤整頓會有時,報國孤忠天鑒之”的愿望。到了冬季,黃遵憲作《病中紀夢述寄梁任父》:“日去不可追,河清究難俟。”此詩黃遵憲作于去世前數(shù)月,此時他已預感到人生大限將至,卻苦于尚未找到治愈時局的良方,發(fā)出終究難以見到“河清”的哀音,“河清”意象盡顯悲愴的氣息。甲午戰(zhàn)爭以來詩歌中的“河清”寄寓著緊迫的救世理想,其中遺民詩人的書寫值得注意,展現(xiàn)出了“河清”的復雜性與多義性。
辛亥鼎革之際,清遺民在治統(tǒng)與道統(tǒng)上的分裂造成其思想具有特殊性,筆下的“河清”似與時代齟齬。清亡后,追隨溥儀的帝師陳寶琛的詩中常見對故朝的眷戀,尤其是見到民國初年動亂之狀后,他理想地認為重回清王朝統(tǒng)治,可使百姓免予流離疾苦,1912年的《九月二十九夜大風不寐作》中的“河清”就直指復辟王朝:“馀生皈佛戀桑下,敢望身及黃河清。”直至1918年,《梁節(jié)庵六十壽詩》中仍包含不改臣節(jié)的清遺老心態(tài):“河清倘可俟,火井寧竟熸。”1918年,纏綿病榻多日的沈曾植作《病起自壽詩》,記錄他參與復辟卻旋即失敗后的個中滋味:“反復豈能逃易意,婆娑還得俟河清。”沈曾植一方面用易理寬慰自己,另一方面又遺憾自己時日無多而難見帝制復辟。然而,不同于留守小朝廷、為復辟奔走呼號的詩人,不以遺民自居的陳三立于1915年作《哭于晦若侍郎》云:“迫攖崩坼痛,擔簦俟河清。”此句看似“表于晦若的幽懷孤忠”,其實也是陳三立自比個人追求,意在不以遺老身份沽名釣譽,不執(zhí)念一姓之興衰,而要以詩人的孤忠氣節(jié)支撐起亂世中的生存希望,堅守文人士大夫的精神氣度。在近代變革潮流中,一些遺民對于“河清”的理解不免要打上落后的標簽,但促使他們汲汲奔走,以“河清”傳達亂世責任與使命的,并非封建政權(quán)的震懾力,而是出于新舊之交對國家與文運的傳承責任,他們的不斷思考與嘗試,促使著近代文人逐漸走向開明的世界。
清末民初的世變不僅是詩歌中“河清”的創(chuàng)作背景,更推動祥瑞內(nèi)涵的去粗取精。隨著時代風云激變而起伏的詩人,始終懷揣著憂國憂民的責任情懷,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已突破封建統(tǒng)治思想的束縛,筆下的“河清”不再針對一家一姓統(tǒng)治政權(quán)而言,也超越了華夷之辨的觀念,而是借助“河清”意象強調(diào)個人與國家、民族的相互依存,以抒寫焦慮、宣揚新知、探索救國道路,既順應著此時社會與思想的變革進程,也使“河清”期盼取得各民族共識,從而真正進入到大眾話語,代表著對于國家民族未來的深沉思考與衷心祝愿。比如在民國中后期詩歌中,郁達夫《客感寄某兩首》站在中華民族立場上表達對祖國命運的憂慮:“半席已知無我分,百年何日果河清。”抗日戰(zhàn)爭中,柳亞子《劉雪耘見顧屬題〈黃鶴樓圖〉,報以一截》云:“河山倘見澄清日,愿挹椒漿酹禰生。”詩歌中的“河清”更是在追求獨立自主道路上頑強自信的民族精神體現(xiàn)。
余論
古典詩歌中“河清”意象的內(nèi)涵就像東去的黃河,在流向大海的行程中不斷有新的河流匯入;這種內(nèi)涵的累積,不僅深入到中國文學的演進中,也影響著民族生活與民族品格的行塑,具有重要的文學文化意義。
其一,豐富古典詩歌表達。從先秦至近代,“河清”意象的應用范疇完成了從人生、政治到社會全方位的轉(zhuǎn)變,成為內(nèi)涵豐富的文化符號,詩歌中采用比興、意象疊加方式促進了藝術(shù)形式的變化。兼融多重意蘊的“河清”無論出現(xiàn)在哪類題材中,均豐富了詩歌的表達層次,加深了詩歌的蘊藉性。
其二,“河清”從生成到最終營造出詩歌空間的過程,是考察中國文學意象演進機制的重要窗口。一是依托于民族心理的積淀,這也是文學意象能夠延續(xù)的心理根基。“河清”由尚清意識衍生出情感表達意涵,充滿著古代的人生哲思與生命訴求,詩人在逆境中的書寫更代表堅韌頑強的民族意志,這種凝聚民族的普遍共識,且經(jīng)歷數(shù)千年積淀的意涵愈加突顯,是民族文化對于文學書寫影響的體現(xiàn)。二是政治驅(qū)動,這也是對文學意象影響最大的外部因素之一。“河清”之所以能夠超越一般水意象的意義范疇,開始附會政治,得益于漢以來官方推崇其祥瑞指向以維護統(tǒng)治的考慮,這種強有力的權(quán)力加持推動了文學對“河清”祥瑞意涵的接受,詩人以其表達政治訴求的同時實現(xiàn)其文學功用,“河清”意象即在參與政治話語建構(gòu)中定型。三是源于文人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力。在已生成的闡釋框架下,隨著時代際遇與文學風尚的變遷,詩人積極開拓意象生新的可能空間,以疊加的形式擴展其文學承載力,為河流文學書寫提供了借鑒模式。可見,中國文學意象的生成是一個傳承與創(chuàng)新交織的演變過程,在融合民族文化與現(xiàn)實表達基礎上,實現(xiàn)了源源不斷的傳播可能,成為寶貴的民族文化財富。
其三,作為傳統(tǒng)文化的組成要素,“河清”已成為代表民族文化心理的特定話語。在中國詩歌史上,除了上述所提“河清”比較突出的內(nèi)涵外,還可以發(fā)現(xiàn)一些獨特的用法。如宋以來流傳的包拯笑比河清,《夢溪筆談》云:“天性峭嚴,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希仁笑比黃河清。”后世或以難展笑顏說明心境之愁郁,陸游退居山陰后依舊為山河零落揪心:“危坐但愁悲,一笑黃河清。”或直以此贊譽包拯,李鴻章《笑比河清》:“欲求一笑閻羅易,須俟千年德水清。”這種表達連同“河清”對人生情感表達的作用、對黃河安瀾的衷心企盼、對國家民族命運的美好祝愿等,共同融入社會大眾的話語表述中,彰顯著民族的凝聚力與向心力。值得一提的是,“河清”意象也影響了域外文人的創(chuàng)作,日本、韓國、越南等詩歌中亦有“河清”書寫,延續(xù)著其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內(nèi)蘊構(gòu)成。域外詩人或親臨黃河勝景感發(fā)“生圣果然征泰運,振君應及此時清”,或依靠想象的方式抒發(fā)“秦分會獻河清瑞,海晏今應啟圣年”,這些黃河文化對外傳播的見證,是東亞文化圈層對中華文化認同的體現(xiàn)。時至今日,“河清”意象仍被廣泛應用于政治、社會、文化生活中,承載數(shù)千年積淀的民族文化,帶著歷史的厚重與滄桑,成為啟迪現(xiàn)代社會的重要民族文化基因。
[責任編校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