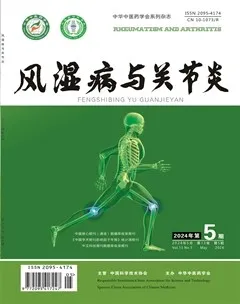痛風的證治
李滿意 劉紅艷 陳傳榜 王頌歌 楊英 馮文杰 付建利 婁玉鈐 張攀科 劉傳慧
【摘 要】 收集研究歷代醫家論治痛風的經驗,結合臨床實踐,總結出痛風的病因病機(虛、邪、瘀)和證治方案,辨證分為3候6型:正虛候(肝腎陰虛證、脾虛濕阻證、氣血兩虛證),邪實候(濕熱蘊結證),痰瘀候(痰濁阻滯證、痰瘀互結證)等。臨床應用,取得良好的效果。
【關鍵詞】 痛風;痛風性關節炎,類風濕關節炎;特殊痹;風濕病(痹病);虛邪瘀;證治;中醫藥
本文所說痛風,是中醫學所述痛風[1]。“痛風”一詞出現較早,在南朝梁代陶弘景《名醫別錄》中即有記載。元代朱丹溪在《格致余論》中專門列有“痛風論”,明確提出“痛風”的病名。其后,明代孫一奎、張介賓,清初喻嘉言等皆宗其說。綜合以上可得出:痛風是指以關節腫痛,疼痛劇烈,反復發作為特征的風濕病。為特殊痹之一[2],是風濕病的三級痹病[3]。痛風之名對后世醫家影響極大,多認為是疼痛較為嚴重的一種特殊痹病。應該與西醫學的痛風性關節炎、類風濕關節炎、急性風濕熱、紅斑肢痛癥等急性發作期相似。中醫藥對痛風的治療有顯著的臨床療效。
1 病因病機
本病多由感受外邪,飲食不節,或陰陽失調,內外合邪,濕熱、痰濁、瘀血等留滯體內,氣血瘀滯不通,留滯肢體關節,而發本病。
1.1 飲食失調 飲食不節,或因嗜酒,或肥甘厚味,或過食溫燥辛熱之品,脾失運化,濕熱痰濁內生,痹阻肢體關節,而發本病。如明代龔廷賢《萬病回春》曰:“痛風肢節痛者,……膏梁之人,多食煎炒、炙爆、酒肉,熱物蒸臟腑,所以患痛風……者最多。”
1.2 邪氣壅滯 感受風寒濕等邪,祛邪不利,邪氣壅滯,痹阻經絡氣血,而發本病;或邪郁久化熱,濕熱邪阻,壅滯肢體關節,而致本病。如明代李中梓《醫宗必讀》曰:“寒氣凝結,陽氣不行,故痛楚甚異,俗名痛風。”《類證治裁》曰:“痛風,……三氣入于經絡,營衛不行,正邪交戰,故痛不止。”“初因寒濕風郁痹陰分,久則化熱攻痛,至夜更劇,……若痛處赤腫焮熱,將成風毒。”清代劉清臣《醫學集成》言:“由風寒濕雜合成病,近世曰痛風。”
1.3 正氣虛弱 素體脾弱,或勞倦過度,氣血虧虛,經絡枯澀;或肝腎不足,肢體關節筋骨失養,而致本病;或房室過度,腎虛失調,氣化不利,清濁不分,濁毒稽留,而發痛風。如明代龔廷賢《壽世保元》曰:“痛風者,皆因素體虛弱,……其病晝靜夜劇,其痛如割。”“痛風,……乃血虛氣弱,經絡枯澀,寒滯而然也。”清代何其偉《雜證總訣》曰:“偏身走痛名痛風,……此雖血瘀筋不養,總由血虛不內榮,寒氣凝滯濕痰結。”
1.4 痰濁瘀血 瘀血痰濁氣滯是痛風的一個重要病理變化。肝郁氣滯,氣滯血瘀;或嗜食辛辣膏粱厚味,積熱熏灼津液為痰,痰濁瘀血阻滯,發為痛風。如《格致余論》曰:“痛風因濕痰濁瘀血流注為病。”《解圍元藪》曰:“痛風,……或郁蓄私念不得發泄,激蕩氣血而成,或勇怒、饑飽、傷感、疾風、迅雨、逆塞充漫四肢經絡,為之行痹也,其痛轉展不定。”《醫方考》曰:痛風“所以痛者,濕痰死血留結而不通也。”“瘀血,濕痰畜于肢節之間而作痛。”皇甫中《明醫指掌》曰:“遍體煩疼曰痛風,濕痰風熱若相攻;或因血弱寒凝澀,流注渾身骨節中。”《萬病回春》曰:痛風“肥人多是濕痰,瘦人多是痰火。”清代謝映盧《得心集醫案》云:“熱傷營血,血液涸而不流……,名為痛風也。”
綜上所述,痛風的發病原因雖多,但概括起來不外“虛邪瘀”三個方面[4]。其基本病機為脾腎功能失調,邪濁痰瘀,留滯于骨節,不通不榮。核心病機為脾納運和腎升清降濁功能失調[5]。病位主要在四肢關節,涉及脾腎肝等臟腑。發作期以邪實為主,緩解期以正虛為主。實以濕熱、痰濁、瘀血為主,虛以脾腎虧虛及功能失調為主。本病初起發病急驟,反復發作;部分患者久則變形殘疾。
2 診斷要點
本病多見于男性,常因飲酒,嗜食高嘌呤食物等誘發。初發以第一跖趾關節多見,單關節發病。繼則出現足踝、足跟、手指和其他小關節腫痛。反復發作后,可伴有趾、指骨間關節周圍及耳廓、耳輪出現“塊瘰”。其疼痛特點:①多呈發作性。發作時局部關節疼痛劇烈,活動受限,持續時間1 d~1周。②多呈晝輕夜重,局部可出現腫脹及灼熱感。
3 辨證論治
痛風的辨證要點主要是辨虛實。本病實證以關節紅腫熱痛為主要表現,身體不虛;虛證多見關節隱痛或疼痛間歇期,多伴見面色蒼白,倦怠乏力,短氣自汗,心悸,頭暈,耳鳴,失眠,多夢,爪甲色淡,食少,便溏,舌淡(陰虛火旺則舌質紅),脈細弱。本病治療以“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為原則:急性期、發作期清熱利濕,消腫止痛,以祛邪為主;緩解期、間歇期健脾補腎,以扶正為主。按“虛邪瘀”辨證可分為3候6型,強調長期堅持、雜合以治,重視調護及“治未病”。
3.1 邪實候 濕熱蘊結證:關節紅腫熱痛,發病急驟,初起一個關節發病,可累及多個關節,局部灼熱,得涼則舒,關節活動不利,舌質紅,苔黃膩或厚,脈弦滑數。以關節紅腫熱痛,發病急驟為本證辨證要點。
分析:濕為陰邪,其性趨下,為病多發于下肢,濕與熱合,黏滯纏綿,流聚無常,痹阻關節,故見下肢關節紅腫熱痛,發病急驟,病及一個或多個關節,關節活動不利;熱為陽邪,熱邪痹阻,故見局部灼熱,得涼則舒;舌質紅,苔黃膩或厚,脈弦滑數均為濕熱蘊結之象。
治法:清熱利濕,通絡止痛。
方藥:四妙散(《成方便讀》)加味。黃柏20 g,蒼術、牛膝、薏苡仁、萆薢各15 g,威靈仙、忍冬藤、山慈菇各10 g,甘草6 g,木瓜15 g,苦參15 g,防己10 g。
方中蒼術苦溫燥濕;黃柏苦寒清下焦濕熱,配薏苡仁健脾利濕;牛膝通利關節,強壯筋骨;木瓜、防己除濕通絡止痛;萆薢、苦參清熱利濕,有利于邪去正安。濕熱蘊結是痛風急性發作期,因此,此期強調清利,使邪有出路,邪去正自安。若熱甚者,加梔子10 g、連翹30 g、赤小豆30 g;病程較長者,加赤芍15 g、丹參20 g;痛甚者,加海桐皮10 g、虎杖30 g、秦艽15 g;熱甚傷陰者,加生地黃20 g、龜板10 g;尿路結石者,加金錢草、海金沙等;神疲乏力、頭暈明顯者,加制首烏、枸杞子等;若瘀熱內郁者,痛風湯加減。
3.2 正虛候
3.2.1 肝腎陰虛證 關節腫痛不甚,筋脈拘急,頭暈耳鳴,局部關節變形,屈伸不利,顴紅口干;舌紅少苔,脈弦細或細數。以關節腫痛不甚,筋脈拘急,頭暈耳鳴為本證辨證要點。
分析:肝腎陰虛,筋脈失養,則見關節腫痛不甚,筋脈拘急,屈伸不利,局部關節變形;陰虛津虧不能上榮頭面,故見頭暈耳鳴,顴紅口干;舌紅少苔,脈弦細或細數均為肝腎陰虛之象。
方藥:養陰活血湯加減。青蒿20 g、玄參20 g、生地黃20 g、白薇15 g、知母15 g、連翹15 g、黃芩15 g、牡丹皮15 g、銀柴胡20 g、赤芍1g、雞血藤20 g、川芎10 g、絲瓜絡15 g。
方中玄參、生地黃、牡丹皮、白薇、知母、連翹、黃芩、銀柴胡、青蒿養陰清熱;赤芍、川芎、雞血藤活血養血;絲瓜絡疏通經絡。全方共奏養陰清熱、活血通痹之功。若關節痛、紅細胞沉降率(ESR)快者,加威靈仙20 g、絡石藤25 g、海風藤20 g、海桐皮20 g;頭痛頭暈者,加鉤藤20 g、白菊花10 g、蔓荊子15 g、白芷15 g;血壓高者,加生磁石20 g、紫石英20 g、石決明20 g、草決明15 g、夏枯草15 g。
3.2.2 脾虛濕阻證 有輕微的關節癥狀,或無癥狀,可見脘腹脹滿,身困倦怠,納食減少,舌質淡胖,苔白或厚膩,脈弦滑。以有輕微的關節癥狀,或無癥狀,可見脘腹脹滿為本證辨證要點。
分析:本證多出現在痛風間歇期或緩解期,關節癥狀輕微或不明顯;脾虛濕阻,運化無力,故納食減少,脘腹脹滿;脾虛不能生氣,故見身困倦怠;舌質淡胖,苔白或厚膩,脈弦滑均為脾虛濕阻之象。
治法:健脾利濕,益氣通絡。
方藥:防己黃芪湯(《金匱要略》)加減。黃芪、白術、薏苡仁各15 g,防己、桂枝、獨活、羌活各12 g,防風9 g,當歸、淫羊藿各10 g,萆薢、土茯苓各20 g,細辛、甘草各6 g。
在痛風間歇期治療中,注重從“脾腎”論治。方中土茯苓、白術、薏苡仁、萆薢、防己健脾利濕;黃芪、甘草補氣健脾;桂枝、細辛、淫羊藿溫陽化濕;獨活、羌活、防風祛風濕、通經絡;當歸活血通絡。全方共奏健脾利濕、益氣通絡之功。
3.2.3 氣血兩虛證 輕微的關節癥狀,或無癥狀,倦怠乏力,面色蒼白,指甲色淡,短氣自汗,頭暈心悸,舌淡苔白,脈細弱。以輕微的關節癥狀,或無癥狀,倦怠乏力為本證辨證要點。
分析:本證多出現在痛風緩解期、間歇期,關節癥狀輕微或不明顯;氣血兩虛,失其榮養,故見倦怠乏力,面色蒼白,指甲色淡,短氣自汗,頭暈心悸;舌淡苔白,脈細弱均為氣血兩虛之象。
治法:益氣養血通絡。
方藥:圣愈湯(《蘭室秘藏》)加減。黃芪30 g,黨參、山藥各15 g,熟地黃、白芍各12 g,當歸、白術、川芎各10 g。
方中黃芪、黨參、山藥、白術益氣健脾;熟地黃、白芍、當歸、川芎補血養血活血。全方共奏益氣養血通絡之效。若夾風濕者,可酌加羌活、防風、豨薟草、桑枝之類;夾濕熱者,加木瓜、薏苡仁。
3.3 痰瘀候
3.3.1 痰濁阻滯證 關節腫痛,周圍漫腫,胸脘痞悶,多部位可見“塊瘰”硬結,目眩,面浮足腫,舌胖質淡,苔白膩,脈緩或弦滑。以關節腫痛,周圍漫腫,胸脘痞悶為本證辨證要點。
分析:痰濁阻滯經絡,故見關節腫痛,周圍漫腫,局部腫痛;痰濁停聚,凝結壅滯,多部位可見“塊瘰”硬結;痰濁阻遏清陽,故見目眩;痰濁壅阻中焦,故胸脘痞悶;痰濕不能運化,故見面浮足腫;舌胖質淡苔白膩,脈滑或弦滑均為痰濁阻滯之象。
治法:祛痰散結,分清化濁。
方藥:程氏萆薢分清飲(《醫學心悟》)合二陳湯(《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加減。川萆薢15 g、黃柏12 g、石菖蒲12 g、茯苓15 g、白術15 g、蓮子心10 g、丹參15 g、車前子12 g、橘紅12 g、半夏9 g、甘草9 g、炒白芥子6 g。
方中茯苓、白術、橘紅、半夏、甘草、炒白芥子祛痰散結,川萆薢、黃柏、石菖蒲、丹參、車前子、蓮子心分清化濁。全方共奏祛痰散結、分清化濁之功。若兼腎虛者,加菟絲子、淫羊藿、巴戟天、枸杞子;兼瘀血者,加赤芍、桃仁、王不留行;兼肝郁氣滯者,加柴胡、刺蒺藜、川楝子、延胡索、荔枝核;兼正氣虛者,加黃芪、當歸、黨參。
3.3.2 痰瘀互結證 關節漫腫或刺痛,固定不移,或關節腫脹、變形,屈伸不利,時緩時急,晝輕夜重,或痛不能任地,日久不愈,反復發作,皮下結節,舌質暗或紅,苔薄黃,脈弦滑或沉細澀。以關節漫腫或刺痛,固定不移為本證辨證
要點。
分析:瘀血痹阻,故見關節刺痛,固定不移,晝輕夜重,或痛不能任地;痰濁痹阻,故見關節漫腫,皮下結節;痰瘀互結日久,故見關節腫脹、變形,屈伸不利,時緩時急,日久不愈,反復發作;舌質暗或紅,苔薄黃,脈弦滑或沉細澀均為痰瘀互結之象。
治法:化痰散結,活血化瘀。
方藥:二陳湯(《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合身痛逐瘀湯(《醫林改錯》)加減。茯苓15 g、半夏10 g、陳皮10 g、當歸12 g、生地黃6 g、川芎15 g、
紅花10 g、桃仁10 g、地龍10 g、沒藥6 g、土鱉蟲10 g、五靈脂10 g、懷牛膝15 g、秦艽15 g、羌活10 g、生續斷30 g、香附10 g。
方中陳皮、半夏、茯苓、地龍健脾燥濕,化痰散結;桃仁、紅花、當歸、川芎、沒藥、五靈脂活血化瘀,通絡止痛;羌活、秦艽、土鱉蟲、香附祛風濕,行氣止痛;牛膝、川斷補肝腎,強筋骨。全方共奏祛痰化濁、通絡止痛之功。
4 病案舉例
患者,男,72歲,2023年4月24日初診。以間斷性雙下肢關節腫痛6年為主訴。6年前患者無明顯誘因出現雙踝關節腫痛,繼而出現雙足趾腫痛,在當地診所給予藥物治療后稍緩解,未正規治療;2019年3月因勞累后出現雙踝、雙足足趾、右手第三遠指關節腫痛,行走不利,在當地縣醫院給予激素等藥物治療癥狀明顯減輕,停藥后癥狀反復發作;2019年4月8日至某醫院就診,給予藥物治療,效果不明顯,4月28日經人介紹遂來我院。時癥見:雙踝關節、雙足足趾腫痛、右手第三遠指關節腫痛,固握困難。脈弦細,舌質紅,舌苔黃膩。以痛風、肢體痹(濕熱阻絡)為診斷。予以清熱祛濕通絡。中成藥:熱痹清片、著痹暢片,每次3~8片,每日3次,口服;瘀痹平片,每次3~6片,每日3次,口服;雙氯芬酸鈉緩釋膠囊0.1 g,每日1次,口服;中藥外敷以消腫止痛。經治療癥狀好轉,中成藥服用半年停藥。2021年
5月6日因喝酒致右足第1跖趾關節腫痛復診。中成藥繼服7個月停藥。患者近期癥狀加重于2023年4月24日來我處就診,現癥見:雙膝關節腫痛,右足趾腫痛,局部發熱,活動不利,脈弦數,舌淡紅,苔薄。復查ESR 59 mm·h-1,類風濕因子(RF)118.90 IU·mL-1,抗鏈球菌溶血素“O”(ASO)97.61 IU·mL-1,C反應蛋白(CRP)101.31 mg·L-1,抗環瓜氨酸肽抗體(抗CCP抗體)35.6 IU·mL-1;血尿酸偏高。DR示:雙膝髁間嵴、左髕骨邊緣可見骨質增生樣改變,雙膝關節間隙顯示可。西醫診斷:類風濕關節炎,痛風性關節炎。中醫診斷:頑痹,痛風(濕熱痹阻證)。治法:清熱利濕,通絡止痛。方藥:川牛膝15 g、牛膝15 g、
木瓜30 g、透骨草30 g、伸筋草30 g、腫節風30 g、車前草30 g、醋延胡索20 g、生薏苡仁30 g、炒薏苡仁30 g、香附15 g、白茅根15 g。15劑,水煎服,2 d 1劑。中成藥繼服;西藥予艾拉莫德片25 mg,每日2次,口服;雙氯芬酸鈉緩釋膠囊50 mg,每日2次,口服;中藥外敷10組。
2023年5月9日二診,患者雙膝關節及右足趾腫痛基本消失,外敷藥已停5 d,西藥已停3 d,關節腫痛無反復。囑其堅持服藥,中藥外敷可以停用,其他藥繼續應用。中藥守上方15劑,水煎服,2 d 1劑。中成藥:熱痹清片、著痹暢片、瘀痹平片每次各8片,每日3次,口服;西藥艾拉莫德片25 mg,每日1次,口服;雙氯芬酸鈉緩釋膠囊50 mg,每日2次,口服。
2023年5月25日三診,患者現雙腿酸痛,余無不適,囑其堅持服藥。中藥守上方加丹參30 g、千年健15 g、菝葜30 g。15劑,水煎服,2 d 1劑。中成藥繼服。
2023年6月21日四診,患者癥狀明顯改善,關節酸痛基本消失,停用西藥。中藥守上方,15劑,2 d 1劑。中成藥繼服。
2023年7月24日五診,患者訴癥狀基本消失,行走如常,脈弦細,舌淡紅,苔薄黃。復查ESR?10 mm·h-1,RF 109.35 IU·mL-1,ASO 2.12 IU·mL-1,CRP 5.29 mg·L-1,抗CCP抗體29.9 IU·mL-1。中藥停服,中成藥熱痹清片每次8片,每日3次,口服;著痹暢片、瘀痹平片每次5片,每日3次,口服。
2023年9月12日六診,患者關節無癥狀,囑其服藥鞏固。中成藥繼服1個月鞏固治療。停藥至今病情穩定。
按語:本案西醫診斷為類風濕關節炎合并痛風性關節炎;患者下肢多關節間斷性腫痛,反復發作,疼痛較甚,屬于邪實候濕熱痹阻證。故治療清熱利濕為主。方用川牛膝、牛膝、木瓜、腫節風、車前草、生薏苡仁、炒薏苡仁、白茅根清熱利濕消腫;透骨草、伸筋草祛濕通絡;醋延胡索、香附活血通絡止痛;同時牛膝、薏苡仁又有扶正作用。配合中成藥熱痹清片、著痹暢片、瘀痹平片,共同達到祛邪(濕熱之邪)為主,輔以活血祛瘀(瘀血),同時兼以固本(虛),虛邪瘀兼顧。急性期配合西藥以抗炎鎮痛(祛邪),很快控制患者癥狀;之后西藥停服,病情無反復,中藥、中成藥也逐漸撤停,病情穩定。
5 預防與護理
①發病期間應臥床休息,但臥床時間不宜超過1周,待疼痛緩解后,即可下地活動。②節飲食。特別要注意減少飲食中的肥甘厚味,宜食清淡易消化之品。蔬菜、水果可適當多吃,并可適當多飲水,使大小便保持通暢。③防外邪。居處不能潮濕,勞作汗出以后,要及時更換內衣,夏季不可貪涼,冬季注意保暖。④勤鍛煉。體育鍛煉可增強氣血疏通,使筋骨堅強有力,因此患者可選擇適合于自己年齡和愛好的體育項目,堅持鍛煉[6]。
6 轉歸及預后
痛風如及時治療,并注意調攝,可使發作減少,以至完全治愈。反復頻繁的發作,(下轉第52頁)
(上接第42頁)不僅重傷氣血,而且可導致關節腫脹、畸形,活動受限,影響正常的工作生活。
7 結 語
痛風既是中醫古老的疾病,也是臨床上常見病、多發病,歷代醫家對其論述也較多。元代朱丹溪明確地提出“痛風”的病名,其認為痛風病因病機有風、痰、濕、瘀之分。現代中醫所論痛風包括西醫學的痛風(痛風性關節炎),西醫學的痛風是尿酸鹽沉積在關節囊、滑囊、軟骨、骨質、腎臟、皮下及其他組織引起相應的病損及炎癥性反應的一種風濕病。痛風的發病原因眾多,但概括起來不外“虛邪瘀”三個方面。其核心病機為脾的納運和腎的升清降濁功能失調。痛風發作期以邪實為主,緩解期以正虛為主。實以濕熱、痰濁、瘀血為主,虛以脾腎虧虛及功能失調為主。本病多數患者初起發病急驟,反復發作,病程較長;部分患者久則變形殘疾。因此,痛風一旦確診,應積極及時正確治療,可完全治愈;若不積極面對,無忌飲食,失于調攝,病情將會逐漸加重,嚴重者將會影響生活工作。
參考文獻
[1] 李滿意,婁玉鈐.痛風的源流及歷史文獻復習[J].風濕病與關節炎,2018,7(6):57-62.
[2] 婁玉鈐,李滿意.特殊痹的源流及臨床意義[J].風濕病與關節炎,2013,2(11):49-57.
[3] 婁玉鈐,李滿意.風濕病的二級病名及其相互關系探討[J].風濕病與關節炎,2013,2(12):53-57,64.
[4] 婁玉鈐,婁高峰,婁多峰,等.基于“虛邪瘀”理論的風濕病學科體系建立及相關研究[J].風濕病與關節炎,2012,1(1):10-15.
[5] 婁玉鈐,陳永前,李滿意,等.應用風濕病虛邪瘀理論診治痛風的體會與探討[J].風濕病與關節炎,2018,7(5):58-61,72.
[6] 路志正,焦樹德.實用中醫風濕病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6:336-342.
收稿日期:2024-01-21;修回日期:2024-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