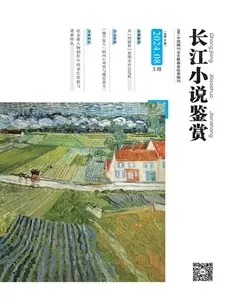本土·詩意·現(xiàn)實性
韓正路
[摘? 要] 承續(xù)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本土化寫作,范小青在21世紀的小說創(chuàng)作中繼續(xù)還原江南水鄉(xiāng)的水澤風貌和文化景象,并以蘇城景觀之名擬定小說標題,彰顯出濃郁的地域特色。作家以慣有的生活體驗進行了小說語言的本土化提煉,吳儂軟語和文學性語言的融合流露出靜謐典雅的江南古韻。經(jīng)歷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年變法”后的范小青在21世紀的小說創(chuàng)作中進一步剖析城市建設和小人物的命運軌跡,在追尋江南詩意情調(diào)的同時,以現(xiàn)實性的關懷盡顯吳文化以人為本的獨特韻致。
[關鍵詞] 范小青? 新世紀? 長篇小說? 倫理建構
[中圖分類號] I06? ? ? ? [文獻標識碼] A? ? ? ?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08-0031-04
自1987年創(chuàng)作長篇小說《褲襠巷風流記》以來,范小青關注蘇州地域文化,為吳地的小說寫作打開了新的局面。在接下來的十年時間里,范小青沿著“蘇味小說”的步伐穩(wěn)步向前,專注于書寫蘇州的地理風情和人文景觀,將寫作的視角聚焦于蘇州小巷、蘇州市井人物以及蘇州的歷史典故等,并憑借蘇式“文化小說”在文壇出名。1997年出版的長篇小說《百日陽光》成為范小青寫作的轉折點,此后的范小青帶著樸素的情懷和作家的責任感優(yōu)雅地走出蘇州文化的圈子,開始接觸重大現(xiàn)實生活題材。在21世紀的小說創(chuàng)作中,范小青一面保留江南水鄉(xiāng)區(qū)域文化的印記,以詩性的風格延續(xù)吳文化的魅力;另一面關注凡俗生活的蕓蕓眾生,直面?zhèn)鹘y(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發(fā)展的融合與碰撞,探索當下人的身份缺失與追尋等。作家敏銳地把握古城蘇州的脈搏與氣息,在荒誕式的書寫背后投注現(xiàn)實倫理的深度哲思。“敘事視點、敘事人稱、結構安排、文體風格選擇、詞匯選擇、不同的敘事時間意識、人物形象的塑造等形式因素都會透露出人意表的倫理維度。”[1]江南吳文化所滲透出的倫理意識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形構著作家范小青特有的思維觀念及人格作風,并制約著她的小說創(chuàng)作,使其作品打上了深刻的地域和時代烙印。范小青新世紀小說中的敘事背景、標題命名、敘述語言、文體風格等要素都以不同的視點揭示出吳地人家敘事特有的倫理尺度。
一、固定的吳地敘事背景
范小青雖出生于上海松江,但三歲便隨父母來到蘇州,“也是蘇州的小巷里長大起來的”[2]。作為純粹地道的蘇州女性,她小說中出現(xiàn)的區(qū)域自然都是以作家生活過、體驗過的現(xiàn)實場景為原型加以構建的。她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力求還原故鄉(xiāng)風景的本真面貌,于文學的想象和虛構中建構特有的精神家園,并傳達出自我熟知且真實的故土生命體驗。“吳地素有水鄉(xiāng)澤國之稱,水面占土地總面積的17.5%。京杭大運河西北東南貫通,成為著名的江南水鄉(xiāng)。”[3]這里位于長江三角洲下游的沖積平原區(qū),流域內(nèi)河網(wǎng)縱橫,湖泊密布,水路四通八達,商貿(mào)發(fā)展自古繁盛。江、湖與河的描繪在范小青的小說中隨處可見,構成了小說敘事的背景和鮮明的文化符號系統(tǒng),印證了吳地水網(wǎng)密布,交通便利的區(qū)域特點,也營造出江南水鄉(xiāng)寧靜悠遠的詩意氛圍及超凡脫俗的浪漫情調(diào)。作家用心領略江南水鎮(zhèn)的靜謐與溫柔,勾勒出一幅象征和諧、安寧的詩意世界,作品流露出沁人心脾的水文化韻味。
“季小玉的家,在蘇州鄉(xiāng)下的一個小鎮(zhèn)上,那個鎮(zhèn)叫黎里,是一個水鄉(xiāng)小鎮(zhèn),境內(nèi)河道縱橫,湖泊星羅棋布,連它的名字也是水淋淋的。”
——范小青《城市片斷》
吳地水網(wǎng)密布,河道縱橫,來往船只自然也成了吳地主要的交通工具。“吳人以船為車,以楫為馬。”[3]船只往來于吳地的各條河流之間,承載著不同時代珍貴的航行記憶,在交通運輸和金融發(fā)展中發(fā)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水之柔,舟之緩,交相輝映,營造出夢幻般的江南水鄉(xiāng)情境,彰顯出吳文化區(qū)雅致的人文底蘊。
“蘇杭班在繼續(xù)開著,它仍然是那樣的速度,仍然是那樣的姿勢,船頭把水劈開,船尾那兒,水又合攏了。”
——范小青《蘇杭班》
特殊的江南水鄉(xiāng)環(huán)境也使得蘇州處處點綴著大大小小的橋梁,為古城蘇州增添了古典的韻味與魅力。蘇州橋梁在作家的筆下有著自然精準的勾勒和把握,還原出吳地小橋流水的景觀特色和各類橋梁的水韻形態(tài)。
“大橋有大橋的氣勢,小橋亦有小橋的風姿,蘇州的小橋小巧玲瓏,靜臥于碧波之間,別具匠心。”
——范小青《城市片斷》
除了地理景觀,范小青的小說還描寫了許多的吳地區(qū)域文化景觀。如長篇小說《城市表情》中的豆粉園,《城市片斷》中的奪園、知音軒和漏透窗,以及系列短篇小說中的鷹揚巷、南園橋、定慧寺等。它們不僅再現(xiàn)了蘇州古典園林和橋寺街巷的景觀構造特色,更融入作家的生命體驗中,抒發(fā)了濃郁的江南詩性情懷。范小青以自己的故鄉(xiāng)面貌作為小說創(chuàng)作的藝術原型,將吳地的地理文化景觀選為小說敘事的背景,正是一次現(xiàn)代意義上的精神返鄉(xiāng)之旅。這些文化小說以范小青的故鄉(xiāng)作為藝術原型,滲透了作家最真實的生活體驗,形構出最真切的環(huán)境變遷和最地道的吳地人家生活面貌,暗含著傳統(tǒng)古典文明和現(xiàn)代都市文明的融合與碰撞,也印證了范小青的蘇州經(jīng)驗仍在新世紀發(fā)揮余熱。作家用心勾勒古城生活面貌,專注于書寫江南水鄉(xiāng)的婉約與淡雅,飽含著自我對吳地文化的深沉眷戀和時代變遷的無限感慨。一篇篇固定敘事背景的江南水鄉(xiāng)故事在作家的筆下自然流露,娓娓道來。它們溫柔、淡雅,一如平靜緩動的太湖水,閃動著溫潤的光澤,滲透著詩性的韻味,展現(xiàn)出江南吳文化特有的風采魅力。
二、本土化的標題語言
范小青適時選取蘇州本土的地域景觀之名來擬定小說標題,選用和仿用的兼顧營造出久違的親切感和歸屬感。這些章節(jié)標題中的地域景觀涵蓋蘇州的橋、寺、園林及街巷等各類江南地標,以貼近現(xiàn)實生活的本土特性彰顯江南吳地的濃郁文化氣息,以新舊景觀的跳躍式書寫還原江南古城的歷史變遷。如長篇小說《城市片斷》中的“奪園”“豆粉園”等章節(jié)標題,體現(xiàn)的恰是江南園林的古典特色。“幽蘭街”“鷹揚巷”“南園橋”“定慧寺”“桃花塢”“六福樓”等短篇小說標題呈現(xiàn)出特有的詩意景觀和璀璨人文。涵蓋本土印記的標題命名為新世紀的范氏寫作打開了小說敘事的另一扇窗口,以通俗醒目的特色吸引讀者進入?yún)堑貧v史文化及建設變遷的走訪探尋中。作家采用平等化的定位和交談式的口吻來建構小說內(nèi)容,以類似全知化的視角和吳地人民樂于接受的敘述方式再現(xiàn)蘇州古城的歷史滄桑。作家描摹古典園林遭受的現(xiàn)代文明的沖擊,披露吳地子民在不同時代環(huán)境下經(jīng)歷的考驗和命運抉擇,呈現(xiàn)出具有民間生活質感的文化體驗。
范小青常年生活在蘇州古城,吳地方言的影響和滲透使她擯棄了精英化和藝術化的處理,力爭呈現(xiàn)出具有濃郁生活質感的蘇州方言,韻味豐富且樸素生動。范小青慣用蘇州人民習以為常的說話方式來鋪陳故事的敘述,用耳熟的口吻和經(jīng)過提煉處理的吳區(qū)方言來還原江南世俗的點點滴滴,試圖用純正地道的本土語言喚起吳地人民潛在的情感共鳴。由于作家對蘇州人民的思維方式、心理情緒及行為習慣等有著細致的觀察與切身的感悟,她在小說創(chuàng)作中側重以源自本土的視野來塑造人物及描繪社會重大現(xiàn)實問題,以原初的眼光還原特定時代和環(huán)境下蘇州人民生活的斑駁紋理。作家以詩性的視角觀察吳地人民的日常生活,在自覺回歸江南本土的過程中,打開了歲月沉淀下的蘇州記憶和慣有的生活體驗,將吳地人民熟知的吳儂軟語融入作品的語言表述中,于字里行間盡顯溫婉典雅的江南古韻,極大地提升了作品的民俗化色彩。“吳語體現(xiàn)了濃濃古老的遺韻和一種書卷氣,句子結尾的語氣詞不用‘了而用‘哉,一個‘哉字便能拖出無限的韻味。”[6]在吳儂軟語的耳濡目染下,范小青小說語言的“蘇味”氣息顯得格外濃厚,它喚起了當?shù)鼐用駶撛诘娜粘;貞洠瑤Ыo人回歸故鄉(xiāng)的親近和舒適感。
“蘇州到梅埝,坐船坐煞人哉。蘇州到梅埝,老早就通汽車哉。他會不會不曉得噢。他會不會頭一次來噢。”
——范小青《蘇杭班》
“坐煞人哉”和“通汽車哉”正體現(xiàn)出吳語軟糯的特點,暗含吳地方言習用的傳統(tǒng)音韻。作家對吳儂軟語的信手習用,使得小說語言的“蘇味”氣息顯得格外濃烈,緩慢的節(jié)奏蘊藏著江南吳地方言特有的精致柔美和委婉細膩,其中滲透著閑適和愜意,也暗含言有盡而意無窮的從容和淡雅。
“醉里吳音相媚好”,吳方言唯美柔和,婉轉動人,清雅綿軟,如太湖水般至柔至善,緩慢的節(jié)奏盡顯江南文化特有的人文底蘊。在范小青的新世紀小說中,文學性的敘述語言和蘇州地區(qū)的地域方言完美融合,作者營造出原生態(tài)的江南水土氣息和生活質感,極為貼近吳地的風土人情和民風民俗。太湖流域悠久的水文化指引著作家的文學創(chuàng)作,吳地親切的方言也在不斷規(guī)范著作家講故事的方式,進而成為范小青作品里一道靚麗的風景線,建構起作家自我與吳地人民在精神文化上的血脈關聯(lián)。
三、詩意與現(xiàn)實的徘徊
丹納的《藝術哲學》對于希臘的氣候環(huán)境和當?shù)厝嗣竦男愿裉刭|有著這樣的描述:“(希臘)沒有酷熱使人消沉和懶惰,也沒有嚴寒使人僵硬遲鈍。溫和的自然界使人的精神變得活潑,平衡。”[4]無獨有偶,吳文化區(qū)的蘇州地處亞熱帶季風氣候區(qū),屬溫暖濕潤、梅雨顯著的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帶。得天獨厚的江南環(huán)境滋養(yǎng)出性格溫和、溫文爾雅的蘇城民眾。太湖流域如詩如畫的水鄉(xiāng)美景營造出愜意浪漫的醉人情境,水澤湖泊氤氳的江南古典氣息使得當?shù)厝顺缥纳械拢瑧T以詩性的思維和態(tài)度來賞析事物。在21世紀的小說創(chuàng)作中,范小青適時引用古典詩文來醞釀江南詩性的情調(diào)。長篇小說《城市片斷》中,范小青引用大量的詩詞對聯(lián)來描述軒、亭、窗、閣、扇等古典景觀文物,以詩性的筆觸追尋歷史文化的淵源。
“……韋應物:洞庭須待滿林霜——待霜亭;蘇軾:三峰已過天浮翠——浮翠閣;李俊明:借問梅花堂上月,不知別后幾回圓”
——范小青《城市片斷》
這里對古詩文的引用闡釋了景觀命名的詩詞淵源,以詩意的筆觸營造蘇州古城濃郁的古典文化氣息。女作家溫和婉轉的敘事基調(diào),也使她不經(jīng)意間流露出特有的詩性氣質,盡顯江南吳地細膩而淡雅的古典氣息。這種詩意的情調(diào)還可體現(xiàn)為作品所營造的煙雨江南的情境氛圍,這在范小青小說的情節(jié)和場景的敘述中時隱時現(xiàn)。
“他現(xiàn)在常常回想起當年父親拉著他的手去到南方小鎮(zhèn)的情形,那個小鎮(zhèn)是濕漉漉的,天老是陰著點雨,小街上的石子是濕潤的。”
——范小青《醫(yī)生》
煙雨中的江南小鎮(zhèn)如詩如畫,以陰濕的氣候環(huán)境盡顯水文化因子的獨有脈搏和飄然氣息。作家以詩意的筆觸描繪細雨如絲的江南,在煙雨中醞釀溫婉動人的情感,營造出含蓄典雅的南方底蘊。詩意的精神內(nèi)涵在范小青作品的人物性格塑造和文化內(nèi)涵的闡發(fā)中亦有所折射。《女同志》中的主人公萬麗的“小家子氣”恰是江南水鄉(xiāng)文化的性格影射。《城市片斷》中的奪園、豆粉園以及長洲路等古城風貌所滲透的歷史文化和人物傳說,包括對蘇州評彈彈詞的摘錄,都蘊含著蘇州豐富的吳文化底蘊。
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隨著范小青當選為江蘇省作協(xié)副主席,其小說創(chuàng)作也在悄然間開啟了“中年變法”[5]。現(xiàn)代工業(yè)和商業(yè)化的浪潮逐步?jīng)_擊著江南傳統(tǒng)的生活方式,都市化的潮流促使這座古城進入到一種全新的蛻變和建設之中,也讓心系地域的范小青在創(chuàng)作中進入轉型期,逐步聚焦時代現(xiàn)實,關注城市發(fā)展中面臨的改革考驗和經(jīng)歷的陣痛痼疾。早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的小說創(chuàng)作中,范小青就嘗試摒棄過往的純粹地域性寫作,轉而以當下社會熱點問題作為寫作的素材。如《城市民謠》對下崗工人錢梅子在商業(yè)大潮中炒股、開飯店等經(jīng)歷的敘述,《百日陽光》對鄉(xiāng)鎮(zhèn)發(fā)展和房地產(chǎn)投資的描述,均表現(xiàn)出了作者對市場經(jīng)濟發(fā)展和時代氛圍的感觸與哲思。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城市經(jīng)驗的不斷豐富,作家對現(xiàn)實剖析的程度也不斷加深。長篇小說《城市表情》聚焦南州市的舊城保護與改造;長篇小說《城市之光》描繪青年農(nóng)民田二伏進城務工后的尷尬處境;長篇小說《桂香街》講述下崗女工林又紅陰差陽錯地當上居委會主任后經(jīng)歷的瑣碎生活和基層紛爭;長篇小說《女同志》敘述女教師萬麗在進入機關工作后經(jīng)歷的升遷變化以及機關同事之間的相互嫉妒、欣賞、斗爭……范小青的作品聚焦社會現(xiàn)實問題,印證著當代本土作家日益豐富的生活體驗。對日常重大現(xiàn)實題材和小人物命運的關注,不僅源于作家本人成長閱歷的豐富,更可以從吳文化的具體元素中尋求合理的闡釋。“吳地是‘耕讀文化,‘耕是謀生存,‘讀是謀發(fā)展,象征經(jīng)世致用的實干精神。”[6]范小青對古城發(fā)展的關注和對小人物命運的關切,正體現(xiàn)出以人為本的吳地文化精神,可視為耕讀文化的現(xiàn)實指涉。
現(xiàn)代都市文明的體驗和吳地古典文化的糅合融會,使得21世紀的范小青既堅持了自己古典詩性的藝術準則和價值立場,同時也在當下的時代境遇中不斷貼近現(xiàn)實、觀察時事、直面改革,于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的融合中描摹群體百態(tài)和人性諸貌,以包容性的心理呈現(xiàn)出詩意與現(xiàn)實的徘徊姿態(tài)。這種徘徊姿態(tài)也可視為“變”與“不變”的兼容,不變的是范小青對吳地水鄉(xiāng)文化的堅守和對小人物的刻畫,變的是范小青對于現(xiàn)實邊界和內(nèi)涵的擴充。《香火》《我的弟弟叫王村》《滅籍記》和《戰(zhàn)爭合唱團》等作品中對人物身份危機和事物混沌性的探索,更是為這種現(xiàn)實視域增添了現(xiàn)代主義的意味。
四、結語
范小青的21世紀小說創(chuàng)作始終堅持以吳地作為作品的敘事背景,在江南水鄉(xiāng)的自然和社會環(huán)境的熏陶下開展地域化的寫作,與蘇州地區(qū)的吳文化建構起深層的關聯(lián)。作家承續(xù)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區(qū)域設置,在回歸江南水鄉(xiāng)的過程中,以本土作家固有的筆觸構建吳地小說敘事的新型倫理模式,力圖呈現(xiàn)具有原生態(tài)生活質感和濃郁詩性韻味的蘇州古城。“所謂地域文化特征,應是就整體而言的,構成其整體特征的單個文化因子也許并不獨屬于該地區(qū),但各因子的獨特組合(包括量的多少和組合的方式)卻是該地區(qū)獨有的。”[7]水文化的共有因子與太湖古城的獨有氣息水乳交融,以特有的地域性組合造就了范小青小說浪漫的氣息與詩意的風格。從古城改造到基層治理,范小青在時代車輪的推動下轉型聚焦社會重大題材,以作家的良知持續(xù)關注當下社會熱點。對下崗工人、農(nóng)民工群體、基層群眾及官場女性的命運書寫和心理探微,充分彰顯出范小青強烈的社會責任意識和崇高的使命感。吳文化以人為本的元素指引著作家的現(xiàn)實思考與人性探索,蘇州古城的文化余熱也促使作家在現(xiàn)實與詩意中徘徊兼顧。范小青21世紀小說的創(chuàng)作內(nèi)容既可從吳地的時代及環(huán)境要素中尋求相應的解釋,也可從蘇州的傳統(tǒng)文化及地域景觀中獲取合理的歸屬。在保持與蘇城人民精神文化的血脈聯(lián)系中,范小青以本土作家的融入性姿態(tài)勾勒出吳地人家的世俗百態(tài)和地域變遷。
參考文獻
[1] 伍茂國.現(xiàn)代性語境中的文學敘事倫理學[J].北方論叢,2011(3).
[2] 范小青.小巷人家[M].北京:知識出版社,1994.
[3] 許伯明.吳文化概觀[M].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
[4] 丹納.藝術哲學[M].傅雷,譯.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8.
[5] 范小青.在變化中堅守,或者,在堅守中變化[J].揚子江評論,2009(1).
[6] 徐國保.吳文化的根基與文脈[M].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18.
[7] 朱曉進.“山藥蛋派”與三晉文化[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責任編輯 羅?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