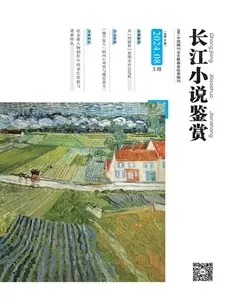《葡萄牙的高山》中的身體現象探析
鄧微
[摘? 要] 《葡萄牙的高山》巧妙地熔煉了哲學思辨、宗教隱喻與身體敘事等多重元素,創造出一個意蘊深廣的文學世界。揚·馬特爾于細微之處關注與身體相關的生命體驗,借由圣多美黑奴的身體苦難闡明被囚禁壓制的身體只能陷入蒼白枯竭的陰郁狀態,而瑪麗亞夫婦身體的性愛知覺則凸顯了美妙的生命體驗。托馬斯倒著行走的身體姿勢潛藏著對信仰的懷疑,其備受蹂躪的多毛身體暗示了人的動物性,從而引發了信仰的崩塌。另外,拉斐爾魔幻尸體中的各色物品賦予了身體全新的生命媒介意義,從獨特的視角描摹了其作為農夫的一生。同時,拉斐爾身體的獸形幻化與蘊含其中的深刻宗教隱喻,激發了讀者對神、人與動物之間微妙關系的思考。
[關鍵詞] 揚·馬特爾? 《葡萄牙的高山》? 身體現象
[中圖分類號] I106.4? ? ? [文獻標識碼] A? ?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08-0080-04
揚·馬特爾是加拿大著名作家,他的作品亦真亦幻、意涵豐富,布局結構奇特精巧,敘事引人入勝。《葡萄牙的高山》是一部具有出色文學想象力的長篇小說,充滿哲學思辨、宗教隱喻與動物敘事,糅合了信仰、理性、生態、身份建構、家園意識等多重意蘊。相較《少年Pi的奇幻漂流》,《葡萄牙的高山》受到學界的關注并不多。自該小說于2016年付梓,學者主要從家園意識、信仰焦慮、動物批評、意象研究、生態批評、創傷視域等方面探析文本深層符碼。小說中的身體敘事與生命體驗、宗教信仰、人與動物的關系等深層文本內涵相關,是理解小說的一個關鍵切入點。本文聚焦小說中典型的身體現象,依據身體理論與相關的文本細節,分析黑奴與瑪麗亞夫婦的生命體驗,研究托馬斯與拉斐爾身體所具備的豐富意蘊,以期拓寬文本研究視野。
一、生命體驗:黑奴的身體苦難與瑪麗亞夫婦的性愛知覺
身心關系問題是西方哲學史的核心問題之一,有關身體與意識的思辨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斷演變,身體則經歷了從壓抑缺席走向價值凸顯的過程,即由傳統的意識哲學轉向身體哲學。在傳統西方哲學中,身體與意識素來處于二元對立的思維范式下,哲學家們高揚意識而貶斥身體,把人視作精神性存在。尼采“一切從身體出發”的原則掀起了一場身體革命,解構了以往形而上學的哲學理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里欲望化身體的出場提示著人類的生命激情;梅洛龐蒂的身體現象學發展了具身性,從知覺出發構建身體、心智與世界三者的一體化;福柯的身體理論則探究了被權力、話語、知識等塑造的身體,考察了身體如何客體化的進程;后現代消費社會對身體更加關注,消費文化允許大眾表現身體,身體也被視為欲望與快樂的載體……可見,19世紀末以來的西方哲學理論愈來愈聚焦身體研究,身體的重要性不斷被挖掘并闡釋,相應的,與身體相關的生命體驗也成為許多作家描繪的焦點。《葡萄牙的高山》中,馬特爾同樣關注身體中的生命氣韻,無論是蒼白枯竭的生命力量還是豐沛美妙的生命體驗都在小說里有所展現。馬特爾書寫了圣多美黑奴的身體囚禁與苦難,黑奴勞苦的身體只是擁有枯竭的生命力。相反,小說通過瑪麗亞夫婦和諧的性愛生活,凸顯宗教道德壓制下美妙的生命體驗。
首先,烏利塞斯神父的布道經歷彰顯了殖民地權力規訓下黑奴的身體苦難,折射了身體蘊含的生命氣息對精神涵養的重要性。烏利塞斯神父觀察圣多美島,他的日記展現了眾多黑奴的視覺身體由于嚴苛的環境而陷入的陰郁狀態與絕望的沉默。圣多美作為17世紀“中間通道”的中轉站,遍地都是失落的非洲靈魂,而烏利塞斯神父主動要求承擔拯救黑奴靈魂的傳教使命。他堅定信仰、忠于上帝,為販奴船上的黑人洗禮,向他們誦讀《圣經》,但并不關心他們能否理解陌生的語言信仰。他篤信“無論從何而來的靈魂都是靈魂,他應當被祝福,應當被帶到上帝的仁愛之前”[1]。烏利塞斯神父對上帝的過度信賴與過分強調導致他對身體的無知及對黑奴勞苦身體的無視。在面對圣多美潮濕的季節和惡劣的環境時,他的身體歷經磨難、虛弱不堪,身體上直觀的痛苦令他開始關注非洲黑奴身體的苦難。殖民者以黑奴身體作為規訓的場域,在圣多美確立話語統治權。為達到肉體最大的經濟學效益,死亡或者生病的奴隸被無情拋入大海,生存下來的奴隸則要接受暴力管理。其中一名女性因為反抗監工被打成重傷死去,在權力的角斗場中,處于劣勢的黑奴只能接受身體飽受摧殘的命運。“身體時常是人類原始情緒指向的目標, 懲罰最終涉及的也總是身體, 因此身體變成各種權力的角斗場。”[2]失去自由的黑人他者在暴力懲戒中轉化為缺乏生氣的身體機器,變得“麻木、消極、冷漠”[1],他們絕望地虐待自己的身體,陰郁地吞食土壤或自相殘殺。烏利塞斯神父先是無動于衷地注視著這一切,直至與一位垂死女奴哀傷的目光相對,于是頓悟:他的祈福僅僅是“言不由衷的布道詞句”[1],被白人殖民者宣稱為更低賤的黑人其實與白人平等。身體是意識的載體,缺乏身體的支撐,烏利塞斯的布道是徒勞無功的,他的精神祈禱對黑奴勞苦的身體幾乎沒有影響。小說借由黑奴身體上的苦難展現了殖民者的罪惡與殖民地宗教的虛偽,也暗示了自由健全的身體對接納精神信仰的重要意義。
《葡萄牙的高山》還書寫了瑪麗亞夫婦生活里美妙的身體體驗,突出身體的性愛知覺。梅洛龐蒂指出:“性愛的知覺通過一個身體針對另一個身體,在世界中而不是在意識中形成。”[3]性欲不是簡單作用于意識的知覺刺激,而是具備置身性情境中人與人之間情感交流的意向性。瑪麗亞與丈夫拉斐爾在婚姻中保持著親密和諧的性關系,他們的性愛達到靈肉合一的境界,展現二者身體主體的交流意向性。瑪麗亞贊美身體,坦率地談論性欲:“我的身體已經準備就緒,心也蠢蠢欲動,性欲卻依然沉睡……然后拉斐爾和我走到一起。在樸素的衣服和羞澀的舉止之下,我們發現了自己身體的美好,仿佛土地里隱藏的金子。”[1]他們享受性愛的愉悅,注重身體的快感享受,并在這種享受中生成生存的意義。相反,瑪麗亞父母只會對婚姻與性愛保有暗夜敏感的羞澀性,把性欲比作沙漠,除此之外就是艱苦的勞作。他們堅守基督教禁欲主義的思想,壓抑生命本能與身體激情。因為基督教神學強調靈魂凌駕身體,應服從于上帝。身體只是欲望的滋生之地、原罪的負載之所,唯有禁欲主義與順服靈魂才能與至善融合,獲得上帝恩典的永恒幸福。這種認知模式最開始在柏拉圖的哲學中體現,他的“理念說”論證了靈魂的高尚不朽與身體的污穢卑下。中世紀的基督教神學中,揚心抑身的柏拉圖主義得到綿延與改造。而近代笛卡爾“我思故我在”的意識哲學令身體受到理性靈魂的詰難,尤其是啟蒙哲學將感性身體視為機器,人則被抽象為意識與精神,身體陷入被理性遮蔽的黑暗與失語中。殊不知身體同生命一樣,是尼采所強調的旺盛的權力意志與充溢攀升的本能,不應受到上帝、神學或意識的壓制。正是由于瑪麗亞關注性愛體驗,她才非常熟悉丈夫的身體,了解丈夫死前的生活。因此,從瑪麗亞的角度來看,拉斐爾的離奇尸檢是合理的。而歐賽比奧只是在精神上認識他的妻子。這部小說對歐賽比奧夫婦的日常生活著墨不多,僅表現了他們對宗教信仰的討論。歐賽比奧的妻子被描繪成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她以約伯自勉。即使作為一名病理學家,歐賽比奧由于缺乏對妻子身體的了解,不可能查明她的死因。兩相對比,馬特爾暗示了缺乏身體意識的后果,頌揚了突破神學壓制的身體性愛知覺的意義。
二、信仰崩塌:托馬斯的身體書寫
托馬斯的身體是馬特爾重點描繪的對象之一,托馬斯的身體現象隱喻著其生存狀態與信仰的變化。親人接二連三死去后,托馬斯總是無緣無故地哭泣,此時他的身體承載著悲傷與脆弱。而倒著行走的身體姿勢直接表明精神上的創傷,背對上帝的身體象征著拒斥未來與抗議信仰。之后,托馬斯懷著對基督教的挑釁精神,在驅車前往葡萄牙高山區的途中,身體飽受蹂躪,寄生蟲令他的身體瘙癢無比。當他涂抹去虱藥膏時,身體的灼燒感與導致其身體的不適感增強。身體的痛苦侵蝕著他的精神,某種程度上他成了患難中受試煉的約伯式人物。他軋死瑪麗亞的孩子后,罪惡感加重了身體的痛苦。不過身體的痛苦并沒有使他對信仰頓悟開竅,反而讓他注意到自身的動物性,猩猩十字架苦像的發現則直接促成了其信仰的崩塌。
托馬斯最為引人注目的身體現象是倒著行走,這種身體姿勢表達了家庭創傷,蘊含著對未來的拒斥,潛藏著對信仰的懷疑。“身體是一種自然表達的能力”[3],梅洛龐蒂認為身體本身是一個富有表現力的空間,蘊含著個人存在的意義。“情境的變化又對身體顯現出新的外觀,提出有待回應和解決的新問題,從而又提供新的實踐意義,引發新的本能行為。這使得身體與情境之間,或者毋寧說意識與世界之間,通過身體形成一種可持續進行的、類似‘提問-回應的對話過程。”[4]托馬斯在一個星期之內失去了兒子、妻子與父親,他對世界徹底心碎。面對家庭的巨變,托馬斯未能疏解內心的創傷,開始倒著走路。一方面,這種走路姿勢是一種奇特的默哀方式,象征性地為其提供了重溫過去記憶的機會。由于喪親之痛,托馬斯不知所措,倒著走是他生活中唯一能繼續前進的方式。拉斐爾在失去兒子后也是如此:他向后走去哀悼他的兒子。在小說第三部分,倒著走的姿勢發展成為圖伊澤洛鄉村的送葬習俗,因此,倒著走成了一種吊唁的儀式,也成了一種隱喻——因為死者不再有未來,倒著走是生者緬懷死者的一種方式。這種身體行為表達了失去親人后的悲傷,同時“向后走”還象征著記憶的向后回溯。正如瑪麗亞·卡斯特羅在這部小說中所說:“從前,回憶僅僅是偶爾的娛樂。忽然之間,它成了你的僅剩之物。”[1]倒著走讓失去親人的他們陷入重溫過去記憶的絕望境地。另一方面,這種向后走的姿勢是對普通向前走路姿勢的一種違背,象征著對未來的拒絕。眾所周知,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因素之一就是人類總是保持向前看,追求更光明的未來,所以面朝前走表現了人類探索未知世界的希望。而托馬斯倒著走的身體動作則表明了對命運無常現實的逃避與未來的拒絕。與此同時,托馬斯用背對上帝的走路姿勢表達對宗教的懷疑與抗議。他的妻子在臨死前始終緊握一尊十字架苦像,而虔誠的信仰并未令她得到上帝救贖,于是托馬斯內心對宗教信仰產生懷疑。他的身體成為信仰動搖的能指,之所以倒著走路,“他是在抗議”[1]。身體動作實施的過程同時也是意義表達的過程,意義在身體姿勢的變形中生成并被理解[5]。托馬斯變形的身體姿勢傳達著內心創傷與對上帝的抗議。
此外,托馬斯多毛的身體遭受的苦楚使他覺察到自身的動物性,進而引發信仰的崩塌。毛發是文學中重要的象征符號,傳達著豐富的信息,例如《圣經》中參孫的頭發是超人力量的來源。托馬斯全身毛發濃密,活像一只猿猴,所以他厭惡多毛的身體,重視理發,保持干凈整潔。旅途中,他的身體感染了虱子,備受瘙癢折磨。于是他在荒野里瘋狂抓撓,發出像動物般舒爽的叫聲,露出動物般的表情動作。馬特爾還把托馬斯的手比作動物的爪子和蜂鳥的翅膀,在這種頗具喜劇氛圍的場面里,讀者仿佛能窺見人類的返祖現象。通過托馬斯,作者暗示了人類的動物性。除了濃密體毛招致的虱子,托馬斯還需忍受事故中火焰上身的燒灼感,焦黑的臉與燒焦的頭發訴說著他旅途中經受的苦難。砍樹與換輪胎則使托馬斯身體酸痛難當,他開始思考苦難對人的意義。痛失至親、身體飽受折磨的托馬斯成了約伯式的人物,約伯的虔誠在患難中的試煉未減分毫,而托馬斯卻越來越堅定反抗上帝的決心。在圖伊澤洛發現耶穌苦像時,他的信仰瞬時崩塌。因為耶穌苦像本應是人的模樣,但烏利塞斯神父雕刻的十字架苦像卻是一只黑猩猩,這無疑諷刺了基督教的信仰。上帝之子被降格為動物,展示了人類的墮落。如此一來,人類的優越性被剝奪,苦像令托馬斯頓悟:人類是“直立行走的猿猴”[1],這一頓悟暗合托馬斯如猿猴一般的多毛的身體,表明人的動物性。十字架上的猩猩則顛覆了人與上帝之間神圣的聯系,呼應了達爾文的科學進化論,至此,托馬斯的信仰在與上帝的角逐中全面崩潰。
三、身體變形:拉斐爾的魔幻尸體
《葡萄牙的高山》的死亡主題突出,小說三部分均涉及了摯愛的死亡,存在眾多尸體描寫。例如,托馬斯兒子加斯帕爾的尸身輕柔,“仿佛一只大號的毛絨娃娃”[1];圣多美一個死去的奴隸“身上刻著深深的傷痕,頭被劈掉了一半”[1];瑪麗亞孩子的傷口與十字架上耶穌的傷口一致,“折斷的手腕、折斷的腳踝、身側很深的傷口,擦傷和刀傷”[1];存有巨人觀的尸體腐敗膨脹的過程敘述;彼得妻子臨死前呆滯身體的刻畫等。其中,拉斐爾變形的身體極富魔幻現實主義色彩。尸體中的生活物品從新奇的角度賦予身體以生命媒介的意義。同時,拉斐爾身體的獸形幻化與其中的宗教隱喻則重新探討了人與動物之間的關系。
馬特爾運用魔幻現實主義手法塑造拉斐爾的尸體,闡明身體與日常生活的積極聯系。身體與日常生活緊密相連,生活是身體權力意志鍛造的結果,身體則是生活的觀照物[6]。身體總會默默流露出生活與歲月的痕跡,正如小說中提及的:“每具遺體都是一本寫滿故事的書,每個器官都是一個章節,所有的章節由共同的敘述者來聯結。”[1]拉斐爾以身體話語表述生前的狀態,非理性的尸體解剖結果再現了他的生活軌跡。按照科學理性的解剖步驟,病理醫師歐賽比奧應該從頭或者胸腔開始檢查死者的生理異常,但是瑪麗亞告訴他應從腳開始解剖。經過瑪麗亞的指引,歐賽比奧雖無法說明拉斐爾的死因,卻獲取了拉斐爾如何生活的跡象。拉斐爾的尸體表面正常,可是身體內部包含了許多展現他日常生活特征的東西:
手臂里的物品琳瑯滿目。他從中取出了一把榔頭、一把鉗子、一支長刀、一個蘋果、一團泥土、一把麥穗、三個雞蛋、一只腌鱈魚、一副刀叉。拉斐爾·卡斯特羅的腦袋里空間更大。他在里面找到一方紅布;一件手工木制小玩具——一匹馬和一駕馬車,車輪可以轉動;一面隨身攜帶的鏡子;更多羽絨;一個染成赭黃色的木制小玩意兒,瑪麗亞·卡斯特羅也說不清是什么;一支蠟燭;一綹深色長發;還有三張撲克牌。他在兩只眼睛里各發現一枚骰子,在視網膜的位置有一片干枯的花瓣。脖子里有三只雞爪,還有干樹葉和樹枝——看起來像是引火用的。舌頭里全是灰,只有舌尖里填著蜂蜜。[1]
以上諸多身體里的物品對拉斐爾的生活至關重要,共同描摹出拉斐爾——葡萄牙高山區農夫——樸素的一生。這證明身體不僅是生命的媒介,還是生活的一種直接展示。
與此同時,拉斐爾身體的獸形幻化及其蘊含的宗教隱喻,為重新審視人與動物之間的關系提供了獨特的視角。拉斐爾的尸體里除了生活物品,還藏有抱著小熊崽的黑猩猩,小熊崽象征著拉斐爾死去的兒子,黑猩猩則象征著愛子的拉斐爾本人。他兒子尸體的姿態與受難的耶穌類似,所以村民奉其為“金童”,還為他向羅馬教廷申請“可敬者”的封號。某種程度上,拉斐爾的兒子就是耶穌,死后又在人民心中復活,給祈禱的人帶來神跡。他母親的名字是瑪麗亞,這也從側面印證了上述宗教隱喻。那么拉斐爾連同體內的黑猩猩就是上帝耶和華的化身,其中的神圣象征與獸形表達明確了神、人與動物之間存在的緊密聯系。馬特爾慣以動物意象承載其形而上的隱喻,《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中的黑猩猩“橘子汁”曾被描繪成十字架上的“猿基督”,與《葡萄牙的高山》中烏利塞斯神父制作的猩猩十字架、拉斐爾體內的黑猩猩有異曲同工之妙。馬特爾將黑猩猩與圣子/圣父并置,不僅顛覆了動物被視為獸性化身的傳統認知,還為動物注入神性,打破了神和動物之間的區隔。拉斐爾尸體變形為猩猩則寓意著猿類與人類之間巨大的生物聯系,后文彼得與猩猩奧多的相處更是破除了人類中心主義,展示了人與動物的和諧共處。
四、結語
《葡萄牙的高山》中,身體敘事不僅關聯著人物的生命體驗,更是表達宗教信仰、人與動物關系等深層內涵的重要手段。這種身體敘事不僅豐富了作品的內涵,還引導讀者重新審視自我與身體的關系,思考身體在生命中的價值意義。
參考文獻
[1] 馬特爾.葡萄牙的高山[M].亞可,譯.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
[2] 福柯.規訓與懲罰[M].楊遠纓,劉北成,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
[3] 梅洛-龐蒂.知覺現象學[M].姜志輝,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4] 劉勝利.身體、空間與科學:梅洛-龐蒂的空間現象學研究[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
[5] 唐清濤.沉默與語言:梅洛-龐蒂表達現象學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6] 汪民安.身體、空間與后現代性[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
(特約編輯 劉夢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