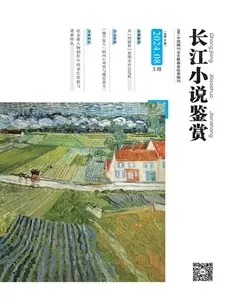性別視角下母女關系書寫
屈凡 張云麗
[摘? 要] 母女關系是人類最親密的關系之一,也是作家筆下經久不衰的表現主題。在傳統社會結構中,母系譜系湮沒在男性書寫之下,文學作品中關于母女關系的敘述相對匱乏。隨著女性主義的發展,男性與女性作家都以更大的熱情展開對母女關系的探索,在創作中表現更加多元、復雜的母女關系。譚恩美的《喜福會》與蘇童的《婦女生活》以不同的性別視角對母女三代人的童年經歷、婚姻生活、代際關系進行細致入微的刻畫。本文首先探討這兩位作家不同性別視角下建構母女關系的相似之處;其次從心理和社會文化語境兩個角度,解讀小說中母女關系出現的沖突、代際創傷等問題;最后探討不同性別視角下母女關系書寫的差異。
[關鍵詞] 性別視角? 母女關系? 代際創傷? 身份建構
[中圖分類號] I06? ? ? ? ?[文獻標識碼] A? ? ?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08-0102-04
20世紀80、90年代以后,女性主義理論研究迅速發展,成為文學界關注的熱點之一,性別視角也逐漸被引入文學研究領域。本文將以性別視角為依據,選取蘇童的《婦女生活》和譚恩美的《喜福會》為研究對象,探求這兩位作家同題材作品中的不同之處。選擇這兩位作家的作品做比較,是因為兩位作家自身的特殊性。蘇童作為崛起于20世紀80年代的作家,在這一時期先后發表了《妻妾成群》《大紅燈籠高高掛》《婦女生活》《紅粉》等一系列表現婦女生活的作品,表現了蘇童對女性的高度關注、對女性命運的深刻書寫。他對女性投注了不同于同時代男性作家的人文關懷,這讓他被評為“最懂女人”的男作家;華裔女作家譚恩美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文學創作,母女關系是她書寫的一貫主題。兩位作家在作品中建構了以母系為鏈條的家庭譜系,并以不同的性別視角和敘述策略展開母女間的代際沖突與創傷書寫。
一、家庭倫理中母系譜系的建構
家國同構的傳統社會,父系血緣作為建構家庭譜系的紐帶,確立了父權的統治地位。女性只能以“妻子”“母親”“女兒”的身份過著從父、從夫或是從子的生活。在父權社會中,母女倫理關系被逐出了父權譜系之外。母女之間的親情聯系伴隨著女兒的出嫁而斷裂,母女關系被男性血緣家庭結構所分裂、割斷、打碎[1]。因此在傳統文學作品中,關于母女關系的敘述十分匱乏,在男性主導的主流話語層面未得到充分的表現與肯定,母子關系、婆媳關系成為男性筆下更為重要的敘述對象。在中國傳統文學中,男性作家所建構的母親形象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合乎禮教,父權意志的擁護者,如《西廂記》中的崔夫人、《孔雀東南飛》中的焦母;另一類則是克勤克儉、賢良慈愛、奉獻自我的賢母,如為子三遷的孟母與為兒刺字的岳母。母親就這樣被固定在了一個由男性構筑的“母性神話”中,“母親”成為泯滅自我的一種空洞能指和一種符號式的存在。而傳統女性對母女親情的書寫盡管未曾斷絕,卻始終未能成為被人們普遍關注的文學母題。隨著女性主義的逐步發展、社會時代的變遷、女性的政治經濟地位不斷提高、自我意識的不斷覺醒,女性在諸多方面取得了更多的獨立性與自主性,這些外部的力量和女性自身的發展為“母女倫理走進公共話語領域提供了歷史機遇”[2],這一時期對母系譜系的梳理成為許多作家創作的特點,此時蘇童與譚恩美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向母女關系這一題材,兩位作家在《婦女生活》與《喜福會》中將母女關系放置于父親缺席的敘事空間內,擱置了傳統家庭內來自男性的權力,削弱了男性語言的權威,實現了家族權力中心的置換。傳統文本中以父權意識占主導的家族文化被解構,家族中的女性得以浮出水面。
1.家族女性命運的悲歌
《婦女生活》與《喜福會》通過不同代際間母女形象的構建,組建了一個由女性構筑的王國,這條清晰的女性譜系連接了母女間的情感紐帶,串聯起家族女性幾代人宿命般的悲劇命運。《喜福會》中第一代華裔母親在經歷不幸童年、無愛婚姻、顛沛流離的戰爭之苦后,遠渡重洋,對新生代的女兒們寄予厚望。她們雖然飽含愛意地對待與自己迥異的下一代,但在無意中又將多舛命運所帶來的生命陰影照進女兒們的生活。母愛成為羈絆,悲劇的命運輪番上演。第二代的女兒們帶著美好的憧憬進入婚姻殿堂,在理想婚姻破滅后陷入絕望。如小說中吳宿愿所說:“盡管我對女兒的教導與此恰恰相反,但她仍是如出一轍……我們三代人猶如階梯,一級跟著一級,有上有下,不過總是朝著同樣的方向。”[3]創傷所帶來的痛苦融入血液、刻進了基因,在母女間代代延續。《婦女生活》中,嫻、芝、蕭母女三代人也陷入了宿命般的悲劇循環,嫻的母親得知情人王老板與女兒芝私通后,悲痛欲絕投河自盡;嫻在虛榮的驅使下做了電影老板的情婦并意外懷孕,在對孟老板的恨意中產下女兒芝,后又做了醫生的情婦;芝在既無父愛也無母愛的環境中長大,極度缺愛的芝將內心的不安轉為對丈夫病態的控制,最終精神崩潰;第三代女兒蕭出于現實的需要與大學生小杜組建了無愛的家庭,婚后慘遭背叛。兩位作家在譜寫家族女性命運的悲歌中,還原了歷史文化處境下女性的真實處境,飽含對女性困境的人文關懷。
2.對抗與沖突的母女關系
對抗與沖突是兩部作品相似的母女關系形態,這種矛盾沖突主要表現在母親對女兒的專制控制和女兒的反抗中。矛盾中的母女關系解構了“母慈女孝”的傳統敘事模式,打破了“母性神話”的禁錮,還原了以母系鏈條為結構的現實家庭內多元的母女關系。《喜福會》中吳菁妹為了反抗母親的壓制,獲得母親對真實自我的認可,與母親展開了長達半生的戰役。來到美國的第一代華裔母親吳宿愿為女兒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讓女兒剪明星少年同款發型、以天才少年的故事測試智商……孩童時期的吳菁美在母親失望的表情中察覺現實中的真實自我與母親渴望的理想女兒形象相去甚遠。她在自我審視時,“看到的仍舊是自己那張永遠都只會是平凡無奇的臉……我發出如此癲狂的野獸一般的尖叫,拼命想將鏡中的那張臉抓撓掉”[3]。不知所措的吳菁美將這種混亂矛盾的憤怒情緒發泄在自己身上,不明智地選擇了以消極的方式反抗母親,以此贏得母親對真實自我的接納。吳菁美對母親的要求表現得心不在焉、做事不專一、半途而廢,畢業多年后才修完大學學位。吳菁美性格中的淘氣、執拗、叛逆讓她以自我破壞的方式反抗母親,為內在的真實自我取得了另一種形式上的勝利。《婦女生活》也同樣上演了母女“像一對冤家那樣,在占有與反占有、監控與反監控中相依為命”[4]的情節。母親嫻以愛的名義事無巨細地干預、控制女兒芝的生活,極端扭曲的母愛加劇了母女關系的疏離。母親嫻先是反對女兒芝與同班同學鄒杰的婚姻,表現出歇斯底里的痛苦。芝的婚姻成為母女之戰的導火索,引發了母女間的矛盾沖突。在芝婚后,母親嫻竟在暗中偷窺女兒芝的性生活,芝由于沒有自己的房子而無法擺脫母親病態的監控,母女倆像囚籠中的困獸,無法解脫。
二、母女沖突與苦難命運的根源
譚恩美與蘇童在作品中解構了男權秩序的價值觀,建構了母系譜系,通過將母女設置于矛盾緊張的關系內,于平凡瑣碎的家庭空間中敘述母女的現實命運,從而揭示出導致母女矛盾與苦難的社會歷史根源和深層的心理機制。
1.矛盾與苦難的社會歷史根源
兩部作品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歷史變遷中展開母女沖突,書寫女性苦難命運。蘇童在《婦女生活》中通過建構具有時代特色的場景和物象,實現了文本內每個故事間時代的流轉。跑馬場、舞廳、電影院,勾勒出嫻所處的20世紀30年代的都市文化。深受小資情調浸淫的嫻與女兒芝產生了文化觀念上的沖突。女兒芝中專畢業后與工人出身的鄒杰產生情愫,而母親嫻則希望女兒能嫁給更有地位、權勢的有錢人,母女之戰一觸即發。第三代女兒蕭是上山下鄉的城市青年之一,體驗過偏遠農村的艱辛。回城后的她與祖母、母親也因觀念不同產生摩擦。祖母嫻即使在生活窘迫的狀況下,依然要求孫女蕭滿足她每日都喝牛奶的要求。《喜福會》中第一代母親出生于20世紀初的舊中國,她們經歷了父權文化的壓抑與迫害,所遭受的苦難是同時代女性的縮影。封建男權對女性身體與精神的雙重壓迫,使女性處于“第二性”的他者地位。出生于名門望族的瑩映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傳統下,下嫁給了只有一面之緣的男人,即使婚后遭遇丈夫的背叛、拋棄,但直到丈夫因病逝世,她才得以擺脫這段無愛的婚姻。在男權社會中女性長期被物化為勞作、生產的工具,如西蒙·波伏娃所說,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喜福會》中的江林多在咿呀學語、蹣跚學步之時,母親已為她定下娃娃親,計劃成年后與鄰鄉黃家的獨子成親。兩歲的江林多在媒人與黃母眼中 “是一匹壯實的好馬,長大后會是一個干活的好手,等你老了會好好服侍你”[3]。
為了逃離封建男權的束縛,第一代華裔母親遠渡重洋,來到美國后又因無法躋身于主流社會,處于邊緣位置。后殖民主義帶來的文化創傷表現在第二代女兒們曲折的婚姻中。《喜福會》中當母親許安梅得知女兒羅絲·許·喬丹開始和美國男性約會時,感到十分苦惱。在許安梅看來,亞裔與美國白人間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身為華裔的女兒,與中國男孩組建的家庭才更穩固。第二代華裔女兒麗娜·圣克萊爾與白人哈羅德相識、相戀步入婚姻。由于華裔與美國白人社會地位的懸殊,婚姻中麗娜始終處于低價值、低自尊的一方。即使她有著魅力四射的外表、敏銳的商業目光、出色的工作能力和成功的事業,卻絲毫不能減弱她對失去丈夫哈羅德的恐懼。她對婚姻、對事業無所保留地付出,仍無法避免失衡的婚姻。丈夫在與麗娜共同經營的公司利益上拿走了七成的收益,但在生活用品、飼養寵物等日常花銷上卻保持著財務均分。社會時代的變遷帶來母女文化觀念上的沖突,也在母女代際繁衍中延續著相似的悲劇命運。
2.矛盾與苦難的深層心理機制
文本中出現的母女矛盾折射出依戀共生對母女關系的影響。“共生幻想”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他認為在兒童發展早期,個體將完成性別認同。這一時期女兒與同性別的母親形成了一種不分彼此的親密與依賴,這一心理模式阻礙了女兒成為獨立的個體,因而被稱為母女共生幻想。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學家也提出過類似的觀點:“母女間早期的親密關系中最為突出的特點是長期的共生感和自戀的、不分彼此的統一感。”[5]在這種共生關系下,母親往往將女兒視為自我生命的延續和自我意志的承擔者,表現出對女兒生活的強烈控制,這與女兒對母親禁錮的反抗形成惡性互動,最終造成緊張、對抗的母女關系。《婦女生活》中嫻被電影導演哄騙意外懷孕,生下了女兒芝。對于嫻而言,青春時期愛情上遭遇的挫折與苦痛,如藏于心底的傷疤,隱隱作痛。嫻在潛意識中把女兒當成了自己生命的延續,希望通過為女兒挑選符合自己心意的婚姻伴侶,彌補自己當年因愛情中的錯誤而帶來的傷痛,消除自己潛意識中的焦慮。《喜福會》中的韋弗里從小就在象棋上表現出過人的才能,她厭惡母親江林多將她取得的榮譽視為自己的功勞并當作炫耀的談資,韋弗里與母親為此產生沖突,正如波伏娃所說:“母親把女兒當成了自己替身,把與自己相關的一切曖昧投射到了女兒身上,所以當與女兒的相異性逐漸得到證實后,母女之間的關系便逐漸惡化。”[6]
女性自身的軟弱性與依附心理也導致了悲劇命運的發生,文本中的女性沒有改變自身苦難命運的意識。《婦女生活》中,蘇童設置了男性缺位的家庭環境,聚焦母女三代人的生命歷程;但未出場的男性卻決定了女性的命運走向。高中畢業的嫻,寧可做不妻不妾的情人依附于孟老板,也不愿自己辛苦打拼;第二代女兒芝將丈夫鄒杰作為精神上的救命稻草,希望他拯救自己于無愛的家庭。母女三代人之間循環的悲劇命運如同宿命般代代相傳,這固然與給女性帶來苦難的男權社會有關,但女性自身的軟弱性也是導致女性陷入苦難命運、永遠徘徊在歷史之外的重要原因。
三、不同性別視角下建構的母女關系
譚恩美與蘇童在《喜福會》與《婦女生活》中通過家族女性譜系的建構,還原了現實生活中的母女關系和女性的生存狀態。文本內部有許多相似之處,但也由于性別差異在敘事方式與立意上存在不同。
語言作為文本內容的外殼與載體,是文學文本的組成元素。不同敘述語言的運用影響著文學文本的最終呈現。《喜福會》與《婦女生活》同為表現母女關系的作品,卻采用了不同的敘述策略與方式。蘇童在《婦女生活》中采用了非聚焦的全知視角講述女性的故事。女性作為被述者,在文本中承載著作者蘇童的意志。盡管蘇童的性別意識被隱藏于這樣一個中性的敘述聲音里,但還是無意識中流露出男性立場。在小說末尾,蘇童將蕭作為自我的代言人:“你們做男人的不知道做女人有多苦,有多難。女人不一定非要結婚,可他們離不開男人,最后都會結婚。”[7]“女人永遠沒有好日子過”表明了蘇童對女性無法擺脫悲劇命運的同情,另一方面也體現了蘇童對女性價值的某種否定,因此小說中無論是女兒還是母親,只能以死亡、墮落、依附男性等消極手段面對生命中的創傷與苦難。在敘述策略上,蘇童在文本中設置母女三代人循環式的命運使母女相互映射,在母女互為鏡像中,讓女兒陷入審母、厭母、到承續母親悲劇命運的結局而告終。無法認同母親的芝找不到同性形象作為自我認同的對象,導致芝對女性身份的厭惡,這也解釋了芝為何對養女蕭的性別一直心懷不滿。作為文本中的第三代女性蕭,在女性意識覺醒后也陷入了自我建構的精神危機中,正如小說中蕭所言:“我不知道為什么,我瞧不起女人,我也瞧不起我自己。”[7]
蘇童雖然對文本中的女性苦難充滿同情,卻因持有的男性立場阻礙了他對母女關系更深層次的挖掘。小說中沒有出現母女惺惺相惜、相互理解的場面,也未曾有女兒對母親苦難命運感到憐憫的書寫。作者未深入到母女的內心深處,去揭示被壓抑的生命苦痛。蘇童通過對父權文化所構建的“母慈女孝”的反思,完成了對母女關系現實的回歸。但卻在母女鏡像審視中,讓女性陷入了悲觀無路可走的困境,使文本內的母女始終找尋不到自我身份的認同之路。
譚恩美在《喜福會》中采取了女性的敘述視角,作為隱含作者的譚恩美,賦予了文中母女自我敘述的權利,讓她們發出自己的聲音。小說中的母女于細膩與溫情中相互訴說著自己的生命歷程,訴說著希望與傷痛。吳菁美在母親死后追溯了母親述說的人生歷程,踏上了尋親之路。在找到母親遺失的兩個女兒后,理解了母親生命中的傷痛,解開了因母女情感糾葛而引發的生命困惑。韋弗里·江回顧了母親生命的點滴,理解了母親的嚴苛與挑剔,完成了對自我身份的定位。在母女互為鏡像的書寫中,女兒一代完成了性別認同與自我身份的建構。
《婦女生活》與《喜福會》實現了女性從被述到自述的轉變。女性從無聲到發出自己聲音的這一過程,體現了女性于歷史的“空白之頁”,譜寫家族女性故事的華美篇章。
參考文獻
[1] 劉傳霞.被建構的女性:中國現代文學社會性別研究[M].濟南:齊魯書社,2007.
[2] 喬以鋼.林丹婭.女性文學教程[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
[3] 譚恩美.喜福會[M].李軍,張力,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6.
[4] 高小弘.認同與對峙——論20世紀90年代女性成長小說中母女關系的書寫[J].文藝評論,2011(3).
[5] 多諾萬.女權主義的知識分子傳統[M].趙育春,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6] 波伏娃.第二性[M].陶鐵柱,譯.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
[7] 蘇童.婦女生活[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3.
(特約編輯 劉夢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