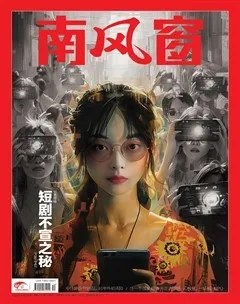小國政治家的現實感
董可馨
新加坡正在變成一個日益亮眼的國家,這兩年,它是旅行和移民的熱門地。如果今天去到新加坡,不僅會看到它是一個經濟發達、街道干凈的國家,而且會發現它的社區設計非常開放,同時又保持了居民生活的平和,不同族群在一起共同生活、相處得融洽而自然,他們以自己的國家為豪。
這很不容易。新加坡是1965年獨立建國的,之前的它,沒有自己的國家歷史,在它1963年嘗試與馬來西亞合并但失敗并且被后者踢走之后,新加坡面臨的局面非常棘手:它的人口由信仰、語言、文化、歷史很不相同的華人、馬來人、印度人,以及荷屬東印度群島的各種族群的移民組成,他們并不具有共同意識,族群差異明顯;它是殖民地,必須處理好宗主國英國的遺產以及與英國的關系;獨立之初,它周邊的國家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對它都抱有敵意,而且比它大得多;新加坡的體量太小了,歷史學家湯因比還曾預言新加坡這樣一個城市國家,作為政治單位太小,并不實際可行。
這樣的新加坡,處在生存的夾縫之中,不是生存就是毀滅,必須走好平衡,既擺脫對周邊的絕對依賴,實現獨立自主,又和其他國家建立良好的交往關系,同時發展自己的經濟,給各族群提供值得期待的共同愿景,和可以共處的生活方式。
在這種國際環境和生存處境中成長起來的新加坡的領導人,身上的突出特點是務實。他們并不過分糾纏于意識形態,而是講求實際效用,并且基于充分理解的現代原則,理性且小心地處理國家事務。
比如第三任總理李顯龍,在俄烏沖突中表態反對俄羅斯,理由是從新加坡自身來考慮的,“新加坡是一個小國,如果不堅持立場,不明確表態,萬一有一天面對侵略,國際上就不會有人為新加坡說話了”。在他被問到中國的國企能不能走淡馬錫的路時,承認兩國國情不同,但坦誠地說關鍵在于國營企業是不是有競爭力,根據市場原則運作的,高效的,不享有特殊的有利條件。
他的務實風格,顯然繼承自他的父親,新加坡第一代領導人李光耀。根據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的回憶,李光耀在美國對越戰爭期間曾訪問哈佛,美國自由派的教授在他面前表達反對越戰的態度,并以為會得到他的贊同,但李光耀請對方不要從他身上尋找意識形態上的共同點,而要和他一起探討需要做些什么。
有美國人贊揚李光耀在新加坡采納了女權主義的原則,他回復說是出于實際的考慮,因為好的發展必須有女性的參與。李光耀非常積極地招商引資,被人質疑是引來“資本主義剝削”,他說新加坡只有勞動力,要是想剝削,盡管來好了。他還說過如果獨立運動和宗主國能通過合作來實現獨立,這樣的獨立就最成功。這些話都很現實,不強調道德原則,好處是減少了爭執不清的對抗,反而有利于境況的實際改善。
李光耀時代,新加坡講漢語的華人占人口75%,但他不考慮把官方語言定為漢語,因為他認為如果這樣做,不是華人的那25%會堅決反抗,他讓英語成為新加坡的通用語言,但并不以強制的方式,因為那樣會帶來糟糕的后果。他實行雙語政策,所有學校也要教授英語,在長期的自由選擇下,新加坡慢慢變成了英語第一,母語第二的國家。
新加坡領導人身上的這種特點,來源于他們極強的現實感,這種現實感在小國領導人身上往往更為突出。因為他們更迫切地對世界的變化和自己國民的真實需求保持敏感,也會讓他們懂得節制和審慎是一種必備的政治素養。這一點,是今天的政治家尤其稀缺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