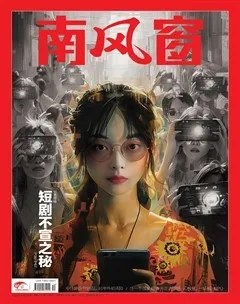謠言為什么頑固存在?
肖瑤
謠言分為幾類,其中生命力最旺盛的一類就像病毒,往往靠寄生依附于故事而存活。
一套固定的敘事體系、一種熟悉的行為范式,都可能與多數人的普遍生活經驗產生聯系。當一個模糊的傳聞缺乏細節,卻又由于各種原因,聽眾并不能且知道自己永不能獲知具體細節,想象便填充了從信息接收到挖掘真相之間的空隙。在這當中,那些越是與普通人日常生活最貼近的情景,越是容易成為謠言的溫床,比如婚姻戀愛、日常公共設施與政策。
謠言發揮效用,有時倚賴的是事物的重要程度,而非真相的重要程度。疫情期間,戴口罩到底會不會得肺結節、吃藥究竟是否有順序,這些原本不是問題的問題因為與此時此刻的生活聯系密切,緊繃的狀態下,構建完整認知的順序鏈可能被動搖。
謠言往往同時鉆“認知”與“認識”的空子。認知是可以被長期塑造的,包括必要的、經專業標準驗證過的常識。比如推送里的致癌物其實并不致癌、熏醋并不能殺死病毒。
但認知也極可能建立在經驗與印象之上。美國心理學家戈登·奧爾波特在《謠言心理學》里說:“認知的變化過程(包括對謠言的人為加工)和情感的激化過程(包括對謠言的興趣因素)都是混雜在一起的”,而后者的變化往往難以為理性察覺。
認識,則是針對具體的事件與細節產生的信息量把握。認識需要可靠的信息來源,扎實的邏輯推理。謠言發生的時候,有一句常常被用來當擋箭牌的障眼法,叫“并非空穴來風”,一語帶過從核認事實到判斷之間的模糊地帶。
謠言與“陰謀論”不同,從接受者的心理體量來說,后者更沉重,因而叫人下意識更為嚴謹。而前者,由于它往往與我們的生活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隱秘聯系。因此,謠言常常依附于那些與世俗生活有關的瑣事,比如家庭情感、生活小竅門等等。
不過,家庭群里轉發的那種常識類謠言,是可以通過既成信息的補全和傳播來逐個擊破的認知。但永遠存在一種謠言,是無法通過既有科學信息攻破的,而是需要靠信息權威者提供武器,替人們拓開真知的前路。
1750年5月,法國巴黎出現了大面積兒童失蹤案。民間出現傳言,稱兒童失蹤案實乃政府所為,因為國王路易十五需要沐浴兒童的鮮血來治療麻風病。甚至有流言說,因北美殖民地密西西比缺少勞力,需要抓捕孩子到那里去勞動。連高等法院的秘密報告中也采信了此種說法。
這樣看來,除了道德審判中的弱勢者,權力上的強勢方,也容易成為謠言的主角。
百余年后,遠在東亞大地上的晚清,也出現了由兒童失蹤案引發的謠言。
鴉片戰爭后,國門打開,基督教廣泛傳入中國,許多教會如雨后春筍在各地出現,不可避免地與本土文化產生了沖突。當時,一些民間群體就與地方天主教會產生了嚴重的矛盾,甚至演化為暴力事件,歷史有記載的如古田教案、巨野教案等等。其中,發生于1870年的“天津教案”,就是多起兒童綁架事件衍生的傳言引發的:民間認為,是教會綁架了兒童,甚至出現教會以兒童作為藥材制作藥品的驚悚版本。
是偏見印證了謠言,還是謠言的堆砌催化了偏見,這是一個流動的狀態。但不可否認的是,任何謠言都不可能脫離當時的社會情景,它們也一次次證明,作為一種模糊信念的謠言,多數時候都是社會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