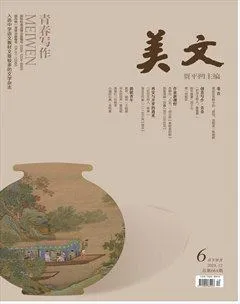小城的心跳
金純真
天邊逸出白光時,榮生離開都市。他眼望著客車從汽車站那端冒出頭,一路發出哆哆嗦嗦的振動聲。榮生老家是個小縣城,一周只有一趟接客的中巴,他也只有一年到頭的春節才來與這中巴相會。大年三十,回鄉的人早起身候車,提著大包小包的節禮,成群結隊地擠進客車的金屬欄桿,才終于找到一個穩當的座位歇會腳。大城市里流浪的人們卸下倦意,就這樣緩緩流回縣城。
客車在公路上顛簸起落,如同汪洋中的一艘船。由江南到江北,回縣城需要三個半小時。榮生認為最明顯的變化是溫度——城市是一席冷寂的盛宴,收束著人群的欲望;而他的縣城是個微熱的巢穴,生養著注定要漂走的浮萍。榮生坐的位置靠窗,因此一直望著外面也并不膩煩。這一路的風景與他回憶里童年的土路已是不同,那時候芳草萋萋,泥土濕潤,路旁往往有啃著青草的牛犢、枯稻草做的瓜棚頂,水塘上偶見些叫嚷的野鴨。而縣城的國道興建在他上初中的時候,半舊不新的水泥忽然被顏料遮掩住,路邊古怪的新式地標藏起了小城淳樸的風情,雄心勃勃地去彰顯新興的縣城風貌,可惜火候未到,行而未成。榮生的老太往往稱之為“毫不搭調”。小城在歲月流變里自顧自地涂抹著時代的色彩,可倘若你側耳諦聽,便會發覺那小城竟是有股和諧未變的心跳,人與物安然如故。榮生撐著雙眼想尋覓那“咚咚咚”的心跳聲,安恬的困倦卻模糊了他的意識。
“榮生又躲懶了!”妹妹氣鼓鼓的,敲了敲他的頭,又拿了幾根稻草去燒爐子。榮生忽而轉醒,也跟著去灶間生火。老太的屋子是很常見的自建房,廚房是土灶,客廳鋪瓷磚,樓頂有天臺,外墻貼大理石,說不準那是古樸無華還是寒酸寡陋。過年時,他和妹妹就從自家小套間里搬到二樓,跟著老太過完整個春節。榮生搬了矮腳凳來,劃根火柴,放入妹妹拿的曬干的稻草。慢慢地,稻草里冒出濃濃的煙,“轟”的一聲響,火苗猛地躥了出來,灶膛里一下子亮堂起來。火舌有生命似的,或明或暗地搖曳生姿。妹妹和榮生就守著甫燃的灶膛口,添柴加火等著老太。不一會兒,集市上采買的大包小包的菜先進了屋,隨后才望見老太有些佝僂的身影。她麻利地抽出一撮身后的稻草,彎曲成合適的弧狀,嫻熟地送進面前的灶膛。待灶膛里的稻草快要燃盡,她便再添入一把。爭先恐后,灶膛里的火苗躥動著,灶膛里的火花跳躍著。火的爆炸聲嗶哩啪啦,如此奏出了一段幻想曲。春節的夜晚,常常是爆竹聲與嬉笑聲交替間雜。雪落得極厚時,孩子們聚集起來踩著深雪,挨家挨戶串門吃飯,老太就任由街上的孩子們分著她做的肉菜湯粥。鱈魚湯的香氣、孩子們的相聚、灶火的溫熱……這些生活的碎片在榮生的生命里一晃而去,只留下小城那隆隆的心跳聲。
年深月久。老太那張被旺騰灶膛火映亮的臉,在小縣城的天空下始終如一地忙碌著,瘦小的身影映在焦黃的墻面上,腰上的圍裙轉過來又旋過去,月落星沉、桑榆暮影,不覺沾染了一身小城灶火的氣息。吃酥餅時掉在書桌上的酥皮還沒來得及清理,千里之外的榮生得來了老太過世的消息。她沒有出過小城,小城也就承載了她的一生。人的死亡都是絕對的,是絕對個體的深淵,是永不返回的出離。但是于一座城而言,死亡總是伴隨著像風一般難以捕捉的神秘,流入了她沉睡的土地,化為了小城風的囈語。她與曾親吻過的灶火、撫摩了的雪糝久別重逢,她的生命就這樣成為縣城的一部分。榮生記得那天匆匆與返鄉的中巴相會,一路顛簸著回了縣城。彼時他對生與死的體悟還不深刻,暫時的茫然失措在那片土地捉摸不透的悲憫里漸次溶解。小城留給生者的況味,也只有祭奠亡者時一杯酒的辛辣了。榮生與妹妹一同回到老屋收拾遺物。妹妹不經意提及,老太在時二樓房里應該還有一張小小的硬板床,從藍色玻璃的窗往外看,就是無盡的田野伴著天空悠悠流動。老太走后,屋子里便收拾一空,只余下干燥的稻草和煙火的氣味,可窗外仍是云天共游,依然故物。它們的氣味又很快融化在微茫的歲月里,融化在浮動的田野天空之間。
“嗚——”汽車的一聲長鳴喚醒了榮生的夢。榮生漂泊了許多年,時間長得讓他忘記了許多縣城的人與物,卻依舊能感受一個城鎮生命的脈搏,能聽見一個城鎮心跳的轟鳴。縣城似乎是鄉村與都市之間的影子,隨著人類的潮汐式的遷徙,離別的癡悵擦出光與暗之間影的界限,成了小城喘息的天地。小城人的欣喜與黯然兼收并包,異鄉客的憂與愛難分難解,他的心跳就這樣在轟隆隆的時代聲中被淹沒又被浮起。然而激蕩之中,小城始終懷著對人與物豐沛的仁慈,這兒生命和暢諧美,他的心跳也就不輟不止。
天邊洋溢白光時,榮生終于回到了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