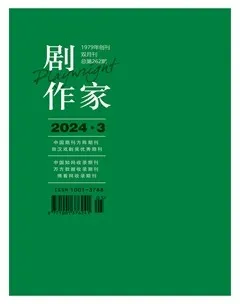沒有馮耿光,就沒有梅蘭芳嗎?
封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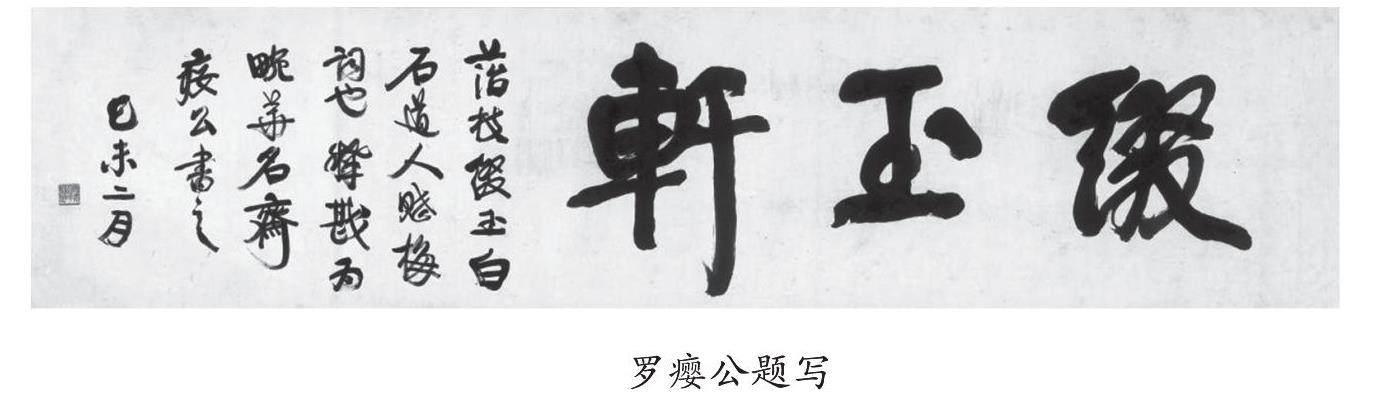

摘 要:由靳飛所著的《馮耿光筆記》出版,封面“沒有馮耿光,就沒有梅蘭芳”深深吸引住了我。該書首次書寫了京劇藝術家梅蘭芳背后的“幕僚”——馮耿光,全面記述了其橫跨政治、金融、戲曲領域的傳奇人生,進而展現出近現代中國文化界和金融界的人物群像,可謂京劇研究領域的一本力作。本文通過記述馮耿光對梅蘭芳的幫助和影響,著力梳理了梅蘭芳的藝術人生。
關鍵詞:《馮耿光筆記》;馮耿光;梅蘭芳
難道真如作者所言“沒有馮耿光,就沒有梅蘭芳”嗎?在我認真拜讀這本書后,的確感到無論是從藝術方面、生活方面,還是理論方面、藝術取向等,真是沒有馮耿光,就沒有梅蘭芳。而這里的馮耿光,應該是以馮耿光為代表的“馮耿光們”。但此時的“馮耿光們”還沒有形成后來被人們熟悉的“梅黨”。書中提到,青年的馮耿光初識梅蘭芳時,梅蘭芳才十三歲左右,尚是云和堂中的一名歌郎。但是這時馮耿光的關注點卻是在一名叫若蘭的演員身上,并為他滿師舉辦了宴席。然書中寫道:“遺憾的是,在云和堂所留下的相關資料中,竟然找不到若蘭的蹤跡。”這里,我補充一點資料,若蘭即王蕙芳,其字湘浦,號若蘭,為云和堂十二弟子之一,與梅蘭芳為一師之徒,譽名“蘭蕙齊芳”。
不久,馮耿光就開始關心起了梅蘭芳。此事書中寫到在曹汝霖回憶錄中得到記載:“時蘭芳方十二三歲,未脫稚氣,然態似女子,貌亦姣好,學青衣工夫孟晉。幼偉月入銀四百兩,以其半助蘭芳成名,始終如一。后蘭芳藝術日進,于四大名旦推為旦首,幼偉與有力焉。”(《馮耿光筆記》第12頁)1912年,十八九歲的梅蘭芳在藝術上已呈上升趨勢,生活上也開始安定下來,購置了鞭子巷三條的一所院落。然而以梅蘭芳當時的實力對于購置“上房五間,左首兩間是祖母的住房,右首兩間伯父母帶著兩位未出閣的妹妹住。梅先生住在左邊廂房,對面是廚房,廚房隔壁是養鴿子棚。外面靠大門的倒座是兩間客廳和一間書房,開間都很小,經常有些愛好戲曲的朋友在那里向雨田伯父商討一些音樂場面的問題”(《馮耿光筆記》第14頁)這樣一所四合院,可能還勉為其難。其中很有可能得到了馮耿光的資助。然京劇界和戲迷們在談到梅蘭芳的經歷時,常常會提到馮耿光的名字,只知道他是中國銀行的總裁,人稱“馮六爺”,但是具體的經歷卻全然不曉。這里有必要簡要介紹一下這位“馮六爺”。
馮耿光出生于1882年,字幼偉,是廣東番禺人。早年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步兵科第二期畢業。1905年至1911年,歷經北洋陸軍第二鎮、廣東武備學堂、清政府軍咨府第二廳等要職。武昌起義后,被清政府派為參加南北議和的北方分代表。中華民國建立后,任袁世凱總統府顧問,參謀本部高級參議。1918年至1928年兩度擔任中國銀行總裁。幾十年間,還兼北洋保商銀行、大陸銀行、中國農工銀行、新華銀行等董事(長)職位。
就是這樣一位銀行界的權威人士,卻對京劇有著濃厚興趣,尤其是對藝術成就蒸蒸日上的梅蘭芳投入極大的精力,并團結吳震修、李釋戡、舒石父、許伯明等人一起,為梅蘭芳出謀劃策。這幾位出身均曾就學于日本軍校,且都在國內政(軍)界供職,都有一定的實力,為梅蘭芳打開局面,起到一定的影響力。這就是大家熟悉的被稱為“梅黨”的基本成員。
在形成“梅黨”雛形的同時,還有一批“捧梅”學子,也起著積極的作用。他們與那些“智囊團”的人不同,因年齡相近梅蘭芳,彼此的交流可能更融洽,狂熱程度更旺。像其中的郭逋仙還提出“非梅郎之劇不觀;對于梅郎之言論有褒無貶,永不詆毀;不因梅郎開筆墨之陣以傷梅郎之心;梅郎設有色藝衰落之一日,不因之改變宗旨”(《馮耿光筆記》第47頁)捧梅標準。而像樊樊山、羅癭公、李釋戡、易哭庵等晚清遺老,他們身上有著深厚的傳統文化修養,以詩人的身份在宣傳梅蘭芳方面的確出力不少。如“一笑萬古春,一哭萬古愁”就出自易哭庵的詩句。而且易哭庵對梅蘭芳說:“當一個藝人是容易的,但當一個名藝人不可沒有文墨,更不能不懂詩歌。”在這些詩人中還有大家知道的一位,他就是對程硯秋成長關懷備至的羅癭公。這也就可以想象當時嗓子出現問題的程硯秋為什么能夠拜在梅蘭芳的名下。當然,也正是因為有了這些詩人或者說是文化人的參與,不僅使梅蘭芳演出的劇目提升了文化層次,更是對梅蘭芳本人文化修養的提升也給予了很大的幫助。大家一起為梅蘭芳裝點書房,并由李釋戡為其取名“綴玉軒”。
事實證明,“馮耿光們”的參與對梅蘭芳的藝術成長確有很大幫助。1913年11月,梅蘭芳跟隨王鳳卿“首戰”上海演出,馮耿光和李釋戡也來到上海幫助聯絡各界人士,宣傳梅蘭芳。大家見梅蘭芳的演出勢頭漸旺,便決定讓梅蘭芳學演一出刀馬旦戲《穆柯寨》。起初梅蘭芳演出時,總有低頭的習慣,臺下觀眾看時會感覺人物弓腰駝背,有損穆桂英的英雄形象。“馮耿光們”商議只要梅蘭芳出現這種情況,他們便以“擊掌為號”作為提示。據梅蘭芳后來講述:“第二次貼演《穆柯寨》,我在臺上果然又犯了這個老毛病。我聽到包廂里的拍掌聲音,知道這并不是觀眾看得滿意的表示,而是幾位評判員發出的信號,我就立刻把頭抬了起來。這一出戲唱到完,一直接到過三四次這樣的暗示。在他們兩邊的看客們還以為他們看得高興,所以手舞足蹈的有點得意忘形哩。其實是穆桂英特地請來治病的大夫在那里對癥下藥呢。”(《馮耿光筆記》第54頁)這里寫到的實情,很少被現今的研究“梅學”的人所重視。
“上海之行”可以說是“馮耿光們”初戰告捷。它不僅使梅蘭芳的名氣得到提升,更主要的是使梅蘭芳的眼界越來越開闊。“馮耿光們”和梅蘭芳在上海的十里洋場經過一番“搏擊”都清醒地意識到:只有跟上時代的步伐,才能贏得屬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此時的梅蘭芳和“馮耿光們”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排演新戲上,這才有了《孽海波瀾》《牢獄鴛鴦》等戲的面世。尤其是馮耿光推薦給梅蘭芳的《宇宙鋒》,如梅蘭芳所說:“我一生所唱過的戲里邊,《宇宙鋒》是下功夫最深的一出。”正是經過幾十年的不斷打磨,才使一出比較溫吞的老戲得到了“復活”,并成為了梅派經典劇目之一。而梅蘭芳為表達對兩位的友情,在1918年馮耿光再度榮任中國銀行總裁時,特在馮耿光借母親壽誕舉辦的堂會上演了一出新創演的《麻姑獻壽》。梅蘭芳在演出《春香鬧學》《滿床笏》后,上演了神仙戲《麻姑獻壽》。其中參考了古典繪畫和雕塑設計出來的新服飾和創編的“杯盤舞”成為亮點。張厚載(聊公)于《馮幼偉氏宅大堂會》中記載5月26日在王府井那家花園的演出盛況:“《麻姑獻壽》,此為梅蘭芳特為馮宅祝壽所編排之歌舞妙劇。梅飾麻姑,唱工身段,繁妙已極。為王母上壽一場,歌聲婉轉,舞態翩躚,尤為全劇最精彩之點,實奄有《散花》《奔月》兩劇之長。座客觀賞之余,莫不驚嘆,以為得未曾有。陳德霖扮王母,扮相年齡,均屬最適當之人選,唱工亦甚吃重,頗為全劇生色,朱幼芬、姚玉芙諸伶,分飾仙女均妥。”(《馮耿光筆記》第90頁)此段文字清晰地表明了梅蘭芳對馮耿光的感激之情,同時也準確地點明了《麻姑獻壽》首演的具體時間和地點。一反多年來“梅學”研究者將《麻姑獻壽》首場演出時間定為1918年秋季、地點是吉祥戲院的說法。
京劇有“三大賢”之說,所指的是楊小樓、梅蘭芳、余叔巖。其中的楊小樓與梅蘭芳是兩代人,楊小樓曾帶著幼年的梅蘭芳到戲園子演出,對梅蘭芳多有幫助和提攜。兩人在有些老戲中多有合作,在新編劇目中也常有配合。如《霸王別姬》中的項羽最初的飾演者就是楊小樓。其一段“力拔山兮氣蓋世”唱段,我聽前輩講,楊小樓最早的演法是坐在桌子后面唱的這段。梅蘭芳與余叔巖的合作在書中有所表露。而真正能夠走到一起還是起源于馮宅堂會上余叔巖與楊小樓、梅蘭芳、王鳳卿、朱桂芬、范寶亭、尚小云、高慶奎、俞振庭、錢金福、許德義等人的大合作戲《八蠟廟》。事后,余叔巖托人請馮耿光說項,有意加盟梅蘭芳的班社。10月19日,余叔巖與梅蘭芳首次合作演出于北京吉祥戲院,上演劇目為《游龍戲鳳》。對于演出之前的排練情況,梅蘭芳在《舞臺生活四十年》中有記載:
在研究戲碼時,首先要避開與鳳二哥合唱過的戲,一則我與王先生合作多年,不能換人,二來叔巖的嗓音尚未完全恢復,相形見絀,反為不美。叔巖提出《戲鳳》(《綴白裘》里有梆子腔《戲鳳》的劇本,起初京劇叫《戲鳳》,后來也叫《游龍戲鳳》,又名《梅龍鎮》,還有寫作《美龍鎮》的),我立刻同意。我曾向路三寶先生學過這出戲,始終沒有唱。這里有兩種原因:一、我和鳳二哥的調門不合適,依了我的調門,他壓得慌;照他的調門,旦角唱調面,我嫌太高。二、這出戲屬于閨門旦性質,花旦的本工,青衣如余紫云也是拿手戲,但他還能踩蹺。當時,唱《梅龍鎮》的李鳳姐,幾乎沒有不踩蹺的。我雖然練過蹺工,在臺上沒有踩過蹺,如果穿彩鞋唱《梅龍鎮》,恐怕觀眾不以為然。現在叔巖提出來,我覺得調門合適,同時,這出戲是譚老中年常唱的戲,他也可以見長;至于大腳片的李鳳姐,雖無前例,但我認為嘗試一下,不至于失敗的。我對叔巖說:“這雖是一出常演的熟戲,但我們要好好兒排對一番,找幾位看過譚老板和您的老爺子《戲鳳》的內外行朋友,看我們排戲,請大家來指點。”叔巖說:“您說的對,我們雖然都會這出戲,但沒有在臺上合演過,先把詞兒溫一下,從后天起,我到您這兒對戲。”馮先生說:“可以找陳十二來研究唱腔,修改臺詞。”我說:“老票友陳子芳是學余老先生(紫云)的,應該找他來幫忙。”有人反對說:“陳子芳號稱余紫云第二,但唱的味兒很怪,做工也有過火的地方。”叔巖對我說:“唱腔您可以自己琢磨,不必聽他的,但陳子芳的確跟先父學過這出,身段地方都有譜,找他一起研究,好的我們采用,不合適的就改,只要我們掌住主心骨是有益無損的。”我說:“好!就這么辦,后天我在家里等您排戲。”
之后,梅、余合作演出了多出劇目。同時“二次出山”的余叔巖在藝術造詣方面由于接觸了“馮耿光們”,眼界更加開闊。直至后來,齊如山加入“馮耿光們”團隊。1931年梅蘭芳、余叔巖、張伯駒、莊清逸、傅蕓子參加齊如山主持成立的北平國劇學會。
我們今天大談梅蘭芳于1919年首次走出國門到日本演出取得巨大成功的時候,卻恰恰忘記了幕后“推手”——馮耿光。這主要是1918年國內外的時局發生了變化,日本朝野也改變從前的對華政策。其中有位財閥大倉喜八郎來到中國聯絡商界人脈。時任中國銀行總裁的馮耿光與此人結交時發現,二人都對本國的傳統藝術頗感興趣,意氣相投。而且大倉喜八郎在日本興建了專為傳統派藝術家提供演出基地的帝國劇場。然而,事態并沒有按照之前約定的邀請梅蘭芳“以中日親善”的項目發展。次年的四月間中國爆發了反日高潮,這對于梅蘭芳出日顯得尤為不合時宜。“馮耿光們”決定此行改為在展示梅蘭芳藝術的同時,研究日本的表演藝術,以兩種藝術交流為目的。當梅蘭芳于4月25日晚抵達東京車站后,受到日本各界人士的歡迎。幾天后,中國駐日代辦公使舉辦了盛大的酒會。時日本內閣總理、全體閣僚及多國駐日大使到場,規格之高,可謂前所未有。在當時的環境下,能夠舉行如此盛事,是因為事前做了充分的準備工作。“其一,大倉喜八郎遵守與馮耿光的承諾,承擔了在日本接待和演出的各項準備工作,動員社會各界迎接梅蘭芳的到來。其二,馮耿光通過王克敏的關系,獲得中國駐日使館的幫助,其三,馮耿光委派中國銀行高級職員許伯明前往日本,協助梅氏訪問。”(《馮耿光筆記》第102頁)
馮耿光作為年長梅蘭芳十余歲的師友,在梅蘭芳的藝術發展和人生關鍵時刻都為其操勞,無論是劇目創作、表演風格,還是安家置宅、后續妻房。即使是馮耿光在中國銀行總裁的位置上已漸漸地失去勢力,無法調動行內資金來支持梅蘭芳到美國演出,但他仍在運用自己的人脈關系幫助梅蘭芳完成此行;同時也多次勸告梅蘭芳鑒于美國經濟危機,最好暫時取消前往。但梅蘭芳等人執意而行。對于此事,梅蘭芳在美國的演出雖然是盛況空前,但“滿譽而歸”后,在經濟方面的確付出了很大犧牲,連帶著“自掏腰包”的馮耿光也賠累其中。隨后,國內政局動蕩,梅蘭芳也是常常向馮耿光請教。像梅蘭芳南遷上海、隱居香港、再返上海、設計避難、撰回憶錄、重回北京等,都有一位重要高參為其“掌舵”。
縱觀馮耿光的人生歷程,曾與政(軍)界的袁世凱、馮國璋、段祺瑞、蔡鍔等人交往過密,在許多關鍵時刻起到過重要作用。馮耿光與銀行界的王克敏、曹汝霖、張嘉璈、王紹賢等人不斷有交往,推動著經濟的發展。尤其馮耿光的特殊身份,使他與商業界大佬保持著密切的關系。僅從書中附錄《中國銀行北平股東概覽表(1930、1931年)》便可以看出,個人持100股之上的資本家就有120位。每個人名都列在其中,只有“永增合”沒有顯露真名。“永增合”是當時創辦北京“永增軍裝局”的民族資本家封竹軒,字永修。
梅蘭芳從美國演出回來后,在京劇的表演和理念方面又有了新的創作思想,他的藝術觀和世界觀已經成熟。尤其是在梅蘭芳登上天安門城樓與新中國的領導人和嘉賓們共同迎接新中國的到來時,梅蘭芳從一個舊社會的藝人,真正成為了新中國的文藝工作者。
梅蘭芳在《舞臺生活四十年》中表示了對新中國的熱愛和對藝術發展的渴望。特別是在慶祝新中國成立十周年之際,上演了新排劇目《穆桂英掛帥》,親飾穆桂英。劇中“捧印”一場的唱詞“我不掛帥,誰掛帥。我不領兵,誰領兵”表明了梅蘭芳此時的雄心。然而,回顧十年來梅蘭芳的藝術經歷,我們不難看出,此時的梅蘭芳煥發了青春。
那是1949年6月下旬的一天,梅蘭芳收到一封從北平寄來的信。原來是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發來的邀請函,署名是政務院總理周恩來。24日,梅蘭芳攜家人回到闊別多年的北平,出席了“文代會”,被推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會上,毛澤東主席講道:“我們相信,經過你們這次大會,全中國一切愛國的文藝工作者,必能進一步團結起來,進一步聯系人民群眾,廣泛地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文藝工作,使人民的文藝工作大力發展起來。”梅蘭芳聽周恩來總理說到“文藝工作者是精神勞動者,廣義地說來也是工人階級的一員”后,心情非常興奮,說道:“我在會場中看到的是光明、團結,一種活生生新鮮的力量鼓舞著我,使我感覺到逝去的青春又回來了。”9月,在周恩來總理的提議下,梅蘭芳應邀出席了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并發表了心聲:“我們地方戲的工作者,在舊社會里面,向來是不被當人看待的。今天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翻身了,做了新中國的主人。”“現在我們既然在政治上的地位提高了,更應自覺,更應努力本位工作,在毛主席領導下,前進!”
1950年4月3日,中國戲曲研究院成立,周恩來總理應梅蘭芳邀請,題詞“重視與改造,團結與教育,二者不可缺一”祝賀。毛澤東主席題詞“百花齊放,推陳出新”。7月6日,梅蘭芳任職中央文化部戲曲改進局京劇研究院院長。1955年1月6日,中國京劇院在周恩來總理的支持下成立,梅蘭芳擔任院長。幾十年后,我曾聽時任中國京劇院黨委書記、副院長馬少波說,當年周恩來總理接見梅蘭芳時言道:“梅先生可以到各地巡回演出,起示范作用。可以整理舞臺經驗,著書立傳。中國京劇院的工作,由少波同志負責。”
馬少波還說,周恩來總理對梅先生想入黨的事很是關心,有意做他的入黨介紹人。但梅先生認為,“如果大家入黨都由中央領導同志做介紹人,那中央領導的負擔就太重了。我是一個普通的演員,最好找最了解我的同志做我的入黨介紹人。當然,最了解我的是您(指馬少波)和張庚同志”。梅蘭芳在入黨申請書中寫道:“在黨的極大關懷和教育之下,我認清了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通過革命的偉大勝利,祖國的偉大建設和黨大公無私地為人民、為整個人類謀福利的偉大措施,我深深地受到了感動,使我真正認識到黨的馬列主義的真理,也認清了作為一個藝術勞動者所應走的正確的光明的道路。”梅蘭芳以飽滿的熱情和學習姿態終于在1959年7月1日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新中國成立后的十幾年,梅蘭芳以極大的熱情參與到人民的戲曲事業中。他的活動日程排得很滿,到京、津、滬、漢和東北工業區演出,赴朝鮮和華南慰問解放軍,訪問維也納、蘇聯、日本等國,以藝術促進外交。即使是在去世前夕,梅蘭芳還在惦記著新疆鐵路通車典禮前祝賀演出的事宜。這段時間,梅蘭芳身邊雖然沒有了“馮耿光們”這些高參,但在共產黨的指引下,梅蘭芳的藝術造詣得到了更高的提升,已經從“伶界大王”朝著高標準的藝術家攀登。從之前的“玩意取悅闊佬”向著“藝術為人民服務”轉化,真正在文化自覺和理論修養方面成為了京劇界的領袖人物,其“移步不換形”等藝術思想至今還指導著當今的京劇界人士為京劇的繼承發展而貢獻力量。
(作者單位:國家京劇院)
責任編輯 王彩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