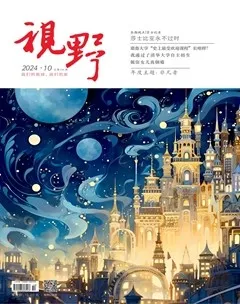莎士比亞是不是科學家?
曹玲

人們熟知的莎士比亞有很多身份,唯一沒有的是科學家,但人們梳理了他的作品,從中讀到了新興的宇宙學論述以及形形色色的精神病學描寫,甚至有人認為他開創了現代醫學……
宇宙學靈感
午夜時分,哈姆雷特父親的幽靈來到埃爾西諾城堡。值夜崗的守衛伯納多告訴哈姆雷特的朋友霍雷肖,夜空中出現一道亮光時幽靈便會出現。“昨夜,正當北極星西邊的那顆星,在同一位置照明了此夜空時”,伯納多的話被幽靈的到來打斷。
《哈姆雷特》中出現的那顆星很可能是超新星爆發。1572年11月,一顆出現在仙后座的明亮新星照亮了夜空。今天我們知道那是一顆超新星,超新星意味著一個巨大的恒星爆炸死亡,它是如此明亮,幾個月時間內亮度都超過了金星。丹麥天文學家第谷觀測到它,并發表了一個簡短的描述,這個奇特的幽靈現在被稱為“第谷新星”。
莎士比亞的作品中充滿了天文學事件,以往被認為是文學手法,天體即某種預兆。但是近年來,人們對莎士比亞的星空有了新的視角。研究者認為,莎士比亞生活的年代(1564~1616)適逢科學革命時代,很多新研究、新發現和根深蒂固的舊有學說發生猛烈撞擊。
哈姆雷特在獨白中隱約問到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很久以來人們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1543年哥白尼出版了《天體運行論》,提出日心說,認為地球圍繞太陽運轉,打破了地心說的壟斷地位。地心說最早起源于亞里士多德的理論,他認為整個宇宙是一個多層水晶球,地球位于水晶球的中心,恒星、行星、太陽和月亮都在各自的軌道上圍繞地球旋轉。公元2世紀,希臘天文學家托勒密進一步完善了地心說,建立了數學模型。由于亞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聲望,加上這種理論迎合了后來羅馬教廷的宗教思想,直到哥白尼之前很少有人對此提出異議。
最初,哥白尼的觀點沒有改變這些看法,據天文學家羅伯特·雷科德于1556年出版的《知識的城堡》一書記載,此時哥白尼在英格蘭已經有了一些追隨者。20年后,天文學家托馬斯·迪格斯出版了第一本詳細分析哥白尼學說的論述,這本名為《天體運動的完整表述》的書中甚至包含了一個太陽系圖表,恒星無限地向外擴展,將亞里士多德的有限宇宙拓展為無限宇宙。
《哈姆雷特》劇本誕生于1599-1602年。在第二幕,王子預見自己是“無限空間之王”。這可能暗指一個新的、無窮的宇宙。莎士比亞很可能受到第谷的影響,第谷在黑文島對超新星進行了詳細的觀測,距離《哈姆雷特》一劇中主要場景發生地艾爾西諾城堡非常近。值得注意的是,第谷的兩個親戚分別叫作羅生克蘭和蓋登思鄧,與暗中監視哈姆雷特的間諜名字雷同,而這兩個名字在丹麥人中并不普遍,劇中其他角色均采用普通名字,命名手法非常不一致。
最近剛從賓夕法尼亞大學退休的天文學家皮特·亞瑟認為,整個戲劇可以被看作一個席卷歐洲的科學革命的預言。“劇中弒兄篡位的角色克勞狄斯,名字與提倡地心說的古天文學家托勒密相同,莎士比亞在給人物命名時別有用心。”
科學革命的沖突也反映在戲劇的行動和對話中。當哈姆雷特宣布他打算返回維滕貝格繼續學業時,克勞狄斯宣布這樣的舉動“有悖我們的愿望”。亞瑟認為這暗示行星逆行,正是這種星體的運動最初激發人們了解天體運行。雖然亞瑟的觀點很可能夸大了劇中天文學的影響,但是《哈姆雷特》暗示劇作者已經吸收了一些新的天文學理論。
在《特洛伊羅斯與克瑞西達》中也反映了新的天文學觀點。第一幕第三場中,俄底修斯說:“諸天的星辰,在運行的時候,誰都恪守著自身的等級和地位,遵循著各自的不變的軌道,依照著一定的范圍、季候和方式,履行它們經常的職責;所以燦爛的太陽才能高拱出天,炯察寰宇,糾正星辰的過失,揭惡揚善,發揮它的無上威權。”牛津大學的喬納森·貝特指出:“強調太陽中心可能暗示著以太陽為中心的宇宙學。”
1609年,意大利天文學家伽利略改良望遠鏡,人們用肉眼即可看到更多的星體,進一步動搖了地心說的地位。1610年,伽利略發現了木星的四顆衛星,它們的位置不斷改變,不符合古典天文學的宇宙觀。
1611年首次公演的《麥克白》最后一幕,主人公辛白林進入夢鄉,四個家族的鬼魂圍著他轉,并呼叫羅馬神話的眾神之王朱庇特(Jupiter)。聽到他們的請求,朱庇特下降出場,四個鬼魂圍繞他旋轉。這一幕是否暗指木星(Jupiter)以及伽利略新發現的四顆木衛星?亞瑟和馬薩諸塞大學莎士比亞研究學者斯科特·梅森諾以及牛津大學的約翰·皮徹都這樣認為。
但是16世紀90年代莎士比亞開始創作戲劇時,他知道這些新的觀點嗎?1572年只有八歲的他,怎么會記清夜空的情況?目前沒有任何書信或者日記有確鑿證據表明他對天文感興趣,只有跡象表明他可能接觸過這些新知識。學者發現莎士比亞和迪格斯家庭有大量聯系,他們的住處在倫敦北部只距離幾個街區。迪格斯讀文學的小兒子倫納德是莎士比亞的戲迷,曾為莎士比亞撰寫過首批出版劇目封面上的詩句。
莎士比亞很可能和布魯諾也有聯系,當時布魯諾在歐洲宣揚哥白尼的學說。他不太可能認識布魯諾,但可能會通過街坊兼御用印刷師理查德·福爾德獲得布魯諾的天文知識,因為理查德曾經在印刷過數本布魯諾著作的印刷師手下當學徒。莎士比亞也可能認識布魯諾的熟人,來自意大利的翻譯家約翰·佛羅里奧,佛羅里奧是莎士比亞一個贊助者的家庭教師,他也曾列舉過幾段佛羅里奧翻譯的蒙田散文。
這些觀點剛開始被主流學術界所注意,也可能是夸大了莎翁作品中“科學”的影響。但不可否認的是,莎士比亞有一顆永不滿足的好奇心,超越了人類,直指自然本身。
精神疾病記錄者
癲癇、精神崩潰、睡眠障礙……16世紀的醫學非常粗陋,但莎士比亞筆下卻描寫了大量的現代醫學細節,劇中一些角色的行為往往和現代醫學所描述的神經疾病癥狀有著驚人的相似性。莎士比亞細致的描述激勵了后世的研究者,其中一個例子是弗洛伊德。他在兒時讀過莎士比亞,并在精神分析學作品中加以解讀。弗洛伊德曾經說:“早于我的詩人和哲學家發現了無意識。”耶魯大學的文學評論家哈羅德·布魯姆認為弗洛伊德所指的即是莎士比亞。
佛洛伊德對莎士比亞的興趣可能是在參加了醫學先驅讓——馬丁·沙可的講座之后形成的。沙可是法國神經學家,被稱為“神經病學之父”,他關于神經官能癥和癔癥的理論讓弗洛伊德從神經病學轉向了心理學。沙可常常分析莎士比亞筆下人物的行為和性格特征,至今為止仍有很多神經科學家在課堂上使用莎士比亞筆下的人物作為案例。他作品中豐富的細節描寫意味著一些癥狀的靈感很可能來自真實生活。或許大師被來自倫敦圣瑪麗伯利恒醫院的故事所影響,這原本是一個小修道院,1377年開始用來收容精神病人,后來成為臭名昭著的瘋人院,早年人們經常在作品中描寫瘋人院的故事。當然,沒有人會認為莎士比亞的作品應該被當作醫學報告來讀,但這些來自生活的觀察可能會幫助他塑造更加生動的人物形象。
神經科學家如何解讀莎士比亞筆下的人物?以麥克白夫婦為例。麥克白經常出現幻覺,他走向鄧肯的臥室時,“一把滴血的刀在他眼前晃動”,有聲音告訴他,他再也無法入睡。這些癥狀表明他有認知功能受損、無意識舉動、失眠和精神崩潰。是否有一種精神疾病能夠囊括他的行為?一些病人,特別是來自蘇格蘭的病人,表現出了類似的退化,麥克白可能患有朊病毒病,這是一種人和動物共患的亞急性海綿狀腦病,被認為是庫賈氏綜合癥的變種,簡單來說另一個版本就是瘋牛病。
麥克白夫人則是另一回事,她患有典型的異睡癥,異睡癥包括夜驚、夢游、磨牙、尿床、夢囈等等。麥克白夫人有夢游癥,夢游時會洗手。15分鐘洗一次手說明她有強迫癥,試圖洗掉想象中的污點。她說,這雙手就永遠洗不干凈嗎?如今,洗手被認為是減輕情緒壓力的做法。
再比如李爾王。80多歲的李爾王遠遠超出了當時的平均壽命,他說話狂妄,往往不由自主地加快語速,這是帕金森癥的癥狀之一。他有時候不認識自己的女兒,有時候又能認出來,甚至還相信自己已經死了,這是科塔爾綜合征的癥狀,這樣的患者感到自己已不復存在,并認為其他人,甚至整個世界包括房子、樹木都不存在了。李爾王的整體癥狀提示他可能患有路易體癡呆,這是老年癡呆癥的一種形式,僅次于帕金森癥而居癡呆的第二位,主要臨床表現為波動性認知障礙、帕金森綜合征及以視幻覺為突出代表的精神癥狀。
以哈姆雷特為例,剛剛喪失親人的哈姆雷特認為人活著不值得,說“我早已把生命看得輕如鴻毛”。他沖動、意外地殺死了女朋友的父親。他的情緒極度搖擺,忽高忽低。他會很溫柔地對待奧菲麗婭,也會展現出殘忍和暴力。他的機智和洞察力首屈一指,同時又憂郁、猶豫不決。根據最新的《精神疾病分類和診斷標準》,哈姆雷特的癥狀暗示他患有抑郁狂躁型憂郁癥。
諸如此類的分析還有很多。布魯姆甚至說莎士比亞“發明”了人類。意思是雖然各種性格特點的人都早就存在,但在莎士比亞之前沒有人如此詳盡地記錄他們,激勵后代更深刻地認識到自己的行為。不管你是否贊同這個觀點,莎士比亞對近代精神醫學有著無法否認的影響。
莎士比亞為何吸引我們?
利物浦大學的文學教授和心理學家菲利普·戴維斯和班戈大學的心理學家紀堯姆·蒂里第一次見面時,他說:“我的夢想就是理解莎士比亞如何改變大腦。”蒂里這樣一位神經科學家能幫他忙嗎?他們加入了一個小范圍的研究團隊,通過詞匯、微妙的雙關以及對觀眾心理的把握來檢測作家的天賦。
數世紀以來,學者們認為莎士比亞掌握的詞匯量比同時代的人更大,他暢游在這個巨大的詞匯池塘里捉魚。但是澳大利亞紐卡斯爾大學的休·克雷格卻發現莎士比亞的詞匯量并不比他同時代的劇作家克里斯托弗·馬洛、湯瑪士·梅道登和本·瓊森更大,使用的術語也沒有比同時代的人更復雜,制造新詞匯的比率也沒有什么不同尋常。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莎士比亞天才的精髓,為什么他的作品如此扣人心弦?莎士比亞自己寫道:“我最擅長的是給舊詞穿上新裝。”戴維斯和蒂里集中研究莎士比亞熟練運用的詞類轉換,這在西方被稱為“功能轉換”。比如《奧賽羅》中,當伊阿古說服奧賽羅相信妻子苔絲德蒙娜不忠,他告訴奧賽羅:“這是最刻毒的惡作劇,魔鬼的最大玩笑,讓一個男人安安心心地摟著枕邊的蕩婦親嘴,還以為她是一個三貞九烈的女人!”這段臺詞把動詞kiss(吻)替換成名詞lip(唇),同時使用wanton(放蕩的)這樣一個形容詞作為名詞。再比如《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中寫道:“他用話騙我,姑娘們,他用話騙我。”其中word本是名詞,這里化作動詞,形容巧言令色的行為。
蒂里說:“莎士比亞常常在場景轉換時使用‘功能轉換,這讓大腦有一個‘哇哦的時刻,從而加強戲劇感。”莎士比亞這種“功能轉換”的修辭手法,讓讀者感覺到與正常的語法不符合,但是卻又不妨礙他們理解這個句子的意思。這種手法在不傷害傳達意思的基礎上,產生了一種新奇性,喚起讀者更多的注意力和認知水平,讓閱讀變得更有挑戰性。
這類似于魔術表演,人們雖然明知其中隱藏著一些小花招,但卻不知道這是怎么發生的,這種困惑會讓大腦十分興奮。蒂里說:“伊麗莎白時代的其他作家也這樣用,但是莎士比亞沉迷于此。”
當他們發現如此微小的語法轉換卻會在大腦中引發不小的觸動時,他們驚呆了。腦電圖和功能磁共振成像掃描顯示,莎士比亞的句子激活了大腦中與情感以及自傳體記憶有關的區域,自傳體記憶是關于個人復雜生活事件的混合記憶,此外還激活了基底核,這是一個雙語切換時會激活的區域。蒂里說:“他迫使大腦更加運轉,更深層地處理信息。”
除了詞匯,莎士比亞的舞臺指示也說明他非常敏銳地理解了觀眾的想法。牛津大學進化心理學家羅賓·鄧巴在同一時間追蹤很多人的思想活動,他的研究表明,我們真實的社交活動會受到一些限制,三個或者更少人在場時,我們會交流一些流言蜚語,比如別人的想法或感覺;如果有四個或者更多人在場,我們會傾向于談論那些沒有多少爭議的話題,比如天氣。
鄧巴和他的同事分析了莎士比亞的舞臺指示,顯示他如何以類似的方式約束人物談話。在莎士比亞的劇中,通常情況下只有兩三個人談論另外一個角色的想法和感受,比如苔絲德蒙娜對奧賽羅的副將凱西奧的致命感情;而四個或四個以上的人談論的則是更普通的主題,比如一場戰爭。另有學者研究了同時期其他作家的作品,發現其他作品中關于感情的談話只有半數發生在兩三個人之間,而莎士比亞戲劇中這樣的比例達到90%。“這說明莎士比亞是一個多么偉大的觀察家。”鄧巴說。目前,鄧巴的論文正在審核中。
對于鄧巴來說,這是一個為期三年的研究項目,他將研究戲劇心理學。或許這些研究可以讓我們更接近戴維斯的目標,更好地理解英語世界最偉大的劇作家如何改變我們的頭腦。用神經科學的方法分析文學,諸如此類的研究隸屬于一個方興未艾的交叉學科,名為“神經文學”。“這給我提供了一個新的方式來思考我對戲劇的直覺和反應。”鄧巴說。或許這是一個探索莎士比亞的勇敢的新世界。
(摘自《三聯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