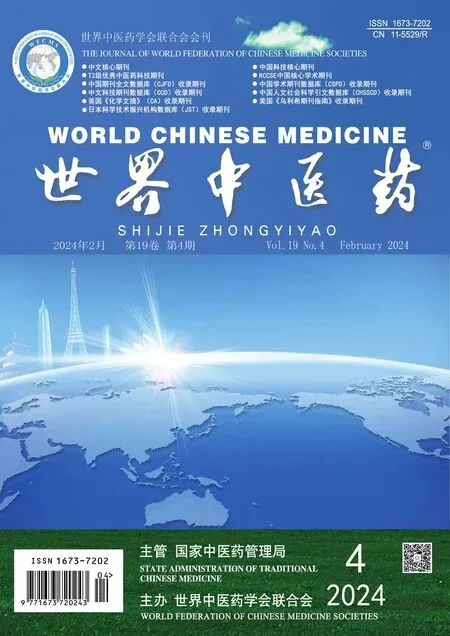林蘭教授從心論治糖尿病經驗
陳玉鵬 湯怡婷 龐 晴 楊亞男 吳善瑛 倪 青
(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北京,100053)
糖尿病是由于胰島素分泌障礙和(或)機體靶組織或靶器官對胰島素敏感性降低引起的以血中葡萄糖水平長期升高為特征的代謝性疾病[1]。國際糖尿病聯盟研究數據顯示全球大約有5.37億成年人患糖尿病。預計到2030年達到6.43億[2]。隨著人口年齡結構與生活方式的改變,我國糖尿病患病率顯著增加,至2017年已高達11.2%[3]。持續的高血糖水平累及心腦血管、腎臟、神經等,是導致心血管疾病、失明、腎衰竭和下肢壞死等并發癥的重要原因[2]。糖尿病及其并發癥嚴重影響了患者的生命質量,給個人和社會帶來了沉重的經濟負擔。糖尿病屬于中醫學“消渴”“脾癉”范疇,首見于《素問·奇病論篇》:“此五氣之溢也,名曰脾癉……夫五味入口,藏于胃,脾為之行其精氣,津液在脾,故令口干也,此肥美之所發也,此人必數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內熱,甘者令人中滿,故其氣上溢,轉為消渴。”中醫學對消渴的認識歷史悠久,歷代醫家對消渴論述頗多,積累了豐富的診療經驗,現代臨床研究亦證實中醫藥具有降低糖尿病發生風險、降低血糖、改善癥狀和體征、提高生命質量等作用,治療糖尿病及其并發癥療效明顯和優勢獨特[4-6]。
林蘭教授是全國名中醫、首都國醫名師、全國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指導老師、中國中醫科學院首席研究員,從事醫療、科研、教學等工作50余年,致力于中醫、中西醫結合治療糖尿病等內分泌疾病的臨床診療工作,創立了糖尿病“三型辨證”理論,引領糖尿病領域的醫療、科研、新藥研發等,為糖尿病的診治提供了寶貴經驗。古今醫家多認為消渴病性為本虛標實,以陰虛為本,燥熱為標,治療多遵循三消理論,重視從肺、脾、腎論治,而對于糖尿病與心的關系論述較少。林蘭教授認為消渴的發生發展與肝、心、脾、肺、腎五臟皆密切相關,辨證施治中尤為重視從心論治糖尿病,本文將林蘭教授從心論治糖尿病的獨到見解淺析如下。
1 心與糖尿病
1.1 心氣郁結——消渴之源起 《素問·陰陽別論篇》曰“二陽結,謂之消”,明確指出消渴病的淵源為“二陽結”,“二陽”即是陽明也,為足陽明胃和手陽明大腸,廣義則為中焦脾胃及大、小腸。“結”字《說文解字》訓:“結,締也,從系吉聲;締,結不解也。”由此可知“結”是氣機郁滯交合不散之意。李杲言:“二陽結謂之消,二陽者陽明也……結者津血不足,結而不行,皆燥熱為病也。”[7]氣機郁結,久而化熱,內火煎灼津液耗傷氣血則致消渴。
二陽結而致消的始動因素歸于心氣郁結。《素問·陰陽別論篇》言:“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其傳為風消。”王冰注云:“二陽,謂陽明大腸及胃之脈也。”由此可知本處之“二陽”當與“二陽結,謂之消”中的“二陽”同義。“發心脾”當作“發于心脾”,張介賓曰:“二陽,陽明也,為胃與大腸二經。然大腸小腸皆屬于胃……蓋胃與心,母子也;人之情欲本以傷心,母傷則害及其子……故凡內而傷精,外而傷形,皆能病及于胃,此二陽之病,所以發于心脾也。”據楊上善考證“心脾”當為“心痹”[8],《素問·四時刺逆從論篇》“陽明不足病心痹”亦可證。《素問·五臟生成篇》闡釋心痹之病機在于“有積氣在胸”,《金匱要略》亦云“胸痹,心中痞氣,氣結在胸”“胸痹,胸中氣塞,短氣”。《靈樞·五變》曰:“其心剛,剛則多怒,怒則氣上逆,胸中蓄積,血氣逆留,髖皮充肌,血脈不行,轉而為熱,熱則消肌膚,故為消癉。”林蘭教授認為情志不暢是導致糖尿病的重要因素,現代生活節奏快,持續壓力狀態,不良情緒累積致使氣機郁結,正如《素問·舉痛論篇》所言:“思則心有所存,神有所歸,正氣留而不行,故氣結矣。”病初在氣分,隨著病情的發展,累及臟腑經絡。《類經》載:“心為五臟六腑之大主,而總統魂魄,并賅意志,故憂動于心則肺應,思動于心則脾應,怒動于心則肝應,恐動于心則腎應,此所以五臟惟心所使也。”心為一身之君主,總領魂魄意志,故情志失調首先致心氣不暢而后應于五臟。心氣痹阻不通,心火上炎,消爍津液,陰虛熱盛,消渴始生。研究發現不良情緒可增加糖尿病的風險和嚴重程度,伴有抑郁的成人發生2型糖尿病的風險較普通人增加37%[9-10]。
1.2 心火不降——消渴糖毒生 糖尿病的發生發展與B細胞功能損傷及數量減少直接相關[11],胰島B細胞長期暴露于超生理濃度的葡萄糖中,發生氧化應激反應導致細胞凋亡,即糖毒性[12]。林蘭教授認為糖毒性可理解為中醫的“火盛成毒”,心火不降致使火化為毒是導致糖尿病發生發展的重要病機。《臨證指南醫案·三消》云:“心境愁郁,內火自乃消癥大病。”《醫宗己任篇·消癥》亦曰:“消之為病,一原于心火熾炎。”心火在消渴病機演變中具有重要地位。高血糖的毒性作用是指在高血糖持續狀態下,多元醇旁路激活,產生山梨醇及果糖堆積致細胞內高滲狀態和細胞水腫,使細胞形態及功能改變,細胞破損,可理解為中醫的“熱郁為毒”[13]。心火不降是熱毒之源。《溫疫論·服寒劑反熱》言:“氣為火之舟楫,火賴氣運,氣升火亦升,氣行火亦行,氣血火熱膠著,終致火熱內蘊成毒。”心氣郁結日久則致心火不降,獨盛于上。《成方便讀》言:“毒者,火邪之盛也。”明確指出毒為火之聚,火盛化為毒。
火毒為陽邪,易傷津耗氣,“火”為元氣之賊,“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氣虛失于生化,陰傷無以濡養,津液氣血虧損,臟腑受損。火毒為病,無其不焚,其害無窮,損及多臟。“肺為水之上源”,津液輸布有賴于肺氣宣發肅降,火性炎上移熱于肺,火亢乘金,火釀成毒耗傷肺氣,則津液無以敷布,機體無以潤澤,見口干多飲、氣喘痰嗽。火炎金燥,傷及肺陰,虛火上炎,則面紅潮熱、口舌糜爛,咽喉腫痛。脾胃居中央為人體上下升降之樞紐,具有傳輸、布散津液及水谷精微的作用。心火化毒乘其脾胃之位,母實傳子,“壯火食氣”,心火亢盛耗傷脾胃元氣,使脾土運化失司、轉輸失常,發為消渴。心火不下行,停滯于中焦則見多食易饑;心火耗傷中焦陰液,陰虛陽亢則見大渴恣飲;毒傷脾氣,精微外泄則見形體消瘦、尿甜。腎主水,封藏之官,具有統攝人體陰液和潛藏五臟六腑之精氣的作用。心火太過,反侮腎水,腎陰消灼,相火益亢,火獨盛于上而陰水虧虛只降不升,陰陽水火不交引發消渴。腎陰為陰液之根本,腎陰消耗,人體失于滋養則見形體消瘦、眩暈耳鳴等;毒損腎氣,固攝無權則見飲一溲二、溲似淋濁。糖毒性導致胰島B細胞損傷的關鍵在于其引發醛糖還原酶活性增高,有藥理研究證實具有清心降火作用的黃連可通過抑制醛糖還原酶活性的作用,降低高級糖基化終產物形成,并對小鼠心、肝、腎等組織器官起保護作用,為心火不降,釀生火毒致使糖尿病發生發展提供了病理生理學依據[14]。此病理階段屬于“三型辨證”中陰虛熱盛證范圍,為糖尿病早期階段,病程相對較短,一般小于5年,發病年齡較輕,基礎胰島素水平高,呈現高胰島素血癥,并發癥少而輕,以胰島素抵抗表現為主。
1.3 君火不明——消渴變證生 李中梓言:“火者,陽氣也。天非此火不能發育萬物,人非此火不能生養命根,是以物生必本于陽。”火是推動生命活動、維持機體能量代謝的原動力。火衰陽弱,機體失于溫煦則痰濕、瘀血等陰邪泛溢,而痰濕、瘀血是導致糖尿病諸多并發癥的主要病因。陰陽互根互用,相互依存,消渴內熱傷陰,久病難復陰虛損及于陽,氣虛不能助陽,而致陽虛。林蘭教授認為陰陽兩虛是糖尿病發展的必然趨勢,此階段并發癥多且嚴重,表現為胰島功能衰竭[15]。君火寄于心,為五臟六腑陽氣之用,心為火之源,故消渴日久陰損及陽,當先傷其心陽。
《素問·調經論》載:“寒氣積于胸中而不瀉,不瀉則溫氣去,寒獨留,則血凝泣,凝則脈不通。”心主血脈,心陽虧虛,血脈凝澀不通,血行不暢,瘀血乃生。同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提出“心生血”,即心參與血液生成。唐容川言:“食氣入胃,脾經化汁,上奉心火,心火得之,變化而赤,是之謂血。”[16]水谷由中焦脾胃運化,受營氣和取津液入脈,經心陽的作用赤化為血。心陽受損,一則化生血液不足,血虛不運極易成瘀;二則赤化無力,脾胃運化之精微物質無以赤化入血滋養臟腑經絡而留溢于外,血濁內生,血液黏滯導致血停成瘀,故見血糖、血脂升高。
君火不明,心陽虧虛,痰瘀內生,流注于不同的臟腑經絡,變證叢生。《醫碥》曰:“脾之所以能運化水谷者氣也,氣寒則凝滯而不行,的心火以溫之,乃健運而不息,是為心火生脾土。”心火不足,火弱土虛,脾土運化無權,水液運化輸布失司,清者不升,濁者不降,水液停聚凝結而為痰濕。心陽溫煦,助肺金敷布陰液,金賴火暖才能升降正常。心陽虧虛致金寒水冷,宣降失司,津液停聚而成痰。心火下交于腎助其氣化以調節津液代謝,火衰水寒,水液清冷難行,凝滯為痰濕。“脾為生痰之源,肺為貯痰之器,腎為痰之本”,肺、脾、腎不得心火溫煦,水濕貯滯不行,痰濕積滯。痰瘀互結阻滯經絡,氣血不能通達四肢經脈,發為糖尿病周圍神經病變、糖尿病足等;痰濕、瘀血交互為患,痹阻心脈,導致糖尿病性心臟病發生;痰濁內擾,瘀血阻滯腦絡,蒙蔽清陽,清陽不升,氣血不通,發為消渴中風。證候學研究發現[17]痰、瘀等病理產物是2型糖尿病及其并發癥患者中醫證候規律分布和演變的關鍵因素。此病理階段屬于“三型辨證”中氣陰兩虛、陰陽兩虛范圍,病程較長,一般大于5年,并發癥多,隨著年齡和病程的增長比例有所增加,以胰島B細胞功能紊亂、衰竭胰島素抵抗表現為主,為糖尿病中、晚期階段。
2 從心論治三步法
2.1 調神 《養生論》云:“精神之與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喪于外,猶君昏于上,國亂于下也。”神意即人體的精神思維活動,是人體生命活動的最高主宰。林蘭教授從心論治糖尿病強調以調神為先。憂愁思慮等情志異常導致心氣郁結化火,火聚成毒,火毒上炎,易擾亂神明,臨床癥見焦慮失眠,心悸怔忡,口舌生瘡,煩熱渴飲等,故調神之法以清潤安神為要。林蘭教授創清潤方,組方包含黃連、黃柏、知母、虎杖、大黃、地骨皮、百合等,方中黃連性寒味苦,專入心經以瀉實火,《本草逢源》載其“氣薄味厚,降多升少,入手少陰厥陰。苦入心,寒勝熱,黃連、大黃之苦寒,以導心下之實熱”;黃柏味苦,性寒,入腎、膀胱經,功擅清熱瀉火,《本草新編》中指出“黃柏,味苦、微辛,氣寒,陰中之陰……專能退火解熱,消渴最效”;大黃味苦性寒,能瀉火解毒,清熱涼血,引熱下行;黃連、黃柏、大黃三者相須為用,一方面清解邪熱,另一方面引心火下行而交通心腎。知母味苦,性寒,入肺、胃、腎經,具有清熱養陰生津之效,配伍三黃達潤燥除熱之功。百合與知母相伍,清心火安心神;地骨皮滋陰清熱,增清潤之力。虎杖味苦,性微寒,可清熱解毒,利濕散瘀血。諸藥同用,以清為主,清中有潤,共奏滋陰清熱之功。林蘭教授指出治心安神以清潤為妙,心火宜引降,而不在苦寒直折,故黃連、黃柏、大黃劑量不宜過大,否則苦寒傷胃、阻遏氣機,臨床用量多以6~9 g為主,取“治上焦如羽,非輕不舉”之意。調神法為“三型辨證”理論中陰虛熱盛型證治特點之一,以清泄邪熱,清潤養陰為治則,以改善癥狀、減輕胰島素抵抗、降低血糖、預防并發癥的發生和發展為目的。
《靈樞·本神》曰:“兩精相搏謂之神。”精與神關系緊密,精是神之體,神是精之用。林蘭教授指出調神應重視滋精養神,“精”分為腎所藏的先天之精與脾化生的后天之精,臨床可用黨參、白術等健運脾胃生后天之精,配伍肉蓯蓉、女貞子、生地黃補腎填先天之精。健脾補腎,生精養神,使精足神旺。調神之法亦因重視調暢情志,臨床中林蘭教授尤其重視患者的健康宣教及心理疏導,注意增強患者信心,消除患者思想負擔,保持良好情志狀態,引導患者形成早上7點前起床,晚上10:30前入睡,一日三餐定時定量,早、午餐后步行20~30 min,晚餐后步行40~60 min的規律生活方式,以平穩患者心志。調暢情志以調心神,截斷糖尿病的致病因素,有效發揮心身同治的作用。
2.2 調氣 心主血脈,心氣推動血液滋養濡潤周身。消渴日久,氣隨陰脫,內火耗氣,必致氣虛。心氣虧虛則行血無力,血脈不行,氣又為血所阻,不得上升,津液不能隨氣上布,加重糖尿病病情,臨床癥見心悸怔忡,失眠健忘,氣短乏力,神疲自汗等。林蘭教授指出調氣之法當以益氣為先,首創益心湯以益氣養心,常用方藥為太子參、麥冬、五味子、炒酸棗仁、柏子仁等。方中太子參大補元氣,又生津液;麥冬甘寒,養陰清心泄熱,補陰津以載氣,具有開心結、通脈絡之功,《神農本草經》載其“主治心腹結氣……胃絡脈絕”;二者相合,氣陰雙補,益氣生津復血脈。加用酸溫之五味子,收耗散之氣。酸棗仁味酸入肝,色赤入心,心之肝藥也,可養肝氣、除心煩、安心神,為滋養安神之圣藥。柏子仁性平,不寒不燥,補益心脾,滋養肝腎,有養心安神之功。諸藥合用,共奏益氣養陰安神之功。方中五味子屬酸斂之品,兼夾痰濕、血瘀時不可過早使用,以防閉門留寇。林蘭教授強調益氣養陰法為糖尿病治療基本法則,但臨床應用中仍應細究益氣、養陰之次序。氣屬陽,津血屬陰,滋補陰液之品有賴氣之化生方能濡養機體。若患者氣虛甚,當以補氣為先,輔以補陰之品避免滋膩耗氣傷陽。若患者津液虧虛、陰血不足,則以補陰養血之藥為主,酌加益氣之品以化津血。
周之千言:“心腎相交,全憑升降,而心氣之降,由于腎氣之升,腎氣之升,又因心氣之降。”[18]心氣引心火下降以交腎水,使水火既濟,陰陽平和。林蘭教授指出通降心氣亦為調氣的重要治法,通降心氣當治從肝、脾。肝主疏泄,調節氣的升降出入,臨床常用柴胡、香附、枳殼、白芍等,養肝之體、利肝之用以協心氣下降交于腎。脾土位于中央,交通上下,脾氣助心氣引心火俯宅坎中,《問齋醫案》“緩交心腎,必謀脾土”,臨床常用陳皮、白術、茯苓、半夏等。另可酌加黃連,借其苦寒之性引降心火;石菖蒲“辛苦而溫,芳香而散。補肝益心,開心孔,利九竅”(《本草備要》);郁金開心竅、行氣解郁;血中之氣藥川芎行氣活血以開心腎相交之道路。調氣法為“三型辨證”理論中氣陰兩虛型證治特點之一,以益氣養陰為治療大法,輔以通降心氣,以降低胰高血糖素水平,增加胰島素受體數目,改善胰島素抵抗,延緩并發癥的發展為目的。
2.3 調形 消渴日久難復,痰濕、瘀血內生,因實致虛,并發癥多而重,胰島功能衰竭,病位深入,功能紊亂,致臟腑經絡形質損害。何夢瑤言:“子和謂心火太盛津液耗涸,在上則為膈消,甚則消及肺臟,在中則為腸胃之消,甚則消及脾臟,在下則為膏液之消,甚則消及腎藏,在外則為肌肉之消,甚則消及筋骨,四藏皆消,則心自焚而死矣……”[19]明確指出消渴終致心臟形質損害而不治。流行病學研究發現心血管疾病是2型糖尿病患者發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20]。林蘭教授指出治療糖尿病過程中尤應重視調心復形以防止心血管事件發生,提出以活血化瘀、化痰除濕為基本治法。臨床常用糖心平加減,常用方藥為黃芪、太子參、枳實、水蛭、全瓜蔞、薤白、清半夏等,方中黃芪性微溫味甘,為補氣之圣藥,《藥性論》載其“逐五臟間惡血”;太子參益氣健脾生津;枳實破氣消積行氣,三者相伍,補而不滯,溫而不燥,補氣助血行津,痰瘀自除。水蛭味咸、苦,性平,破血化瘀而不傷正氣,《醫學衷中參西錄》“凡破血藥多傷正氣,惟水蛭味咸,專入血分,于氣分絲毫無損,而瘀血默消于無形”。瓜蔞理氣寬中,導痰濁下行;薤白辛溫,通陽散結以化濁音;半夏增強降逆化飲,三藥相配化痰濁、散陰寒、宣氣機。全方寒溫并用,補通兼施,補而不礙邪,攻而不傷正,共奏活血祛瘀、化痰除濕、寬胸通脈、益氣養陰之功。
《景岳全書》言:“然則痰之與病,病由痰乎,痰由病乎,豈非痰必由于虛乎?可見天下之實痰無幾,而痰之宜伐者亦無幾。故治痰者,必當溫脾強腎以治痰之本,使根本漸充,則痰將不治而自去矣。”林蘭教授強調痰瘀必由之虛,故調形之法應以調神、調氣為基礎,以“溫和”為要,不可過用攻伐。“溫和”之法其一在于祛痰逐瘀時酌加補氣溫陽之品如桂枝、黨參等以助痰化血行,從其正化使津自津、血自血;其二在于用藥精簡,藥性中正平和,少用苦寒瀉下、辛熱燥烈、大補滋膩之品,循序漸進,以緩圖之。在“三型辨證”理論陰陽兩虛型證治中調形法尤為重要,通過化痰逐瘀、溫補脾腎等治療,防止心血管事件發生,以改善癥狀,緩解并發癥,解除痛苦,提高生命質量,延長壽命為目的。
3 驗案舉隅
某,男,58歲,就診時間:2020年9月29日。因“間斷口干多飲2年,加重伴失眠多夢1月”就診。現病史:患者2年前出現口干多飲,于當地醫院檢測空腹血糖7.4 mmol/L,未予重視。1年前患者體檢空腹血糖9.4 mmol/L,完善相關檢查診斷為“2型糖尿病”,予二甲雙胍片0.5 g口服3次/d,并轉至望京醫院就診。2020年6月復查空腹血糖為9.72 mmol/L,糖化血紅蛋白11.3%,調整降糖方案為二甲雙胍片0.5 g口服,4次/d,西格列汀片0.1 g口服1次/d。1個月前出現失眠多夢,空腹血糖波動在7.7~9 mmol/L,餐后2 h血糖波動在8.4~11 mmol/L,為求進一步診治來我處就診。刻下癥見:口干多飲,困乏,煩躁,怕熱,出汗多,頭面部尤甚,偶見心慌,周身酸痛,頭昏蒙,失眠多夢,納可,大便干,1次/d,小便黃,有泡沫。舌尖紅,苔薄白膩,脈弦。平素情緒急躁易怒。既往高血壓病史10余年,脂肪肝病史10年,冠心病、房性早搏4年。治療以清潤瀉火、養陰安神為主,具體方藥如下:百合30 g、知母20 g、黃柏6 g、生地黃30 g、地骨皮30 g、梔子6 g、淡豆豉15 g、夏枯草30 g、制香附15 g、虎杖15 g、蒼術15 g、郁金10 g、陳皮15 g、姜黃30 g。14劑,水煎服,每日1劑。加用中成藥參芪降糖顆粒1袋,口服,3次/d。
2020年10月12日二診:患者口干多飲、多夢煩躁好轉,仍有乏力、周身疼痛,偶有胸悶氣短,活動后加重,偶有心悸,余諸證減輕,腰部怕涼,無腰酸腰痛,偶見胃脹,脅肋憋悶感,偶有入睡困難,大便1~2次/d,成形,小便可,尿中少量泡沫,夜尿2次,舌暗紅,苔白膩,脈弦。處方:黃芪30 g、太子參30 g、麥冬20 g、五味子15 g、酸棗仁30 g、柏子仁30 g、全瓜蔞15 g、薤白10 g、法半夏9 g、陳皮15 g、桑枝30 g、姜黃30 g、制香附15 g、郁金15 g、延胡索15 g。14劑,水煎服,每日1劑。
2020年10月26日三診:患者訴乏力、胸悶氣短、身痛較前減輕,偶有下肢畏寒,小便有泡沫,尿頻,夜尿1~2次,納眠可,大便調。舌略暗,苔白微膩,脈弦。以益氣健脾除痰、活血化瘀為治法。具體方藥:黃芪20 g、麥冬15 g、全瓜蔞15 g、薤白10 g、法半夏9 g、當歸6 g、赤芍10 g、川芎6 g、桂枝10 g、茯苓30 g、水蛭3 g、桑螵蛸6 g、益智仁10 g。服用上方加減1個月余,諸證減輕,空腹血糖控制在5.3~7.2 mmol/L,餐后2 h血糖控制在7~9 mmol/L,糖化血紅蛋白6.7%,停用湯藥,改芪蛭降糖膠囊,5粒/次,3次/d,隨訪至今血糖控制可,癥狀未見反復。
按:此案病起于情緒失調,內動于心,心氣郁結則化火亢盛灼津,加之熱阻氣機,津液運化輸布失常,發為消渴類病。津液不能上承,故見口干;陰虛內熱,熱迫津出故見怕熱、多汗;心火不降,心火擾神故見心悸、眠差、多夢;氣郁不行無以布津行血,痰瘀凝聚經脈,加之運化不足水谷精微無以充養四肢則見周身酸痛;心火獨亢不能下交于腎,水濕停滯,腎失固攝,精微外泄則見小便泡沫。病性屬虛實夾雜,本虛標實。
初診以心火亢盛、熱擾心神為主,故首先以調神法清熱滋陰降火兼安神治其標。方用百合清心火兼能安神,養肺陰以滋水之上源;生地黃入腎經,滋養腎陰;知母滋陰清熱助腎水上濟心火,三藥合用滋陰降火,清潤安神;配以地骨皮、黃柏清熱除煩,梔子與淡豆豉共奏宣發郁熱;輔以調氣之法,陳皮、蒼術健運脾胃,助痰濕運化,推動氣運輸津液;夏枯草清熱散結;郁金、香附疏肝理氣,健脾疏肝調氣以助心火斂降。同時用參芪降糖顆粒益氣養陰,滋脾補腎以治其本。二診患者熱象大減,以胸悶氣短、周身疼痛為主訴,病機為氣虛血瘀,氣虛推動血運無力,瘀血痰濕內阻,肢體失于營血濡養。治以調氣法為主,減清熱之品,以益氣為先,方用益心湯加減,加陳皮、香附、郁金、延胡索理氣以防補滯化熱,全瓜蔞、薤白、法半夏寬胸理氣、散痰結。三診患者諸證減輕,以治本為主,以調形為法,健脾除濕、活血化瘀防止并發癥的發生發展。用當歸、赤芍、川芎、桂枝、水蛭加強活血通脈之功,桑螵蛸、益智仁收斂氣血,補腎固精,防精微物質外泄。續用芪蛭降糖膠囊益氣養陰、活血化瘀,緩復其形。
利益沖突聲明: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