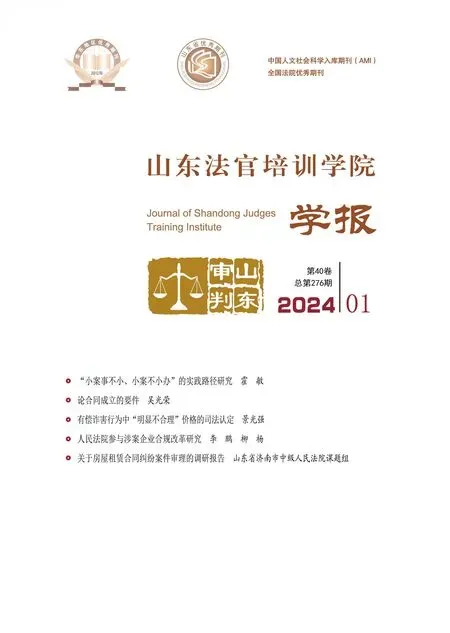庭審翻供的預防與應對
——以偵查訊問為視角
郭沛若 畢惜茜
引 言
庭審翻供在我國刑事司法領域并非罕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翻供,有時能夠及時糾正先前的錯誤供述,使司法人員對案件事實的判斷更貼近客觀真相,從而確保法律的公正實施。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翻供問題已經對刑事司法工作造成了困擾,這一突出現象不僅可能打亂案件的正常偵辦進程,還可能導致原有的證據鏈斷裂,進而影響到訴訟程序的順利進行,造成司法資源的浪費。
長期以來,學界和實務界對如何解決翻供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討,現有的研究成果更多地關注了審判階段翻供后作為證據的排除和采信問題,對于如何應對翻供的措施,更多側重于事后救濟而非事前防范。從偵查取證的角度來看,對于如何有效地預防和減少翻供問題的研究還相對較少。為全面了解翻供現象,并為偵查機關制定出合理且有效的應對措施以提供幫助,本文整理了與翻供相關的文獻和數據。在此基礎上深入分析了翻供產生的內在成因,梳理總結庭審翻供的審查方法,并就如何在偵查過程中消除庭審翻供的隱患,提出了相應的偵查訊問對策。在輕罪治理體系背景下,探究預防與應對庭審翻供的實現路徑不僅有利于更好地落實“少捕慎訴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還能節約司法資源,更好地實現尊重和保障人權的目標。
一、司法實踐中庭審翻供的現狀考察
翻供是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先前對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做出有罪供述后,在刑事訴訟程序的某一階段中重新作出口供,全面否認或部分推翻有罪供述中的犯罪事實和情節。在某種意義上,法庭審理過程中的翻供是控辯雙方相互質證的一種具體表現,也是審判實質化推進過程中難以避免的結果。翻供在本質上具有兩面性:從對抗性維度來看,被告人的翻供顛覆了原有口供,給現有的證據體系帶來相當大的沖擊,增加了認定被告人有罪的難度;從辯護性維度來看,翻供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正當行使以辯護權為核心的一系列訴訟權利。而辯護性是翻供的本質屬性,對澄清案件事實、防范冤假錯案起著十分重要的積極作用。①參見郭名宏:《論被訴人自主性辯護的價值及實現》,載《法學評論》2016 年第1 期。
(一)庭審翻供的司法現狀
一直以來,翻供大多發生在庭審過程中,被告人對其偵查階段所作出的有罪供述提出推翻性的陳述。為了能夠了解刑事司法領域有關庭審翻供的種類和裁決情況,筆者針對刑事案件中的判決書進行了檢索分析。以中國裁判文書網公布的翻供案例為研究樣本,利用網站的“高級檢索”功能,將“案件類型”統一鎖定為“刑事案件”,文書類型為“判決書”,裁判時間為“2013 年1 月1 日—2023 年9 月30 日”,以“庭審翻供”和“庭審中翻供”為關鍵詞進行檢索,共獲得2862 份刑事判決書。隨后,將這些刑事判決書按照相關性進行排序和篩選,剔除未涉及被告人翻供內容、案情重復或無法通過文書把握整體案情的判決書,將所屬同一中級人民法院的基層人民法院翻供案件合并分析,最終得到1933 份可供分析的裁判文書。隨后在選取的1933 份裁判文書樣本中就翻供后的法庭采信問題進行分析,統計整理發現,被告人在庭審中翻供未被法庭采納的案件數量共有1694 件,比例高達87.6%。相比之下,最終被法庭采納的僅有239 件,占樣本總數的12.4%。
1.庭審翻供與案件裁決情況的總體考察
為進一步了解庭審翻供的具體情況,采用隨機抽樣的方式,在上述樣本中選取了四個不同地區中級人民法院的裁判文書作為主要分析樣本,利用裁判文書網的檢索功能對涉及翻供的案件判決書進行統計,匯總整理了隨機抽取的案件樣本總數,其中包括被告人翻供的原因以及庭審中翻供是否被法庭采納的統計數據,共得到130 份有效分析樣本。對以上樣本中庭審翻供的采信情況數據進行分析研究發現,被告人庭審翻供后的供述受到法官采信的案件僅有7 件,占樣本總數的5.4%。需要明確的是,上述得到法官采信的翻供案件均影響了被告人的定罪或量刑,其中有3 件對被告人在量刑上予以從輕,有4 件因翻供受到采信而影響定罪。在對罪名認定產生影響的4 件案件中,甚至有林某某詐騙罪一案因被告人的翻供與書信內容相印證得到采信而最終改判無罪。①參見(2013)深中法刑二終字第719 號。通過對樣本數據的分析研究可得出,被告人在庭審中翻供對案件判決會有以下兩個方面的影響:其一,翻供在審理過程中對訴訟程序有明顯影響,而對事實認定的影響相對較小,主要體現在判決的量刑階段;其二,法官通常更傾向于信任公訴方提出的指控以及被告人在庭前的合法供述,被告人在庭審中翻供的可信度較低。
2.庭審翻供與案件裁判結果的實證考察
樣本數據顯示,被告人常見的翻供理由有刑訊逼供、誘供、騙供、記憶產生偏差、訊問筆錄有誤等。首先,受到刑訊逼供而翻供,要求進行非法證據排除是被告人翻供最常見的理由,共有945 件案件,占樣本總數的42.4%。而以受到威脅、引誘、欺騙為翻供理由的共有317 件,占樣本總數的14.2%。基于威脅、引誘、欺騙在法律層面的界限相對模糊性,除了明顯的指示引供,被告人在被訊問的過程中可能無法正確感知,從而在庭審中不會以此為由翻供。其次,被告人以記憶有誤或訊問筆錄有誤為由進行翻供的案件共有303 件,占樣本總數的13.8%,導致此類翻供的原因主要是存在訊問筆錄記載不規范,筆錄記載內容與供述不統一等問題。最后,被告人法律專業知識的匱乏可能使其難以用專業術語準確概括翻供原因,但在司法實踐中,被告人翻供的理由往往并非真實,可能只是掩飾真實翻供心理的借口。
筆者以翻供理由與駁斥依據為線索,從法官予以采信和不予采信的兩個角度選取了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庭審翻供案件進行逐案比對分析,力求更為直觀的體現被告人翻供理由、法官對庭審翻供的態度以及庭審翻供對裁判結果的具體影響。通過案例分析發現,被告人在司法實踐中不僅會以刑訊逼供等常見理由翻供,而且基于不同刑事案由還會提出不同翻供理由。例如,在余某某詐騙案中,被告人否認主觀上的詐騙故意,將所實施的行為辯稱為民間借貸行為,并無非法占有目的。最終法院根據被告人余某某先前存在的虛構借款事由、隱瞞自己無力償還巨額債務的真相,騙取借款后積極轉移贓款和個人財物,逃避被害人追償等一系列行為而不予采信。①參見(2019)浙刑終第141 號。在黃某某、何某某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案中,兩名被告人均以受到刑訊逼供、威逼利誘為由進行翻供,由于全案證據不能排除有罪供述是通過刑訊逼供獲得之可能,并且現有證據無法證明二人與毒品有直接聯系。法院最終采信被告人的當庭供述,將兩名被告人改判為無罪。②參見(2015)粵高法刑四終字第453 號。值得注意的是,通過比對翻供是否得到采信,發現采信與未采信的理由主要依賴于其他證據的印證。比如,在審理受賄案件中,被告人的當庭翻供得到采信,在進行事實情節認定時,如果某筆受賄金額缺乏證人證言或者僅有證人證言而無其他證據相印證,一旦同步錄音錄像的內容與訊問筆錄有出入,便不能充分證明被告人庭前供述的真實性,進而無法認定被告人收受過該筆賄賂。③參見揭向東、張建兵:《我國賄賂犯罪證據制度面臨的困境和對策》,載《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15年第4 期。而在被告人的當庭翻供未得到采信的案件中,被告人在主張非法取證時,法官會以訊問過程的同步錄音錄像能夠證實庭前供述的合法性與真實性來否定被告人的當庭供述。
通過梳理和總結庭審中翻供的案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翻供行為大致可分為善意和惡意兩類。善意翻供指的是犯罪嫌疑人在初始供述期間沒有獲得應有的人權保障,受到多種壓力,被迫作出與個人真實意愿以及客觀事實不符的認罪供述。比如,可能由于偵查人員在審訊期間使用非法手段如隱性的刑訊逼供或在訊問中運用威脅、誘導、欺騙等不當手段,從而獲得被告人的供詞。惡意翻供則通常是被告人出于害怕法律制裁或心存僥幸,聽取庭審中雙方質證后覺得自己的犯罪事實沒有被充分把握,在這種情境下,試圖通過翻供來逃避審判。隨著錯案追責機制的建立和執法規范化的不斷推進,偵查機關在偵查過程中嚴格遵守法律規定,刑訊逼供等侵害犯罪嫌疑人權利的行為已經大幅減少。因此,當下的惡意翻供大多是被告人有意為之的辯護對策,其背后并沒有正當的翻供理由,而是為了混淆事實、干擾訴訟進度,破壞依賴供詞為主要內容的刑事證據體系,并試圖通過拖延審理來逃避法律懲罰。
(二)庭審翻供對刑事訴訟的影響
目前,一般情況下,對于庭審中被告人翻供的案件,法院會展開特定的調查程序。如果公訴方提出的證據確實且充分,足以證明被告人在庭前所做的認罪供述是合法的,并且在綜合評估所有相關證據后,庭前供述與案件中的其他證據相一致,能夠排除合理懷疑并得出唯一的結論,進而形成穩固的證據鏈的,法院最終往往不會接受被告人在庭審中的新供述,而是維持庭前的、有證據支持的合法供述,據此認定被告人有罪。上述樣本數據表明,在刑事訴訟中,盡管被告人在庭審中的翻供實質上對定罪和量刑的影響有限,然而,惡意的翻供仍然可能直接破壞證據鏈的完整性,浪費司法資源,降低訴訟效率,給法庭審判程序的正常運行產生不容忽視的負面影響。
1.加重公訴負擔
在部分刑事案件的審判中,公訴方可能未預見被告人在法庭中會全面或部分否認偵查階段的認罪供述,導致翻供發生后無法立即進行指控,需要在庭審之后補充證據,這會拖延案件的公訴進展。通常,被告人庭審改變供述時聲稱原供述是在非法的取證手段,如刑訊逼供下作出,這要求公訴機關證明用于定案的供述的真實性與合法性。因此,公訴方在法庭審理后需承擔證明被告人供述是通過合法手段獲取的舉證責任,防止非法證據被法庭采納。這無疑增加了公訴方的舉證負擔,干擾、延緩了刑事訴訟過程的順利進行。
2.延緩訴訟周期
首先,在被告人對指控的犯罪事實提出異議的情況下,庭審無法按照簡易程序進行,而需要按照正常的庭審程序進行審理。這通常意味著庭審將更加復雜耗時,需要更多的客觀證據和證人證言等來支持公訴方的指控。其次,如果被告人在庭審中改變供述并提出新的對案件事實認定起決定性作用的證據,且公訴方無法即時提出有效證據予以反駁的情況下,法庭可能宣布休庭,并指示公訴機關補充偵查。法官在休庭期間可能需要再次為將來審問被告人進行一定的準備工作,這在司法資源不足以應對繁重案件背景下,無形中增加了法官的工作壓力。最后,在某些類型案件中,比如涉及賄賂和經濟犯罪的案件,證據形式復雜且情節認定困難,這些案件普遍比一般刑事案件審理周期長。因此,被告人在庭審中翻供可能會對整個審判程序產生難以忽視的反向推動,將極大地延緩審理時限。
二、庭審翻供的心理成因
在庭審過程中,被告人的翻供可以被理解為一種態度的反映。根據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所謂“態度”,是指對特定的人、特定的對象或觀點等的評價和反應。①參見[美]阿倫森等:《社會心理學》,侯玉波等譯,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5 年版,第178 頁。這種態度包含不愿承認罪行并承擔相應刑事責任的心理狀態以及由此產生的情緒和感受,尤其是針對其先前作出供述行為的一種綜合性評價和行為傾向的拒絕。②參見趙桂芬:《犯罪嫌疑人拒供態度改變的結構化引導方法研究》,載《公安學研究》2021 年第4 期。社會心理學對于態度的研究為理解被告人在庭審中翻供行為提供了理論基礎。然而,庭審翻供發生在特殊的刑事訴訟環境中,這一場景與社會心理學研究通常關注的環境有顯著不同,特別是在庭審中,公訴人追究刑事責任與被告人尋求免責之間存在極大的立場差異。因此,要將社會心理學中的認知失調、態度變化等一系列理論應用到對被告人庭審翻供的司法實踐分析中,就需要深入探討并理解被追訴人的內在需求和心理障礙。
(一)罪責壓力下產生的畏罪心理障礙
在偵查訊問學中有關供述心理障礙的研究發現,犯罪嫌疑人到案后的總體心理傾向是趨利避害,企圖逃避刑罰懲罰,表現出畏罪、僥幸、抵觸、戒備、悲觀的心理障礙。畏罪心理源于個體自我保護機制調節下對承擔刑事責任的恐懼和逃避,是犯罪嫌疑人普遍存在的一種心理狀態,會伴隨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反復出現。犯罪嫌疑人對罪責的感知及壓力是畏罪心理形成的原因之一,這種觀點的形成,是基于將罪責感的壓力作為妨礙犯罪嫌疑人如實供述的心理因素來認識的。①參見趙桂芬:《犯罪嫌疑人罪責感的理論建構與實證考察》,載《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 年第5 期。罪責感的核心源于對即將承受刑罰懲罰的應然性認知,但這種認知的存在依然不會改變逃避刑事責任的態度,畢竟承擔刑事責任要求個體付出極大代價,包括忍受刑罰所帶來的痛苦。在犯罪心理學研究中,罪責感被歸納為一種自我譴責的情感,當個體產生要突破社會規制的動機時心理上就會激發內心良知與緊張感,能夠積極抑制犯罪動機的形成。無關犯罪次數的影響,犯罪主體實施行為后,其心理會萌發不同程度的罪責感和負疚感,負疚感的產生是出于個體心理上對所要承受社會貶抑的恐懼,這些情緒情感因素會對犯罪心理的再次產生起抑制作用。②參見羅大華、馬皚等:《犯罪心理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2012 年版,第111-113 頁。研究發現,罪責感中的羞恥感是對犯罪嫌疑人作出如實供述起消極作用的情感因素。以謊言去遮掩犯罪行為是富有羞恥感犯罪嫌疑人用以平衡犯罪行為被公之于眾所產生痛苦的心理慰藉。③See Cynthia E.Cryder,Stephen Springer,Carey K.Morewedge,Guilty Feelings,Targeted Actions,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vol.38,no.5,2012,pp.607-618.在刑事訴訟場景中,犯罪人對自己行為的羞恥感是一種強烈的情感反應,它可能導致個體感到無法面對自己和他人的批評。比如性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面對法庭審判時的開放環境以及眾多參與者會對自己的道德和倫理標準感到羞愧,更傾向于選擇逃避,因而出現否認先前供述的翻供行為。
(二)自我保護動機驅動下的自我防御狀態
心理學研究表明,當個體處在焦慮不安的情境下,會激發個體的適應性防御機制,進而產生一定的適應性和防御性或者保護性行為,對這些不良的刺激做出各種不同的應激反應用以擺脫不快和焦慮的心理。④See Anna Freud,The Ego and the Mechanisms of Defense,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1936,p.37.根據自我保護動機理論,⑤“自我保護動機理論”是由美國心理學家Mark R.Leary 在他的著作“Th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Belonging to a Stigmatized Group: The Case of Homosexuality”(1983 年)中首次提出的。這本書探討了屬于被污名化群體(如同性戀者)的人所面臨的社會和心理后果,并介紹了自我保護動機理論作為解釋這些后果的框架。自我保護動機理論后來在心理學和社會科學領域得到廣泛研究和應用。個體在面臨威脅、壓力或不利情境時,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和減輕責任而采取的自我保護行為。這些行為旨在減輕個體的責任感、避免損失或負面影響,并維護個體的權益和自尊。具體而言,其一,自我防御。個體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和自尊,采取的一系列防御性行為。這些行為可以包括否認錯誤、逃避責任、尋求借口、轉移責任等。其二,責任減輕。個體為了減輕自己的責任感,可能會將責任歸咎于他人、環境或其他外部因素。這種責任減輕的行為有助于個體保護自己的形象和避免負面后果。其三,損失規避。個體為了避免損失或負面影響,可能會采取措施來規避潛在的風險或威脅。這種規避損失的行為有助于個體保護自己的利益和減少不利后果。這種保護或防御機制通常是一種無意識的心理過程,是調節壓抑心理與外界現實之間關系,維持內心平衡的一種手段。然而,伴隨防御機制被喚起的應對則是一種自知行為。在刑事訴訟中,犯罪嫌疑人在防御機制的作用下通常會產生心理投射,潛意識里否認自己的錯誤行為的違法性,將自己的行為動機與后果歸咎于客觀原因的影響。投射化心理作用機制會使犯罪嫌疑人歪曲認知思維或者阻斷心理過程,將不符合自我概念的違法犯罪行為正當化、合理化,使其主觀心理免于道德譴責的焦慮或罪責加身的壓力,推動犯罪嫌疑人構筑起一道抗拒審判、逃避罪責的心理防線。
(三)“態度系統”支配下的認知不協調
個體對自己的定位和認識有一個完整的系統,叫做態度系統。該系統包括行為意向、行為、態度、認知、情緒反應。行為是個體態度的一種外現,態度又會加強個體行為,當行為與態度矛盾時,就會出現認知不協調。①See Leon Festinger,Cognitive Dissonance, Scientific American,vol.207,no.4,1962,pp.93-106.由于犯罪嫌疑人在案件證據掌握情況方面的信息缺失,加之在審訊環境的高壓氛圍,審訊人員的權威身份,以及各種不同的審訊策略方法的使用等多重因素作用下,犯罪嫌疑人心理受到限制,此時其思維呈現被動反應狀態,在審訊人員的發問與出示證據面前,完全受信息導向的支配,不由自主地產生供述的心理內推動力,最終基于其內心罪責感壓力交代問題。這些覺醒的內推動力與犯罪嫌疑人最初逃避罪責的理念相違背,便造成了犯罪嫌疑人的認知失調。犯罪嫌疑人因認知失調而帶來的痛苦體驗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刑罰的恐懼。當犯罪嫌疑人已經產生供述時,他們會意識到刑罰懲罰的必然性,懲罰的迫近足以對其心理上產生畏懼的外部威懾力。二是在等待未知結果的過程中產生的焦慮。盡管犯罪嫌疑人具有一定程度的罪責感,但仍然會在面對懲罰時本能地趨利避害,理性地期待得到較輕刑罰。這種對能否獲取從寬處理的不確定性常使犯罪嫌疑人產生強烈的焦慮不安情緒。②See De Hooge I E,Zeelenberg M,Breugelmans S M,Moral sentiments and cooperation: Differential influences of shame and guilt.Cognition and emotion,vol.21,no.5,2007,pp.1025-1042.為了降低這種認知不協調的程度,在脫離審訊人員所營造的環境之后,犯罪嫌疑人會試圖暗示自己什么都沒有發生,繼續反復回憶進而強化原有態度以降低內心自我譴責,作出辯解使供述事實非犯罪化,以符合原有逃避罪責的態度,進而達到更高的認知協調,避免痛苦體驗。①See Philip G.Zimbardo,Michael R.Leippe,The psychology of attitude change and social influence,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91,p.117.
三、刑事偵查中口供取證策略
在刑事訴訟的任何一個環節中,翻供現象都有可能發生,導致對犯罪證據判斷的不一致。為此,偵查機關在偵查和取證階段應當維持這樣一種取證意識:即使在缺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情況下,只要其他證據真實、充分,能夠形成完善的證據鏈,也足以判定被告人有罪并施以相應的刑罰。偵查人員需多方位、多角度、深層次地搜集證據。審訊階段是與犯罪嫌疑人直接對話的關鍵環節,偵查訊問對案件的最終結局有重要影響。在這一過程中,訊問人員應敏銳地察覺可能出現的翻供動向,并根據犯罪嫌疑人的個性特點,制定切合實際的審訊計劃。通過提升訊問效率,構建穩固的證據鏈,并做好將來面對翻供的應急預案,可以確保將有罪者繩之以法。
(一)建立以審判為中心的取證模式
以審判為中心的理念應成為公安機關對照檢察機關和法院在實際辦案中樹立的法治理念。“審判中心”理念強調證據意識,在搜集證據過程中要做到合理合法,在審判過程中使所獲取證據經得起對質,避免證據被認定為非法而遭到排除。公安機關應及時適應現行司法體制,建立起一切圍繞法庭審判的案件偵辦模式,將庭審的證據證明力標準貫穿于偵查取證全過程,合法準確及時地收集固定證據,從案件事實與證據的關聯性中審慎核實是否存在矛盾證據、瑕疵證據、以及難以排除的合理懷疑,防范證據體系出現重大失誤。②參見謝小劍:《以審判為中心改革中的統一證明標準:學術爭辯與理論反思》,載《當代法學》2019年第5 期。司法機關在刑事訴訟過程中認定案件事實情況,審查核實涉案證據都是以公安機關制作的刑事案件卷宗為主要參考材料,這就對書面形式的刑事案卷提出了極高要求,應當避免案件事實還原不清,證據收集不完整、呈現形式不合法等紕漏的出現。
(二)依法科學審訊,嚴格規范流程
1.合理使用審訊策略方法,完整體現供述心理變化
偵查人員在訊問準備階段應當透徹調查犯罪嫌疑人背景情況,準確把握其心理特征,制定針對性的審訊方案。犯罪嫌疑人在訊問初期時的供述心理障礙較為明顯,需要審訊人員具備敏銳的觀察應變能力和出色的語言能力來打破僵局,盡量與犯罪嫌疑人建立親和關系,逐步取得其信任,不宜采用激進對立的方法引發對抗情緒。偵查人員在提問時應使用開放式問題,避免誘導式的提問,讓犯罪嫌疑人對作案過程進行自由陳述以充分獲取案件信息,并根據陳述細節進行追問。①參見劉濤:《“融洽關系”理論及其在我國訊問取證中的應用》,載《公安學研究》2023 年第2 期。同時,適時地運用情感感化方法和合理化策略,有助于增強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意愿,促進案件的順利偵破。從目前的司法實踐現狀來看,審判機關對于局限于法律和道德準則以內的誘供、欺騙等訊問取證方式具有一定的接受度,審訊人員應當合理運用能夠對犯罪嫌疑人進行有效心理突破訊問技巧并盡可能地把握好合法尺度。②參見黃金華、黃鸝:《論訊問方法運用的正當性及其界限——以口供獲取為視角》,載《法學》2014年第10 期。
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在其自身心理變化的影響下會呈現出由不供到供的轉變過程。許多偵查人員意識不到供述態度的轉變對口供印證的重要性,認為態度轉變的過程與犯罪事實沒有直接關聯,輕視對于態度轉變過程錄音錄像的收集留存。但殊不知此類證據是有效應對翻供的證明材料,可以證明犯罪嫌疑人在態度轉變過程中的言行表現,完善犯罪嫌疑人主動作出有罪供述的態度轉變過程,與訊問筆錄形成良好的印證,增強駁斥翻供的證明力。偵查人員在訊問時應注意通過合適的提問方式來發掘態度轉變背后的供述心理變化。③參見畢惜茜:《心理突破——審訊中的心理學原理與方法》(第二版),中國法制出版社2020 年版,第57-60 頁。比如,審訊人員在犯罪嫌疑人進行完有罪供述后,可以向其提問“為什么愿意交代自己的事情”。讓犯罪嫌疑人主動描述自己的心理歷程和供述動機,這不僅可以證明犯罪嫌疑人如實供述的真實合法性,還可以排除偵查人員存在誘供、騙供或變相刑訊逼供等非法情形的可能,提前否定庭審翻供的理由。④參見何家弘:《從“硬審訊法”到“軟審訊法”》,載《人民檢察》2008 年第17 期。
2.規范制作筆錄,確保程序正義
目前固然存在基層辦案警力不足的現狀,但偵查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訊問時要雙人參與,確保程序正義。避免訊問筆錄的簽名與實際審訊人員不同,重合時間段同一人的簽名出現在兩份以上筆錄中等問題的出現,以免在證據審查認定階段對訊問筆錄的證明力產生懷疑。偵查人員多次就同一事實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訊問時,不能為了節約時間而復制粘貼先前筆錄材料,由于偵查人員的提問與犯罪嫌疑人的回答不可能每次都分毫不差,因此針對每一次訊問偵查人員都要重新制作嚴謹合規的訊問筆錄,要在訊問筆錄中體現出每一次訊問中所提問題以及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細微差別,而后讓犯罪嫌疑人核實后進行簽名捺印,避免在庭審中出現以“重復的訊問筆錄是對之前審訊過程記錄的機械復制,我本人的真實意思表示無法得到如實反映”為理由的翻供。⑤參見胡志風:《偵查訊問筆錄制作規范化實證研究》,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4 年第4 期。
偵查人員要切實把握訊問筆錄作為證據的法律特征,將口供突破與罪行供述作為兩條主線貫穿訊問筆錄制作全過程,使二者前后有機銜接。第一,如實記錄突破口供方法和犯罪供述過程,體現前后聯結的關系;第二,準確記錄有罪供述和無罪辯解,體現認罪態度的轉變;第三,真實記錄口頭語言陳述和肢體語言反應,體現心理變化的特征;第四,真實記錄犯罪嫌疑人和偵查人員的一問一答與反應表現,體現審訊雙方的博弈。特別是要重點記錄擊潰犯罪嫌疑人心理防御時的訊問情境以及犯罪嫌疑人當場表現的情緒反應,為將來可能的庭審翻供做好應對之策。值得注意的是,訊問筆錄所體現的實質性問答內容應與審訊持續時長匹配對應,即使訊問中并未存在任何有效回答,也應當依法如實記錄,在質證時可以與同步錄音錄像形成很好的支持印證,充分表明邏輯的合理性與程序的規范性。①參見宋維彬:《筆錄證據的證據能力研究》,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21 年第2 期。
3.規范審訊言行,全程同步錄音錄像
審訊過程同步錄音錄像,不僅可以說明訊問筆錄來源的合法性,還可以證明審訊全程的規范性及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如實供述的態度。②參見董坤:《偵查訊問錄音錄像制度的功能定位及發展路徑》,載《法學研究》2015 年第6 期。在實踐中,部分偵查人員為了避免暴露審訊中不規范言行,同步錄音錄像的時間僅與訊問筆錄的起止時間相一致,并非從進入審訊室即開始同步錄音錄像。審訊人員應逐步適應鏡頭下審訊,進一步規范審訊言行,確保錄音錄像從進入審訊室開始同步,力求客觀真實地反映整個審訊過程,完整展現審訊人員的言行舉止,增強錄音錄像在庭審中的證明力。避免犯罪嫌疑人在庭審中以“在正式開始訊問之前受到刑訊逼供,后續有罪供述并非自愿”為由進行翻供。③參見朱奎彬:《訊問錄像推動“以審判為中心”改革之潛力發揮路徑研究》,載《證據科學》2018年第6 期。
(三)完善證據體系,強化口供證明力
1.及時收集完善證據,充實證據體系
單憑犯罪嫌疑人所作出的有罪供述而沒有其他證據印證的,無法最終認定為有罪。偵查人員要清楚有罪供述極易反復,故應堅持實物證據優先原則,在得到相關信息后主動出擊,查證核實供述所涉及的犯罪事實以及其他證據,形成完備的證據鏈,證明有罪供述的客觀真實性。④參見陳瑞華:《論證據相互印證規則》,載《法商研究》2012 年第1 期。一是確保案件發展過程的相關證據得到妥善固定,這包括準確收集犯罪嫌疑人的到案經過,調取接處警記錄、執法記錄儀攝錄影像等原始資料,證明其到案時間和地點等關鍵信息,以免犯罪嫌疑人在庭審階段偷換概念,以自首為由進行翻供要求得到從輕處理。二是做好現場勘驗檢查,全面收集現場遺留的痕跡物證,并移送相關部門進行鑒定,核查現場痕跡物證與犯罪嫌疑人供述間的對應關系,一旦發現供述內容與現場證據存在明顯矛盾或不一致的情況,偵查人員應當及時進行復勘或再次訊問。如果發現新的證據或線索,應當及時跟進并展開調查,不斷補充和完善證據鏈,確保案件的證據充分完整、真實可靠。三是利用調查詢問搜集證人證言,對于犯罪嫌疑人有罪供述中所涉及的人員、時間、地點等關鍵事實均應當尋找現場證人收集證詞,與犯罪嫌疑人有罪供述進行雙向查證核實,謹防遺漏。
在陷入犯罪嫌疑人拒不招供,甚至被害人或證人都推翻先前陳述的偵查困境中,偵查人員必須將偵查取證重心轉移到收集核實間接證據上來。所謂間接證據,就是以間接方式與案件主要事實相關聯的證據,即必須與其他證據關聯起來或通過推理才能證明案件主要事實的證據,亦稱為“旁證”。①參見何家弘、馬麗莎:《間接證據案件證明標準辨析》,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21 年第5 期。偵查人員在調取間接證據過程中務必小心謹慎,保證所有間接證據都是通過合法渠道獲得,與待證事實之間相互關聯并經過查證屬實。通過間接證據有效組合和嚴密的邏輯推理,得出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的結論。
2.全面查清事實,縝密排除矛盾
法院在啟動調查程序對翻供案件進行證據認定時,會審查取得證據與庭前供述之間的先后關系,即審查是“由供到證”還是“由證到供”。在實踐中,“由證到供”類型案件通常不會出現當庭翻供,因為犯罪嫌疑人在證據鏈完整、關聯緊密的事實和證據面前無可抵賴。相對而言,“由供到證”類型案件則存在較大的翻供空間,由于這類案件的大部分證據是基于口供內容獲取的,犯罪嫌疑人可能會針對取得口供前證據掌握情況的缺失進行翻供。為應對此類情況的發生,偵查人員在審訊中獲取到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后,應當繼續對其犯罪動機、犯罪行為實施過程、供述動機理由進行深入的訊問,將庭審證據的印證規則用于訊問過程深入追問,審查核實與其他言詞證據和實物證據是否對應,排查推理邏輯關系是否反常于經驗規則,及時發現矛盾所在。②參見何家弘:《證據的審查與認定原理論綱》,載《法學家》2008 年第3 期。同時應當以口供為支點向外發散,對尚未落實的案件情況進一步探查究竟,這既可以如實反映犯罪事實的發生過程,又可以辨明口供的真偽。外圍查證首先要做到快速反應。一旦從口供中獲取到尚未查證的重要涉案信息,立即部署開展偵查活動,趕在各種證據檢材尚未消失湮滅或遭受破壞毀損之前地將相關證據材料收集在案。其次,要全面細致,重點突出地分析供述細節,捕捉案件關鍵信息,著重收集只有通過親身經歷才可得知的“內知證據”,明確犯罪動機、作案手段與工具、涉案贓物去向等關鍵的事實細節。③參見董坤:《規范語境下口供補強規則的解釋圖景》,載《法學家》2022 年第1 期。最后,要注重強化證據的相互印證關系,保證已有證據所證明的犯罪行為不偏離于犯罪嫌疑人主觀態度,現有證據體系能夠確實充分地印證查明的犯罪事實。辦案人員要靈巧的綜合運用各項偵審措施提取分析證據,對言詞證據進行周密嚴謹的審查,排除合理懷疑,消除矛盾沖突,全面肅清可能導致庭審翻供的潛在問題隱患。
3.有罪供述與無罪辯解并重
公安機關在偵查階段要同步收集有利和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證據,從有罪和無罪兩方面進行調查取證,充實證據體系。如此一來,即便出現庭審翻供,也可以避免出現先入為主的有罪推定,而是根據前期調查所得的無罪證據來審視翻供,辨明真偽。在審訊過程中,有些偵查人員對犯罪嫌疑人的無罪辯解不夠重視,不認真傾聽犯罪嫌疑人的無罪辯解,更有甚者根本不給予犯罪嫌疑人陳述辯解的機會。犯罪嫌疑人辯解機會的缺失勢必會給庭審過程中的翻供留下后患。①參見彭俊磊:《論偵查訊問中的犯罪嫌疑人權利保障——基于審判中心訴訟制度改革的再思考》,載《法學論壇》2018 年第4 期。過度輕視無罪辯解及其背后所隱藏的證據極易導致無辜之人蒙受冤屈,同時無罪證據的缺失也難以斷絕翻供后路,致使錯失有效預防和應對翻供的良機。
四、庭審翻供的審查認定
在庭審中,當被告人翻供時,司法人員應當摒棄有罪推定的觀念,堅守無罪推定原則,以客觀公正的態度來對待被告人的翻供。司法人員應充分尊重被告人在庭審過程中行使辯護權的機會,不得盲目地將翻供視為被告人認罪態度不佳或試圖逃避法律懲罰的表現。當被告人在庭審過程中推翻先前有罪供述,法庭需要通過調查程序,根據已掌握的全案所有證據進行審查判斷,不僅要整體審查現有證據對不同口供的支撐印證關系,而且要逐個排查證據的合法來源、真實客觀和關聯印證。②參見馬朝陽:《對庭審翻供的審查及彈劾證據的運用》,載《人民檢察》2018 年第8 期。在審查證據時,應當從證明力的角度出發,明確認識到言詞證據不穩定性的特征。需要認真辨析證據之間的矛盾和差異,并充分發揮實物證據對主觀言詞證據的支撐作用。此外,還要從有罪供述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外圍證據對口供的增強與印證、排除證據間矛盾的合理懷疑以及被告人庭審翻供的理由和情節合理性等多個方面進行綜合剖析。
(一)合法性審查
合法性是口供證明力的首要考量,因為合法性是口供符合供述人真實意愿的有力保障,而自愿性是保證口供內容真實有效的前提條件。因此,口供的合法性是法庭審理中對證據予以采納的必要條件,必須對獲得口供的訊問程序合法性進行嚴謹審查。③參見馮麗萍:《庭審翻供問題研究》,載《山東法官培訓學院學報》2022 年第3 期。在被告人提出遭受刑訊逼供或誘供、騙供等非法訊問等翻供理由并且提供了相關的線索或材料時,要嚴格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簡稱“《刑訴法解釋》”)所規定的相關程序及要求進行非法證據排除。然而,由于引誘、欺騙所得的有罪供述并未明確規定在《刑訴法解釋》中非法證據排除的范疇,故而訊問行為的合法性應依據訊問時的全程錄音錄像綜合判斷,判斷的標準則是訊問行為的強制性、口供的自愿性和真實性三者的綜合。①參見劉濤:《偵查訊問中威脅、利誘、欺騙之限度研究》,載《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 年第3 期。一旦偵查人員違背司法公信原則,突破了法律許可范圍,在訊問中過度使用引誘、欺騙策略,使犯罪嫌疑人違背真實意愿而作出有罪供述,并且與全案其他證據難以相互印證,則依據《刑事訴訟法》第56 條相關規定,將缺乏真實性的有罪供述作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以雍某故意殺人案為例,被告人與被害人白某某發生矛盾后用斧子猛擊致白某某死亡,雍某在一審開始時便翻供稱有罪供述系刑訊逼供所得,一審法院通過訊問錄像及相關證據材料發現無法排除偵查機關刑訊逼供的可能,其有罪供述被一審法院作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②參見(2014)通中刑初字第23 號。
訊問過程同步錄音錄像也是證明訊問程序合法性的重要證據。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23 條規定,應當對訊問過程進行同步錄音錄像的案件范圍僅限于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并非所有刑事案件。因此,如果被告人以沒有訊問過程同步錄音錄像為由進行翻供,根據《刑訴法解釋》規定,看守所提審登記、出入看守所的體檢證明、偵查人員出庭作證或說明情況等方式均可有效證明被告人有罪供述的真實性。③參見佀化強:《訊問錄音錄像的功能定位:在審判中心主義與避免冤案之間》,載《法學論壇》2020年第4 期。由于同步錄音錄像缺失而造成被告人供述的真實性與合法性被質疑時,被告人有罪供述如果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根據《刑事訴訟法》第56條規定應當將被告人的庭前有罪供述作為非法證據依法排除。
(二)周密性審查
虛假的有罪供述通常會出現邏輯不清晰、細節不對應等顧此失彼的現象,這是由于供述人只是按照其所了解的有限案件相關信息進行認知、加工并陳述案件經過,對發案過程中不為人知的細節根本無從知曉,所以在細節供述上不穩定,經常反復橫跳。④參見龍宗智:《刑事印證證明新探》,載《法學研究》2017 年第2 期。案件的親歷人對于案發過程有更為宏觀且細致的把握,既能夠做到清楚明了地完整復述案件事實經過,又能夠貼合實際地陳述犯罪關鍵細節,并與現存證據相吻合。例如,在茍某故意殺人罪案中,經過現場勘查并未獲取能夠直接證實茍某殺死二被害人的證據,但偵查人員在后續訊問過程中得到茍某的有罪供述,特別是作案過程細節與其他實物證據相互印證,并且成功提取茍某從被害人家中帶走并丟棄的兩件關鍵物證,均系先供后證,證明力強。⑤參見(2007)巴中刑一初字第08 號。后茍某以遭受刑訊逼供為由翻供。二審裁定認為,對茍某的訊問過程以及提取物證過程均合法、客觀、真實,從而推翻被告人的不實翻供,對其有罪供述予以采信。因此,甄別口供真實性的有效方法就是審查有罪供述邏輯條理的細致性以及犯罪細節的完整性與印證性。
(三)穩定性審查
供述內容的穩定不變或者反復無常是區別真假口供的重要依據。犯罪嫌疑人如果在主要犯罪事實和犯罪情節上的供述較為穩定,那么其口供的可信度與證明價值更高。穩定的口供一般是指犯罪嫌疑人兩次以上在訊問時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而作出的有罪供述,特別是關于整體案情和犯罪細節的敘述未出現不合常理的改變。①參見何家弘、林倩:《論重復自白排除規則的完善》,載《證據科學》2020 年第2 期。實際上,犯罪嫌疑人出于其自身趨利避害本能而產生的畏罪心理,在逐步供認犯罪事實的過程中會不時出現辯解和翻供,在犯罪情節方面避重就輕,企圖逃避犯罪責任。當被告人在庭審中以記憶不清等理由進行翻供時,法官的首要任務便是結合全案證據對被告人歷次庭前供述的訊問筆錄進行審查,并著重分析其中所包含的有罪供述和無罪辯解,全過程還原被告人到案后口供的動態變化情況。例如,在林某某故意傷害罪案中,林某某飲酒后同黎某發生爭執,用手擊打黎某頭部致其受傷昏迷,后送醫不治身亡。林某某在偵查階段承認是用雙手打擊黎某頭部,造成其腦部著地,且在偵查階段并未改變過有罪供述。在庭審中林某某以當天飲酒過多,記憶模糊為由改變供述,稱自己忘記黎某是怎樣倒地,庭前供述是偵查人員提示的結果。辯護人提出林某某當天喝了酒,對于事件細節記憶模糊在情理之中,其行為是過失致人死亡的辯護意見。法院并未采納其翻供,認為被告人林某某犯故意傷害罪。②參見(2018)川16 刑初26 號。最終,二審法院作出了維持一審原判的終審裁定。
(四)外圍證據對口供補強印證的審查
在刑事訴訟中,為了解決“證據孤島”③“證據孤島”是指在司法審查過程中,某些證據因為缺乏與其他證據的相互印證或聯系,而形成了獨立的、無法與其他證據構成完整證據鏈的孤立狀態。問題,司法人員需要綜合運用各種證據規則和方法,進行證據的綜合分析和評估,辨析證據之間的矛盾和差異,尋找證據之間的聯系和相互印證,以形成完整、穩定的證據鏈。依據《刑事訴訟法》第55 條規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得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這一規定體現了對于有罪供述的關聯印證采信原則。被告人在庭審中翻供后,要將庭前供述置于全案證據體系中,審查核實是否能與所獲取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等言詞證據以及物證、書證等客觀實物證據達到相互印證并予以采信的程度。在進行證據審查核實的同時,應當注意到在合理范圍內接受證據間的差異性矛盾,如果口供細節與全案證據體系嚴絲合縫,不存在任何偏差,審查判斷中則應當重視這種細節上的高度一致是否暴露出人為印證痕跡。如果外圍證據與有罪供述關聯印證程度高,不存在無法合理解釋的沖突性矛盾,形成完整的證據體系并據此得出了唯一結論,那么有罪供述就具有可采性。①參見陳嵐、杜厚揚:《刑事證據關聯性之司法審查》,載《山東社會科學》2020 年第5 期。以前述茍某故意殺人罪案為例,不僅其有罪供述中的作案過程細節與尸檢鑒定結論相吻合,而且對關鍵物證手機的外觀特征、短信內容、通話情況的供述也與手機檢查筆錄證實的情況相吻合。另外,在審查該案的過程中,相關證人證言表明被告人茍某具備作案動機和時間,并且茍某在案發后的行為表現異常,這一反常舉動側面印證了茍某的犯罪事實,為案件的定罪提供了重要依據。
庭審翻供需要一定的理由支撐,翻供者必須說明之前做出虛假有罪供述的理由并提供足以支持翻供理由的線索或材料。翻供情節是指被告人在翻供中陳述的與之前有罪供述所不同的案件情節。審查翻供理由和翻供情節是否合情合理,是否能夠與其他證據形成相互印證,是辨別互相矛盾口供真偽的重要舉措。依據《刑訴法解釋》第83條規定,被告人庭審中翻供,但不能合理說明翻供原因或者其辯解與全案證據矛盾,而其庭前供述與其他證據相互印證的,可以采信其庭前供述。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辯解存在反復,但庭審中供認,且與其他證據相互印證的,可以采信其庭審供述;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辯解存在反復,庭審中不供認,且無其他證據與庭前供述印證的,不得采信其庭前供述。因此,外圍關聯證據對于庭前供述和庭審翻供任意一方的印證補強都可以有效辨別兩者的孰真孰假。
(五)證據間相互矛盾之合理懷疑的審查
基于現實案件的復雜性,被告人翻供后會破壞原有證據鏈,使得關聯證據之間無法相互印證。依據《刑事訴訟法》第55 條規定,證據確實、充分應當符合的條件之一就是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而翻供使先前證據所認定的事實存疑,因此需要通過證據審查來對互相矛盾的口供進行證偽來排除合理懷疑。需要注意的是,對于被告人的口供出現相互矛盾情形時,不能單純通過口供內容來認定口供的真實性。比如,在辦理黑社會性質組織案件中,部分從犯可能會在主犯的威逼利誘之下,包攬全部罪行而作出不利于自己的有罪供述。因此,判斷互相矛盾的口供的真實有效性不能盲目排除犯罪嫌疑人的身份特點和環境的影響,應當仔細揣測其供述目的,結合口供中的細節區別,判斷供述真實性。②參見李昌盛:《證據確實充分等于排除合理懷疑嗎?》,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20 年第2 期。以陳某故意殺人罪案為例,被告人陳某與弟弟陳某1 有矛盾,陳某使用粉末致陳某1 飲酒昏迷,而后將其扶至路邊連刺數刀致陳某1當場死亡。陳某在偵查階段的前幾次訊問中否認犯罪,在后期訊問過程中作有罪供述,但其在一、二審庭審中均翻供,堅持無罪辯解。陳某在有罪供述和無罪辯解中均提到一過路男子,雖未找到該男子本人,但被害人銀行卡丟失以及陳某鞋子沾有被害人血跡的鑒定意見使得本案存在過路男子為劫財將陳某1 殺害的合理懷疑。①參見(2012)沈刑一初字第271 號。二審法院審理認定陳某在偵查階段所作有罪供述得到證人證言、法醫鑒定和監控視頻等證據的印證,可以采信為定案根據,能夠排除過路男子圖財害命的合理懷疑,應認定陳某故意殺人事實。
司法工作人員在證據審查和事實認定上應當摒棄有罪推定和盲目拔高刑罰兩種錯誤傾向,而應基于防范冤假錯案和保障被告人法定辯護權的需要,允許被告人一定程度上的合理翻供、有據翻供。同時,這也有力踐行了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以及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相結合的原則。②參見穆書芹:《偵查階段刑事錯案防范之偵查理念、行為與制度構建》,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16年第1 期。庭審中,對待被告人的翻供必須秉持全面客觀的原則,既要給予翻供足夠的重視,也不能盲目地完全采納,單一地依賴翻供做出判斷。應當嚴謹地審查被告人的心理狀態、翻供的具體內容及其與案件的關聯性證據,同時,要結合被告人在庭前的供述來辨別其口供的真實性,以便準確地揭示事實真相,從而確保程序的正義性和司法的公正性。
結 語
在偵查取證過程中,公安機關應保證證據的合法性、取證行為的規范性以及筆錄供述的嚴謹性,妥善保存相關證明材料。此舉在庭審中對抗被告人可能的惡意翻供至關重要,并能增強法官對審判公正性的信心。偵查人員應秉持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并重的訴訟理念,仔細分析翻供的內在邏輯,提高訊問技巧,并根據案件性質有針對性地開展細節訊問。以強化對庭審證據標準的理解為基礎,客觀全面地搜集證據,同時堅決擯棄非法證據。在處理犯罪嫌疑人翻供時,要全面貫徹無罪推定原則,結合不同策略和方法,制定周密的應對計劃,目的在于減少庭審中的惡意翻供現象。在司法實踐中,處理庭審翻供問題需要考慮變化復雜的原因,審理時應堅持尊重人權的原則,準確把握以審判為中心的現代司法理念,辯證地看待被告人自主辯護的價值,確保被告人擁有完整的訴訟主體地位,并防止侵害其辯護權。同時,應超越僅以口供為核心的思維模式,樹立以證據為基礎的裁判意識,依循正當程序審慎施行司法權力,提升訴訟效率,保障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