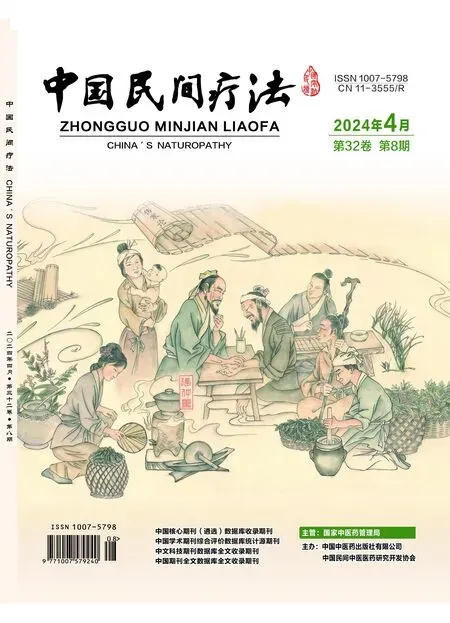敦煌醫學中神志病相關文獻研究概述※
顧曉霞,劉馨遙,田云夢,梁永瑞,王川,李應存
(甘肅中醫藥大學,甘肅 蘭州 730020)
自敦煌經卷面世以來,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敦煌醫學卷子作為其重要的組成部分,不僅為古醫籍的校勘提供了依據,也為醫史文獻研究中長期存在爭議的若干問題找到了答案。考古發現的敦煌經卷計5萬卷左右,其中醫學卷子約有130多種,在這些醫學卷子中不僅對“怒”“恐”“悸”“悲”“狂”“卒”“煩”“恍惚”“不眠”等神志病癥狀的描述較多,而且也記載了很多治療神志病的方法與方藥,有較高的學術研究價值[1-2]。
神志病是臨床常見的一類病證,臨床中由于腦神經功能失調,或惡性情志刺激而導致的神志異常,主要包括如癲癇、抑郁和狂躁病等精神類疾病,以及在疾病發作過程中,其發病與神志變化有密切關系的其他系統疾病,均屬于中醫神志病的范疇[3]。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生活節奏的加快,人們的生活壓力和工作壓力越來越大,人們的心理負荷不斷增加,也導致神志病的發病率不斷升高,因此對神志病的研究也越來越重視。神志病不僅給患者身體上造成巨大的傷害,而且給患者及其家屬帶來巨大的心理負擔[4]。此外,現代使用的抗精神類藥物對于現代醫學中精神神經系統類疾病的治療也具有局限性[5]。有關神志病的研究已引起越來越多人的重視,關于神志病的臨床報道也越來越多,然而在其發展過程中仍然存在很多需要解決的問題[6]。
基于目前發掘的敦煌醫學文獻,本文從醫理類、本草類、醫方類、針灸類、敦煌形象醫學及其他有關敦煌醫學神志病的記載6個方面對敦煌醫學中神志病的相關內容進行梳理與總結,以期為今后敦煌醫學中有關神志病的研討提供一定的文獻依據,使敦煌醫學更好地服務于臨床。
1 醫理類相關內容記載
《五臟論》《明堂五臟論》《傷寒論·傷寒例》《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五臟脈候陰陽相乘法》《占五臟聲色源候》中均有關于神志病相關內容的記載[7]。建立在五行學說基礎上的神志是神志理論的中心。五神是指神、意、魂、魄、志,五志是指喜、怒、思、悲、恐,五神和五志均由七情轉化而來。五神和五志基本涵蓋了人的情感、情緒、意志和認知等方面,主要與情感活動相關,是精神障礙和心理障礙的整合體。借助五行學說,可以將五神、五志與五臟進行聯系,進而衍生出各種心理結構和人格結構,由此構建中醫心理學的理論體系[8]。五神外候五志(七情),五神活動不僅影響人格、意識、思維的形成,而且影響情志的表達和調節,其中魂、魄偏于對情志活動的感應與釋放,意、志偏于對情志活動的調節與制約[9]。五臟-五神-五志的和諧統一是身心健康的標志。在病理上,五志過用則內傷五神、五臟,五神失調則損及臟腑形體。如在敦煌卷子《五臟論》中記載:“戲言者心病,多欠者腎邪,啼哭者損肺,呻吟者脾疾……心風者則好忘,脾虛則喜饑,腎冷則腰疼,肝實則多怒。”[10]不僅解釋神志病發生的病因病機,還說明神志病的臨床表現。《明堂五臟論》記載:“膽為貫也,決曹使孫,能怒能喜,能罡(剛)能屬……故知膽熱,晝夜多睡;膽冷,無睡多悶;膽風,口吐清水。”表明臟腑對人體神志活動有重要的影響[10]。《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記載的“肝虛則恐,實則怒”“心虛則悲不已,實則笑不休”等內容表明臟腑對神志活動具有重要的調節作用,各臟腑的寒熱虛實變化也會進一步引起情志意識活動的改變,導致神志疾病的發生。
2 本草類相關內容記載
中藥在治療神志病方面有獨特的優勢。敦煌卷子《五臟論》記載:“故本草云:靈瑞之草,然則長生;鐘乳餌之,令人愉悅。犀角有抵觸之義,故能趁疰祛邪;牛黃懷沉香之功,是以安神定魄。藍田玉屑,鎮壓精神;中臺麝香,差除妖魅……澤瀉、茱萸,能使耳目聰明;遠志、人參,巧含開心益智。”《新修本草》記載桔梗、莨菪子、白蘞、梅實等具有治療神志疾病的作用,其中桔梗可治療驚恐悸氣;莨菪子可治療癲狂風癇、顛倒拘攣,多食可令人狂走,久服輕身;白蘞可散結氣,治療小兒驚癇;梅實即烏梅,可除煩安神。《食療本草》亦記載有治療神志疾病的藥物,如胡桃可除風;軟棗可鎮心,久服令人輕健,悅人顏色;榆莢可治療癇疾;葡萄可益臟氣,強志;冬瓜主益氣耐勞,除心胸氣滿;獼猴桃可祛煩熱;楊梅可調脾胃,除煩潰,消惡氣;藕可養神益氣,除百病,常服還可生肌肉,令人喜悅;芡實可益精,使人耳目聰明。《本草經集注第一·序錄》分類記載治療心煩、驚邪、癲癇、癭瘤、失眠、多寐等神志疾病的藥物[11]。魏丹丹等[12]研究認為,敦煌香藥具有興奮中樞神經系統、鎮靜安定、調節胃平滑肌、利膽、增加血流量、調節微循環、抗炎、抗菌等多種藥理作用,應用于熱病、心腦血管、骨科、外科、婦科等疾病的治療中,還明確提到敦煌香藥可以治療中風、昏迷等神志病證,為運用敦煌醫藥治療神志疾病提供更多的依據。
3 醫方類相關內容記載
在現存的1 200多首敦煌醫方中,記載有較多治療喜、怒、憂、思、悲、恐、驚等情志病變及癲狂、昏迷、健忘、多寐等神志病證的方藥[13]。如《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中的五臟病證文并方可治療相應臟腑的神志疾病,救諸病誤治瀉方中如瀉肝湯可治療驚煩不寧,瀉肺湯可治療神志迷妄如癡癥狀,瀉腎湯可治療心中悸動不安,調中補心湯可治療心老脈極、心中煩悸、神志恍惚等癥,P.2565中記載的四時常服方、令人醒睡方、常服補益方,P.1467和P.1467-2中記載的安神定志方(又名丹雄雞湯)、茯神湯、雞心湯、治百病鱉魚甲湯方、定志丸、九物牛黃丸方,P.2882中記載的四時常服三等丸方,P.3930中記載的昏迷方,佛教醫方有P.5598中記載的毗沙門天王豐宣和尚神妙補心丸及P.3230中記載的金光明最勝王經香浴方,道教醫方有P.4038中記載的補益壯身方和八公神散等方藥[14]。
4 針灸類相關內容記載
在《火灸療法》(P.T127、P.T1044)、《灸法圖》(S.6168、S.6262)、《新集備急灸經》(P.2675)均記載有神志疾病的治療方法[15-16]。如《火灸療法》(P.T127)記載“中風部歪斜浮腫,上牙風癥和蟲蛀,致使神志昏迷,于腮骨如卵石處,火灸五壯,即可治愈”及“頭暈昏沉,中風眼花,頭腦迷亂,頸筋僵直,于耳背軟骨突起處的外側,下壓有卵石狀處,火灸七壯即可治愈”,描述運用火灸療法治療中風昏迷[16]。
《灸法圖》(S.6168)記載:“灸人雜癲,當灸兩玄角,灸鼻柱,灸兩乳頭,胃管,關元,兩手小指頭,足兩小趾頭,凡十一處,兩邊各灸五百壯。其鼻柱及小指頭各一百壯,余五百壯。”有針灸治療癲狂的記載[15]。《新集備急灸經》(P.2675)記載“患癲風,心狂亂,加兼卒不語良久,取鼻孔下名人中穴,灸七壯,立差”及“患頭眩,暗風,兼生頭疼,白屑,頭心上灸百會穴二七壯”,均是關于中風、神志疾患、情緒改變的灸法治療。
5 敦煌形象醫學
叢春雨在《論敦煌石窟藝術〈經變畫〉中的情志因素與形象醫學》一文中提到敦煌形象醫學及其包含的情志因素,通過對石窟中記載的經變畫、佛像畫、飛天、供養人、裝飾圖案的研究觀察,以及當時社會各階層、各種人物在生產、生活中的喜、憂、思、悲、恐、驚等情志因素的變化觀察,了解當時人們生、老、病、殘等生命運動現象[17]。如通過對治病救人(隋開皇302窟《福田經變》)、子病請醫(盛唐217窟《得醫圖》)、講究衛生(盛唐159窟《彌勒經變》)等圖畫的分析,生動地體現了中醫理論中關于生理變化、心理變化與病理變化等相關內容一致的辨證統一理念。敦煌石窟藝術不僅是獨具匠心的佛教藝術系列群體之佳作,還是一部珍貴的形象醫學史料。
6 其他有關敦煌醫學神志病的記載
此外,對于心理精神疾病的治療,還提出運用佛家哲理、氣功、運動等方法。在佛教養心方(P.3777、P.3244)中就提到“息世緣、離貪愛、制情欲、親善友、樂正法、勤觀察、廣慈悲、普恭敬、深慚愧、大歡喜、常精進、順軌儀、巧方便”的精神和心理治療方法[18]。翟奎鳳等[19]還提出靜坐和坐禪,要求思想內斂、凝心守意、以靜坐為主的功法,從而調身、調息、調心(調神),以求達到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健形的目的。吳新鳳等[20]通過脈診法判斷和治療疾病,運用敦煌遺書中記載的脈象特征以了解疾病的發生及其臨床表現與內在特征,可提高臨床疾病的診斷率。在敦煌醫學脈象特征的記載中亦有關于神志病內容的記載,如《傷寒論·辨脈法》“病六七日,手足三部脈皆至,大煩,口噤不能言,其人躁擾,此為解”,表明通過觀察人體脈象及外在神志活動,可以進一步了解疾病的轉歸。
7 敦煌醫學神志病相關內容研究述評
敦煌醫學是伴隨敦煌莫高窟的發現而逐漸形成的一門地域性顯學[21]。敦煌醫學的研究與整理已經取得豐碩的成果。在文獻研究方面,不僅包括文字整理、校勘、醫理醫方闡述等內容,而且還正在向數字化階段邁進;在實驗藥理研究方面,敦煌醫方的藥理作用機制正在逐步揭示,不少醫家依托敦煌醫方進行加減配伍,將其運用于實驗藥理學研究中,研究并揭示其治病機制;在臨床研究方面,越來越多的敦煌醫方被運用到臨床診療中[22]。
敦煌醫學包括中醫藥學、藏醫學、印度醫學、西域醫學、壁畫醫學及佛教醫學,其中對于神志病的記載也較豐富。神志病基本涵蓋了現代醫學中的各種獨立的精神疾病,也包括各科疾病病變波及中樞神經系統及其他疾病所致的精神異常癥狀。神志病與當今人們的工作、生活密切相關,其他疾病的發生也與神志病有重要的關系,筆者希望通過對敦煌醫學神志病相關內容的挖掘與整理,豐富敦煌醫學的研究內容,為今后敦煌醫學神志病的研討提供文獻依據。